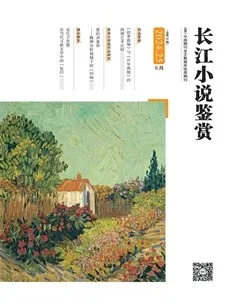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他者”欲望下的異化存在
[摘要]《無聲告白》以美籍華裔詹姆斯一家的生活為內容,揭示了美國少數族裔在他者影響下被逐步異化的生存狀態。運用拉康的他者理論分析跨種族婚姻家庭中成員主體性的喪失,我們發現混血兒面臨的主體性危機,其根源在于父母“他者”欲望的操控、社會“大他者”的影響,以及懼于向“他者”言說的共同結果。這種主體性危機的悲劇折射出現代少數族裔群體的生存困境,雖然死亡在某種程度上重構了主體的存在,使之達到一種向死而生的身份認同,但積極地向“他者”表達自己才是構建主體性的理想途徑。
[關鍵詞]他者欲望" "異化存在" "《無聲告白》" "主體性危機" "向他者言說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5-0056-04
一、引言
新一代華裔作家伍綺詩的小說《無聲告白》講述了一個少數族裔女孩因身份焦慮而自殺的故事,再現了20 世紀70年代美國華裔混血家庭的生存狀態及精神困境,探討了種族、性別、父母對個人主體性發展的影響,從中我們看到的是為平等而抗爭,對不同族裔的文化雜糅共生、和合共存的文本實踐[1] 。
以往華裔文學中反復提及但又有所回避的問題在這里被放大,尤其是“他者”與“欲望”的問題[2]。伍綺詩筆下的人物儼然是拉康概念下的主體——遭受閹割、分裂,被“他者”的欲望所掌控。在這里,主體被徹底顛覆。拉康的“他者”概念與西方傳統話語中的“他者”截然不同,拉康的“他者”是主體與他者的關系中處于強勢的一方,既位于主體之外,又決定主體的構成。現代西方哲學越來越關注外在力量對主體的制約,而不是主體的能動性。主體之外的力量指涉的是“他者”,而“他者”的在場支配著主體的真正欲望,拉康由此提出欲望本質上是對“大他者”欲望的欲望[3]。如同拉康“他者”理論所述,小說中身為“小他者”的母親、父親和作為“大他者”的社會制度、種族主義和性別文化等共同操控著個人主體性的建構過程。“他者”的欲望影響自我的主體性建構,成為個人發展過程中的阻力,甚至是主體性危機的悲劇之源。作家在小說中不僅質疑了這種話語建構,同時也強調了向“他者”言說的必要性,激發讀者對個體主體性的深思。
二、父母他者:混血兒主體性發展的桎梏
拉康對“他者”作了大小寫之分(Autre / autre)。小寫的“他者”最初出現在鏡像階段,嬰兒將自己與周圍世界區分開來,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完整的個體,代表主體意識的產生。母親作為主體的第一個“他者”出現,她的來來往往,象征著在場與缺場。一旦母親成了“他者”,母親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拉康突出了“他者”的地位,把“他性”置于一種根本的位置之上。
1.母親欲望的操縱
母親瑪麗琳作為“他者”操縱了“乖女兒”莉迪亞,導致莉迪亞個體主體性的喪失。在小說中,莉迪亞的本真欲望被瑪麗琳的欲望所引誘。
瑪麗琳的母親沃克爾教育瑪麗琳要做個賢妻良母,她認為女人的人生價值取決于家庭生活,女人的活動中心就是廚房。而瑪麗琳拒絕成為像沃克爾那樣沒有自我的人,因此她努力擺脫社會對女性的傳統定位,在學業上處處表現出與男性一樣的能力,成為化學課、物理課上唯一的女生并表現優異;她立志做一名醫生,因為在她看來,醫生這一職業是男性氣質和權利的象征。然而,迫于現實,婚后的瑪麗琳只能相夫教子,仿佛不需要,也不應該有任何與家人無關的欲望與追求。于是,瑪麗琳策劃了一場逃離。瑪麗琳的逃離實際上是一種“缺場”,而一旦說到“缺場”,它已是一種“在場”,一種“作為缺場的在場”[4]。瑪麗琳“作為缺場的在場”干擾著詹姆斯與孩子們的生活,因為她的“缺場”反而更能凸顯其存在的價值。“好像只要走進廚房,就能看到媽媽站在爐子旁邊,用愛、親吻和煮雞蛋歡迎他們。然而每天早晨,廚房里只有他們的父親。” [5]回歸家庭后的瑪麗琳再次陷入家庭生活中,被迫終止了自己的學業和夢想。然而,杰克母親的醫生形象卻進一步加強了瑪麗琳的“他者”欲望的顯現。對年僅六歲的莉迪亞而言,她的心理臍帶仍與母親牢牢相連,母親是她早期身體和心理發展的依靠。母親早年的離開導致莉迪亞喪失了安全感。母親的期望就像一把無形的枷鎖,在努力滿足母親的期望中,莉迪亞漸漸失去了自我,她的每一個選擇,每一次努力,都是為了變成母親眼中的完美女兒。 久而久之,莉迪亞的個人意愿被“他者”的陰影吞噬,她的主體性在母親的期望下逐漸消融。
2.父愛與期待的綁架
作為“幫兇”的父親剝奪了莉迪亞的主體性。父親詹姆斯一直深受種族身份困擾,渴望撕掉自己的族裔標簽,完全融入美國社會,他寄望于莉迪亞能實現這一愿望。他讓莉迪亞學跳舞,因為大家都去跳舞;他送給莉迪亞銀項鏈作為生日禮物,因為“今年大家都戴銀的”;“他送給莉迪亞的圣誕禮物是一本有關人際交往的書籍,希望能幫她贏得朋友,因為他覺得女兒需要這個”[5]。詹姆斯對莉迪亞的格外關注與期望,實際上是他內心深處渴望的折射。莉迪亞為了不失去父母的愛,不斷迎合他們的期望,但這些舉動也令她窒息。隨著莉迪亞的成長,她意識到自我的分裂與鏡像階段的理想自我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在代表權力場域的象征界發生了根本性的斷裂,最終導致她走向了死亡。
莉迪亞被父母的欲望攫住,在一定意義上,父母的欲望就是莉迪亞的行動空間。這里的欲望完全不是莉迪亞自己的欲望,亦不是她對父母的欲望,而是她母親或父親的欲望。在不斷的“詢喚”力量之下,在家庭共同體的語境中,在反叛和順從之間所面臨的掙扎中,莉迪亞再現了主體建構過程中的分裂和壓抑。“他者”的欲望變成了一種暴力,雖然這里的“他者”的欲望也包括被扭曲的父母的愛。
三、社會“大他者”:主體性危機的悲劇之源
社會“大他者”的桎梏帶來了主體性的危機。作為欲望的主體,母親和父親的欲望又是社會“大他者”之欲望的產物。詹姆斯和瑪麗琳的婚姻是雙方截然不同的社會身份愿望的投射。瑪麗琳和詹姆斯在美國主流社會中備受壓抑,陷入嚴重的主體性危機,而他們的危機最終被轉移到莉迪亞身上。
1.周圍人的“凝視”
在莫里森的《最藍的眼睛》中,皮科拉一直渴望擁有一雙藍眼睛,她相信如果她擁有一雙像白人一樣的藍眼睛,她的生活就會幸福美好。然而,她最終卻因這份渴望而陷入瘋癲。莉迪亞則因為天生的藍眼睛,在“他者”的欲望之下不堪重負,最終選擇了死亡。表面上,兩個女孩的悲劇都與藍眼睛有關,但本質上,她們的故事控訴的是藍眼睛背后的社會話語體系,以及這種體系對她們的持續壓迫。即使擁有藍眼睛,她們也并未擺脫被“凝視”的命運。瑪麗琳在物理和化學課上受到的輕視,詹姆斯一直承受的美國主流社會的排斥,內斯受到的同齡人的嘲弄,以及莉迪亞遭遇的雙重焦慮——這些都讓他們真切感受到了社會機制的壓迫。“你會發現,走廊對面的女孩在看你,藥劑師盯著你,收銀員也在盯著你,你這才意識到自己在他們眼中的形象,格格不入。他們的眼神仿佛帶著鉤子。每次站在他們的視角看自己,都會再次體驗那種感覺,想起自己的與眾不同。” [5]在這樣一種居高臨下的凝視中,他們的主體性逐漸瓦解,剩下的只是自卑與不堪。
“凝視”蘊含的便是一種“他者”的目光和立場,在這種“大他者”的凝視下,少數族裔難以獲得對其“美國人”身份的認同感。在這個意義上,“凝視”的本身就被施加了種族限制的色彩。少數族裔通常是被“凝視”的對象,處于“凝視”的被動地位,既無凝視“他者”的權力,也無權決定如何被“他者”“凝視”。詹姆斯一生渴望合群,渴望普通,渴望將自己隱藏于人群中,卻始終未能如愿。
2.“他者”的生存環境
主體需要尋求社會文化的認同,從而成為受接納的社會性主體。我們往往需要“他者”的認可來確認自身的存在的價值。在美國主流文化的影響下,少數族裔往往對自己的主體身份感到難以定位。在自傳作品《父與子》中,劉裔昌提到自己終于明白不管他多么美國化,但身上的族裔標簽使得他在美國社會享受不到公平。即使擁有高學歷,但常常連就業的機會都沒有。於莉華的小說《考驗》則刻畫了華人鐘樂平在終身教授評審過程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華裔作家筆下的這些人物都存在強烈的疏離感。在華裔女作家劉愛美的小說《臉》中,主人公是一位具有四分之一華人血統的女性,她在唐人街長大,因為碧眼紅發的外貌,經常受到華裔孩子的排擠與欺負,同時也受到白人社會的歧視。莉迪亞因其擁有的藍眼睛——一個顯著的白人特征——成為父母的寵兒,承載了更多的家庭期望,這雙藍眼睛恰恰反映了父母對自身主體愿景的投射。
如果說《臉》呈現給讀者的是梅波利作為混血兒所面臨的來自白人和華人的雙重種族歧視,那么伍綺詩的《無聲告白》則進一步探討了美國白人主導的社會對華裔混血家庭造成的主體性危機。在這個背景下,詹姆斯的經歷猶如《天堂》中的優素福,在傳說和凝視中對白人社會進行符號性委任,同時也辯證地進行符號性的自我認同,將自己認同為主動的臣服者[6]。詹姆斯和莉迪亞分別扮演著“好公民”和“好孩子”的角色,而這些角色并不符合他們真實的自我,他們過分沉浸于這些角色中,導致內心產生矛盾與對立,嚴重危害了他們的主體性選擇。社會通過各種規訓使少數族裔保持溫順,使其逐漸缺乏反抗的意識,久而久之成為美國主流社會的邊緣人和犧牲品[7] 。
四、哀悼與言說:主體重構的表征
在學會如何言說、如何哀悼、如何愛時,我們便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建。巴特勒強調生命的脆弱本質,并呼吁人們相互依存,爭取基本生存權利。真實在斷裂處呈現,白人母親、華人父親及孩子在家庭中最大的事件——莉迪亞的死亡之后,開始審視自我和周圍的世界。
1.言說的生命
生命主體渴望在一個自由的社會環境中成長和發展,在“自由”的前提下,身體、思想和心理能夠自在成長的主體[8]。莉迪亞的悲劇充分表明“他者”并不能為我們構建自己的主體身份。什么能幫助我們建構自身,把握自我的主體性?他者在主體建構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但主體的建構更強調在借鑒他者的同時保持自主性和創造性。選擇的主體雖然會受到客觀規定性的限制,但選擇還是主要取決于主體自身,取決于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9]。那些塑造我們的社會條件、影響我們的事情并不一直伴隨著我們的行動,因此,我們不能將自己的行為歸結為自己所受的影響[10]。
語言是主體認識到自身存在的前提,向“他者”言說是主體走出自我言語的藩籬,在外部世界領悟自身欲望的途徑。主體言說其欲望,把欲望帶入存在之中,這種欲望本質上代表著存在。在言說欲望的過程中,主體創造并表現了某種新的存在。即便在日記這個“文本化”的空間里,一個似乎可以暫時消除人與人之間距離,讓人得以試探性地表達、交流心聲的場域,莉迪亞卻完全選擇了沉默。如果她選擇向母親言說,向父親言說,向所有的“他者”進行言說,她的悲劇可能不會發生。通過言說,主體的欲望才能真正地進入象征界。主體的欲望只有在他人面前被闡明、被命名,才能在某種程度上得到認可。在對“他者”言說的過程中,在“他者”對我們的反饋中,我們形成了自己語言的意愿和規范,并與“他者”構建起一種意義上的對話,不要向欲望讓步。只有這樣,正如伍綺詩所言,我們才能擺脫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2.哀悼的力量
在黑格爾、福柯、弗洛伊德、拉康、德里達、克莉絲蒂瓦等哲學家的思想啟迪下,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了“生成中的主體”概念及 “哀悼”理論。詹姆斯一家通過哀悼莉迪亞的死亡來重構各自的自我認同,這一過程促使家庭成員之間實現了新的“共處”模式,促進了彼此間的理解和接納。面對莉迪亞的死亡和瑪麗琳的困惑,詹姆斯經歷了身份認同的危機,但在短暫的迷失后,他選擇回歸家庭,正視并接納自己作為個體的種族身份,決定與瑪麗琳以真正能被理解的方式進行溝通;瑪麗琳糾結于莉迪亞的真正死因,認識到自己的過分要求使得孩子不堪重負,她決定放下過去,學會真正去愛孩子;哥哥內斯跳入莉迪亞葬身的湖中,通過體驗妹妹身體下沉的那一刻,完成了個人的精神凈化與自我救贖;家庭中曾被忽視的成員漢娜逐漸得到了應有的關注和重視。
通過哀悼的儀式,缺失的對象被主體所內化,重新建構為主體自身的一個想象的部分。
哀悼不僅是對逝者的思念,更是對過去和歷史的反思。身份就是記憶,記憶就是身份。悼念或者愛,恰恰是在斷裂之處建立連接,修復和拯救了個人的歷史和身份[11]。所幸的是,莉迪亞的悲劇之后,這個家庭沒有沉溺于過度的悲傷,而是利用它作為力量,繼續前行,家人之間互相撫慰。在哀悼的同時,家庭成員開始思考生命本身的重要性,開始反觀自我與他者的存在方式,莉迪亞的死亡最終重構了家中每個人的主體性以及家庭關系。
五、結語
在雷祖威所著的《愛的痛苦》一書中,主人公阿偉希望能制造一種噴霧劑,以消除家庭成員之間的隔閡與傷害,幫助他們忘卻過去的痛苦。與此相似,伍綺詩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人類和而不同、和諧共處的愿景。莉迪亞在父母欲望的操控下,走上了自我主體性迷失的人生之路,她的悲劇是大/小“他者”欲望的書寫和懼于向“他者”言說的境遇所共同造成的結果。具體而言,莉迪亞的悲劇源自她對父母欲望的被動接受,而這些欲望實質上反映了社會大他者(即主流社會)以及男權制體系下的欲望。因此,她的悲劇之源可歸咎于美國主流社會及男權統治的雙重影響。
參考文獻
[1] 蒲若茜.華裔美國文學中的共同體書寫[J].廣東社會科學,2023(1).
[2] 劉秋月.華裔美國女性小說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3] 嚴澤勝.穿越“我思”的幻想——拉康主題性理論及其當代效應[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
[4] Lacan J.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M]. New York:Norton,1999.
[5] 伍綺詩.無聲告白[M].孫璐,譯.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5.
[6] 蘇根英,丁建新.優素福的選擇:從拉康的凝視理論視角解讀[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23,34(5).
[7] 李卉芳,蒲若茜.亞裔美國文學研究歷史與前沿——蒲若茜教授訪談錄[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23,34(5).
[8] Alphin C, Debrix F. Biopolitics in the “Psychic Realm”: Han, Foucault and Neoliberal Scho-politics[J].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2021,48(4).
[9] 聶珍釗.倫理智慧與倫理選擇——關于文學倫理學批評核心范疇的思考[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61(2).
[10] 巴特勒. 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與暴力的力量[M].何磊,趙英男,譯. 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
[11] Barnes J. 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M]. New York:Alfred A. Knopf,2008.
(責任編輯" 余"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