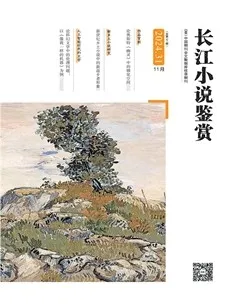韓愈兩次貶謫時期詩歌用典比較
[摘 要]韓愈一生經歷兩次貶謫,先后被貶至陽山與潮州。他在貶謫期間創作的詩歌多處使用典故,這些典故反映了他心態的微妙變化。通過比較韓愈在陽山和潮州期間的詩歌用典,能發現它們反映了韓愈在貶謫期間所共有的棄逐失意與生存恐懼,也揭示了韓愈在潮州期間的詩歌相比陽山時期,攻擊性有所減退,流露出妥協圓通之意。
[關鍵詞]韓愈" "貶謫心態" "用典" "比較研究
用典是中國古典詩歌常用的修辭手法,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言“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也”[1],以此對用典進行闡述。韓愈是中唐時期重要詩人,大量用典是其詩歌的重要特點,這一特點在他的貶謫詩歌中亦有所顯露。
韓愈一生經歷兩次貶謫。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因《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一奏及朝內復雜的政治斗爭而貶謫陽山,至元和元年(806)方得歸京師。元和十四年(819)韓愈以《論佛骨表》觸怒憲宗,被遠貶潮州,于元和十五年(820)回朝為官。兩次貶謫對于韓愈均是重大人生打擊,貶謫期間韓愈借詩歌抒發情志,詩歌中征引的典故多與他在貶謫期間的復雜心境相合。悲劇性的際遇使韓愈兩次貶謫期間創作的詩歌具有共通的情感,在對典故的選用上也有相似之處。同時,韓愈兩次遠貶相隔十六年,在這期間韓愈詩風發生了轉變,兩次貶謫期間創作的詩歌在種種因素作用下呈現出不同風貌,對于典故的選用也呈現不同特點。
一、韓愈兩次貶謫用典情況
以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2]為據進行統計,韓愈貶謫陽山期間創作的詩歌(以下簡稱“陽山貶謫詩”)共64首,有56首詩歌用典,用典詩歌占比為87.5%。使用典故數目總計221次,平均每首詩用典3.5次。按照內容劃分,典故可分為事典與語典,從這個角度進行分類統計,這一時期韓愈詩歌用語典有158次,用事典共63次。語典中,化用頻次較高者有:《楚辭》22次,杜甫詩句11次,《詩經》10次,《禮記》7次,《尚書》6次。事典所涉典籍有:《史記》7處,《左傳》6處,《淮南子》6處,《后漢書》6處,《莊子》5處,《楚辭》5處,《漢書》4處,《論語》4處,《戰國策》3處,《晉書》3處,《尚書》2處,《世說新語》2處,賈誼賦2處,《呂氏春秋》1處,《孝子傳》1處,《答客難》1處,《越絕書》1處,《南史》1處。
韓愈貶謫潮州期間創作的詩歌(以下簡稱“潮州貶謫詩”)共44首,其中23首用典,總計用典61次,用典詩歌占比為52.3%,平均每首詩用典1.4次,這一時期詩歌用語典有40處,用事典共21處。語典中,化用頻次較高者有:《楚辭》8次,《左傳》5次,《詩經》4次,《禮記》4次,《莊子》4次。事典所涉典籍有:《漢書》4處,《尚書》2處,《史記》2處,《吳志》2處,《莊子》2處,《淮南子》1處,《韓非子》1處,《世說新語》1處,《東京賦》1處,《左傳》1處,《南史》1處。
由此可見,韓愈有超過一半的貶謫詩歌使用了典故,在事典與語典中偏重于用語典。其中陽山貶謫詩無論是用典詩歌的比率還是平均用典頻次均要高于潮州貶謫詩,這與韓愈詩歌創作的變化有關。韓愈的詩歌創作可分為前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貞元十九年被視作韓愈前期創作至中期創作的分界,元和十四年則被視作韓愈中期創作至晚期創作的分界。在這三個時期,他的詩風有著從平正古樸到雄奇險怪再到沖淡平緩的轉變。貶謫陽山時期,韓愈創作了一批風格奇險的詩歌,而貶謫潮州時期的詩歌則以平易為主。韓詩雄奇險怪的藝術風貌與韓愈的“尚古”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僅就詩歌用語而言,用字奇崛是韓愈險怪風格的重要表現,這與他在詩歌中力避熟語,大量使用經史子集中的生詞僻典入詩的做法密切相關。即使是韓愈自鑄的奇語,語源大多也可追溯至先秦典籍與漢魏六朝詩賦,正如李重華所言“詩家奧衍一派,開自昌黎,然昌黎全本經學,次則屈宋揚馬,亦雅意取裁,故得字字典雅”[3]。這與韓愈兩次貶謫詩歌用語典較多相對應,也造就了他在主張“惟陳言之務去”的同時詩歌大量用典的現象。元和中后期,韓愈詩風趨于古質清雅,爭奇斗險的古體詩創作減少,詩歌奇險成分逐漸減退。在潮州貶謫詩中,他少用艱深生僻的語言,部分詩歌平直如話、不假雕飾。隨著詩歌語言與詩風的變化,潮州貶謫詩對于典故的使用相較陽山貶謫詩也有所下降。
二、陽山貶謫詩與潮州貶謫詩用典相同處
1.棄逐的失意
韓愈自陳“事業窺皋稷,文章蔑曹謝”,表明他既是文采斐然的文學家,亦是立足現實有著濃厚參政意識的儒士。在兩次貶謫期間,他仍保持著對政治的關切。貶謫陽山期間,這種關切主要表現為對“小人”明里暗里的嘲諷與攻擊。至晚年貶謫潮州時,其政治關切則轉變為驅逐鱷魚、釋放奴隸、興辦鄉校等實際舉措。與韓愈對政治一以貫之的積極態度相呼應,考察其兩次貶謫期間詩歌典故的內容,其中涉及的人物不少與政治關聯緊密,如在陳絕糧的孔子、十次上書秦王卻無果的蘇秦、在渭水邊垂釣待用的姜太公、因直言而被遠貶的虞翻等。對于這些人物,韓愈關注的不是他們安邦經國、立德立言的事業,而是他們失意時的事跡,這折射出了韓愈被遠貶后的失意苦悶。韓愈以古道自守,身懷兼濟之志,但兩次直言上疏的結果卻是貶謫地方,前途不知、生死難卜。遠逐意味著遠離政治中心,意味著政治理想的失落與生命價值的萎縮,也使韓愈有了強烈的“被棄感”。這種“朝為青云士,暮為白首囚”的境遇使韓愈與歷史上種種有志難伸的人物有了共鳴,并借此來抒寫自己的政治理想與訴求。
在貶謫書寫中,屈原與賈誼是常用的貶謫符號,往往寄予了忠君愛國卻遭棄逐的悲涼。在陽山貶謫詩與潮州貶謫詩中,韓愈亦多次使用屈原、賈誼的典故。屈、賈二人不僅是政治人物,他們也是對自身處境格外敏感的文學家。在用屈、賈的典故時,韓愈關注的顯然是與他們政治際遇密切相關的事跡。與屈原相關的事典中,韓愈多次引用屈原自沉汨羅的典故,諸如“靜思屈原沉”“清湘沉楚臣”“魚腹甘所葬”“南遷才免葬江魚”“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之類。屈原是最早的貶謫詩人,他“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際遇、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及貶謫情感是后世貶謫詩歌創作的重要主題。在這些貶謫詩歌中,韓愈借征引典故重復了這些主題,強調了屈原不見容于世的人生與政治悲劇。陸時雍在《詩境總論》中言“讀韓昌黎詩,知其世莫能容”,韓愈因其峻直的個性常受謗傷,盡管他曾自省要全身避禍,但他畢竟做不到同流合污。因此他實質是借屈原的人生悲劇自況內心的無限感傷。
賈誼在《史記》中與屈原合傳,二人的人生際遇存在一定共性。因此韓愈在“靜思屈原沉”的同時亦會“遠憶賈誼貶”,會聯想到二人所共有的“椒蘭爭妒忌,絳灌共讒諂”的遭際,并以此對應自己在仕途上所受的打擊。地位與年齡的變化、貶謫路途與貶謫緣由等細節的不同使韓愈在兩次貶謫期間的心態存在一定差異。但毫無疑問的是,貶謫生活使韓愈體會到了心靈的苦痛,他對于屈、賈二人被遠貶的詠寫實質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磊塊”,以表達謫居的孤苦哀傷與棄逐之感,而這種失意體驗與他的用世之心密切相關。
2.生存恐懼
韓愈命運多舛,他幼年喪父,兄弟、寡嫂、侄子亦相繼英年早逝,他的身體狀況也不健康,在詩書中他一再向人表白自己壯年早衰、眼目昏花。死亡對韓愈來說是隨時可能降臨的危險,痛切的生命體驗更是使韓愈對死亡與生命有異于常人的恐懼及留戀。這種憂恐畏死的心態貫穿了他的一生,并在其貶謫詩歌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身體是生命的物質基礎,周裕鍇指出由于親人的死亡與身體種種早衰的征兆,韓愈的詩歌中有大量對身體的關注與書寫[4]。在貶謫時期,韓愈保持了這種對自我身體的關注,他常用道家典故對身體狀況進行描繪。如《落齒》“我言莊周云,木雁各有喜”化用《莊子·山木篇》中“木雁”典故,典故原意是宣揚人當處于“材與不材”之間的避禍處世哲學。但韓愈在此顯然并未使用典故本意,反而以調笑的方式指出人生禍福無端,自己的牙齒相繼脫落未必不是好事。韓愈有意翻用典故以作滑稽,但在詼諧幽默的表達中亦有對于自己壯年早衰的哀嘆。又如《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化用《說苑》中老子問疾之事,該典提出了一種委曲求全、全身忍讓的生存哲學。這里韓愈借用老子語意對自己的剛強做派表示追悔,卻在有意無意間與自己落齒的身體狀況貼合,其中或許潛藏了作者內心對生命的隱憂。
三、陽山貶謫詩與潮州貶謫詩用典相異處
1.攻擊性的減退
韓愈長時間沉淪下僚,人生經歷頗為坎坷,對社會不公、官場險惡有切身體會。他主張“不平則鳴”,借詩歌舒憂娛悲以道己身之不幸,在發泄內心憂憤的同時,韓愈與社會環境的沖突也往往顯現于詩,并使這些詩歌表現出外露的攻擊性。松本肇認為韓詩攻擊性的展露是以韓愈兩次貶謫為契機,其中陽山之貶促使韓愈壓抑已久的攻擊性得到爆發,而遠貶潮州時韓愈的攻擊性則明顯減退[5]。這與韓愈兩次貶謫的心態變化相關。貶謫陽山時韓愈正處壯年,心氣狂放,他自認其貶謫是小人讒陷而致,心情不免郁怒不平,自然發出對政敵的攻擊;晚年貶謫潮州時,韓愈已年老力衰,加上此次貶謫是因為得罪了最高統治者,故而心氣不復。從韓愈對同一類型典故的選取及使用能看到韓詩的這種變化。
韓愈在貶謫詩歌中數次引用“四罪”“四兇”的典故,在不同時期對這類典故的使用存在差異。“四罪”出自《尚書》,其中記載了堯“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的事跡。“四兇”則出自《左傳》:“舜……流四兇族,渾敦、窮奇、梼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魑魅。”陳斯懷指出“四罪”與“四兇”具有同構性,他們均是典型的反面被逐者,往往被認為是現有秩序的危害者[6]。對他們的清除與放逐也因而具有正當性,執掌權力的統治者的正面形象也在對“四罪”“四兇”的懲處中得以建構。貶謫陽山時期韓愈往往以“四罪”喻王坯、王叔文之黨,典故在此表達的是韓愈對政敵的怨憤指斥。如《永貞行》“膺圖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鯀死羽”句以共工、鯀喻二王;《憶昨和張十一》“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熊”以鯀喻二王之黨;《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赫然下明詔,首罪共誅吺”則以共工、驩兜喻王坯、王叔文。韓愈在此將二王比作“四罪”這樣的奸佞,對政敵進行否定、批判的同時也寄希望于撥亂反正的“明天子”。這時他憂憤之情的抒發向度朝外,詩歌也因此顯現出攻擊性與政治性。
貶謫潮州之時“四罪”“四兇”之典不再是批判的武器,韓愈反而以此喻己,表現出對自我處境的體察與感嘆。如《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其四》“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辰”,以言自己與“四罪”一般負罪遠貶、生死難知的處境,其中寄予了作者對于前途未卜的傷感與恐畏。在《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我來御魑魅,自宜味南烹”句中,韓愈更是用“四兇”喻己,其中不乏苦中作樂的嘲謔色彩。
2.妥協圓通
與攻擊性的減退相表里,韓愈在潮州貶謫詩中表現出向最高統治者輸忠納誠的妥協。韓愈的身體狀況素來不佳,死亡對他來說是實在的威脅,晚年貶往路途遙遠、環境險惡的潮州之時更是如此。韓愈并不甘心終老潮州,渴望能重返京師,為此他在詩文中一再表白心跡,因此潮州貶謫詩與陽山貶謫詩相比更顯柔曲圓通。
這種妥協性主要表現在韓愈對朝廷政治人事的態度上,韓愈在貶謫陽山與貶謫潮州之時均對憲宗有所稱頌,但側重點并不相同。貶謫陽山期間,韓愈傾向于贊美憲宗即位后肅清朝綱、提拔賢臣的作為,因而往往以明君賢臣之典來比憲宗及其朝臣。如“復聞顛夭輩,峨冠進鴻疇”,“顛夭”指泰顛、閎夭,都是《尚書》中提到的周文王的賢臣。此處韓愈是以泰顛、閎夭喻杜黃裳、鄭馀慶,認為他們作為宰相輔佐憲宗就正如泰顛、夭閎輔佐周文王一般。又如《感春四首·其二》“幸逢堯舜明四目,條理品匯皆得宜”,前句用《尚書》舜服堯喪三年后咨詢四岳、布政教,明通四方耳目之典,后句則出自《晉書·孝友傳序》“資品匯以順名”。此處以舜來比喻繼位不久的憲宗,對他的政治舉措進行肯定,同時寄予了自己被棄置江陵的抑郁。貶謫潮州期間,韓愈則偏向于稱頌憲宗的德行,渴望得到皇帝的寬仁。如《路傍堠》“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句,此處用《禮記·經解》之中的語典,稱頌君王德配天地,如日月一般照臨四海。但從史實來看,憲宗自平定淮西后驕侈之心漸生,好神仙方士之說以圖長生,任用讒佞,韓愈的頌圣之語自然是名不副實的。方世舉注此詩時點明了韓愈的心態:“此時方之潮州,乃望恩或免也。”韓愈性格曲直并存,貶往潮州時經險惡貶途的磋磨之后,其個性中“曲”的一面便顯現了出來。
從韓愈在貶謫陽山與貶謫潮州時對《楚辭》語典使用的差別也可一窺韓愈潮州貶謫詩中時常流露出的妥協之意。貶謫陽山時期,韓愈數次化用《楚辭》中的語句言說自己被貶的怨憤與哀傷。如《醉后》“煌煌東方星,奈此眾客醉”化用《漁父》篇句,對朝廷政局進行諷喻的同時又抒發了自己“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復雜感受,多少有些孤高。《雜詩四首·其三》“解轡棄騏驥,寒驢鞭使前”則化用《九嘆》“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蹇驢服駕兮,無用日多”。韓愈在此以騏驥自比,對朝廷中“蹇驢”橫行的現象予以抨擊,流露出才高卻不得用的悲哀。但在貶謫潮州期間,韓愈使用《楚辭》中的語典時不再涉及對朝廷政治人事的批評,多言自己遠貶的悲哀以及能夠將自己悔罪意圖上達天聽的渴望。如“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化用《九章》“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表現出韓愈對于自己晚年遭貶、前途難測的迷惘失措。正是在這種悲涼心境下,他寫下了《琴操十首》,其中《殘形操》“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句反用《離騷》“巫咸將夕降兮”,道出了作者與天意難以溝通的無奈。而在去往袁州的途上,韓愈寄給張端公的詩中更是有“上賓虞舜整冠裾”句,化用《離騷》中“就重華以陳詞”的句意,包含了韓愈對于能“上賓于帝所”,讓皇帝知道自己悔罪意圖的希冀。
參考文獻
[1] 劉勰.文心雕龍注[M].范文瀾,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2] 韓愈.韓昌黎詩系年集釋[M].錢仲聯,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3]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卷一[M].影印清道光二十四年吳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壬集補編本.
[4] 井慧.韓愈詩歌用典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17.
[5] 周裕鍇.痛感的審美:韓愈詩歌的身體書寫[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
[6] 松本肇.韓柳文學論[M].孫險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14.
[7] 陳懷斯.桀與四罪:先秦兩漢典籍中的兩類被逐者形象[J].歷史文獻研究,2017(2).
(責任編輯" 夏" "波)
作者簡介:張敏,福建師范大學,研究方向為唐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