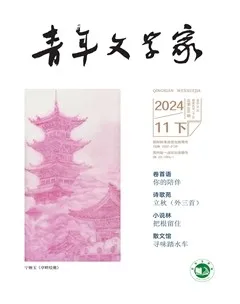懸壺濟世
“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答理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我的祖父是一名鄉村醫生,仁愛,慈悲,智慧,淳良。
村里人找他看病,他從不急著收錢,總是笑瞇瞇地在賬簿上隨手畫幾筆,就當先欠著。村民來還錢時,他也總讓他們拿回去,說讓他們留著以備不時之需。我尚年幼,不懂祖父這樣做的原因。當我提及此事,祖父總是搖搖頭,笑而不答。
平日里,祖父總是研究醫書,還總希望我能和他一樣從醫,救死扶傷、懸壺濟世,常半開玩笑地說道:“咱家世代行醫,可不能斷了傳承。”我萬分不屑,以為他讀書讀傻了。我立志當一個穿金戴銀、呼風喚雨、馳騁商場的大老板,絕不像他一樣當什么醫生。
童年的夏天,我最愛在村邊的池塘靜坐。濟南的荷花從來都是這么美,一抹粉紅掛在荷花的眼角,引得夏蟬為她歌唱,蜻蜓為她舞蹈。我真想就這樣待一天—如果沒有耳邊祖父的嘮叨:“荷花也可以入藥,味甘,微苦,可以用來祛濕止血。”祖父每時每刻都在給我灌輸藥理知識,甚至語氣都有些著急,像是在和時間賽跑一樣。
某天夜晚,明明是滿月,月光卻被重重烏云遮住,讓人沒來由得感到壓迫和緊張。祖父把我叫到房里,嚴肅地盯著我:“再教你最后一課,你長大要干什么,我都不再過問。你不是總問我為什么不收村民的錢嗎?你看房間這塊匾,是我剛從醫時在舊貨市場花三十塊錢買的,后來房子燒毀了,鄉親們合資幫我又蓋了一間房,題了這塊匾,我用三十年歲月才換得這‘懸壺濟世’四字,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拿得出手的東西了……”
感嘆著,祖父把我的手放到了他的脈搏上:“記清楚這種脈象,這就是所謂的死脈,脈象虛浮,忽強忽弱……”
我一臉震驚地望向祖父,似乎意識到了什么,祖父卻只是輕輕點頭,將我推出門外。門內,“懸壺濟世”四字照耀著祖父的一生;而門外,烏云不知何時已然散去,雪亮的月光灑下,和祖父的遺囑一起,照耀著我的余生。
祖父仙逝,他一生救死扶傷,死后也將大部分財產捐贈,只將那間藥房和那塊匾留給了我。送葬那天,幾乎全村的人都來送祖父最后一程。我獨自坐在藥房里,愣愣地盯著祖父留下的古書,上面密密麻麻的很多名字,仿佛這不是醫書,而是精神的譜系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