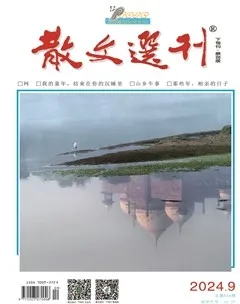她從未見過大海
最后一次見曾祖母時,是兩年前的深冬,寒鴉在村莊的枯枝上叫囂著,天空是被凍住的,慘淡、蕭瑟。
曾祖母坐在暖爐前,詢問我一個人在外的狀況,我告訴她我身處在一座靠海的現代城市,那里沒有真正的冬天。曾祖母一輩子生活在平原,在她九十七載滄桑歲月里,從未見過大海。在她的意識里,大海應該和天空一樣,藍藍的,一望無邊。這些年來,我對她最常說的道別語便是:“春天就好了。”她總是像個孩子一樣半信半疑地點點頭,然后從灰棕色的貼身布袋里掏出皺巴巴的紙幣,顫巍巍地遞給我,并囑咐道:“別讓你爸爸知道。”
1922 年,曾祖母誕生于世。生活在舊思想家族的她,年紀不大時便裹起了“三寸金蓮”,17 歲時便離開母家嫁給了幾十公里外的曾祖父。饑荒歲月里,受生活所迫,曾祖父去千里之外的鐵路部門闖蕩,一別便是整整十五年。在用書信溝通的日子,曾祖母拿著遠方寄來的信件,找村里的教書先生讀信,支撐她的除了那一封封真摯的信件,還有身邊的五個孩子。艱難營生的時刻,她帶著五個孩子去江南地區乞討,其間她心愛的小兒子因“破傷風”離世,年僅六歲。
關于“小兒子”的故事,是我同父親在整理陳舊族譜時意外發現的。幾十年來,我們小輩們竟從未知曉這位“爺爺”的存在。當父親向曾祖母考究此事時,他第一次目睹曾祖母號啕哭泣。于心不忍間,父親不愿繼續揭開這道沉重的傷疤,這位“爺爺”的名字安靜地躺在族譜里。
神龕前堆積的香灰很久沒有清理,像歲月飛揚的塵埃,層疊在人生的關口。
曾祖母的生命,似神像前燃燃的香燭,在風聲的摧殘中消失殆盡著。曾祖母生前經歷的最后一個春天,爺爺用三輪車載著她去鎮上的戲棚聽戲。臺上唱的是她喜愛的《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曾祖母緩緩閉上眼睛,用手指比畫著戲曲的音調起伏,她瘦到連筋絡都呈翡翠色一般映在皮膚上。天色漸沉,曲終收場之際,她喃喃自語道:“喂羊的老頭兒又中風了,翠芝家的老太太在城里去世了……這戲到底是越聽越沒意思了。”
我畢生的憾事,是她臨終前,我沒有見她最后一眼。我終究是離曾祖母越來越遠了,每當我在現代城市的漩渦里墮入浮躁時,總是能夠想起曾祖母,她一生知足于藍天、土地,即便從未見過大海。
曾祖母姓唐,沒有具體的名字,身份證上記作“逯唐氏”。她說自己也許大概是叫“秀棠”或者其他,因為她出生的地方長滿了令她難忘的“垂絲海棠”。有時候她在凌晨驚醒,隱約中聞到海棠散發的香氣,總以為自己真的“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