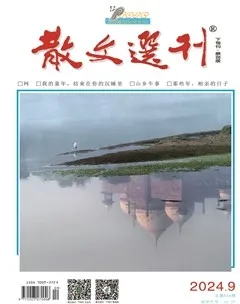老師
事情發生在好幾年前。
一天,我接到地區作協主席楊建英的電話,他在電話里對我說:“老海啊,內地的一個女作家在阿勒泰,來了好幾天了,她想親眼體驗一下哈薩克族飲食方面的風俗習慣,你能不能找個朋友家安排一下,讓她邊喝著奶茶,邊了解一下所想知道的情況。”
楊建英是我兄弟一般的好朋友。我考慮都沒有考慮就說:“兄弟啊,這不是小事一樁嘛,你把客人請到我家來吧,干嗎要麻煩朋友呢?我讓婆姨展示一下手抓肉是怎么煮熟的,桌上的食物又是怎樣擺設的。”我就這么輕易地答應了人家,因為婆姨好幾天沒有煮肉了。家里來客人了,我也沾沾他們的光,可以大吃大喝一場嘛。因為一般在家里,婆姨不讓我吃肥肉,又不讓喝酒,認為肥肉吃多了不好,說什么導致“三高”等慢性病。但我是牧羊人的孩子,一輩子吃著一把一把的牛羊肉長大的,連那些困難時期也沒有斷過,哪能說不吃就不吃呢。如果遠方的貴客來到,按哈薩克族接待規格,宰殺一只羊款待也不過分。不過,我們在城里又是冬季,哪有現成的活羊啊,只能煮上一鍋風干牛肉接待了。再說了,我家的風干牛肉有的是,因為我們還保持著牧羊人原有的冬宰習俗,每年的入冬前必須宰殺一頭大畜,把肉裝進冰箱里儲存起來,一直吃到來年的夏末。
婆姨先問了一下客人的來意。我把楊建英的話變了個意思,告訴她一個大作家專程來看望我。一聽到遠方的作家千里迢迢地跑過來看我,婆姨緊張得不得了,腳不落地地忙乎起來了。她把家里好吃的東西都拿了出來,裝在盤里擺在了桌上,又煮上了一鍋風干牛肉。她還問我炒幾道熱菜又要準備幾道涼菜。我也假裝緊張的樣子,叫她先把幾瓶好酒放在廚房里,因為我不知道那些好酒藏在哪個角落里。
客人們很快來到我家。他們還沒有坐穩,楊建英就向我介紹起那個女作家,地委宣傳部的一個副部長和本地的幾個文友也一起來的。楊建英又向他們介紹了一下我。女作家和她帶的幾個學生一聽到我十幾個字的名字,臉上都掛出一絲哭笑不得的表情,茫然地眨了眨眼。女作家瞅了瞅楊建英,斷斷續續地說:“楊主席,這……這位大哥的名字咋這么長啊,實在不好意思,能不能再說一遍。”
平時,楊建英叫我老海,如果他不看紙上寫好的,也不一定能一下子說出我的全名。我立馬反應過來,因為一般文化水平較低的人都反應得快嘛,就解釋說:“我的全名叫海拉提別克·拜依扎合帕爾·哈依夯。海拉提別克是我的名字又是筆名,拜依扎合帕爾是父名,哈依夯是爺爺的名字。一般,我們在本人的名字后面加上父親的名字,因為我們的族群同名的人較為多一些,如果想再清楚一些,還把爺爺的名字也排到兩人名字的后面。你叫我老海就行,名字實在太長,一下子不好記。”
女作家捂住嘴唇細聲笑了一下,才瞧著我說:“明白了,我覺得吧,你有兩個特點。一個嘛,名字太長,另外一個嘛,頭上的東西少一些,這樣吧,我叫你海老師。”
人家不愧是個作家,一眼就戳穿了我的缺陷,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她指的是我的頭發少還是腦殼里面的東西不多呢?這下我被女作家說的“海老師”這一稱呼整茫然了,且望起她愣住了。因為我頭一次被稱呼為“老師”,女作家被我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自在了,她扭過頭望了望楊建英,又瞅了瞅在場的其他人,她可能以為自己說錯了什么話。我想解釋一下自己尷尬的原因,但女作家帶的幾個學生齊聲說起問候的話:“海老師好!”
“海老師好,麻煩您和嫂子大人了!”
“海老師,您的頭頂真好看,聰明的腦袋不長毛嘛……”
他們一口口叫著“海老師”,在我的耳邊回響了好一陣。
那天在我家,客人們邊說說笑笑吃著飯,邊議論起哈薩克族飲食方面的禮數和風俗。我發現他們對肥肉沒有多大興趣,都時不時伸去筷子,夾起蔬菜和別的食物細嚼慢咽。這樣也沒關系,反正盤里的肥肉一紅一黑地擺在眼前,早晚會裝進我麻袋一樣大的肚子里。其實,我平時一看到肥肉,絕不會分神旁邊的人在說什么,只像惡極了的狗一樣,連把所有的塊塊兒骨頭都啃得干干凈凈。那樣的時候,婆姨實在看不下去,她不斷地向我使眼色,提醒我克制一點兒嘴巴。她一提示,我才意識到自己失態了,就立刻收起手靜坐起來。
那天,我又不等客人舉杯提議,便把一杯又一杯的白酒倒在嘴里,這一點也是我的不良習慣之一。還好,客人們光顧著談論哈薩克族的飲食文化,好像沒有發現我狼吞虎咽般的丑相。
客人們高高興興地都走了。我鼓起好多天沒吃進肉食的肚子,半醒半醉地坐在沙發上。婆姨邊收拾起餐具,邊開始恨恨地說我,說我是不懂禮貌的鄉巴佬,是個瞎了眼的餓野狼。禮貌與野狼沒有什么關系嘛,所以我把她的話只當耳邊風,反正強風刮不了多久的。但問題并沒有那么簡單,今后的幾天里,她會讓我喝些幾乎沒幾顆玉米粒的稀粥和不加葷的涼菜,目的就是懲罰。因為我不會做飯,所以從來沒有碰過鍋碗瓢盆什么的。
我心不在焉地拿起遙控器打開了電視,但無法集中已經分散的注意力,還時不時不由自主地想起專屬于教書人的“老師”的那句話。這句話怎么會跳出原來的范疇,成為普遍使用于其他領域的尊稱呢?連半文盲的我也被稱呼為“海老師”了,等于侮辱了這句神圣的雅號呀!
客人們叫我海老師的聲音回蕩在耳邊不散,讓我想起了自己的兩位老師。
我是個正宗的放羊孩子,如果沒有那兩位老師引導,也可能無法改變自己放牧的命運,也可能跟在羊群后面一直到老。因為我們那個時代,牧羊人居住得相當分散,基本保持著千百年來的游牧方式,一年四季在大草原上轉來搬去。好像到了上個世紀的80 年代初,國家開始提倡游牧民族逐步定居下來的號召。一部分人響應號召,開始定居在原來的冬牧點上,為今后的完全定居起了頭。我是在那樣的環境中長大的,而在70 年代中期才入學的。具體地講,我在后山的流動教學地點入的學,地點在茂密的森林里。從此,我一直在流動教學點和流動學校念書,到了1980 年才入住牧場的寄宿學校。我的《遙遠的森林學校》那篇散文,也是把那時的流動教學點作為背景寫下的。那篇散文發表后,引起了很多讀者的關注,有些文友還打來電話,問我文章里的故事是真還是假。嘿嘿,當時牧區的教學情況的確如此,一兩個老師就能擔著所有課程的授課任務,因此,給我授過課的老師屈指可數。
即便我的學歷低得不盡如人意,但我非常敬重兩個老師,一個是教語文課的男老師,另一個是女老師。男老師名叫木拉提汗,是我上初一時的語文老師,他是個詩人,文章寫得也非常好。那年,我寫了一篇有關一只老母羊的文章,因為從我記事的年齡開始,天天能看見的就是牛羊嘛。男老師一看完我的那篇文章,就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夸了起來,夸我是大作家的苗子,還說我的想象力比他的還高。即便當時倍受鼓勵,但我后來才想起來,一個才上初一的孩子哪能超過自己的老師呀!老師是勉勵我的,因為老師的表揚會激發學生積極向上的信心嘛。當時,那個男老師還牽著我的手,帶到每個不同班級的教室,在他們上語文課的時間,讓我朗讀那篇老母羊的故事。從那以后,我在全校的師生當中有了小小的名氣。不過,后來男老師對我提了一些建議,讓我將文章改成那只老母羊帶著兩個羔子平安回了家。因為我的文章中,那個老母羊產下雙胞胎羔子,而后自己被公狼吃掉,兩個羔羊也被狐狼叼走。前幾年,我搜索記憶中所剩的碎片,把那篇老母羊的故事改寫為中篇小說,發表在本地的一個雜志上。可惜的是,在畢業20 年的初中同學聚會上,我只對著母校教室的黑板鞠了三個躬,因為那個男老師早已被請到天堂去了。
我的女老師也不錯,她是我上初三的語文課教師。她經常看我課程外所寫的文章。記得她對我的《酒鬼之死》的文章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那個文章里的酒鬼喝多了以后,沿著山梁上的小路回家。他到了自家上面的山頂時,想走懸崖邊上的盤道,結果從懸崖上掉了下去,落到一塊大片石上碎成油餅。女老師讓我改寫文章的結局,但文章里的情節是真實的。在她的再三要求下,我讓那個酒鬼墜落在厚厚的雪堆上,只摔斷了一條腿,被經常起夜的鄰居老人發現,才沒有凍成冰塊死掉。我這樣改寫了以后,女老師還是不滿意文章的結局。她嘆了一口氣,說:“海拉提,我擔心你將來的文章會充滿悲劇色彩,這樣不好,讀者也不喜歡的……”
我毫不猶豫地對她說:“老師,生活中發生的有些事,比書中所描述的情節還真實一些,我們何必把它假裝成美好的東西呢?”老師緊鎖起眉頭,又嘆了一口氣,說:“那當然了,但我覺得多寫一些正能量的東西好一些。”
那女老師還給我買過一雙黑棉鞋。到了那時,人們的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買一雙棉鞋是不成問題的。即便這樣,我也比較懶散,根本不在乎自己穿衣方面的問題。也可能是經常踢球的原因,我右腿的大腳趾穿出了氈襪和鞋子頭,就像頭上包著羊毛巾的女人一樣吸引同學的目光。很快,我穿出鞋子頭的腳趾被同班的一個女同學發現,成為全校同學的笑柄,因此女老師才破費送給我一雙鞋子。
初中畢業以后,我再也沒有見過那個名叫古麗柱帕爾的女老師。因為我初中一畢業就成為社員,放了一年多的羊,到了第二年又入伍走了。我復原回鄉時,她已經調到省城工作了,再后來又和家里人一起移民到國外定居了。
就這樣,我唯一敬重的兩位老師都不在了(當然一個在國外)。不過,我把他們的名字和尊稱老師的雅號一直銘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