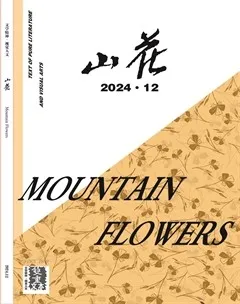寂寞喧囂(節選)
精神的河流和秋天在葉脈上枯萎。
晚霞披滿山巒。
誰,剪開憂傷,又撲騰著翅膀把春天密密縫合?
欲望開始泛濫——
時間寂寞地坐在失語者的門口。
花朵開放出語言。
船帆紛紛流放在歷史的江面上。
世界被收藏在一粒塵埃里。
長長短短的經文把道路鋪向遠方。
劍,游走在血脈里,所有的年代都顯露著傷口。喧囂寂寞打開斑斕的天空,黃昏的血流進夜的深淵。
佇立蒼茫,古老的神諭水一樣漫來,漫到足以淹沒的高度。
逃遁和面對的竟是同一塊界碑。
那些冰冷的石頭啊!那些被卡死在愛愿里的頭顱!
有種凝視溫暖如初。
總有向上的手勢在沙漠里長成大樹。
前進在歸途里的匍匐者啊,誰的雙手,觸摸到了赦免的盾牌?
青花瓷瓶碎落滿地,刻著我們生命密碼的那塊卻無影無蹤。
2006年,注定是個偽年份,我們一生的功課,就是漏掉所有的光陰。
忘川無語。思念洶涌。兩岸隔水相望。
層層疊疊的秋天,已被麥稈撐得高遠。
憂郁蒼藍。
命運再次沿著掌紋,深入到未知的盲區。
在每個人心里都點燃一盞燈吧,讓它亮在歲月的窗臺上。
時空在經輪里左右突圍,像搖搖晃晃的醉漢在方向中迷失。
荷花仰面,躺在歸鄉的夢里。
露珠滾動著吮吸星光。
寺廟金頂在陽光中揮霍沉默。
生命與死亡來來往往。
在國畫恰到好處的線條中,在母狼藍色夢幻的凝視中,在春天落滿枝頭的濕潤中,在母性的平原和父性的高原板塊的沖撞中,我又一次在血嘯癲狂的大夢里復活。
我,是世界的開始和結束。
我,是欲望的喧嘩與騷動。
一首詩開始了我的長征——
在絕壁穿越,在一念間高飛,在漢字里輪回,在意義中空白。
我,用一首詩丈量人性的高度,隨一首詩墜入神性的深淵。
雙手合十,關住自己的內心卻打開了欲望。
一扇門洞開宇宙,時間大開大合,對弈的生死落下虛無的棋子。
月光——智者的語言,遍及一切又超越一切。
我只是我夢境的一個部分,它大如虛空,又包容虛空。
善與惡是一片葉子的兩面;
嬰兒的眼神;
落入雨中的水滴。
小溪解開春天的歌喉,鵝卵石的童年在水底發出嘹亮金光。
一滴水,從另一滴水里流出,
停在半空,卷成一片云。
一只鳥從另一只鳥中飛出,
飛越太陽,成為蒼穹。
云把這只鳥收容在自己的夢里,
鳥將這滴水噙在自己的眼中。
愛情鋪天蓋地,大雪是部行動的情書。
春暖花開,滿坡的野孩子攢集成基因的圖譜,向日葵般滿天尋找太陽的蹤跡。
蜂巢——最后的精神家園。
每天午后,我都看見我的詩歌在陽光里飛進飛出。
整個春天又回到一片苦丁茶的嫩芽里。
頑皮的小孩,拿著綠色蠟筆把世界涂成單一色調。
高原空闊,夏日被滿滿當當地盛在饑渴的湖水里,天空藍得一絲不掛。
金色果園里,秋天的夢總是那么香甜。
雪花,少女般無邪,在天鵝翻飛的圣湖邊,無遮無攔地與大地野合。
在四季轉變的背后,我看見命運無情地在鍵盤上敲打出不可逆轉的程序。
整個下午,我都在等待那束光,等待歸巢的翅膀越過潔白的天空。
等待神,等待神告訴我:星球,和星球背后的故事。
等待結果,等待結果來照亮全部的意義和過程。
黃昏之后,黑暗比光明更早到達。
天地茫然,圣湖的鏡面漸漸模糊。
燈滅了,孤獨亮著。
肉體睡了,靈魂醒著。
失明的琴師坐在萬籟寂靜的雪夜里,彈斷了自己的心弦。
磷火溫暖的冷焰,浮現出祖先親切的面龐。
誰是誰活著的依據?
誰是誰死亡的憑證?
在繁華人群里,離群索居的孤魂,回到了靈魂出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