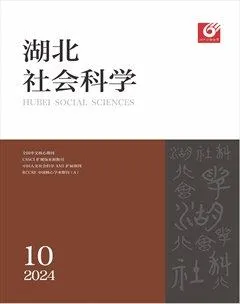王夫之君主思想對“德政”理念的重構
摘要:作為明清之際的一位“畸儒”,王夫之的政治思想與同時期的其他思想家有著顯著的區別。在君主思想方面,如今學界過多地片面強調他思想中反君權的一面,而較少地關注他尊君與集權的主張。王夫之的君主思想實則并不應當在“反君主”與“維護君主”的框架下被討論,而應當置于對儒家古典德政理念的遭遇困境之時代背景下,解讀其思想對于重構這一政治理念的重要歷史意義。王夫之從性才論入手,重新解讀了君與臣的不同職能,圍繞君德建構起“環相為治”的君權保障體系,并初步提出以絕對任免權制衡行政權的制度設計。在這一設計下,“德政”的內涵不再是滿朝皆是正人的“君子政治”,而是“以德馭能”“以德為‘樞’”。
關鍵詞:王夫之;君主制;德政;性才論
中圖分類號:D69"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3-8477(2024)10-0043-11
作為明清之際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王夫之的政治思想歷來廣受研究者的關注。然而相比于激烈批判專制的黃宗羲,王夫之政治思想中的“反專制”傾向并不那么明顯。目前,學界關于王夫之“反專制”最主要的論據當是他所設計的君主、宰相與諫官“環相為治”[1](p122)制度,如許蘇民認為這一制度下“相權和諫官的權力都是為了制約皇權”[2](p43),吳根友更是認為這一思想“包含了可貴的權力制約的思想因素,蘊含著突破儒家傳統圣賢政治的理念的新因素,而與現代民主政治的權力制約思想有更多的可溝通性。”[3](p31)在主張王夫之政治思想有著分權制衡理念的基礎上,王夫之“有天子之若無”[4](p474)的主張則被進一步引申為某種“虛君”論,吳根友稱之為“類似于現代民主政治中的‘虛君共和’的理想”[3](p31),蕭萐父、許蘇民也認為這一觀點“與現代‘虛君共和’的君主立憲制度的根本精神是相通的”[5](p15)。
那么王夫之確有制約君權的思想嗎?至少在“尊君”的問題上,他與更具“反專制”傾向的黃宗羲持有相反的觀點。黃宗羲僅將君主視作高等級的掌權者,主張“非獨至于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6](p8),反對君權的絕對化與神圣化。然而王夫之極為強調君權的絕對性并力主神化君臣之義,提出“君臣之非獨以名為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4](p73),并申明“立國有大分,則君者神人之主,而其尊莫尚矣”[7](p916)以神化君臣尊卑關系。另一方面,王夫之也極力維護君主制度,認為天下必要設立君主而后得治,提出“人不可一日而無君”[4](p724)。這顯然都是維護君權的思想。
那么王夫之的君主思想是否出現了“矛盾”呢?筆者認為,這一誤解在于目前學界將其部分思想不恰當地解釋為削弱君權,在君權的問題上,如同蔡尚思在《王船山思想體系》中所指出的那般,王夫之是毫無疑問的集權論者。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王夫之的君主思想是保守的,相反,筆者認為,王夫之對君臣關系與君臣職責的解讀有著極具開創性的、重構儒家“德政”理念的重要思想意義。本文將以明代“德政”理念所面臨的困境為引,解讀王夫之如何從才性論入手以重構君臣關系,以此基礎對“有天子而若無”與“環相為治”作出新的解釋,并重新闡明王夫之君主思想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傳統德政理念的困境
作為儒家政治的重要理念,“德政”的淵源可上溯孔孟,如孔子言“為政以德”(《論語·為政》),孟子言“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而落實于具體政治實踐之中,先秦儒家德政的理念亦不僅僅見于“君德”而亦見于“臣德”。在理想的德政體制之下,作為中堅政治力量的“臣”也應當保有極高的道德水平。無論是從士人本身出發的倡議修齊治平,還是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倡議養賢、用賢,其最終政治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賢士盈庭的“君子政治”。
若論賢士對政治的積極意義,先秦諸子中當屬荀子闡明得最為詳備,如其所說:“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具體而言,荀子指出君子的政治作用為:
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后君子之所長也。(《荀子·儒效》)
依據此言,君子對政治事務近乎可以說是“全能”的,而他們之所以能在政治事務上表現出“全能”,又幾乎僅僅是因為他們有著豐富的經學知識與較高的道德修養水平。如荀子說:“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歸是矣。”(《荀子·儒效》)治道不出于經典,士君子通過研讀經典、得治道之精要便可持一應變,化裁萬事萬物,這就是荀子提倡“君子政治”的邏輯。
在這一政治邏輯的指導下,個人道德與經學能力就成為了后世歷朝歷代選拔考核官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多數士君子也以修身為本務,堅信通過個人道德修養及研讀古代經典就能成為當世所需要的政治人才。這種觀念在生產力較為落后的先秦時期并不一定會產生太大的負面作用,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各政府部門的專業化程度也是必然會提升的,而秉承著“萬能論”的士君子們也會越來越脫離政治實用。
這一現象在明代已然表現得較為突出。一方面,一些秉承“萬能論”并同時具有淵博學識與高潔品行的士君子會因其不識實務而在具體政治實踐中表現出了近乎滑稽的“低能”,如明初倡議恢復井田、數改官名服飾而終究“無濟實事,為燕王籍口”(《明史·王叔英傳》)的方孝孺,如明末面對軍政危局無一實著、只知勸崇禎帝正心養性而被指責為“迂闊”(《明史·劉宗周傳》)的劉宗周;另一方面,部分切近實務的官員也在其職能領域的專業知識上進行了具有創見的理論探索,如丘浚之于經濟學,戚繼光之于軍事學,徐光啟之于農學。他們雖未能建構出一門新的專業學科,但其治學方法及理論主張都與傳統迥異。可見至于明代,“君子政治”背后“才出于德”的邏輯已然與現實政治需求產生了較大的分歧。
明清之際是中國政治思想的高度活躍期,鑒于“君子政治”理念與實際政治需求之間的張力,儒者的從政方法與政治作用也成為了這一時期的熱門政治議題。而鑒于一眾明末儒者空談心性不切實用的現狀,“經世致用”就成為了這一時期思想家們的普遍主張。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儒者們所言的“經世”未必真的可以“用世”。或許他們僅僅是將政治議題納入自己的思考范圍之內,但其政論與政見仍不能出于三代之治因而全然不切實用。如極重實踐,要求弟子于天文、地志、律歷、兵機皆有所研習的顏元,不可謂缺乏“經世致用”的精神,然而其在《存治篇》中的復井田、復封建、復宗法之論又是嚴重脫離政治實際的學者之見。以往,學界更多地關注于這一時期思想家們提出主張“經世”的言論而不深究他們實際的“經世”主張是否真正具有改良現實政治的積極意義,這樣的研究視角是不全面的。
面對著明末一眾書生見諸國政的“無用”現狀,顏元、陸世儀、呂留良甚至包括黃宗羲等思想家多將其歸因為書生們主觀上“不學治世之道”,然而事實上這一狀況背后更深層的原因是書生們所研習的“治世之道”已然不切實用了。而能深刻地認識到古今異制,承認三代之后政治文明曲折發展的歷史事實并積極提倡適時改制的,于明清之際實唯有王夫之一人。王夫之亦不僅指明了三代之學與三代之政已不切實用的現狀,他實則進一步反思并批判了“君子政治”背后“才出于德”的底層邏輯,建構出了自己的性才論。
二、才性二分與君臣分職
才與性的分合是理學重要議題,從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是性與才是否有著不同的來源;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即是技術知識是否蘊含于道德知識之中。程頤主張分才性為二,指出“性出于天,才出于氣”[8](p252),朱子則主張和才性為一,主張“人有是性,則有是才”[9](p334),這都是偏重形而上學的說法。而明代心學家則更多地關注認識論的方面,且大都認為“才性不分”,認為“才出于德”。如陽明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10](p111)就蘊含著“才出于德”的思想。又如唐順之說:“至于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起,其切實用處即謂之藝;藝非粗跡,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11](p16b)
王守仁與唐順之提倡“才德一致”的目的實則都是為了鼓勵原本閉門修德的書生們積極投身實踐活動,二人自身也都是不世的文武全才。然而二人或許并未很好地意識到他們所取得的政治軍事成就并非全然來源于他們的“良知”而可能是他們特有的政治天賦,而政治天賦并非像“良知”那般為世人所共有。作為工夫論的“致良知”對于天賦卓絕的王守仁本人或許是可行的,但這或許并非可普及于他人的修行方法。
對于心學“才出于德”思想論述最明確的當屬明清之際的唐甄。唐甄曾直言批判高攀龍、劉宗周等東林人求“名”而不求“實”,主張將富民而非清廉作為考核地方官員的標準,不可謂沒有尚功崇實的精神。然而對于性才關系,唐甄卻仍論述道:
道惟一性,豈有二名!人人言性,不見性功,故即性之無不能者別謂為才。別謂為才,似有歧見;正以窮天下之理,盡天下之事,莫尚之才,惟此一性。別謂為才,似有外見;正以窮天下之理,盡天下之事,皆在一性之內,更別無才。[12](p25)
唐甄的這一思想亦可見于他對兵事的談論。他好談兵然并無實績,他在《五行》《審知》等篇目中談論的“兵事”也多為《兵法》中的通論。他還批評陽明說:“對刀殺人之事,非身習不能。孔子謂軍旅未學,亦非謙言”[12](p21)是“擒區區一小賊,遂以傲仲尼”[12](p21)的狂妄之論。唐甄認為圣人既有其德,則圣人必然知兵,即是說軍事專業知識已然包含于充性明德之內。
“好言兵”雖是明清之際思想家的一個共同特點,但其中大多數都在“言兵”的同時輕視軍事知識的難度,貶低軍事知識的價值,如黃宗羲便認為兵事:“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6](p35)。既然兵事潛而易知,因此“合文武為一途”就成為了他們的共同主張,黃宗羲、顧炎武及顏元皆有此議。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夫之毅然反對合文武為一途,明確提出:“若以古今之通勢而言之,則三代之后,文與武固不可合矣,猶田之不可復井,刑之不可復肉矣。”[4](p190)不僅如此,他還對那些自詡“知兵”的文士們辛辣諷刺道:
于是有甫離帖括,乍讀孫、吳者,即以其章句聲韻之小慧,為尊俎折沖之奇謀。見荷戈者而即信為兵也:見一呼一號一跳—擊者,而即詡為勇也;圖畫之山川,管窺之玄象,古人偶一試用之機巧,而寶為神秘:以其雕蟲之才、炙轂之口,言之而成章,推之而成理,乃以誚元戎宿將之怯而寡謀也,競起攘袂而爭之。[4](p923)
除了“才出于德”的觀點外,“義戰論”也是當時思想家們主張文武合一的重要論據。即唐甄所說:“德者,乳也;兵者,藥也,所以除疾保生也。”[12](p248)因此要慎殺,講求以德服人。而既然義戰為上兵戰為下,那么儒者也自然可依據書本上所寫的義道執行兵事。王夫之的觀點與此相反,他指出三代之后的戰爭多為“與夷狄爭生死存亡”的戰爭,而他認為“夷狄者,欺之而不為不信,殺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者也。”[4](p1081)他既認為三代之后的戰爭不可再以仁義之道規之,則自然也認為三代之后的軍略知識再難以由仁義之理所推演。如他在評價北宋韓琦、范仲淹兩位“賢士”面對西夏戰爭時的“無能”道:
韓、范二公,憂國有情,謀國有志,而韜鈐之說未嫻,將士之情未浹,縱之而弛,操之而煩,慎則失時,勇則失算。吟希文“將軍白發”之歌,知其有弗獲已之情,四顧無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豈足與狡詐兇橫之元昊爭生死者哉?[1](p126)
韓琦、范仲淹固然是仁義之士,然而正是這一“仁義”妨害了他們與“狡詐兇橫”的李元昊對抗,屢受元昊所詐。而正是在對韓、范二人才能的歷史評價中,王夫之提出:“人之不能有全才也,為其才之有所獨優也。”[1](p128)否定了唐甄等人“充性”而“全才”的觀點。
王夫之的這一認識論思想亦有其形而上學的依據。他的形而上學思想多繼承于張載之學,而他的性才論也是基于張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性之偏也”[13](p23)的觀點,而進一步申發道:
才者,成形于一時升降之氣,則耳目口體不能如一,而聰明干力因之而有通塞、精粗之別,乃動靜、闔辟偶然之機所成也。性借才以成用,才有不善,遂累其性,而不知者遂咎性之惡,此古今言性者,皆不知才性各有從來,而以才為性爾。[14](p129)
王夫之堅定指出性與才必然二分,且“各有從來”,從形而上的角度講,性與才截然分為二物。性源于理,是普遍的,是人人皆有、人人皆同的;而才源于氣,形成于“一時升降”,人生而各有不同。然而性與才雖有本質區別,亦有其聯系,“才”可視作“性”的“顯能”,即“才以就功,功以致效,功效散著于多而協于一,則又終合于道而以始。”[15](p980)這一“成才”的過程亦有“可盡”與“不可盡”之別,而其中的樞要在于“情”,即“才之所可盡者,盡之于性也。能盡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盡其才者,受命于情而之于蕩也。”[16](p1067)王夫之認為,才本身并無善與不善之分,但“才之用”卻可能因為“情不正”而導向負面的結果。因此他將孟子“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解釋為:“然則才不任罪,性尤不任罪,物欲亦不任罪。其能使為不善者,罪不在情而何在哉!”[16](p1066)
在王夫之看來,軍事是一種才能,擁有這一才能的人乃是天賦所稟,非人人皆有。而要與兇悍的外敵對抗,則國家必然要擇選這些具有軍事天賦的特殊人才,而不是任命那些空有道德而無軍事才能的“賢士”。因此由他的性才論出發,亦不難推出文武必要分途的結論。然而,明季各地方軍閥之兇暴亦是客觀存在的,甚至于南明政權覆滅的直接原因就是左良玉、孫可望等兇暴武人的內釁。黃宗羲之所以怒斥武人為“豪豬健狗之徒”[6](p34),就與他在魯王政權中受方國安等武人排擠的經歷不無關系,而切身經歷吳楚黨爭與三藩之亂的王夫之對此亦必有所認識。
從“制武”這一思想來看,王夫之指出宋代的“銷武”之策就是一個應對驕悍武人的反例,由于經歷了五代的兵禍,宋初出于對武人的猜忌而消解其兵權,弱化武人的地位,即“立國百余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杰為苞桑之上術。”[1](p197)以至于遭遇外族侵略時,一時竟無兵將可用,以至“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糜散于百年之內”[1](p337)。從才性論上說,宋代統治者是不知武人之“才”本無罪而罪在“情”,以及不知正確對待“情”的方式不是“移情”而應是“平情”。不明此理而一味崇文抑武,銷天下之“武用”,移天下之“武情”,屈天下之“武才”,其結果必然導致軍事力量薄弱因而在對外戰爭上不能自保。
在王夫之看來,治理武人的目的并非“移情”,而是“正情”,即在不改變能人原有才情的基礎上防止其情流于“蕩”,是對于武人原有才情的一種節制與引導。即:“情之所發,才之所利,皆于理有當焉。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則才情皆以廣道之用。”[4](p149)因此,王夫之指出正確的“制武”之道也在于使其“平情”,即:“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則知權矣。”[4](p467)具體而言,他提出對武人的封賞必待其有功之后:
大正于上,以正人心,獎之于善,制之以理,而官賞之行,必待有功之日。則義立于上,皎如日星,膏血涂于荒郊,而亦知為義命之不容已。[4](p1041)
又論述漢高祖制韓信之法道:
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審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聽熒,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4](p81)
王夫之提倡的“制武”方式正是以公正坦然之心以“義”相結,平其情,服其心。此“制”并非以文御武,甚至不是道德教化。王夫之絕不主張以文教改變武人原有兇悍的性情(即“移情”),而是順應“武人之情”而使其“平”。不消解武人兇悍的性情是因為對外戰爭的需要,而如何使武人對外兇悍而對內節制就是王夫之理想“明君”的“馭人智慧”了。
縱觀王夫之的史論,他給予最高評價封建帝王是漢光武帝劉秀,他說:“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4](p226)王夫之眼中的劉秀已近乎圣人“從心所欲”之德,其遇事處變不驚,從容應對,察常人不可察之理,見常人不可見之機,在外人看來“神武不可測”[4](p223),而在內又“規模宏遠”[4](p223)。而正是道德境界如此深遠的劉秀,才能以“義”分別處置王郎與劉盆子的請降,王夫之稱之為“與天下昭刑賞之正”[4](p218);又能以“義”賜書勸降竇融,雖是“術”卻又本于劉秀所持之“道”,王夫之評價為“奇而不詭于正”[4](p229)。
王夫之所向往的“馭人智慧”絕不是陰謀權術,而是以“義”為本,持“道”不移,公然其心,賞罰有“正”,這就必然要求馭人者本身具有極高的道德水平。以此,就不難窺見他所理想的“德君”馭“能臣”的政治形態了。在這一理想形態下,君主不必有大“才”,而臣亦不必有大“德”,國事的興衰并不取決于政府官員的道德水平而是取決于臣子之“才”能否在君主之“德”的引導下充分發揮其作用。總結而言,即是:
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樹人者而已矣。[4](p517)
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君主所享有的是任免權及裁斷權,君主并不直接處理政務,因而并不享有實際的行政權,而這才是王夫之所謂“虛君”思想的真正內涵,即:
夫古之天子,未嘗任獨斷也,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雖聰明神武,若有無焉,此之謂無為而治。守典章以使百工各欽其職,非不為而固無為也。誠無為矣,則有天子而若無;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4](p474)
這一段論述源于王夫之對歷史上因皇帝年幼而設置“輔政大臣”制度的批評,王夫之在此明確提出,君主本身就不必也不應享有實際的行政權,君主既毋虛“行政”,大臣“輔政”的說法也就無從談起了。而王夫之反對輔政制度,亦有維護君權、鞏固君主統治地位的目的,使朝中“既無竇、梁擅國之禍,而亦不如庾亮之避其名而其群爭。”[4](p474)
如果僅就君主無須處理各專業政務的角度上看,確可將王夫之的思想稱作“虛君”。然而若說這一思想與近代英國“虛君共和”的思想相近就有些不妥了,因為在王夫之的設想中,各重要部門官員的任免以及裁定國家基本政治方略的權力是牢牢地把控于君主之手的,而君主的權力亦具有不可撼動的神圣性。
而如果僅就此處“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的論述而說王夫之有著法大于君的近似君主立憲的思想,恐怕亦是以偏概全的論斷。在王夫之看來,“前王之法”對于君主而言只是在其年幼時保障其施政的下限。作為明清之際極富政治變革精神的思想家,王夫之絕不主張依一定之法治國,如他在總結《讀通鑒論》的《敘論》中明確提出:
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4](p1180)
自然,不全盤以古法治國也不意味著要全盤否定古法,在王夫之看來,真正的賢君就應如光武帝那般守正于心而又能應事通變。在常人看來“神武不可測”的應變能力是其外在表現,而守正之心則是這一能力的基礎,即所謂:
一氣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蕩之而變化無窮,是以君子體之,仁義立而百王不同法,千圣不同功。[14](p42)
因此,王夫之并不推崇君主恪守前王之法謹慎治國,而是要求他們能夠保有崇高的德性且充分理解前王之法內涵的基礎上積極變法、與時更制。這可稱作“道大于君”,但決不能稱作“法大于君”。
然而王夫之在推崇如此崇德賢君的同時也真切認識到現實政治的殘酷,通觀其史論,三代之后唯有光武帝可稱賢君,宋太祖次之,而廣受史家稱贊的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等都遠無法達到賢君的標準。那么既然君職極重,而君主本人的資質又大都無法獨自勝任這一職位,就務必要為君權提供有效的“輔翼”,這就是如今廣受學界討論的“環相為治”思想。
三、“環相為治”的君權保障體系
如今受到學界廣泛討論的“環相為治”思想出自王夫之對宋仁宗不讓宰相任命諫官一事的評價,其文如下:
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相為治,而言乃為功。[1](p122)
王夫之在此是否表現出了某種類似“權力制約”的思想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要明白王夫之是如何理解宰相與諫官的。由于明代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身處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展開亡國反思時,也通常會提到這一制度問題,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當屬黃宗羲的議論。黃宗羲確有以相權制衡君權的主張,在禮節上主張“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6](p8);在事務上主張“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6](p8)。可以說在黃宗羲的理解下,廢相的后果是“天子之位過高”[6](p8),而“立相”的意義即在于對天子之位產生制約,君權與相權處于某種對立的關系,因而才能相互制衡。以此評價黃宗羲的《置相》篇確有權力制衡思想是貼切的,但是類似的評價能夠適用于王夫之嗎?
王夫之也批判廢相的政策,主張恢復相制,這一點是無疑義的。明初,朱元璋廢相的重要文獻依據是儒家經典《尚書·周官》,他指出:“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并不曾設立丞相。”[17](p4b)而王夫之在論及這一問題時甚至直接對《周官》的文本展開了批判,提出:“讀《周官》而可早識其衰。”[18](p398)王夫之指出,僅當君主有文王、周公之能,且在先秦的封建制度之下,罷相才勉強不至于危害國政,他暗諷朱元璋道:
后世之以勤勞開國者,恃其精明剛健之才,師《周官》而一天下之權歸于人主,禁制猜防,上無與分功,而下得以避咎,延及數傳,相承以糜,彼拱此揖,進異族而授之神器,師古無權,而為謀不遠。[18](p399)
這一段論述準確指出了明初廢相對國政的深遠影響,因為明代廢相的弊病確是在明代中晚期才暴露得更為明顯,這與明初君主多勤政而明末君主多怠政有直接關系。可以說,在對于朱元璋廢相的批評上,王夫之與黃宗羲的主張是一致的,然而他們對于君權與相權的關系卻有著截然相反的理解。
王夫之并不認為君權與相權是對立的,相反,相權是君權的延伸,相制本身是有利于保障君權實施的。他提出:“權者,天子之大用也。而提權以為天下重輕,則唯慎于論相而進退之。相得其人,則宰相之權,即天子之權,挈大綱以振天下,易矣。”[4](p1014-1015)即將設立宰相這一舉措視作君主行權的重要方法。相反,如果廢除宰相制度,那么君主之權反而無法得到有效的落實,即“上攬權則下避權,而權歸于宵小。”[4](p1015)對于明代廢相之后的政治狀況,王夫之的描述與黃宗羲是相反的,他論述道:
因權臣之蠹國而除宰相,棄爾輔矣。宰相廢而分任于六官,以仿周制,是或一道也。乃周六官之長無所不統,而今太仆不統于兵部,太常、鴻臚不統于禮部,光祿、上林不統于吏部,通政、大理不統于刑部,國子監不統于戶部,官聯不審,事權散亂,統之者唯秉筆內臣而已。[14](p567)
黃宗羲認為廢相之后的弊病在于“天子之位過高”,因而主張重新設相的意義在于“分權”。而與之相反,王夫之認為廢相之后的弊病在于“事權散亂”,因而主張重新設相的意義恰恰在于“集權”。王夫之指出,在事權散亂的政局下,群臣紛議過雜繼而進一步激化為黨爭。而朝中一旦陷入劇烈黨爭,君主就將成為文官們相互攻訐的“工具人”,君權也就無法施展了。如王夫之說:
國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于自相朋比,操進退升沉于同類之盈虛,而天子特為其仇恩抱怨、假手以快志之人。[4](p985)
又:
唐、宋以還,敗亡一軌,人君尸居太息而未可如何。[4](p987)
而明代因廢相而導致事權散亂的狀況亦非王夫之一人之言,身處明代政局之中的張居正就曾指出: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于眾,斷在于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決于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19](p2)
而在這一情形下,君權毫無疑問也受到了損害,張居正隨后進一步指出:
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概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19](p4)
正是出于這樣的理解,王夫之才認為設置宰相的意義即在于“集權”,尤其三代之后,中央政府政務極為繁雜,必要在各部門之上設置統領之職,他提出:
故六卿上,必有佐天子以總理之者,而后政以緒而漸底于成,此秦以下相臣之設不容已也。[4](p700)
王夫之指出相制的意義在于“佐天子以總理”,這顯然沒有像黃宗羲那般將相權與君權置于對立關系。而一點還可以從他與黃宗羲對議政問題不同態度上得到佐證。黃宗羲主張恢復相制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加強群臣議政制度,即“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6](p9)而王夫之與他恰恰相反,他主張重設宰相一職的同時亦主張徹底取消議政。他指出:
會議者,大臣免咎之陋術,其何利之有焉。至于登進大臣、參酌大法、裁定大禮,則惟天子之乾斷,與宰相之贊襄,而參以給舍之清議。六官各守其典章,而不可有越位侵官之妄。如使采紛呶之說,以模棱而求兩可,則大臣偷,群臣競,朋黨興,機密泄,其弊可勝言哉?[4](p759)
王夫之如此主張的目的是使國家大計都能一出于“天子之乾斷,與宰相之贊襄”。可以說,王夫之的主張是建構出一個由“天子”與“宰相”共同構成的最高權力體。這一權力體懸隔于其他各政府部門之上,它決定各部主要官員的任免并議定國家基本方略。從君主個人的角度上看,設立宰相的目的正是為了持續保有這一懸隔于群臣之上的絕對權力。這是因為在世襲制下,君主本人很難保證既有識人之明亦有用人之德,而此時擇選一名德高望重的宰相亦可分擔這一職能,如王夫之所言:
操樹人之權者,君也。君能樹人,大臣贊之;君弗能樹人,責在大臣矣;君弗能樹人,而掣大臣以弗能有為,大臣有辭也。[4](p517)
王夫之在此還指出了一種最差的情況,即君主本人無法行使選拔并培養人才的職責而又同時妨害那些“國之大臣”培養人才,那么此時真正明智的“國之大臣”就應當不再貪戀權位而及時抽身而退。縱觀王夫之的史論,最符合這一“國之大臣”形象的當是中唐名相李泌,而他也是王夫之評價最高的宰相。王夫之稱贊他:“識量弘遠,達于世變,審于君心之偏蔽,有微言,有大義,有曲中之權。”[4](p925-926)這種規模宏遠、既知大義又通權變的才德正是王夫之對明君劉秀的評價,而李泌既有此才能,就確能輔佐資質一般的君王成就劉秀的功業。更為可貴的是,李泌不僅有為相之能,亦明為相之分。他絕不貪戀權位,可為則為,不可為則去,在進退之中“因時以保明哲之身,而養國家和平之福。”[4](p888)可以說,王夫之理想中的賢相并不需要熟稔政務、精通文武。君職既不必有全才,作為君職的延伸的相職亦不必有實際的政治建樹。如王夫之在談論諸葛亮時,指出蜀漢政權滅亡的重要原因是缺乏人才,而這正是因為劉備與諸葛亮“勤于耕戰、察于名法,而于長養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講也”[4](p408),而這一點就明顯不如李泌能“返極重之勢,塞潰敗之源,默挽人心、扶危定傾”[4](p861)。正是由于王夫之將相權理解為君權的輔助與延伸,他所設想的相職與相德同樣也就成為了君職與君德的延伸。總結而言,在王夫之看來,相制是君權得以長期順利施展的必要工具,他提出:
論定而后相之,既相而必任之,不能其官,而唯天子進退之,舍是而天子無以治天下。[1](p121)
至于諫官一職,王夫之固然主張諫官有諫正君主、匡正君德的職責,但這亦是他所限定的諫官唯一的職責。王夫之反對用諫官糾察其他大臣的過失,他提出:
若夫群執事之修墜,則六官之長核其成,執憲之臣督其失,宰相與天子總大綱以裁其正,初不藉諫官之毛舉鷙擊、搜剔苛求、以矜辨察。[4](p756)
糾察各部大臣尚不屬諫官之職,更不必說使諫官議論政事了。在明代的機構設置下,六科給事中兼諫官與封駁之職,諫官便有了一定的行政權。對于這一機構,顧炎武是給予高度評價的,他說:
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歷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后,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今人所不知矣。[20](p389)
而王夫之對此則作出了激烈批評,他提出:
六科司抄發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權,糾劾移于下,而君德非所獨任,故詭隨忿戾,迭相進退,而國是大亂。[4](p418)
自宋仁宗允許臺諫議政之后,諫官即多由批評君主轉為批評朝臣,以致朋黨交爭,國事敗壞。而正如前文所言,這些現象在王夫之看來都是君權弱化而非強化的表現。君主正是為了避免這一后果,才應嚴格限制諫官的權力,使他們除了規正君主個人的德行外再無任何政治實權。若以明代諫官的實際權責為標準來看,王夫之的主張其實是在“限制諫官的權力”而非“擴大諫官的權力”,這與黃宗羲及顧炎武的立場顯然是相反的。而如果諫官只能就君主德行的過失加以勸諫,他們既無議論具體事務之權,又無強行規正君主行為之權,幾乎可以說是毫無“實權”,又何談能對君主構成“權力制約”關系呢?
如前一節所述,在王夫之的政治設計下,君主的職責是與其個人德性高度綁定的,君主所能發揮的特殊政治作用必要以君主本人的崇高的德性為基礎。因此,提高君主的個人德性就是在輔助君主發揮其政治作用,亦是保障其權力的有效實施。因此,只有道德勸諫之責而無任何政務職責的諫官應當被視作是君權的保障而非分化。
王夫之所提出的君、相、諫官三者“環相為治”的思想亦是出自他對諫官職責的史論,王夫之提出“環相為治”的目的是“言乃為功”,而與之相對的,如果諫官不以君主而以宰相及其他官員為糾察對象,那么其“言”則必將生亂。結合上下文,王夫之并沒有在此表達任何試圖分化君權的思想。進一步說,既然在王夫之的思想中,宰相是君權實施的必要工具,諫官是養成君德的輔佐工具,那么其實由君、相、諫官三者相互監督所構成的整體就是一個強有力的君權保障體系。王夫之深感明末事權散亂、朋黨交爭之弊,而力主廢棄群臣議政制度,將登進人才、裁定國家基本方略的大權集中收歸于懸隔于百官之上絕對君權之中,而由君、相、諫官三者構成的體系就能保障德性與資質平平的君主也能盡可地發揮賢君的政治作用,從而牢牢地把控這一絕對君權,以此懸隔上下之分,申明君臣之義。這不僅不是反對君主專制的“權力制衡”思想,反而是一種更為精致的君主專制策略。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王夫之的君主思想就是保守的甚至是落后的呢?
四、以君制臣的行政制衡思想
王夫之的尊君思想其實很早就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且研究者多對此采取了批評的態度。如嵇文甫認為王夫之在這一問題上只“教人想到‘君’的好處”[21](p65),以致“君主盡管不好,只能設法救正他,卻總不可以引起人民去反對他。”[21](p65)并據此可見王夫之“受歷史的階級的限制,沒有走出封建圈子以外。”[21](p67)蔡尚思則直接將王夫之的君主思想稱作“絕對君權論”,認為這一思想是“同孟子、黃宗羲、唐甄等的思想對立的。”[22](p18)并批評王夫之在君主的問題上遠比李贄與黃宗羲更保守。而在蔡尚思先生之后,學界就罕有批評王夫之保守、落后的聲音了。然而此后學界亦較為忽視他的尊君思想,而多關注于他重民生以及“公天下”思想(即反對中央政府在行政上過度集中,主張各地方分權自治的思想)。為了論證王夫之是具有啟蒙精神的進步思想家,他明顯的尊君與集權思想似乎被“回避”了。
王夫之主張君主集權嗎?是的。他試圖神化君權以嚴明君臣之分嗎?是的。他的君主思想可稱作“絕對君權論”嗎?從權力等級的角度上看,確實如此。然而僅因為王夫之沒有批判而是維護君主專制,他的君主思想就是落后的嗎?恐怕并非如此。與其重申王夫之是進步開明的思想家并忽視他的“絕對君權論”,不如換個角度分析為什么一位在史觀、史論與制度改革等問題上都如此先進的思想家偏偏在君主制的問題上會主張“絕對君權論”。
筆者在前文指出不宜將“環相為治”視作宰相與諫官對君主的“權力制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王夫之君主思想中就沒有任何“權力制衡”因素。從他主張君臣分職、能人在位的思想中其實可以解讀出“賢君”與“能臣”之間的“最高任免權”與“行政權”之間的制衡。在這一關系下,因為沒有實際的行政權,君主其實很難造成政治破壞,相對而言,君主其實是很容易受到制約的,真正難以受到制約的是擁有行政權的各部官員。
同為遺民,王夫之與黃宗羲的政論都有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對明代政治弊病的反思。然而在君臣權力關系的問題上,二人卻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黃宗羲認為明末政治的弊病在于君主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的制約,因而主張進一步發揚臣權以約束君權,黃宗羲主張發展學校議政制度,要使天下之事非不一出于朝廷。然而這種觀點其實是明清之際的少數派,當時大多數思想家在反思明末政治的弊病時,其實都將矛頭指向了過度膨脹的“臣權”以及由諸臣引發的激烈黨爭。作為東林成員,黃宗羲曾作《汰存錄》為黨爭辯白,然而這并非當時的主流思想。哪怕是對《明夷待訪錄》幾乎全盤贊同的顧炎武,也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23](p70-71)更不必說直言批評東林黨的唐甄,提出:“黨者,國之危及,不治必亡。”[12](p214)并主張以禁絕講學的極端方式遏制黨勢。
王夫之雖不像唐甄那般極端,但對明末的黨爭亦是深惡痛絕。他意識到,朝中黨派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評議權與任免權的下移。面對對東林人毫無政治實著的批評,黃宗羲在《汰存錄》中回復:“籌邊剿寇之實著在于親君子、遠小人而已。”[6](p328)而這在王夫之看來就是“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尚,而以爭為正。”[1](p171)王夫之固然不會反對明末閹黨以及弘光政權中的馬、阮是小人,但王夫之激烈反對君子以結黨的方式攻擊小人,更反對大臣以攻訐小人而非救國定傾為務。如他指出北宋末年正臣:“舍當前腹心之蠱,究已往萌蘗之生,龜山、崔鶠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纖人,顧弗問也。”[1](p206)在激烈的黨爭下,中樞官員往往頻繁調動,中央政策也隨之朝令夕改,王夫之對此指出:“君子小人忽屈忽伸,迭相衰亡,其亂也,更甚于小人之盤踞而不可搖,何也?君子體國,固自有其規模;小人持權,亦自有其技術。”[4](p979)這很難說沒有蘊含對明亡的感慨,畢竟崇禎在位十七年,首輔更迭二十人,閣臣更迭五十人,終至政令混亂,一事無成。
王夫之在分析黨禍時尖銳地指出,黨禍之所以能泛濫成災,從君權的角度上看,便是君主所持有的超越性任免權受到了侵犯。起初,可能是因為君主像宋仁宗那般好言、寬柔、急迫求治而又心無定志,以使群臣紛紛美飾其言以求功名,置政務不顧而唯求在朝政辯論上有所建樹,以致“唯力是視,抑此伸彼,唯勝是求”。[1](p119)而為了進一步在辯論上戰勝政敵,論證雙方又將“各得其朋以相抵牾,而黨禍成矣。”[4](p960)文官利用明代廷推制度相互薦舉,最終導致官員升黜一決于朋黨之門戶,任免大權反操于實際的行政者之手,以致“人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4](p986)。而這就是君主自己“置神器于八達之衢,過者得評其長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抵于敗亡”。[1](p120)
那么如何保持君主的任免權不受侵犯呢?從君主的角度看,應當“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聽,以不輕動于人言”[1](p118);從臣的角度看,真正有志于匡君輔國的大臣應當“衷之以心,裁之以道,持之以權”[4](p960),在人事任免上“鎮靜慎默以贊天子之獨斷”[4](p988);而從制度的角度看,就必要賦予任免權以絕對的獨立性、不可侵犯性與神圣性。因其神圣,故而其權力并不來源于行政者,其評議褒貶、用人擇人才可能完全脫離行政控制,實際的行政者將沒有任何手段干涉任免權。即是說,王夫之激烈的尊君思想實則是希望在行政權之上構建一套絕對權力系統,通過掌控任免權而對行政權進行有效的制衡。
如果從制衡行政權的角度來理解王夫之的思想,那么我們還能簡單地將它稱作保守甚至反動的嗎?如何我們認為制衡君主專制是一種進步思想,那么我們有必要厘清其進步性是在于制衡的是作為具有超越性權力的“君主”個人,還在于制衡這一個人的“專制權”呢?如果是前者,那么王夫之的思想其實是在論證為何必要設置這一超越性權力的意義,且重點在于超越性的權力,并不一定要是一個“君主”;如果是后者,那么其實當王夫之闡述其才性二分、君臣分職的理念后,這一屬于君主個人的“專制權”就已然被消解了。而王夫之之所以要極力尊君,亦是為了防止眾臣取代君主而獲得“專制權”。
如今學界有很多研究者習慣于用近代西方政治精神的視角審視明清之際的政治思想,以此考量王夫之的思想是否“反對君主專制”,是否有“君主立憲精神”,是否有“權力制約精神”,是否有“民主精神”等等。然而,王夫之的思想本身其實也未必一定要受到這些西方政治精神的考量,甚至于王夫之的政治思想恰恰可以反過來處理當代西方國家所存在的重大政治弊病。王夫之所試圖竭力遏制的文官朋黨本質上是一個同時掌控了任免權與行政權的政治壟斷集團。而類似的政治壟斷集團在當代部分西方國家中仍然存在,如美國華爾街的財團,俄羅斯的政治寡頭以及韓國的財閥等。在這些國家中,“擁有雄厚資金實力的壟斷資本支持政黨和候選人展開政治公關、媒體傳播等政治營銷活動,以有效影響選民”[24](p5),以至于“在這個過程中,能參選和當選的只能是富豪或富豪支持的人”[24](p5),這與中國古代文官朋黨以輿情為工具造成唯門戶取士的結果有頗多的相似性。王夫之嘗試以“尊君”思想解決的問題,實則是近代西方政治也尚未解決的難題。
而王夫之君主思想的進步意義還不限于此,筆者認為王夫之這一思想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他重構了儒家的“德政”理念,使其能夠應用于專業化更高的現當代政治中。
五、德政理念的重構
在王夫之看來,滿朝皆是正人的君子政治是不切實際的。他明確提出:“夫欲使天下之無小人,小人之必不列于在位,雖堯、舜不能。”[1](p171)所謂良好的政治環境,也只不過是“君子勝也,君子勝而非無小人”。[1](p171)朝中既有君子亦有小人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常態,但只要君子之風占據主導,則“雖有小人,不傷君子,其有君子,不患有其小人”。[1](p118)
而除了君子與小人外,王夫之指出大多數官員其實都是既有利欲之心亦知廉恥的“中人”,只要賢人能善加引導,中人便皆為可用之才,即:
中材之士,不絕其利祿之徑,而又滌除其僉佞之名,亦何為不濯磨以自新耶?[4](p275)
那么王夫之既然反對君子政治,他又是如何理解“為政以德”的呢?其實就是要求擁有著絕對權力的統治者必要持有的崇高的德性,如他說:
治道之極致,上稽《尚書》,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樞,則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則怠荒刻核,不及者倦,過者欲速也;其大用,用賢而興教也;其施及于民,仁愛而錫以極也。[4](p1179-1180)
君主德,臣主能,君馭臣,此曰以德馭能。而臣之才能見效與否,一決于君之德性,因而從根本上講,天下得治與否就取決于君主的德性,此曰德為政之“樞要”。而這二者相結合,便是王夫之在打破君子政治觀念后所重構出的德政內涵。
由于傳統君子政治的理念已不適用于明代政治,這一對“德政”理念的重構就具有了鮮明的歷史進步意義。如何在君子政治理念之外闡釋德政的內涵實則是儒家政治哲學本身所面臨的時代難題,而王夫之的思想可視作對這一時代難題的一個答案,即盡量選用專業性人才掌管各行政實務且不對他們提出過高的道德要求,同時設置一個具有最高權力的道德機關于這些行政者之上,通過賦予其超越性的任免權以制衡行政者,以其崇高的德行引導專業行政者各盡其才。作為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將超越性的、具有崇高道德的任免權賦予了一位具體的君主,但這只是因為王夫之無法跳出自己所在時代以設想一種沒有完全君主的政治制度。這并非他的行政制衡思想必然導向的結論。因此,在研究王夫之的“德政”思想時,我們沒有必要刻意回避他明顯的“尊君”傾向,其“德政”思想的價值也是不能因其“尊君”傾向而被簡單否定的。我們應該認識到儒家“德政”理念的變化,克服“君子政治”觀念可能存在的弊端。
參考文獻:
[1](明末清初)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1冊[M].長沙:岳麓書社,1988.
[2]許蘇民.明清之際政治哲學的突破[J].江漢論壇,2005,(10).
[3]吳根友.王夫之的政治哲學思想簡論[J].船山學刊,2014,(3).
[4](明末清初)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0冊[M].長沙:岳麓書社,1988.
[5]蕭萐父,許蘇民.王夫之政論發微:二[J].船山學刊,2002,(3).
[6](明末清初)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1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7](明末清初)王夫之.船山全書:第8冊[M].長沙:岳麓書社,1988.
[8](宋)程頤.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9](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0](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1](明)唐順之.重刊荊川先生文集[M].南京:江南書局,1904.
[12](清)唐甄.潛書校釋[M].長沙:岳麓書社,2011.
[13](宋)張載.張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
[14](明末清初)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2冊[M].長沙:岳麓書社,1988.
[15](明末清初)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冊[M].長沙:岳麓書社,1988.
[16](明末清初)王夫之.船山全書:第6冊[M].長沙:岳麓書社,1988.
[17](明)朱元璋.皇明祖訓[Z].浙江巡撫采進本.
[18](明末清初)王夫之.船山全書:第2冊[M].長沙:岳麓書社,1988.
[19](明)張居正.張太岳集[M].北京:中國書店,2019.
[20](明末清初)顧炎武.顧炎武全集:第19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1]嵇文甫.王船山學術論叢[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
[22]蔡尚思.王船山思想體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23](明末清初)顧炎武.顧炎武全集:第21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4]周一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壟斷[J].紅旗文稿,2011,(24).
責任編輯" "唐" "偉
作者簡介:董平(1958—),男,哲學博士,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18);胡子恒(1992—),男,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