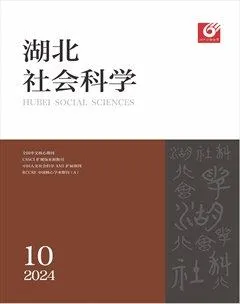再思樂論的當代價值:回到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關鍵向度
摘要:理解先秦儒家治理思想應回到樂論之中,其以貫通天人通達于治的高度,呈現了實現“天下大治”的治理目的,供給了以“仁愛”為核心的治理倫理,塑造了問題意識與政治理想相統一的治理形態。具體而言,孔子樂論的焦點在秩序重建,源于治理現實問題,強調治理價值判斷,重視承繼治理傳統,因而有著現實主義治理底色;孟子樂論核心是治理功能實現,試圖衡量治理現實狀況,揭示儒家治理思想特質,其有著鮮明的民本主義治理傾向;荀子樂論的貢獻則在于治理理論的系統建構,在以樂論深刻闡明“樂”的本質并呈現“和”“正”的治理理念的基礎上,建構了維齊非齊、禮法兼施、化性起偽為核心的理性主義治理系統。先秦儒家樂論始終為后世儒家治理思想“調音協律”,實現了延續性的發展,其當代價值則在于,由于樂論作為一種中國式治理“知識”,蘊含著中國式治理的內涵闡釋,體現著中國式治理的功能統合,能夠啟發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治理理論。
關鍵詞:樂論;治理理論;先秦儒家;自主知識體系,當代價值
中圖分類號:D69"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3-8477(2024)10-0031-12
一、導言
立足“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的時代命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題中之義,因而,治理理論呈現著從引介到吸收再到實現中國化的現實進路。實現治理理論的中國式話語建構、內涵融入,完善和發展當代中國治理自主知識體系,既是發展治理理論的必由之路,更是使之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時代之需。在新時代,“只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1]由于儒家思想蘊含著豐富的治理理論建構資源,使之具備成為發展中國式治理理論的重要切入點的潛在可能。我們應當深刻立足“兩個結合”的中國式治理理論創新邏輯,發掘儒家思想對中國式治理理論的治理概念、治理命題、治理邏輯與治理模式的啟發價值。實現中國式治理理論的概念重塑、命題賦予、邏輯重構以及模式更新,使之有效回應中國式現代化對治理理論發展的緊迫要求。
當代西方治理理論為中國式治理理論發展提供了參考,但是僅僅將治理從概念上界定為“治理指的是自組織的組織間網絡”,[2](p47)從形式上強調其“去除了等級性強制,治理更多的是契約基礎上的扁平化結構”,[3](p69)往往只從關系與形態層面闡釋治理,卻忽視了其對于價值內涵的訴求,更未能站在文明的高度審視治理。在治理實踐中,其不僅可能面臨“國家空心化”、新公共管理矛盾等現實治理困境,更為重要的是其隱含著難以統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理論危機。事實上,治理作為對管理抑或是統治的一種“揚棄”,其“元理論”應當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效統合,這也正是當代西方治理理論所匱乏的。因而,我們有著建構中國治理理論自主知識體系的現實需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其他學說都堅持經世致用原則,注重發揮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對個人、社會的教化同對國家的治理結合起來,達到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目的”,[4]可見,儒家思想蘊含著建構自主知識體系進而克服上述問題的重要思想資源。
具體而言,在儒家從樂論到樂治的治理思想之中,包含著重新賦予治理內涵兼具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益因素,誠如學者俞可平所言“如果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去理解,那樣就會理解中國傳統的‘道統’和‘法統’,‘體’和‘用’,最后才會理解這個關系是怎樣的一個關系。它們并非絕對相互分開的。它們事實上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統一體,或者用一個哲學的話來講是相互構建的關系”[5](p198)。在先秦儒家圍繞“樂”所展開的治理思想中,一方面,樂論既有以“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6](p327)的“治術”關注治理的工具理性,以訴求治理有效的結果;另一方面,樂論更有以“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6](329)的“治道”顯揚治理的價值理性,以追求實現善治的目標。因此,先秦儒家樂論作為其治理思想的關鍵向度,能夠為當代中國治理理論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提供重要參考,從治理的“元理論”層面啟發并滋養中國式治理理論,以此超越西方治理理論知識體系所陷入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沖突的兩難境地。
二、何以關鍵:貫通天人而通達于治
目前,學界對于先秦儒家樂論的研究往往存在拘泥于音樂和倫理領域,卻很少重視其有著從樂論到治理的清晰思維理路和理論導向,更未從中探察并呈現先儒的問題意識與政治理想,也就難以發現其對于解決當代現實治理問題所具有的重要啟示意義。因而,要呈現先秦儒家樂治思想的當代價值,首先需要“走出”對于先秦儒家樂論的種種誤解和偏見。事實上,對先秦儒家治理思想而言,樂論是儒家樂治思想的理論建構基礎,而樂治則是基于問題意識與政治理想的思想聚焦。儒家從樂論到樂治的治理思想之所以關鍵,其前提正是因為“樂能貫通‘天道’與‘人道’。一方面,音樂能再現宇宙、天地、自然的運動規律,音樂以其獨特的方式表現自然的法則,再現宇宙的和諧,表現‘天之道’;另一方面,音樂還能運用一定的節奏、聲音、形象表現人的情志,展現‘人之道’”。[7](p194)在此基礎上,更為重要的是先秦儒家治理思想中的“樂”有著通達于“治”的明確指向,“樂”能夠充分表達上應“天道”,下順“人道”的治理精神。因而,實現“天道”與“人道”之間的貫通不是目的,著眼于體察現實治理問題,達致“盡善盡美”的善治目標,才是先秦儒家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方面對其進行理解:
其一,先秦儒家以樂論呈現治理目的。這主要是通過界分“音”與“樂”的差異實現的。自1958年學者梁啟雄《荀子樂論篇淺解》發表以來,對于先秦儒家樂論思想的探討重點都在于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音樂教育學、音樂哲學等方面,[8](p85-89)學者們取得了諸多有益成果,但是限于學科特點與思維范式,卻常常忽略儒家樂論思想中對于“音”與“樂”差異辨析的重視。由于混淆二者導致似是而非,從而誤讀其思想的實質,將體現“治道”的“樂”與“音”等同視之。在《禮記·樂記》中就系統闡釋了“音”與“樂”之間的不同之處,從形式上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9](p712)強調“音”是外界事物觸發人心的結果;“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9](p712)強調“樂”需要將“音”以樂器演奏有序排列,并將手執禮器的舞蹈融入其中,方可稱之為“樂”,其凸顯了“樂”在形式上對于參與者及其程序、秩序的講求。從本質上看,“樂者音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9](p713)盡管“樂”源于“音”,但是“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于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9](p716)先秦儒家通過剖析“聲”“音”“樂”之間層層遞進的關系,凸顯“樂”通達倫理的內涵與特質。更為重要的是在先秦儒家看來,“音”與“樂”之辨不是純粹的學理推究,而是在于實現“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9](p716)的治理理論建構,強調“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9](p713)由此可見,先秦儒家正是以“音”與“樂”之分為切入點,從而引入對現實治理議題的深刻關切,凸顯其追求社會安定、渴望天下大治的治理目標。
其二,先秦儒家以樂論供給治理倫理。談及先秦儒家樂論思想肇基者時,有學者認為“然孔子論樂從根本上說是詩學的,藝術的,其本質是講人的存在問題的,著重于人的情感與人性”,[10](p32)但是先秦儒家樂論是否僅止步于此成為純粹而又抽象的美學表達,抑或是作為一種懸于空中的倫理訴求呢?或許并非如此,不可否認的是盡管樂論思想有著鮮明的道德倫理指向,但是考察其飽含現實主義特質的落腳點則更為重要,樂論根本的價值旨歸在于樂治。因為,先秦儒家強調“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9](p719)是以“仁愛”之心面向現實的“樂”統合“道”與“術”實現對人的規制和引導,達致有效治理始終是重要目的。誠如徐復觀先生所言儒家樂論“首先是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11](p31)其探討“樂”有著對于“仁以愛之,義以正之”[9](p720)倫理道德遵循,但其又并非空泛的形而上學說教,歸根結底在于實現“如此則民治行矣”[9](p720)的現實治理目標。因此,“可將孔子樂論的依存美理解為是一種規范政治、穩定社會秩序以及實現道德善的音樂之美。這種音樂美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更加注重倫理道德的音樂美學化表達”,[12](p51)進一步而言,肈于孔子的儒家樂論思想正是以倫理為切入點,將視角深度聚焦于現實治理問題之中,樂論所表達的治理倫理訴求是儒家治理思想價值旨歸的如實體現。在儒家看來,正是面對解決現實治理問題的需要,先秦儒家才試圖以樂論供給治理倫理。樂論的終極意義在于建構一套齊備有效的倫理原則,用以回應和解決現實治理難題。
其三,先秦儒家以樂論塑造治理形態。先秦儒家治理思想從形態上涵蓋了問題意識與政治理想兩個維度,其中,問題意識反映的是治理的現實形態,而政治理想則表達了治理的理念形態。先秦儒家以樂論統合了二者之間的有機關系,從思想層面建構了獨特的治理理論。如前文所述,先秦儒家以樂論所表達的治理思想之所以關鍵,不僅在于其在“音”與“樂”的差異之中,凸顯了“樂”所呈現的“治道”,將治理現實作為彰顯樂論道德倫理的真實場域,更在于以“樂”作為重要的中介實現了問題意識與政治理想的統合,“樂”始終貫穿于先秦儒家問題意識和政治理想兩個重要維度的訴求之中:
一方面,先秦儒家樂論思想體現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對于“樂”的探討是由問題意識所產生的線索牽引而來的,孔子所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13](p106)是最典型的例證。正如學者包剛升所言“孔子的問題意識源自他所看到的是一個禮崩樂壞的世界。他所考慮的目標,是如何在這個禮崩樂壞的世界重建一個良善的政治秩序,或者說如何回到那個過去以周朝的制度禮儀為代表的美好世界”,[14](p53)可見,在先秦儒家樂論之中,由于天下之治是探討“樂”的核心論域,現實治理的困境是探討“樂”的動力來源,因而問題意識始終貫穿儒家樂論的始終。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樂論思想清晰勾勒出了其政治理想。“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13](p16)孔子正是在討論《韶》樂與《物》樂時,提出了“盡善盡美”的重要命題,李澤厚先生對此評價道“美善統一始終是個根本性問題”。[15](p22)在儒家看來,盡善盡美作為一個“美”與“善”相統一重要問題,其顯然已經遠遠地超越了音樂的范疇,儒家樂論所關注的不是技藝,不是審美,而是提出了一個足以為后世明確善治目標的重要治理命題,其充分表達了儒家以盡善盡美為終極目標的政治理想。而儒家樂論思想之所以關鍵,正是因為“樂”被賦予了“大樂與天地同和”, [6](p721)“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6](p327)這樣與天地一般協同萬物的功能,避免了思想層面上治理現實與治理理念的二元對立的緊張局面。先秦儒家正是以樂論實現了問題意識與政治理想的有效整合,使得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現實形態和理念形態借由樂論成為了一個有機體。
三、何以理解:從論樂到樂論臻于完善
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形成、發展與定型是以“儒家三圣”即先圣孔子、亞圣孟子、后圣荀子為思想坐標,從而確定其理論方位的,而作為儒家治理思想關鍵向度的樂論亦然。孔子對于先秦儒家樂論思想起著奠基的重要作用,孟子則在此基礎上將樂論思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荀子那里樂論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系統。盡管孔、孟的樂論思想更多的是一種在概念、命題上有所創建的“論樂”,而荀子則是從邏輯、模式層面讓“論樂”成為了系統化的“樂論”,但是,“儒家三圣”樂論的共性在于其思想都有著鮮明的治理指向,充分體現先秦儒家樂論的思想核心在于面向治理,試圖以樂論為載體表達樂治,以樂治為讓現實治理問題“迎刃而解”,以期實現盡善盡美的天下大治。
(一)秩序重建:孔子樂論的現實主義治理底色
面對春秋晚期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孔子首倡樂論,是以論樂的方式建構樂論,以樂論闡明樂治,進而以“克己復禮為仁”[13](p70)的道德倫理重建為核心,重建周朝秩序實現善治。由于孔子之樂論呈源于現實治理問題,強調治理價值判斷,重視承繼治理傳統,因而其樂論體現著強烈的現實主義底色。
首先,孔子樂論源于現實治理問題。在《論語·季氏篇》中,孔子論樂的背景是春秋晚期由無序征伐所導致的一系列治理問題,基于對現實的憂慮,孔子有關“樂”的議題落腳點在于強調“天下有道”[13](p106)的治理目標,在于有效回應現實治理問題。正因為如此,在《論語·憲問篇》里,才記敘著“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13](p90)的情形,就連擔著草筐的路人也能發現擊磬的孔子憂心忡忡,看似對孔子進行指責的“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13](p90)實則是以孔子擊磬這件關涉樂論的事,充分表達了孔子對現實治理問題的關注,并且體現了孔子不愿隨波逐流,而始終堅守以周代制度為核心的“治道”,去努力尋求治理秩序重建的志向。因而,孔子的樂論從來不是玄之又玄的純粹理論設想,是他在面對現實治理問題之時,試圖紓解治理困境而提出明確的解決方案。這種源于現實治理問題的樂論,也一直為后世的儒家所繼承,進而發展成為了一種具有強烈現實主義色彩的治理思想,鋪陳了儒家治理思想以問題為導向的基本底色。
其次,孔子樂論強調治理價值判斷。孔子的樂論思想關注治理的價值判斷,“樂”所要反映的是人們的對于治理的價值旨歸和倫理訴求。在《論語·陽貨篇》中,孔子就明確指出了其樂論思想中的治理價值的態度,“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13](p114)在孔子的樂論思想中,“鄭聲”破壞了代表治理秩序的“雅樂”,因而,孔子給予其“惡”的態度。其對于樂的價值判斷超越了審美與技藝,從而上升為對治理價值理性的關切。而在《論語·八佾篇》里,“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3](p12)可見,在他看來,“八佾”作為天子才有資格使用的樂舞,季氏的行為實際上破壞了以“樂”所呈現的治理規范和治理秩序,孔子的激烈批評的態度生動呈現了其樂論思想所承載的治理價值判斷功能。而在《孔子家語·辯樂》中,孔子樂論對治理價值判斷的強調則更為顯現,他在對子路進行教導時,強調“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16](p290-291)在此,孔子以居于實現社會治理平安穩定的“治世”高度,去辨別“樂”中的“君子之音”與“小人之音”的差異,反映了先秦儒家治理理論鮮明的立場和批判意識。
最后,孔子樂論重視承繼治理傳統。治理傳統本身是現實的,孔子以樂論闡發的治理思想從來不是“憑空而來”,因而他的樂論思想也有著傳統的面向,在春秋時期社會的巨大變動中,強調珍視治理傳統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在“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13](p14)的感嘆中,孔子闡明了復興周代治理傳統的觀點,這正是以其樂論有關“八佾”問題的探討顯見的。而在《論語·衛靈公篇》中,“顏淵問為邦”[13](p98),當孔子面對顏回向其尋求治理之道時,“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13](p98)在這里,孔子不僅指出應重視承繼歷法、工具、禮制層面的傳統,同時,更應繼承《韶》樂、《武》樂所蘊含的治理理念。為此,他緊接著強調堅持“放鄭聲,遠佞人”[13](p98)的重要性,以及避免“鄭聲淫,佞人殆”[13](p98)對于治理的重要意義,孔子將樂論的作用上升到了“為邦”這樣治理國家的高度,他以樂論明晰了繼承治理理念與治國興邦之間的關系,其樂論思想指出現實治理必須有著對于傳統的尊重,不切實際忽視歷史慣性的一味理念“創新”,或許于治理并無益處。為此,基于重建現實治理秩序的需要,孔子把承繼治理傳統視為儒者的一項重要的使命,這也正是“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13](p50)的現實緣由。
(二)功能實現:孟子樂論的民本主義治理傾向
孟子在承繼孔子樂論思想的基礎上,以民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其樂論思想,實現了先秦儒家樂論思想對于治理的再次聚焦。因而,程頤評價道“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17](p186)可見,孔子所言之仁更多是價值訴求,而孟子所言之仁義,則是以“義”的方式將“仁”轉化為極富民本主義的治理實踐,而“仁義”正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概念,其在孟子樂論中得以充分體現,孟子樂論展現了以“仁義”為標識的民本主義功能實現,即樂論必須兼具衡量治理現狀與闡明治理實質的雙重功能,推進了先秦儒家樂論從理念邁向現實的轉換,這就是盡管孟子有關樂論直接探討不多,但卻極其重要的原因,其實現了在思想層面從論樂向樂論的“關鍵一躍”。
一方面,孟子以樂論衡量治理現實狀況良莠。在孟子看來,樂論有著判斷治理優劣的功能。自孔子伊始,先秦儒家樂論有著顯著的現實主義底色,而孟子則將此種現實主義進一步向前推進,使得樂論不僅源于現實治理,更要通過觀照現實治理,為治理狀況提供判斷依據。孟子所闡發的樂論思想重視“樂”的治理評價功能。在孟子和梁惠王的對談中,當梁惠王以“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13](p177)詢問遠道而來的孟子何以利國時,孟子的回答簡明扼要“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13](p177)強調在利國之上,有著追求仁義的“治道”,“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13](p177)的現實例證可以證明,從來沒有仁者會遺棄自己的父母,也從來沒有義者會輕慢君王。可見,在孟子看來相較于利益,仁義才是衡量治理好壞的尺度。但是,仁義的內涵畢竟是抽象的,并非人人都能夠真正理解其精髓,那么我們又該如何在治理中把握作為標準的仁義的實質呢?
為此,孟子將其樂論思想引入上述問題。當莊暴在詢問“好樂何如”[13](p190)純粹只是探討對于“樂”的愛好時,孟子則將話題引向了治理,他回應道“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13](p190)孟子給出了一個看似有些奇怪的結論,即如果齊王好樂,那么齊國就差不多能治理好了。二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在孟子的樂論中,“樂”卻體現著仁義的實質,其充分體現了孟子的民本主義傾向,因而,“樂”也就具有衡量評判治理優劣的現實功能。不同于孔子“惡鄭聲,恐其亂樂也”[13](p391)更多地關注形而上的價值判斷,并通過關注樂與樂之間的差異,體現對治理傳統的堅守。孟子則認為“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13](p190)強調古樂與今樂之間的差異更多只是形式不同,孟子不愿苛求辨識二者殊異,而是指出“樂”作為一種“治道”的載體,其都展現著民本主義的仁義價值取向。在孟子與梁惠王“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乎?’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13](p190)在一問一答的論樂間,仁義這個儒家民本主義治理的核心概念也就能夠為人們所理解了。在孟子看來,所謂仁義就是讓“樂”所帶來的喜悅能夠為人民所共享,“樂”所體現的是一種共治和諧的治理境界,他將其描繪為這樣的一幅圖景,即“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吾王庶兒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音,見羽旄之天,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13](p192)可見,在孟子看來,真正的“好樂”,就是要展現“樂”的仁義本質,以與民同樂這樣一種方式進行治理,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天下大治。
另一方面,孟子以樂論揭示儒家治理思想特質。在孟子看來,樂論有著闡明治理特質的功能。先秦儒家治理思想有其一以貫之對于“仁”的追求,但是在孔子那里更多的是基于“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13](p20)的考量,試圖通過踐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13](p20)的信條,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去接續以盡善盡美、天下大治為己任的“治道”。但是,當處于在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面對以墨家為代表的諸子百家的種種詰難,如同孟子向公都子所描述的那樣,“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12](p262)在這樣緊迫的思想論戰情形之下,面對天下何去何從的時代轉向難題,孟子所代表的儒家必須明確闡明其有關治理的觀點和學說,給予“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13](262)的觀點判定和理論攻訐,這也就賦予了先秦儒家樂論所要承擔的重要時代使命。
而孟子正是以樂論呈現了儒家治理思想的關鍵,他將“樂”視為能夠成為窺見儒家“治道”的門徑。孟子強調“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13](p314)可見,在孟子看來正是因為“樂”的形式中包含著人們對于秩序、條理的深刻見解,因而,只有在展現“樂”的玉振金聲間,人們才能知曉儒家集大成的深厚蘊藉,也只有“樂”才能夠承載儒家對于圣德與智慧的深刻關切。這正如射藝一般,“智,譬則巧也;圣,譬則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13](p314)孟子強調“樂”能夠讓人們充分辨析“術”與“道”的差異,感知由“治道”對“治術”的超越。對此,朱子對其注解道“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為一大圣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17](p294),可見,孟子的樂論發揮著揭示儒家治理思想特質的功能,就是說“樂”能夠將儒家的微言大義“具象化”。那么,孟子以樂論揭示治理特質究竟為何?在《孟子·盡心章句上》中或許能夠找到答案,“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13](p363)在孟子看來,彰顯仁義的“樂”其遠比體現仁義的微言大義更能深入人心,“樂”體現的正是一種極富柔性和韌性的治理特質,這正是實現善教治理的關鍵,而儒家以樂治呈現的善教治理所要實現的,正是對善政治理的超越,而孟子正是以其樂論生動闡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13](p218)這樣一種以仁義為核心的民本主義治理思想。在孟子看來,樂論發揮著闡明儒家治理思想實質,如“畫龍點睛”般凸顯儒家治理思想關鍵的功能。
(三)系統建構:荀子樂論的理性主義治理進路
遵循從論樂到樂論的理論演進邏輯,通過荀子的系統性理論建構,先秦儒家樂論思想逐步形成了完備的思想體系。盡管荀子的思想和孔、孟有所差異,但是誠如徐復觀先生所言“但他因為要繼承孔門的大傳統,所以寫出了一篇完整的《樂論》”[11](20),荀子與先儒在樂論和治理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始終保持是高度一致的認識,樂論最為重要的作用在于為紓解治理問題提供進路。為實現這一目的,荀子在從概念上厘清“樂”的本質基礎上,在其樂論中闡明了“和”與“正”的理念,將儒家樂論中對于秩序重建的現實主義關切,民本主義的功能訴求,融入了樂論所展現的治理系統之中,建構了維齊非齊、禮法兼施、化性起偽為核心機制的理性主義治理系統,進而使得先秦儒家樂論思想臻于完善。
首先,荀子以樂論深刻闡明“樂”的本質。在荀子之前,盡管孔、孟對于“樂”的命題都多有闡發,但是對于“樂”的本質究竟為何卻始終沒有給予明確的答案,這也就制約了先秦儒家樂論從一種觀點表達發展為完備思想體系的可能,這是因為,只有當“樂”的本質愈發清晰明了之后,樂論才可能成為理解治理現實的鏡鑒。在《荀子·樂論》之中,荀子首先闡明的就是“樂”的本質問題,他指出“夫樂者,樂也”,[6](p325)言簡意賅地說明了“樂”的本質就是人對于快樂的追求。不僅如此,荀子還進一步分析了“樂”的功能,以此凸顯“樂”的重要性,強調“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6](p325)正是由于“樂”是人情感表達所必需的,因而人不能沒有“樂”。而從“樂”的機理上說,荀子認為“樂則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6](p325) “樂”是借由聲音而產生的,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也需要通過“樂”來表達。可見,荀子對于“樂”的本質所進行的分析,不僅是有關樂論的“元概念”闡釋,更引入了人性治理的“元理論”,把先秦儒家樂論對于治理問題溯源至對人性的關切,從此樂論不僅“上通”以實現盡善盡美為目標的天下大治,而且“下聯”以對人性情感機制考察為核心的現實基礎。
其次,荀子以樂論呈現“和”“正”的治理觀念。在荀子看來,“故樂也者,治人之盛者也”,[6](p329)其原因在于“樂”中蘊含著對于治理至關重要的“和”與“正”的理念,因而樂論才能夠承載“治道”,樂治才能成為治理最為理想的形式。其一,荀子在闡釋“和”時,強調“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6](p325)指出正是因為人們之間有著相似的情感,故而“樂”體現著天下最大的共識,“樂”蘊含著中正和諧的綱紀。同時,“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6](p329) “樂”體現著使人們和諧而不可變更的原則,這表明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基于人性的情感共通,其強調治理應當重視以整合的形式達致和諧的境界,“和”的理念不僅是治理狀態的描述,更是治理整合方法的呈現;其二,荀子在剖釋“正”時,強調“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6](p329)表明“樂”必須加以有效規制和引導,否則僅僅只是順從人性必然會導致混亂,而“正”的理念匱乏是“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6](327)導致治理失效的直接原因,因而為了避免此種情形,“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6](p329)將“正”的理念融入實踐之中是治理所必須完成的使命,故而“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6](p329)在荀子看來,在“正樂”之中隱含著對于“正治”的訴求,這與孔子所強調的“政者,正也”[13](p74)是一脈相承的,只是荀子通過其樂論使得先秦儒家對于良好治理秩序推崇更加清晰。
最后,荀子以樂論建構了理性主義治理進路。荀子認為“凡論者,貴有其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也。”[6](p381)“辨合”即立論合理,“符驗”即觀照現實,可以說“荀子強調思想領域的合理立論方式,其根基在于由現實而來的持之有據,理論應當通過社會生活進行有效的驗證”。[18](p91)因而,荀子對于先秦儒家樂論思想最大的貢獻在于其以樂論理解治理現實,把握治理規律,進而系統建構了明確的治理進路,呈現出鮮明的理性主義色彩。在荀子樂論思想中,“樂”有著擔綱統管儒家治理思想的作用和功能,荀子對此闡釋道“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6](p325-326)強調“樂”在形態上能夠通過確定主音而使得樂調和諧一致,能夠統御各種樂器調整節奏,因而“樂”是共同演奏完成樂曲的集合。而這一形態的意義在于“樂”能夠表征獨一無二的治道,完全能夠用來治理復雜多變的問題。具體而言,荀子通過其樂論中的三種機制進行闡釋:
其一,是“維齊非齊”的治理機制。所謂“維齊非齊”最初源于《尚書》,荀子在《荀子·王制》中對其解釋道“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6](p325-326)在他看來,這與“樂”的象征是一致的,即“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鑰,似星辰日月,鼗柷、拊鞷、椌楬似萬物”,[6](p331)治理與“樂”所面對的情境都是復雜多元的,而“維齊非齊”的治理機制就是以尊重治理對象差異為前提,實現整合式的多元治理,故而荀子強調“調和,樂也”,[6](p218)正是通過“樂”實現了現實場景中復雜治理情形的有效應對,而不是主觀、武斷地去改變治理場域與改造治理客體。
其二,是“禮法兼施”的治理機制。在荀子的樂論中,“禮”體現著柔性治理的方法施用,“法”彰顯著剛性治理的原則遵循,只有剛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的結合才更能使治理問題“迎刃而解”。但是,“禮法兼施”的有效治理機制卻難以闡釋,荀子則依靠“樂”解決了這一難題。一方面,“樂”作為“治道”的載體有著柔性的一面,即“樂者,圣王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6](p329)在荀子看來禮樂是一體的,其都有著潛移默化、教化人心的功能。另一方面“樂”作為“治道”的載體還有著剛性的一面,即“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6](p327)尤其是荀子強調“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6](p218)樂作為使人們和諧而不可變更的原則,“樂”能夠體現“法”所要求的服從與遵守。荀子強調正是因為有了“樂”的存在,“禮法兼施”這樣的治道才有了便于施行的可能性,故而他以“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6](p332)強調治道的施行是易行的,而“樂”中所包含的“禮法兼施”的治理機制正是“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6](p333)的緣由。
其三,是“化性起偽”的治理機制。如前文所述,相較于孔、孟,荀子更為關注作為治理現實的人性,荀子把個體的人性作為治理的起點,作為治理的關鍵,有效地把“化性起偽”作為其獨創性的思想,“荀子意在強調人性的后天培育和養成的重要性,這里的‘偽’,乃是‘人為’之意,他意在強調人性猶如璞玉,需要以后天之雕琢呈現其美”。[18](p91)而“化性起偽”的機制在荀子樂論中呈現得淋漓盡致,在繼承孔子“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13](p44)強調“樂”對于個人修養塑造的重要功能基礎上,荀子指出“窮本極變,樂之情也”,[6](p332)表明“樂”從其本質上說有著深入人們內心,從根本上改變性情的重要作用。荀子以其樂論中的“化性起偽”機制闡明了先秦儒家對于人性治理現實的精準認識和深刻關切,通過其樂論充分展現了“樂行而民鄉方矣”[6](p339)的現實例證,充分表明“樂”能夠讓人們向往治道。可見荀子之樂論以個體人性治理為切入點,統合了微觀的“人性之治”與宏觀的“天下大治”,將先秦儒家以樂論為載體的治理思想發展到了空前的高度。
四、何以啟發: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治理理論
誠如徐勇先生所嘆“愈是后發現代化國家,愈是前現代歷史輝煌的國家,愈是容易產生歷史落差造成的歷史悲情,也愈是容易趨于這樣的歷史斷裂性的極化思維。”[19](p2)事實上,體現中華文明特質,尤其是有著儒家思想文化深厚底色的治理實踐與治理理論發展從未中斷或停滯,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只是這些實踐智慧尚未被完整地抽離出來,形成一套基于中國文化傳統和當下實踐的統一世界觀和方法論,以構成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20](p15)因而,要走出西方治理的思想與范式“迷思”(mythos),必須建構根植于文明之中的自主知識體系的治理理論。前文所述之先秦儒家樂論思想,其在治理概念、治理命題、治理邏輯與治理模式的價值,有關治理理論的概念重塑、命題賦予、邏輯重構以及模式更新,正是通過啟發中國式自主知識體系的治理理論建構實現的。先秦儒家樂論思想作為一種確定無疑的“知識”,闡明了自主知識體系的治理理論中“治理”的核心內涵與關鍵功能。因而,面對當代中國治理現實要求,我們應當回到先秦儒家的樂論思想之中,再次理解其作為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關鍵向度的重要作用。
首先,先秦儒家樂論是一種中國式治理“知識”。要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治理理論,首當其沖需要理解何為自主知識體系并把握其核心。從概念上看,所謂“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指的是內源于中國歷史與當代實踐經驗所形成的關于人類社會運行規律的認知,按照一定秩序和內部聯系形成的整體”,[20](p15)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是中國知識,其在中國特有的實踐場域之中“應是被驗證過的,正確的,而且是被人們相信的”。[20](p18)先秦儒家以樂論為載體的治理思想正符合這樣的界定,其包含著豐富的中國式治理“知識”。以樂為喻,進而審視治理,正如孔子所強調的“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13](p16)回到樂論之中,中國式治理“知識”同樣是可以為人們所認識和理解的。
第一,從實踐驗證上看,“在中華數千年的文明史中,儒家顯然是中華文明形成以來的歷代顯學”,[21](p96)回溯上千年的治理實踐,儒家借由樂論所展現的治理思想,其作為治國安邦的主流學說得到了有效的實踐檢驗。歷史上,在“儒家全面供給社會政治秩序”[22](p6)的整體進程中,其不僅堅守被視為原則的綱常,并適時、因地、因事調適和發展,使得“儒學的重構一直在進行中”,[22](p5)原本只是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由于實現了與歷史變遷與社會發展的“同頻共振”,樂論所展現王道成為規制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因而其作為一種被驗證過的治理“知識”的價值更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從合理性上說,盡管完全肯定樂論所表達的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正確性失之偏頗,在現代性的沖擊之下,其畢竟只是中國古典時代的思想“孑遺”,存在著一定認知與時空的局限。但是,其所展現的合理性因素是難以否定的,尤其是“文明的難題需要道德合理性的建構來解決,然而對于每一個民族而言其道德合理性建構需要有現實的載體”,[23](p63)而樂論正是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重要載體,其作用正是面對當代治理困境,在樂論之下幫助人們“以儒家美德承載現代道德合理性建構提供了客觀依據”,[20](p63)進而尋求紓解之道。
第三,從獲取信任上看,被社會大眾棄如敝屣或者束之高閣的思想和理論都難以稱得上是一種真正的“知識”,而以樂論表達的先秦儒家治理思想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多數時間都為數量可觀的人群所信任。“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9](p756)儒家樂論體現著人與生俱來的普遍共識,在荀子生活的戰國時代,他能在“吾觀于鄉”[6](p332)的社會生活中發現“樂”所體現的信念為眾人所信服。而在當代,基于儒家文明“在心靈秩序、社會秩序與生活秩序的重建上,分別呈現出儒教、儒家哲學與儒家倫理學三種主要的理論/知識形態,讓傳統儒家在現代處境中,呈現為分科狀態的完備性學說形式”,[22](p7)使得在兩千多年的今天,仁愛、民本、和諧、正義等信念仍然融于國人的信仰,只是承載它們的樂論卻似乎被“遺忘”,亟待再次找回。可以說,先秦儒家樂論所體現的治理思想是一種完備的治理“知識”,其最為主要的現實功用在于為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治理理論源源不斷地供給思想資源。
其次,先秦儒家樂論蘊含著中國式治理的內涵闡釋。理解治理是實現有效治理進而達致善治的前提,而理解治理仰賴于對治理內涵進行恰如其分的闡釋。但是,現實問題在于:一方面,“‘治理’是一個‘被使用’遠勝于‘被理解’的概念。”[24](p120)對中國式治理內涵闡釋則更是如此,面對何為“中國式治理”的疑問,立足中國式治理實踐所建構的現實場域,闡釋治理內涵面臨著“將中國的國家治理與其他國家的國家治理區別開來,產生鮮明的中國特色”[24](p121)的緊迫現實要求;另一方面,不論是治理抑或是中國式治理都存在著被濫用的可能,其結果正是導致治理的內涵出現價值罅隙,“忽視了國家建構治理這一義素所蘊含的崇高價值追求,將公共生活中的一切管理活動,不論其路徑之優劣、技術之工拙、效能之高低,皆冠以治理之名”。[24](p121)如若解決不了上述問題,中國式治理的內涵可能面臨混沌不清與庸俗化的雙重困境,作為中華文明積淀所供給的中國式治理意蘊,也就難以呈現其高遠、深厚、廣博的精髓。
而先秦儒家樂論是闡釋中國式治理內涵的重要切入點。無論是作為“術”還是“道”的治理被普羅大眾所理解都絕非易事,先秦儒家始終將其作為重要的治理命題進行考察,所以孔子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13](p32)在與子路的對談中,孔子由衷感嘆道“由,知德者鮮矣。”[13](p96)可以說,“理解治理”不僅是現實治理面臨的挑戰,更是先秦儒家賦予當代治理的重要命題。為了實現有效的治理概念闡釋,先秦儒家持續引入樂論作為理解治理內涵的“工具”。孔子強調“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13](p12)其充分表明,樂論從始至終都是用以表達作為治理原則的“禮”與價值核心的“仁”的載體,其試圖通過這樣的闡述借以實現治理的邏輯重構。而審視以“樂”為場景的“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13](118)的故事,其與“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13](p48)孔子對于自己人生際遇的扼腕嘆息之間的前后呼應,體現了樂論作為先秦儒家天下大治政治理想的如實呈現,其不僅是以“仁愛”為核心的治理倫理的充分表達,而且更是以“盡善盡美”治理目標的形態描繪。借由樂論在潛移默化與潤物無聲之間明晰了治理之義。
孟、荀則接續了闡釋治理內涵的使命。在孟子這里,由于肩負與楊墨論戰的現實要求,他指出治理內涵是需要被進一步賦予的,尤其是需要使之具備仁義與民本的理念,這無疑是通過對治理概念的闡釋,實現了對治理命題的再造。因而,孟子重申“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13](p210)表明“理解治理”的命題最終要通過理念的融入,將治理的關鍵訴諸“仁政”之中,因而,孟子在“樂”的古今之變中把握其作為“仁義”載體的實質,作出“今之樂猶古之樂也”[13](p190)的論斷。對荀子而言,他從根本上分析了“理解治理”的邏輯與機制,強調“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遍也。”[6](p352)指出主觀上,人的本性可以使我們認識事物;客觀上,事物能夠被認識也是其規律所決定。但是關鍵在于必須遵循一定認知的原則,才能使人們的認知活動有效并持續,“理解治理”進而闡釋治理內涵也不外乎其理。同時,荀子強調“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圣人無兩心。”[6](p337)揭示了闡釋治理內涵的實質就是擺脫蒙蔽的過程,須把握“理”與“道”。而荀子給出的闡釋路徑正是通過樂論,因為,“樂”有著“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6](326)的現實治理原則表達,有著“治人之盛者也”[6](p329)的理想治理形式呈現。可以說,先秦“儒家三圣”的樂論思想無疑都是一種有著中國式話語和敘事的中國式治理內涵闡釋。
最后,先秦儒家樂論體現著中國式治理的功能統合。“雖然中國國家治理理論受到了西方的政府治理、善治與全球治理理論的影響,但在‘治理’話語譯介與使用過程中,既與中華優秀傳統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相呼應,又由改革開放后中國發展的現實語境所支持、規范與框定。”[25](p81)因而,中國式治理需要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治理理論,顯然是對西方治理理論的一種超越,其最終顯而易見的成效需要落實在治理功能實現之上。即“中國‘國家治理’這一概念包含著國家建構、公共管理與社會服務三重意蘊”。[25](p82)而實踐表明,西方治理理論很難去實現這樣的功能統合,先秦儒家樂論卻能夠以概念重塑、命題賦予、邏輯重構以及模式更新,有效地體現中國式治理的功能統合。
第一,從治理的國家建構意蘊上看。西方治理理論更多的是強調在中觀乃至微觀的范圍內“治理意味著參與者最終形成一個自主的網絡”,[5](p20)卻難以在宏觀的維度將國家建構融入治理理論之中,并且有著排斥國家作為主體參與治理的傾向,刻意“強調了國家在實施其宏偉藍圖時的不穩定性和無效性”。[26](p59)而這種武斷的結論顯然同中國幾千年來的治理實踐所獲得的治理經驗相互矛盾,同時,也與傳統中國由“家國同構”進而“家國同治”的治理邏輯相悖。“國家建構”不僅是中國式治理最為重要的內涵,更是實現有效治理的重要模式。而先秦儒家正是通過其樂論思想,強調“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3](p268)以“天下大治”為己任,在其樂論思想中突出“樂”所具有的“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9](p713)的國家建構功能,強調治理價值判斷,以“惡鄭聲之亂雅樂也”,[13](p114)辨別國家建構倫理;以“樂則韶舞”[13](p98),“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13](p34),重視堅守國家建構秩序。可見,先秦儒家樂論所體現的早已不是關乎個人之善、社群之善,而是站在“大樂與天地同和”[6](p721)的國家治理高度,凸顯“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6](p327)的國家建構意蘊,這是當代西方治理思想所遠遠難以企及的。
第二,從治理的公共管理意蘊上看。伴隨著當代治理理論發展,新公共管理呈現出向新公共治理理論發展的趨勢,其表現出特征是更加重視多元主體、網絡關系、持續互動、公共價值等問題。[27](p50)其核心在于強調“必須進行科學、高效的公共管理”,[25](p88)以此實現有效治理的目標。面對西方治理理論實踐中出現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失衡問題,新公共管理理論“它超越了工具理性的淺短視野,包含了民主、公平、責任、回應、正義等價值理性的成分”。[27](p50)那么,在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治理理論的過程中,我們是否實現與治理理論發展潮流進行有效對話,把握住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平衡呢?事實上,先秦儒家正是通過樂論同時考量了治理的兩重維度,其啟發在于通過“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13](p190)的判斷,在“‘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乎?’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13](p190)的對話中,隱喻著以民本主義為尺度的治理衡量標準,民本既是治理的工具理性目標,同時,更是治理的價值理性訴求,使得治理工具理性所關注的結果形態具體,使得治理價值理性所強調的倫理得以伸張。“眾樂”是實現治理主體的多元,“與人”是對治理關系網絡的建構,“好樂”則是持續的良好治理狀態。可以說,“樂”在“金聲而玉振之也”[13](p314)中,既體現了“治術”更表達了“治道”,朱子所謂“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17](p294)概莫如此,最終使得治理“成于樂”。[13](p44)
第三,從治理的社會服務意蘊上看。治理的社會服務“是國家建構與公共管理的終極目標”,[25](p98)因而,其關鍵在于“均衡化與可及性的公共服務的實現”[25](97)。先秦儒家樂論思想不僅試圖以“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13](p266)去揭示“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13](p266)的道理。其更有助于我們在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治理理論中,基于中國式治理“知識”,探索有效的治理方法和路徑。一方面,“中和之紀也”[6](p325)所體現的“樂之和”,其啟示在于社會服務必須形成有效共識,才能在避免沖突的前提下實現社會服務供給力量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6](p329)所強調的“樂之正”,其啟示在于社會服務必須堅持原則,既要保障公共產品供給的適度,更要保證公共產品供給的公平。此外,“維齊非齊”的治理機制強調治理公共服務應當正視多元需求,堅持供給差異化原則;“禮法兼施”的治理機制強調治理不僅要提供“柔性”的社會公共產品,也要確保“剛性”的社會公共秩序;“化性起偽”的治理機制提示治理公共服務應當重視對于個體人性的陶冶和關懷,為實現善治創造條件。
五、結語
先秦儒家樂論是理解儒家治理思想的關鍵向度。回到樂論之中,能夠更加清晰地睹見先秦儒家“天下大治”的治理目標,以“仁愛”為核心的治理倫理和其試圖塑造的“盡善盡美”的治理形態。可以發現“儒家三圣”在統合問題意識與政治理想方面的孜孜以求與悉心畢力,窺見“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13](p198)詰問中所展現的儒者的擔當和使命。先秦儒家樂論在中國政治哲學“道與德”“理想人格與理想社會”“平等與等級”“家國天下的關系”“王道與霸道”“尚民愛民與人民至上”“內圣外王與人民民主”“德治、禮治、法治”[28](p24)等八個重要議題中都有創建和闡發。其在秩序重建中,鋪陳了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現實主義治理底色;在功能實現中,表達了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民本主義治理傾向;在系統建構中,形成了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理性主義治理進路。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先秦儒家的樂論思想,可以發現并解讀“孔子仁知且不蔽”[6](p341)背后的儒家治理思想密碼。
先秦儒家樂論賦“樂”以政治教化的功能,使之成為表達治理話語的重要工具,更為日后的樂論思想奠基定調——既樹立起基本的審美評判標準,又為此后的“樂治”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后來者遵循其批評體系所形成的主流邏輯,聚焦于“樂”與“治”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總結、闡發儒家樂論的價值內涵:無論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漢樂府民歌“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29](p1756)的精神表達;還是“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30](p226)的唐太宗,其命太常卿祖孝孫考古音、正宮商、去“雜聲”,重定大唐新樂,復興雅樂之制;再或是朱熹所言之“圣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31](p1),重申由先秦儒家樂論所明確并延綿的治理傳統。其或基于治理理論,或立足治理實踐,它們結合自身特定的政治語境,不斷補充和創新,使儒家“樂論”的內核逐漸完善、臻于成熟。
回溯儒家治理想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演進,先秦儒家樂論正是以“樂”為載體,錨定了后世儒家治理思想的形態與走向。其深刻影響并明晰了整個儒家治理思想體系所關切的治理目標、治理倫理、治理形態的基本命題,后來者更多的是在其之上的“錦上添花”,但卻始終延續其思想理路。先秦儒家樂論借由中國式治理知識體系建構方式,通過“樂”這樣日常生活的審美形態,以“弦外之音”的獨特方式在觀念層面闡發治理理想,以“黃鐘大呂”的嚴肅探討在秩序維度觀照治理現實。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娓娓動聽”絲毫不妨礙其讓儒家治理思想的“微言大義”歷久彌堅。其為當代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治理理論提供啟發,為探討中國式治理“知識”,闡釋中國式治理的內涵,實現中國式治理的功能統合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和理論供給。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N].人民日報,2022-10-26(001).
[2][英]R.A.W.羅茲.理解治理:政策網絡、治理、反思與問責[M].丁煌,丁方達,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3]江必新,鞠成偉.國家治理現代化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
[4]習近平. 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09-25(002).
[5]俞可平.走向善治[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
[6]荀子[M].北京:中華書局,2015.
[7]丁成際.荀子樂論[J].諸子學刊,2017,(02).
[8]李潤生.荀子《樂論》研究50年(1958—2008)[J].中國音樂學,2010,(01).
[9]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7.
[10]雷永強.論孔子樂論的情感世界[J].中國哲學史,2013,(01).
[11]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2]周世露,楊廣越.孔子樂論之美學特質再思考[J].中國文藝評論,2019,(07).
[13]四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7.
[14]包剛升.儒法道:早期中國的政治想象[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
[15]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先秦兩漢編[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16]孔子家語[M].北京:中華書局,2016.
[17](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8]易星同,李南樞.治理何以可能:荀子“性偽”論價值闡微[J].理論導刊,2024,(02).
[19]徐勇.國家治理的中國底色與路徑[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20]郁建興,黃飚.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及其世界意義[J].政治學研究,2023,(03).
[21]何哲.仁與禮:中華儒家思想及對完善人類現代治理的啟示[J].學術界,2023,(12).
[22]任劍濤.儒教建構與儒家的現代適應性路向[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06).
[23]康宇.現代文明難題與儒家美德合理性基礎論證[J].文史哲,2007,(05).
[24]蘇曦凌.中國“治理”話語的時空規定性及其政治使命[J].探索,2021,(04).
[25]張英魁.中國“國家治理”的三重意蘊:國家建構、公共管理與社會服務[J].中國治理評論,2024,(01).
[26][美]喬爾·S.米格代爾.社會中的國家:國家與社會如何相互改變與相互構成[M].李楊,郭一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
[27]劉強強,包國憲.制度優勢如何提升治理效能:我國政府績效管理邏輯探析[J].學習與實踐,2021,(11).
[28]江暢.中國政治哲學重點關注的八大問題[J].湖北社會科學,2023,(02).
[29](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0](唐)吳兢.貞觀政要:卷6[M].長沙:岳麓書社,1991.
[31](宋)朱熹.詩集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1.
責任編輯" "唐" "偉
作者簡介:易星同(1991—),男,法學博士,貴州省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貴州貴陽,550002);薛雪(1995—),女,文學博士,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貴州貴陽, 550002)。
基金項目: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后期資助項目(CXHQ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