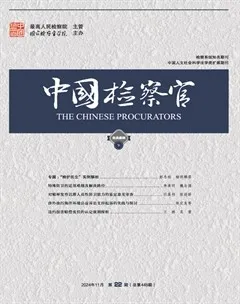涉外油污海洋環境公益訴訟支持起訴的實踐與探討
摘 要:在當前涉外油污海洋環境公益訴訟支持起訴中,存在規范依據確定難、對象主體界定難、審查要點把握難等桎梏。檢察機關可依據《民事訴訟法》第58條作為支持起訴依據,并優先適用《海洋環境保護法》確定的一元化“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為支持起訴對象。在此基礎上,以《1992年油污公約》為主、最高法《關于審理海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為補充,明確不同部門的索賠權種類,明晰損害賠償責任。
關鍵詞:涉外船舶油污 海洋環境保護 檢察支持起訴
涉外油污海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是指因涉外船舶油污泄漏致海洋環境受損,由法定主體依據法律規定提起的,旨在修復與補償受損的海洋生態環境系統,要求責任方承擔環境損害賠償的訴訟。檢察機關通過支持提起涉外油污海洋環境公益訴訟,可以共同構筑起捍衛海洋生態安全的堅實防線。但是檢察機關在支持起訴中尚缺乏充分的實踐經驗和深入的理論探索,本文擬從司法案例出發,圍繞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難點問題進行分析研究,以期為司法實踐提供有益參考。
一、基本案情及辦理過程
2018年,新加坡籍運輸船“ELLINGTON”輪(以下稱“艾靈頓”輪)與錨泊的馬紹爾籍油輪“ZORRO”輪(以下稱“佐羅”輪)在嘉興某海域發生碰撞,導致“佐羅”輪運載的750余噸基礎油泄漏,造成海洋污染面積約1800平方公里,對杭州灣海域的生態環境、漁業資源等造成嚴重損失。2019年,嘉興市農業農村局、生態環境局、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以下簡稱“三原告”)向寧波海事法院提起訴訟。
浙江省嘉興市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嘉興市院”)應三原告請求于2019年8月依法對該案支持起訴。嘉興市院決定支持起訴后,第一時間向寧波海事法院提交《支持起訴書》。嘉興市院發揮法律專業優勢,協助三原告進行針對性的證據補強。一是就機構改革后三原告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等完善證明材料,夯實三原告具有訴訟主體資格的證據基礎。二是針對三原告訴訟請求中的“海洋環境容量損失”,嘉興市院協助補充提供已實際采取的海岸線整治修復、海洋增殖放流等合理恢復措施的資金投入情況報告,以獲得法院最大限度的支持。三是針對本案鑒定報告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問題,嘉興市院多次走訪相關鑒定專家組成員,對評估鑒定報告中有關點位選取、數模建立、損害金額計算等專業技術問題進行分析論證,并要求專家做好當庭接受質證的準備。2021年3月,寧波海事法院判決三原告享有海事債權4600余萬元。
二、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規范依據
目前有多部規范對檢察機關支持起訴作出規定,如部門法中《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訴法》)第15條、第58條以及《海洋環境保護法》第114條,最高檢制定的《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等司法解釋也都對檢察機關海洋環境公益訴訟支持起訴作出了規定,但實踐中對于上述規定的具體適用還存在一定爭議,特別是對《民訴法》第15條能否作為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依據存在分歧,檢察機關在支持起訴中應當準確適用支持起訴的規范依據。
(一)部門法中的規范依據
《民訴法》中有關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規定有兩條,分別是第15條和第58條,因涉外海洋環境保護具有顯著的公共利益屬性[1],而“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提起的訴訟為公益訴訟,契合第58條第1款的解釋;檢察機關對“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支持起訴亦符合第58條第2款的文意解釋,因此應當以第58條作為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依據。至于《民訴法》第15條,從立法淵源看該條承繼于1982年《民訴法》第13條,該條規定生效時我國并未有公益訴訟的相關規定,因此在既定的歷史時空坐標下,該條規范不可能前瞻性地囊括環境公益訴訟這一彼時尚未在法學理論與司法實踐中形成共識的新興議題。另外,《海洋環境保護法》第114條第3款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可以支持對“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提起海洋環境公益訴訟,是檢察機關支持起訴最為直接、明確的規范依據。
(二)司法解釋中的規范依據
“兩高”制定的《關于辦理海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最高檢制定的《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100條,均對檢察機關支持起訴作出了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可以援引上述規定作為支持起訴的規范依據。需要注意的是,對于最高法《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因該條規定系對《民訴法》第15條的具體細化解釋,如前所述《民訴法》第15條規定并不能作為檢察機關支持海洋生態環境公益訴訟起訴的規范依據,因此該條亦不能作為檢察機關支持海洋生態環境公益訴訟起訴的規范依據。[2]
三、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對象主體
根據《民訴法》第58條、《環境保護法》第58條之規定,“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組織”和“行使海洋監管權的部門”均可提起海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但是,《海洋環境保護法》第114條又規定了檢察機關只能對“行使海洋監管權的部門”提起的海洋環境公益訴訟支持起訴,與前述規定存在一定沖突,即檢察機關是否可以支持“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組織”提起海洋環境公益訴訟存在爭議。此外,我國海洋生態損害政府索賠權整體呈現出“分散式監管+分工式索賠”的特征[3],此種索賠模式具有部門分工界限不明晰的天然缺陷,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海洋生態環境索賠的效果。對此,檢察機關在支持起訴中,要準確界定海洋環境公益訴訟起訴主體。
(一)以一元化的“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為支持起訴對象
確定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對象主體,即為確定檢察機關可以支持由誰提起的涉外油污海洋環境公益訴訟。從部門法層面看,《民訴法》《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雖然都對提起海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對象主體范圍作出規定,但《民訴法》《環境保護法》綜合性、概括性的法律規范,而《海洋環境保護法》與之相比,規范的是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特殊部分即海洋生態環境保護領域,因此《海洋環境保護法》是特別性規定[4],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應當優先適用《海洋環境保護法》的規定。從司法解釋層面看,根據“兩高”《關于辦理海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規定,檢察機關可以對“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支持起訴。最高法《關于審理海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條規定中,將“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明確為《海洋環境保護法(2017年修訂)》第5條[5]規定的部門。從司法實踐層面看,對于“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組織”是否可以提起海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問題,審判機關也均予以否認,如最高法在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與榮成偉伯漁業有限公司再審案中,也明確認為社會組織不是提起海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適格主體。[6]
因此,不論是從“特殊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考量,還是從當前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的有力背書看,“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是提起涉外油污海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唯一適格主體。
(二)“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政府索賠權縱向權限的確定
確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政府索賠權的縱向權限,是為確定政府索賠主體的具體行政層級。《海洋環境保護法》在2017年、2023年兩次修訂中均未對政府索賠主體的縱向管轄權作出規定,但原國家海洋局于2014年實施的《海洋生態環境損害國家損失索賠辦法》第4條以海域管轄權為標準[7],對不同層級行政機關的索賠權限進行了劃分。因此在確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政府索賠權主體層級時,應當以海域管轄權為標準,并參照各地“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機構改革后職能配置、管轄權限等確定具體索賠主體層級。需要指出的是,“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并非狹義上具體對該個案進行調查處理的行政機關,只要該行政機關具有海洋環境監管權且海洋環境損害事故發生地在其所轄海域即可成為政府索賠主體,檢察機關可以對其支持起訴。
(三)“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政府索賠權橫向分工的厘清
油污污染海洋環境造成的損失包括海洋生態直接損失、海洋生態環境修復費、漁業資源損失等,厘清“行使海洋環境監管權的部門”政府索賠權的橫向分工,是為確定不同行政機關享有何種損失的索賠權。《海洋環境保護法》第4條對各行政機關之間的分工進行明確,在一定程度對不同部門享受的索賠權種類進行了回應。
本案辦理過程中,當時生效的《海洋環境保護法(2017年修正)》第5條雖然規定了不同行政機關之間的權限分工,但是因2018年國家機構改革中部分行政機關的職能劃轉,該規定并不能為各行政機關享有的具體索賠權種類提供明確指引。為此,嘉興市院協助三原告提供機構改革后職能配置、內設機構設置等文件,從而確定生態環境部門負責海洋污染損害的生態環境保護等工作,自然資源規劃部門負責對海洋生態修復等工作,農業農村部門負責漁業資源監管等工作。因此,在確定不同部門的索賠權種類時,應當以《海洋環境保護法》第4條規定為主要依據,并結合機構改革后部門的職能配置、內設機構設置等規定,準確界定不同行政機關所享有的索賠權種類。
四、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審查重點
在涉外油污海洋環境公益訴訟中,需適用我國締結或參加過的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國際公約,而我國締結或參加過多個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國際公約,如《1992年油污公約》《2001年燃油公約》等。公約適用的不同關系到承擔責任主體、承擔責任份額的不同,檢察機關在支持起訴過程中,要對此類案件的審查要點準確把握。
(一)適用涉外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的確定
我國締結或參加過多個涉外船舶油污污染海洋環境損害糾紛的國際公約,在確定適用的公約時,主要依據是泄漏油污的種類和屬性。《1992年油污公約》第1條第5項、《2001年燃油公約》第5條第6項分別對各自規范的油污種類和屬性進行列舉,因此應以此作為適用不同公約的依據。本案中,“佐羅”輪泄漏的油料系高度精煉的礦物油,屬于《1992年油污公約》中列舉的持久性油類,所以本案應當適用《1992年油污公約》。另外,在“達飛佛羅里達”輪案中,最高法在再審判決中適用的國際條約為《2001年燃油公約》,其依據是船舶碰撞導致集裝箱船“達飛佛羅里達”輪泄漏的油料為燃油。[8]
(二)非漏油船賠償責任的確定
《1992年油污公約》規定了船舶所有人的嚴格責任、獨立的油污損害賠償責任限制制度和強制保險制度,所規定的油污損害賠償責任基金是僅供清償油污損害賠償請求的專項基金。[9]從法律淵源看,《1992年油污公約》承繼了《1969年油污公約》的宗旨和精神。《1969年油污公約》中規定了油污損害的賠償范圍和賠償限額、漏油船所有人的嚴格責任和強制保險等制度,平衡了船方、貨方及油污受損害人等各方利益,國際上實際已形成了針對船舶溢油損害由漏油船直接賠償、國際油污基金補充賠償的一套完整、閉環的體系。因此,根據《1992年油污公約》的規定,除非碰撞完全由非漏油船有意造成,非漏油船均不直接承擔賠償責任,僅由漏油船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即“誰漏油,誰負責”。因此,本案中非漏油船“艾靈頓”輪雖然負有碰撞責任,但并不直接對油污受損害人承擔海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而是由漏油船“佐羅”輪承擔全部的海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
(三)涉外油污污染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種類的確定
《1992年油污公約》第6條對“污染損害”的種類進行了規定,但實踐中對于“污染損害”理解存在一定爭議,其焦點是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損失、海洋環境容量損失、海洋生態環境修復費、漁業資源損失是否屬于上述“污染損害”。對于海洋生態環境修復費,本案事故中泄漏的基礎油持久性油類,從長期來看,溢油事故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危害客觀存在且不容忽視,應認定符合《1992年油污公約》第6條規定的“污染損害”。對于漁業資源損失,其屬于油污污染所導致的直接損害,該項損失亦應認定為《1992年油污公約》第6條保護的“污染損害”損失。
而對于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損失和海洋環境容量損失,本案審理法院認為該兩項損失是按照理論模型計算出的抽象量化損失,并非已經實際遭受的損失,亦未有證據證明實際采取任何合理措施恢復環境,也無證據表明將要采取何種合理恢復措施,故該索賠不屬于上述規定“污染損害”的范圍。對于此項損害請求權,最高法《關于審理海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解釋》)第7條對《1992年油污公約》進行了補充,有學者提出,二者并不是完全的排斥關系,而應利用“提取公因式”的規范方法,在以海洋生態損害賠償為“括號外”的主因素時,識別所有的法律規范,予以準確適用。[10]筆者認為,在處理油污造成的相關海洋生態環境賠償時,亦有適用《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解釋》的余地,而非僅適用《1992年油污公約》的規定,以更好地保護海洋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