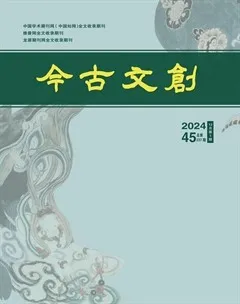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域下探析溝口健二的敘事特征
【摘要】日本昭和時期的電影大師溝口健二以其獨特的鏡頭語言和敘事特征深刻地對女性角色進行了描繪,成為世界電影史上的重要導演。他在《西鶴一代女》(1952)和《雨月物語》(1953)等代表作品中,通過悲劇的女性形象符號、閉鎖的女性空間敘事和先鋒的女性意識敘事構建,不僅表達了對舊社會的父權制反思,也呈現出了女性的主體性與復雜性。研究敘事特征不僅在內容層面更好地理解溝口健二的電影創作風格,也為女性主義電影的創作及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女性主義;溝口健二;電影敘事;女性形象;日本電影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45-009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22
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以及文化教育的進步,讓女性地位得以不斷提升。在“女性主義”或“女性主體性意識”在學術以外的范圍中被廣泛提及的當下,其實過去許多文藝作品中早就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而20世紀中期,日本電影就已經展現了初步的女性主義思想。日本昭和時期的電影大師溝口健二的作品以刻畫女性形象而受到國際的矚目,日本著名的電影評論家巖崎昶曾評價過溝口健二的作品:“日本的電影作家描寫女性的內容雖然不少,但是至今為止,未曾有人超越溝口。”[1]足以可見溝口健二在電影中展現的女性主體性意識以及他塑造的女性形象給當時觀眾帶來的思想沖擊性與其社會影響的先鋒性。本文將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以溝口健二1950年前后的《西鶴一代女》及《雨月物語》等著名作品為例,分析其塑造的人物形象符號及閉鎖的電影的空間敘事的特征,再從女性意識的角度進行分析,從這三個方面總結出溝口健二在女性主義視域下的主要的敘事特征。
一、悲劇的女性形象符號
溝口健二從1924年就已經開始專注于女性形象在電影中的刻畫,而他后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逐漸產生了共通性,正如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在評論溝口健二時所說:“經過苦難的磨煉成為圣善的女人,忘掉過去的一切對男人給予寬恕。”[2]溝口健二一直在構建一種符合自己理想的悲劇且崇高的女性形象符號,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雖然也是一種“凝視”,但其中的憐憫與對社會的諷刺,從電影史甚至從女性主義理論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對于女性符號的一種全新的視角的展現。
(一)情感與欲望的接受者
不可否認在現代社會中的文明中一般會將情欲進行罪惡化,以此規訓人們對情感與欲望的羞恥心,從而維持社會穩定。弗洛伊德在談及情欲時曾認為“文化要求不斷地升華,從而削弱了愛欲這個文化的建設者。由于愛欲的削弱而導致的非性欲化解放了破壞性沖動”。[3]雖然在弗洛伊德的眼中文明在壓抑人類的愛欲,且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但在文藝作品中創作者依然渴求達成一種文明與愛欲之間的平衡,或者實現情感與欲望的自由。而女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作為男性中心主義社會的邊緣存在,成了禁忌的“情感與欲望”的象征,由于男權社會中只有男性的情感具備正當性,她們多數情況在被動的位置。如果這是一種社會與文化的不公允,那么溝口健二在自己的作品中刻畫一種擁抱自己情感與欲望的女性主人公,可以說從另一條道路突破了當時的文化偏見。
溝口健二的女性角色具有高度的主體性,她們通過情欲的表達,彰顯出內心的渴望和掙扎。情欲在他的電影中不僅是個人情感的流露,更是對社會壓迫的反抗和自我認同的追求。田中娟代飾演的女主春子在《西鶴一代女》(1952)中就是情欲的追隨者,她的一生充滿了對愛情的追求和對命運的抗爭。溝口健二在塑造春子時有別于原作井原西鶴的長篇小說《好色一代女》,原作中的主人公更多是被性欲所驅使,而電影在改編的時候讓春子成了追求愛情的女人。她的情欲表達不僅是個人情感的體現,更是對封建社會壓迫的一種無聲反抗,春子通過與不同男性的情感經歷,展現了她對幸福的渴望或是對于真愛的渴求,同時也是對社會束縛的掙扎。春子在這個作品中表達的情欲不僅是個體的情感需求,更是她在封建社會中尋求自我認同和價值的方式。
《雨月物語》(1953)則更加激進,若狹化身為鬼的原因就是死前沒有體會到愛情,而她騙主人公原十郎只是因為她想體驗情欲的快樂。若狹的情欲不僅是對個人幸福的渴望,更是對戰亂和社會動蕩的逃避。她的情感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主體性,揭示了她內心深處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壓迫現實的反抗。若狹不僅在情感上深深吸引著觀眾,也通過她的情欲表達,展示了女性在動蕩時代中的主體性和自我價值,足以見得情欲在溝口健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重要性。
(二)社會悲劇的犧牲者
談及社會時不得不提溝口健二在20世紀50年代創作的時代背景。二戰后的日本在經濟上面臨崩潰,想利用西方的現代化快速恢復本國經濟。東西方思想產生沖撞之外,電影行業也出現了規制的要素。如此情形下為了不讓日本喪失民族主體性,溝口健二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的電影題材雖然多為古代,但其現實主義的內容也成了一種反抗的工具,除了強調艱難處境之外,也通過塑造悲劇的女性形象重新讓觀眾反思自己的選擇。
溝口健二電影中的女性角色常常承受著極大的社會壓迫,她們的命運充滿了悲劇性。這些角色通過她們的經歷,揭示了社會結構中的種種問題和壓迫機制。上文中提及的《雨月物語》的若狹就是典型的悲劇角色,她原是一名貴族,但因戰亂而淪落為野鬼。她的命運是社會動蕩和戰亂的產物,揭示了戰爭會讓社會結構崩潰,這樣的災難是不分性別和階級的無差別的悲劇。《西鶴一代女》的春子也是這樣一個充滿悲劇的人物,女主春子所經歷的苦難并不是她本身造成,她更多是被動地受到社會中男性的拋棄和背叛。女主無能為力的悲劇經歷讓她不得不把希望放在佛教上,使得作品的現實主義特性得到了加強。《近松物語》(1954)從結尾來看雖然歌頌了封建時代的自由戀愛,但是女主人公阿珊依然是無法反抗封建社會毒害的女性形象,以至視死如歸的阿珊反而更加突出一種無力的悲涼感。
20世紀50年代正是日本戰后重建的關鍵時刻,也是日本電影剛剛步入黃金時期的年代,溝口的《西鶴一代女》等作品以女性人物作為重點的影像符號,并不是單純從性別出發,而是以一種文化符號反思了社會的毒害,她們抗爭的態度與愛情的追求,給世界電影史帶來了東方韻味的悲劇女性形象符號,成為世界電影史中女性銀幕形象的經典之一。
(三)自我意識的和諧者
雖然溝口健二構建了在當時來看非常典型且發人深省的女性形象,但是從如今的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溝口健二的作品還是有一部分局限。他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與如今的后現代新女性最大的不同是她們依然是自我意識的和諧者,她們的生活驅動一直是圍繞男性的,展現出了一種男性的不可缺席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溝口健二筆下的女性人物確實表現了自己的情欲,但是正如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露西·伊利格瑞女性在闡述“非一女性”時提到的觀點,女性的“非一”的情感表現著實威脅到了男性話語中欲望的固有概念,至此,女性的欲望無法真正被男權世界所認同,因此由男性所建構的欲望表達系統當中,女性依然還是依附著男性。正如電影《雨月物語》的若狹雖然表達了欲望,但依然需要一位男性伴侶才能達成自我完整。《近松物語》也依然是以兩性關系貫穿了整部電影的敘事。溝口健二雖借助女性形象來表達人在面對世俗的無力,但他依然保有著男性視點,將女性的情欲放在男性邏輯之下,將性別成為性別的綁定關系的籌碼,但在19世紀50年代還沒有女性理論出現,所以這樣的局限同時也是時代的局限,也在未來女性電影創作時能夠脫離男性視點的一種啟示。
二、閉鎖的女性空間敘事
在文字敘事空間與寫真攝影理論的結合發展中,電影的空間研究得以進入到電影研究的視野。與文學不同的是,電影最基本的表現形式是鏡頭,導演與剪輯師通過鏡頭排列組合,由二維畫面構建出了電影空間。電影敘事的空間除了有書面敘事的空間之外,還要由場景、攝影的運動方式構建。而作為觀眾在蒙太奇的影響下不僅接受了故事,也在腦中構建了想象的空間。溝口健二的女性主人公通常是處于閉鎖的表現空間內,這樣特別的空間敘事,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在當時具有開創性。1979年,女性文學研究《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十九世紀文學想象》出版,其中作者桑德拉和蘇珊就女性與閉鎖空間的關系做出了解釋:“女性文學被閉鎖于男性的文本之中,她們要逃脫這些文本的控制,只有通過智謀和間接的方式。”[4]所以在電影的空間敘事中,不同的空間給予了人物不同情感表現,這樣的心緒也通過銀幕傳達到觀眾的心中。從女性角度來說,在社會這樣的公共空間內大部分是閉鎖的或是被壓迫的,在面對這樣的社會困境之時,女性如何抗爭,其人性光輝應當如何展現,成了溝口健二在電影中不斷探索的主題之一。
(一)“不存在”的私人空間
私人空間通常令人感到的是安全與放松。這里的私人空間通常為單獨存在或者處于家庭中,但是提及家庭的建立時,不得不從時代的角度分析。很明顯,封建時期家庭概念依舊是在以男性為中心之下得到完成的,女性在家庭中兼具著不同職責:妻子、母親、女兒。女性的權利和地位逐漸被剝奪,甚至到了極端的地步。如果理想中的私人空間“家庭”對女性而言是夫妻兩人平等,但是實際的封建時期的情況是家是以男性(丈夫或兒子)為中心建立的。從歷史話語的角度來看,男性是家庭的絕對持權者,也代表著話語權,而女性通常是作為依附而存在。從生產力的角度來看,和如今的現代社會不同,生產力沒有得到發展的封建社會或者其他的社會形態,男性因為生理上比女性更加適合進行長時間的體力勞動成為主要的生產力,當男性是生產力時,他們便可以決定生產關系,以至于如何分配資源或者各種制度。封建時期傳統的家庭對于女性的封閉屬性本就存在,只是被意識形態所掩蓋,讓女性無法察覺,也因生產力的原因,她們也無法反抗。
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在封建的男權社會中,男性外出工作掙錢,獨留女性在家打理家務或者照顧老人與孩子。再從家庭的構成方式出發,大部分封建家庭都是以未成年女兒“寄養”在家,成年之后就想要女兒嫁到丈夫家,女性的“家庭”的變動性普遍高于男性。而如果拋開“家庭”的私人空間,則是“完全獨處”,與現在社會不同,在封建社會中的獨處則是拋棄社會資源的不被認同的存在。所以在這兩個社會的現實基礎上,溝口健二在作品中構建了一種“不存在”的私人空間,以表示對女性生存空間的嘆息和諷刺。
影片《西鶴一代女》表現的場景就符合了一種女主的私人空間逐漸消失,向公共空間融合的趨勢。在影片開頭,田中絹代所演的主人公春子穿著和服在夜晚踱步,躲避著周圍的行人,慢慢走到殘垣之間。從影片開頭,暴露在公共空間中的春子,與周圍的街道格格不入,直到她回憶起過去還在當侍女的經歷時,春子的近景增加逐漸成為鏡頭的主題,而關于她的悲劇才真正開始。在故事后面,無論街頭賣藝,還是被買去作妾,又或者是當高級藝妓,這些本應該是私人場景,春子都沒有很好地融入其中,始終是男性在占據主體地位,而春子的歸屬感只有在重回寺廟時獲得了一些。而私人空間的消失其實從電影的開頭一直貫穿到結尾。例如春子其實是為領主生了一個兒子,但是作為妻子的她卻從影片開頭就沒有得到過對方的接受,反而在后面被認為是破壞了家族的聲望。在結尾春子雖然遠遠地見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但是也只能見著最后一面。所謂她心心念念的幸福的私人空間其實從一開始就不存在,而這有很多原因是封建社會所造成的。
(二)閉鎖的社會空間
首先,社會公共空間對于私人空間而言,它的特性是開放且自由的,有比私人空間更多的資源。但當主體不是被社會認可的群體時,社會空間的開放性會消失不見,反而是更加閉鎖的存在,這樣的邊緣群體時刻都在受到禁錮。波德萊爾對于邊緣群體有著分析:“這些局外人或觀察者還包括了詩人、拾荒者、女同性戀、老人和寡婦(一般假定這群人可以躲過令人討厭的異性戀審視),以及娼妓和流鶯,她們在發展中的大都市里全都仰賴機智過活。”[5]而溝口健二的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大部分在上述的群體之中。而從電影內容出發,主人公處在的環境旋即形成了對于社會的批判,正如上一節溝口健二對于舊社會中女性私人空間的困境的展現,也從另一方面說明社會空間也未必會對女性有所憐憫。
例如《祇園姐妹》 (1936)和《祇園囃子》 (1953),兩部作品在中心立意雖然有不同,但是都展現了當時藝伎作為女性的邊緣群體的種種辛酸遭遇,他們雖然在京都祇園這個開放的社會空間之內,依然不被身邊的人理解,被自己的客戶欺騙,并且她們沒有可以逃離的選項,只能不斷忍受。而《阿游小姐》(1951)又與上述兩部不太一樣。如果說祇園姐妹和祇園囃子的女主的身份已經確定好了,這部作品中田中絹代飾演的阿游和乙羽信子飾演的阿靜都是因情所困,她們都有著自己想要追求的愛情,但是陰差陽錯讓他們的角色處于換位的情況,這讓他們三個人生活的場所宛如煉獄,而影片的結尾也由阿游退出阿靜難產死亡作為一種情感的啟示,但是無一例外影片中的女性大多都在無形的閉鎖中,難以自拔。
《進松物語》中的女主人公阿春雖然已經結婚,但是她的丈夫只是想掙錢,也對阿春有了誤解。這個家庭雖然構成,但是從阿春的視角來說并不幸福,因為其結婚的動機只是阿春的家人讓她去結婚。她的姿色與丈夫的財富形成了一種交易,但并沒有形成真正的愛情,這也是封建時代常有的情況。而影片開頭因為通奸而游街示眾的畫面,為這部電影奠定了基調,也就是女性無時無刻不被婦道禮教約束,這是一種社會潛規則,這種社會空間成為這部電影一直貫穿且無法消散的存在。起初被誤解的阿春也在故事的發展中逐漸喜歡了古川,在結尾,阿春和古川也與開頭的游街示眾一樣,只不過這次在馬上的是他們倆。影片最后以眾人的指點以及阿春在馬上的微笑和古川痛苦的表情,這三個立場及象征意義不同的鏡頭做結尾。如果戀愛是私人的,那么在面對社會的禮教時,便從私人空間敘事成了公共的空間敘事。通過對于深陷困擾且無奈的阿春的刻畫,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禮教對于女性的壓迫。
無論是不存在的私人空間還是步步緊逼的社會空間,溝口健二的作品中,他的女主人公都沒有放棄生活的希望,依然在為自己期盼的美好未來去活著,這反而又成了一種諷刺。《雨月物語》《西鶴一代女》等作品中,女性最后的結局都無依無靠并且被社會所譴責。這種電影敘事的空間充斥著的是封建社會吃人的悲涼氣氛,但也形成了他的獨特的閉鎖敘事風格。
三、先鋒的女性意識敘事構建
對于女性意識的概念認定學界有不同的說法,這里采用張阿嬌的碩士畢業論文《巖井俊二電影中的女性意識研究》中的綜合判斷作為本次研究的參考:一種女性主義電影中的精神狀態,創作者無關性別,有意對女性的處境加以照拂,并且從女性的立場出發對自身以外的世界加以注視。[6]溝口健二的作品無疑是體現了女性意識的,但是從年代來看他的作品從30年到50年時就有了女性意識的創作風格,無疑在電影史上有著一定先鋒地位。
溝口健二在創作的時候有意將自己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進行特別化處理,正如日本電影學者斉藤綾子所說,溝口作品中的女性共有兩種,一種是幫助男人出人頭地而甘心奉獻、自我犧牲的女性,另一種同樣會成為社會和男性的犧牲品,卻是拼命抵抗這樣的社會和命運的女性。[7]這兩種女性都是經歷了在男權社會的背景下被迫成為犧牲品的處境,而不論女主人公如何面對困境,其結局大多都是悲劇告終。這符合了大部分男權社會中女性的縮影,有著極強的現實主義與社會批評力度。雖然導演作為男性依然存在一些男性凝視的內容,但對于真實人性的挖掘和對于社會剝削女性的現象的揭露依然是溝口健二創作的初衷。
面對女性的困境,雪兒·海蒂提出這種困境產生的原因;“女性缺少的并不是知識,而是權力——社會權、經濟權、身體權等等。”[8]也就是說,她認為女性想要沖破枷鎖,不應該繼續學習社會的規范,也不應該讓自己適應這個社會,而是要讓自己爭取權利。所以雪兒·海蒂在內的女性主義者們認為女性應該爭取自己身體的主權,對愛欲的有效釋放,也是女性走向自由之路的起點。所以在溝口健二的作品中,基本上出現的女性角色都是包含情感的,她們或是為了追求情感上的自由而深陷旋渦,或是在苦難中依然堅持著自己的愛。在這種極端環境之下,人的本能卻閃閃發光讓人動容,就連溝口健二選擇改編中國的《楊貴妃》中,楊玉環最后也不是為了政權自殺,而是為了自己的愛犧牲,悲劇性的結局讓人更痛心和惋惜,也讓人反思和覺悟。
在男性中心主義為主的封建社會中,女性的意識一直被禮教嚴苛地束縛著。在溝口健二的電影中看到大部分的女性主人公都有著被迫流亡或者無依無靠的場景,例如《西鶴一代女》《雨月物語》《進松物語》等等,她們的生活都需要一個男人。而不論她們一開始的處境如何,從影片的故事開頭到結尾,她們都被當成男性的附屬品,她們知道自己的痛苦,但是她們認為這是自己的命運,根本沒有對于封建社會的反抗,這才是當時舊社會的悲哀。當一個本應該有著獨立的個人意志卻需要社會認同或者男性認同的時候,舊社會的黑暗和悲哀正是溝口健二想表達的。他通過塑造優秀且讓觀眾共情的女性形象表達了對于舊社會的批判。但通過他的作品,觀眾也自然反思女性在舊社會面對的社會困境在如今有何變化。值得一提的是,溝口健二在創作這些作品的時候,女性主義理論還尚未得到長遠發展。從現在的女性主義的視角來看,溝口健二滿足了“女性書寫”的視角,也讓東方女性在舊社會的處境得到了國際的關注,從電影史的角度來看也不失為是一種對女性電影的參考。
四、結語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溝口健二的電影在敘事方面通過表現女性角色的情感和命運,構建了具有在當時獨特作者風格的女性人物符號,對東方女性在封建社會的悲劇進行著重刻畫。而從電影本身,他的作品也自然而然構建了女性人物特有的電影敘事空間。而女性角色作為封建社會的犧牲者,導演通過細膩的視覺符號和獨特的敘事手法,批判了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種種壓迫和不公。基于以上分析,溝口健二在20世紀50年代這個時間點來看,他的作品表現出了當時少有的先鋒的女性思想,還對于當時的電影創作有極大的參考意義。不可否認的是女性意識會一直進化發展,現在女性創作與女性電影也需要脫離過去經典作品的框架才能得到長久發展。誠然,僅依靠影視作品并不能解決當下全球要面臨的諸多問題,但是通過不斷創作與研究,讓這些作品進入大眾視野,也能夠吸引一些大眾對性別現狀的關注,從而真正構建起平等友善的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巖崎昶.溝口健二[J].フィルムセンターFC溝口健二監督特集(48),1978.7.
[2]佐藤忠男.只為女人拍電影:溝口健二的世界[M].陳梅,陳篤忱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137.
[3]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M].黃勇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59.
[4]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芭.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上)[M].楊莉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7.
[5]琳達·麥道威爾.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M].徐苔玲等譯.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210.
[6]張阿嬌.巖井俊二電影中的女性意識研究[D].陜西科技大學,2000.
[7]斉藤綾子.聖と性 溝口をめぐる二つの女[A]//映畫監督 溝口健二[M].東京:新曜社,1999:281.
[8]雪兒·海蒂.海蒂性學報告女人篇[M].林淑貞譯.海南:海南出版社,2002:276.
作者簡介:
李佩霖,男,漢族,山西太原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傳媒學(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