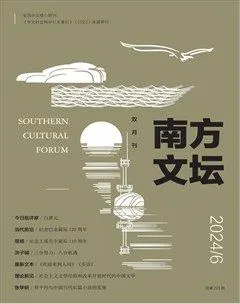社會轉型、思想解放與1980年代現(xiàn)象級小說
1979年《讀書》雜志創(chuàng)刊,創(chuàng)刊號以頭條的形式發(fā)表了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qū)》。該文的發(fā)表石破天驚,迅速引發(fā)了共鳴,人們奔走相告。“讀書”,這樣一個與普通人息息相關的私人行為,釋放出強勁的思想力,催促著“思想解放”向更為廣泛的普通民眾轉化①,同時也讓民眾的讀書熱情加速沸騰。1980年代現(xiàn)象級小說②誕生于一個“讀書”的年代,其“現(xiàn)象級”的生成是寫作者內在精神與外部世界互相激蕩、交織互動之后的向外觸著。對于寫作者而言,現(xiàn)象級小說不僅僅是一種文本實踐,更是其自我建設,與他者、與社會溝通的重要方式。憑借“一顆真誠的熱烈的心”,寫作者以情感內爆的方式重返現(xiàn)場,調動了民眾的心靈世界,使得大量的情緒與感知涌出,整個社會產生了強烈的情感共振。在情感共振中,現(xiàn)象級小說所具有的現(xiàn)實指向性,以及與廣泛的普通民眾的心意相通,又使得文本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互為參照,進而現(xiàn)象級小說所涉及的“問題”得到進一步的轉化與呈現(xiàn),現(xiàn)象級小說具有了中間物的性質。值得注意的是,現(xiàn)象級小說催生了大量相似經驗圖景與敘事樣態(tài)的小說,而擁有虛構權力的寫作者,并不愿意成為他者抑或自我的副本、衍生本,他們渴望“構造適當?shù)母挥幸饬x的表達”③,與不斷變化的經驗世界保持對話,探索更多的可能。
一、“自我重建”作為出發(fā)點
處于轉折期的寫作者,普遍面臨自我重建的問題,比如王蒙談到“復活了的我面臨著一個艱巨的任務:尋找我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時間與空間的海洋,文學與藝術的海洋之中,尋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持點、我的主題、我的題材、我的形式和風格”④。但是相較于王蒙“返場”之初幸運地尋找到“意識流”,呈現(xiàn)出較為清晰的創(chuàng)作主體意識,更多的寫作者最初是以情感內爆的方式出現(xiàn)在民眾的視野里。對于他們來說,最初的寫作,與其說是“寫作”,不如說是“說話”,是將“內心話語”以“小說”的形式“說”了出來,有著濃烈的“我”的在場。不少寫作者在步入寫作之時并不知道什么文學技巧、方法理論,尚不能對寫作應付自如,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寫作”。劉心武寫《班主任》時“只是覺得骨鯁在喉,必須一吐為快”,“憑著一種真摯的責任心,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提筆書寫熟悉的人物⑤。盧新華寫《傷痕》“只是初步意識到文學作品應該真實地描繪人的感情和思想,作者應該交給讀者一顆真誠的熱烈的心”,從涌起創(chuàng)作沖動直至小說完成,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寫作”,只是“一任自己的感情在紙上傾瀉”⑥。同時代的其他寫作者,陳世旭、何士光等也大抵如此。這種相對樸素、有著自我袒露性質的情緒表達,既是寫作者自我重建的方式,同時也深深地觸及了人的共有經驗,是人在相似處境之下可以引申、拓展的,與生命經驗緊密相關的問題。它外化形成了1980年代現(xiàn)象級小說最初的文本形態(tài),一經公開,便從私人領域騰挪至公共空間,沖蕩著人們的思想,使得原本就潛在的情感與經驗得以照亮,混沌朦朧的心靈獲得來自外部的指引,進而在人與人之間蕩漾開來,擴散至社會的各個角落,并彼此激蕩,引發(fā)了限度之下“新時期”的群體性激動。即便某些帶來感性體驗的小說尚處于曖昧不清的狀態(tài),其意義并未獲得正式、公開的確認。大量情緒與感知的釋放,使得整個社會沸騰,產生了強烈的情感共振。
在情感的共振中,其“轟動效應”從外部近似單純的刺激反應逐步滲入人的內心領域,成為寫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相創(chuàng)造,共同成長。寫作與閱讀的過程本身就是發(fā)現(xiàn)自我、自我與社會對話的過程,一度讓寫作者有了“哦!原來生活是這樣,原來我對生活還有這么一段感受”的覺察⑦,周克芹構思《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自言“我是完完全全地參與了進去,我的感受在這些人們身上找到了寄托和歸宿”⑧。高曉聲也曾坦言《陳奐生上城》解剖了陳奐生也解剖了自己⑨。對于讀者而言,現(xiàn)象級小說亦是起著鏡子的作用,人們閱讀小說更傾于從中看到自己的情感與選擇,陜西省電力設計院的工作人員王曉華寫信詢問“為何小說《傷痕》寫的都是他家的遭遇,而他跟作者盧新華素不相識”⑩。有中年教員甚至直接闖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客房,對古華說“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寫的那個秦書田……”11相似的情感與經驗得以被敘述激活了人的生命狀態(tài),同時也推動了社會恢復活力。
《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發(fā)表署名“潘曉”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由此引發(fā)關于人生意義的大討論。從此次討論可以窺見,身處轉折時期的民眾普遍有著迷茫、焦灼、苦悶的心理,迫切地需要處理過去的經驗,渴望得到理解,重新確認自我以及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現(xiàn)象級小說恰恰暗合了這一社會心理需求,其豐盈的情感使得淤積的情緒經由閱讀而得到紓解。在相似經驗被表達的過程中,人獲得了被肯定、被看見之感,逐步對小說所提供的故事產生信任,意識到自己處于“共在”之中,那些攜帶私人性質的“豐富的痛苦”、焦慮、渴望同樣也存在于他人,是屬于人的共同情感。《班主任》《愛情的位置》《傷痕》等小說從“自我”涌動而出,之所以成為“現(xiàn)象級”,很大程度上便是因為其與更為廣泛的人群產生了內在連接,這種連接又激活了人的感知感覺,召喚出民眾自我表達以及表達他者的欲望,進而情感溢出,得以在社會流轉。對于普通民眾來說,“表達”也意味著“自我”的獲得,意味著一個新的“開端”。在現(xiàn)象級小說帶來的新鮮與刺激中,人獲得了勇氣與力量,從對故事的信任延伸為對自身的情感與經驗的信任,進而逐步打破了既有的感知框架。盡管這種打破受多種話語因素的影響,是多方力量博弈之后的結果。換句話說,現(xiàn)象級小說鼓勵與呼喚著“那個個人”,將人的注意力導向鮮活的經驗世界,使得人在與人、與社會的聯(lián)系中獲得實在感,確認“我”的在場,發(fā)現(xiàn)“我”之所是。在“附近”的閱讀分泌出熟悉的氛圍,加強了小說所提供的經驗的真實性,使得人們更加相信文本所構建的世界,進而在現(xiàn)實與虛構的互相參照中建立起新的認知。
不同的現(xiàn)象級小說,事實上,與經驗世界有著不同的聯(lián)結方式,提供了理解與處理經驗的不同參照,以及言說自我與闡釋自我的不同可能。在強烈的主體滲入中,小說中人物的痛苦與歡娛就是自己的痛苦與歡娛,小說中人物的言與行就是自己的言與行。當日常生活中遇到類似的情景,便嘗試著用小說中的思想邏輯或行為方式處理自身的問題,重新構建自己的生活。在文本經驗的拓展與補充中,“屬于我們自己的或我們希望屬于自己的各種能力”12通過現(xiàn)象級小說得到了釋放,并逐步有了實踐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班主任》中張老師式的“啟蒙”地位,也從文本空間延伸到現(xiàn)實生活,得到了確認。在民眾的眼里,寫作者成為擁有強勁力量的主體,幾乎就是“超人”,能夠解決生活、情感、事業(yè)等方方面面的問題。源源不斷的讀者來信,向寫作者傾訴心緒、尋求幫助,甚至將之視為“文化英雄”“人生導師”“青天大老爺”。寫作者承擔的不僅僅是寫作的職責,同時也擁有了社會功能,其書寫成為個人話語與社會話語雙向動蕩的中間物,獲得來自民眾的充分認可。而文學,依托著現(xiàn)象級小說,以“重”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
二、經驗的開拓與問題的轉化
現(xiàn)象級小說生長在寫作者真誠熱烈之心與廣泛人群的互相激蕩之中,與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發(fā)生聯(lián)動,有著一定的公共性。其中所牽涉的問題,已經逐步溢出了文學自身的解釋范疇,而與此一時期的社會語境、歷史情勢緊密相關。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評論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掀起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而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標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到重新確認,以及“改革開放”作為歷史大勢的正式啟動。受益于“思想解放”的鼓勵與庇護,以及文學可以“講述一切”的特殊權力13,1980年代現(xiàn)象級小說往往攜帶突破“禁忌”的色彩。關于“禁忌”,何平提示“禁忌不完全等于社會熱點和公共議題,政治法律、道德倫理、國民心理、文化傳統(tǒng)、人性底線和審美慣例等都可以是某個方面的禁忌,有人有邊界有秩序就會有禁忌,有禁忌就會有突破禁忌的沖動和快感”14。實際上,對禁忌的突破就是不同經驗樣態(tài)與感受類型的不斷敞開,這就使得現(xiàn)象級小說從源頭上便攜帶“解放感”。像《愛情的位置》對“愛情”的觸碰、《喬廠長上任記》對“改革”切入、《人到中年》對“知識分子”的關懷、《珊瑚島上的死光》對“科學文藝”探索、《沒有紐扣的紅襯衫》對世俗觀念的挑戰(zhàn)等,是寫作者對各種經驗樣態(tài)與感受類型的注意與發(fā)現(xiàn),同時也是寫作者以文學的方式轉述現(xiàn)實需求,向國家與社會的小心試探。這種試探與時代精神“摸著石頭過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同構的。在不斷求證、獲得確證的過程中,經驗域得到了不斷的拓展,經驗呈現(xiàn)出它的豐富性與復雜性,而活生生的經驗與感受正是意義生成的基石。
雷蒙德·威廉斯曾注意到“不是與思想觀念相對立的感受,而是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和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15。也就是說,思想觀念與感受并非處于二元對立的狀態(tài),它們彼此聯(lián)系、互相生發(fā)。轉型時期,不同的話語力量事實上也處于自我重建的狀態(tài)中,它們迫切地需要構建自身的合法性,建立或推廣自己的意義體系,它們在“思想解放”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使思想觀念發(fā)生變化,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正在生成或變動的思想觀念“能夠感受到”,因為“只有當個人周圍流行的思想和價值被感知時,它(此處指情境,引者注)所提供的東西才對他或她的思想轉變發(fā)生影響”16。而現(xiàn)象級小說提供了能感知的情境,聯(lián)結了人的內心領域與公共空間。盡管這種提供或多或少受到既有思維框架的影響,也會存在認知的直接給予。
一方面,從文本本身來說,現(xiàn)象級小說構建了令人震顫的故事,使得“友愛”“善”“責任”等相對抽象的價值意識具有了可理解性,更新了人的視野與感受。另一方面,從文本所引發(fā)的整體性聯(lián)動來說,大量現(xiàn)象級小說被改編成廣播、影視、連環(huán)畫等,對現(xiàn)象級小說的生成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17。由現(xiàn)象級小說改編的廣播、影視、連環(huán)畫等承擔了“敘述”的功能,使得整個社會充盈著現(xiàn)象級小說敘述的“故事”。或者可以進一步說,這些改編之作,突破了文藝門類的邊界,是作為“另一種現(xiàn)象級小說”而存在,進而與更為廣泛的普通民眾發(fā)生聯(lián)系,使得現(xiàn)象級小說在不同群體中流轉、擴散,成為社會各個階層廣泛共享的文學樣態(tài)。加之,現(xiàn)象級小說本身所具有的強烈互動性,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個擴大版的感性情境。
在這樣的情境之中,現(xiàn)象級小說所提供的思想價值又進一步呈現(xiàn)出它的可感性,也即通過被改編的廣播、影視、連環(huán)畫等有了視覺、聽覺等多方位的互動,通過現(xiàn)實生活中人具體的言與行變得可知可感。人所感受的思想價值已經不單單是文本本身所提供的,還包括了由現(xiàn)象級小說所延伸、轉化、提純出來的,那些與現(xiàn)實互動強烈,正進一步傳遞、生成的思想價值。而置身于其中的人,既是思想價值的感知者,同時也在被感知,參與了其傳遞、生成。有姑娘一直壓抑自己的情感,直至《愛情的位置》引發(fā)熱烈討論,感受到“正面輿論的支持”,才勇敢地向暗戀對象表白,收獲了愛情18。也就是說,通過現(xiàn)象級小說及其引發(fā)的轟動,人的愛情觀發(fā)生了變化,并實現(xiàn)了從觀念向行為的轉化。通過人的具體實踐,小說所提供的思想價值在現(xiàn)實生活中也形成了一個可感知的情境,而這種思想價值又匯入個人因子,有了新的變化與發(fā)展。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話語力量持有不同的動機,民眾感受到的意義也有著一定的差異。對于主流意識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將“思想解放”導向現(xiàn)代化建設。在《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鄧小平便談到了“新時期”的價值判斷標準,即“對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在總結新時期文學之時,也是著重強調其“解放思想,振奮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個現(xiàn)代化進軍”的積極作用19。寫作者更多的是出于表達的沖動與快感,以及來自于與魯迅、穆旦等人一脈相承的公共關懷與擔當意識。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他們更為關心與切身利益相關的現(xiàn)實問題。而文學期刊也有著自身的定位與價值訴求20。這就使得現(xiàn)象級小說從一開始就夾雜著多方話語力量的博弈,有學者留意到“《傷痕》的‘原意’并不存在,從一開始,各種力量就介入了文本意義的生產。從修改和發(fā)表,到評論、研討和爭鳴,再到獲獎和最終的經典化”21。現(xiàn)象級小說更像是具有了阿倫特所說的“桌子”的功能,使得不同的話語力量“圍桌而坐”,激發(fā)了不同身份、立場的充分表達。這就為國家把握社會心態(tài),調節(jié)社會情緒提供了途徑。
“我寫《人到中年》時,并不像有些評論家所說的那樣,考慮要‘揭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我只是根據(jù)生活中的感受,去寫我熟悉的那些中年知識分子的理想、志趣、甘苦和追求。”22盡管諶容著意強調的是從自我真實的內心感受、經驗出發(fā),但是主流意識卻注意到了小說中那些從個人出發(fā),同時又超出個人的部分。小說中的陸文婷不再是作為一個“普通人”,而是被釋讀為“新人”,提純出“新人”的特質,匯入“社會主義新人”的譜系中,成為新時期的精神典范。像《喬廠長上任記》源于《人民文學》的邀約,且在邀約之時便指定了小說的方向“寫實實在在的生活及人們在生活中碰到的阻力,要寫出怎樣克服這種阻力,給人以信心和力量”23。更何況,報刊、廣播、影視等載體本身就屬于體制的一個部分。也就是說這些“能夠感受到”的價值意識,事實上,也受到國家意識的引導、篩選。
大量的價值意識,經由辨識、轉譯、引錄,而被生發(fā)出新的意義,成為國家意識的一種表達。這種文學化的國家意識,又以“讀者來信”“評論”“筆談”“報道”“小說獎”等方式出現(xiàn),向外推廣為適用于更為廣泛的普通民眾的尺度,催促著原子化的個人向外敞開,走出自我,接近他人,重新確認或建立自我與他者的關系、自我與社會的關系。在情感與經驗、情緒與感覺的共享中,相似的經驗與情感得到進一步融合,參與或被改寫進正在生成的意義價值秩序中,催生著共同的事業(yè)。也就是說,現(xiàn)象級小說在被國家話語、社會話語、知識話語等多種話語力量充分共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現(xiàn)象級小說成為此一時期社會思想價值匯集的中心。在這樣意義互相重疊、彼此關聯(lián)的境況中,寫作者自身也獲得了賦權。反過來,這種賦權又形塑了寫作者的良知系統(tǒng)與美學意識,激勵著他們成為積極的行動者,以文學的方式轉述社會需求,將社會問題文學化,進而文學世界與現(xiàn)實社會互為參照,又掀起一次次轟動。
三、“回到文學自身”:
重建文學與經驗世界的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當社會秩序步入正軌,國家的注意力逐步從意識形態(tài)建設層面轉移開,與文學的關系沒有那么膠著之時,經歷了“轟動效應”,或者說,在“轟動效應”的另一邊,越來越多的寫作者激情消退,有了“下一步踏向何處”的困惑與思考。不斷地向外開拓經驗世界,事實上,成為寫作者的一種蓄力或蓄勢,它與寫作者自身主體性的增益是一個二而一的過程,并逐步轉化成“虛構”的力量,指向對文學可能性的進一步探索。對于重返現(xiàn)場的寫作者來說,“轟動效應”自然有著它正面建設的一面,也即讓寫作者獲得尊重感與自信心,激活了寫作者的生命力與創(chuàng)造力,形成一股由外部而導向內部的驅動力。馮驥才便曾言及“刺激我寫作的另一種力量來自讀者的來信”24,來自讀者的熱情回應,使得馮驥才產生心靈的震蕩,讓他感受到“自己的寫作”與普遍的素未謀面的他者“心靈相通”,進而領悟到“文學的意義”,獲得了力的增益25。然而,另一面,“轟動效應”也會使得寫作者自身沉溺其中,帶來寫作的惰性。不可否認的是,現(xiàn)象級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的是寫作者轉化與提煉經驗的能力,是對瑣碎的、混沌的、處于生活流的經驗的“問題化”。同時,現(xiàn)象級小說所具有的“開拓性”“創(chuàng)造性”,也催生了大量相似經驗圖景與敘事樣態(tài)的小說。這些有著相同質地的小說毫無節(jié)制地涌出,使得寫作逐步浮于表面,失去了其走向深處的意義。部分寫作者甚至沉溺于現(xiàn)象級小說所帶來的聲譽,成為所謂的“文學活動家”。
而擁有抱負的寫作者,并不愿意倚靠曾經獲得的聲望與權威,也不愿意重復光暈之中現(xiàn)象級小說已有的經驗圖景與敘事樣態(tài),淪為他者抑或自我的副本、衍生本。他們渴望沉入鮮活的經驗世界,重新調動或錘煉把握經驗的能力,保持“思想著”的狀態(tài)。比如路遙,面對讀者“人生導師”的角色賦予,一陣喧鬧之后,路遙感受到的是惶恐,他發(fā)出感慨“我不能這樣生活了”,“渴望重新投入一種沉重”26。他將“寫作”通約為“勞動”,意識到“勞動,這是作家義無反顧的唯一選擇”,并為“能干些什么”而痛苦不已27。是維特時期的夢想,即“這一生如果要寫一本自己感到規(guī)模最大的書,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歲之前”28重新驅動了路遙,使得他獲得勇氣與力量,進而讓路遙告別《人生》所分泌的暖融氛圍,再次成為一個行動者,開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寫作。
事實上,在路遙之前,劉心武、馮驥才、蔣子龍等經歷過“轟動效應”的寫作者,就已經有了“下一步踏向何處”的思考。1981年,在給劉心武的信中,馮驥才提及與劉心武的長談,“回想起來,談來談去始終沒離開一個中心,即往下怎么寫?似乎這個問題正在糾纏著我們。實際上也糾纏著我們同輩的作家們。你一定比我更了解咱們這輩作家的狀況。這兩天蔣子龍來信問我:‘你打算沿著《歧路》(《鋪花的歧路》)走下去,還是依照《在人間》(高爾基)的路子走下去?’看來,同一個問題也在麻煩這位素來胸有成竹的老兄了”29。也就是說,“下一步踏向何處”成為此一時期寫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普遍面臨的問題。而對此一問題的思考伴隨著對已有文學現(xiàn)象的質疑與分析,這恰恰意味著文學作為文學本身而被思考,寫作者的創(chuàng)作主體意識的逐步強化,以及新的可能性的浮現(xiàn)。正如馮驥才所覺察到的,“作品獲得的強烈的社會反響會暫時把作品的缺陷掩蓋起來,時間一久,缺陷就顯露出來。這樣下去,路子必然愈走愈窄”30。馮驥才強調的不是不能寫社會問題,而是從藝術構思角度強調不能“簡單地一個個把問題抽出來寫”,要讓作品即使是脫離那些“社會問題”依然能保持自身的魅力,也即強調“寫人生”31。
劉心武則在回信中點出,“問題在于我們有必要在新的形勢下總結一下成敗得失,踏上更廣闊的創(chuàng)作道路”,進一步總結了馮驥才從“藝術角度”生發(fā)的思考,認為“注意寫人生”即“把生活當作一個整體,充分認識到人的活動即人生的復雜性、豐富性、流動性,使社會生活和人物形象在作品中達到充分的‘立體化’”,并補充到“真實地反映人生,并通過作品引導讀者看出人類生活的總發(fā)展趨勢”32。面對像王蒙一樣“重返”文壇的“真作家”,劉心武明顯感受到了危機,他預感到《班主任》式“說真話”的寫作路徑“恐怕就很難在文壇上支撐下去了”33。相較于“轟動效應”所釋放的表面誘惑,劉心武更傾于開拓文學的潛能。也正因如此,劉心武將自己從“轟動效應”所編織的束縛中釋放出來,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寫作策略。在回顧個人的創(chuàng)作史之時,劉心武也是坦然地將《班主任》等一類相對樸素的自我表露之作視為寫作能力不斷生長的一個過程34。1982年,劉心武、李陀、馮驥才等人又以“現(xiàn)代派”回應文學“轟動效應”,發(fā)表了《關于“現(xiàn)代派”的通信》,引發(fā)“下一步踏向何處”的進一步思考。1983年,李陀和馮驥才還編選了《當代短篇小說43篇》,進行“新”的文本實踐。
從上述可以看到,“變”成為寫作者面對“轟動效應”的普遍共識,他們也不約而同地想要回歸文學本身,對“文學”進行重新確認,并以此充分占有經驗世界,重新建立文學與經驗世界的血肉聯(lián)系,試圖尋找到文學性與公共性之間的平衡點。同時,對“變”的四方摸索,也逐步從對個人寫作的驅動延伸為對整個文學發(fā)展的驅動。而寫作者整體上生發(fā)“變”的行動,以及呈現(xiàn)“變”的形態(tài)之時,已是1980年代中期。此一時期,文學的整體氛圍,以及所置身的社會場域,已經有了新的質地。擁有“虛構權力”的寫作者,并不愿意在已有的話語圖式中進行重復的表達,淪為意義象征體系中漂浮的符號,發(fā)出單質的聲音。他們渴望調動想象力,在“怎么寫”中重獲“言語的力量”,尋求相對獨立的敘述品格與精神立場,以實現(xiàn)限度之下更大程度的言說自由。同時,也試圖呈現(xiàn)經驗世界本身的復雜形態(tài),給予新鮮的感知體驗,錘煉把握經驗世界的能力,培養(yǎng)人對豐富性、差異性的理解與尊重。誠如王蒙所言,“一切形式和技巧都應為我所用”35,“怎么寫”只是作為一種方法。而“一切形式和技巧都應為我所用”,以及“復雜化了的經歷、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復雜化了的形式”36“人類生命是一種神秘和極度復雜的東西,是一種需要用思想能力和能夠表達復雜性的語言才能接近的東西”37又生發(fā)出對“新”38的渴望。馮驥才便表現(xiàn)出對“新”的迫切需要,“沒有新東西刺激我,我就要枯竭。新生活,新思想,新藝術,都要!”39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的東西,形塑了寫作者的感知方式與情感結構,使得文本呈現(xiàn)不同的審美特質,而具有辨識度的審美特質正是寫作者彰顯“自我”,是否具有“強力”的體現(xiàn)。《棋王》的獨特性,便緣于阿城與時代潮流相異的知識結構、文化構成涵養(yǎng)了其特殊的感知與表達40。也就是說,文學形塑個人的感知方式與情感結構是一種事實性的存在。盡管按照杜威所言,“我們不可能恢復到原始的淳樸狀態(tài)”,但是他也提示通過一種“嚴肅的思維鍛煉”可以獲得“一種在眼睛、耳朵和思維上被培養(yǎng)出來的淳樸狀態(tài)”41。從一定意義上講,現(xiàn)象級小說正是思維鍛煉的方法,構成了寫作者“介入”的具體行動。語言與形式本身的使用也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成為文學與現(xiàn)實生活互相撞擊、彼此激發(fā)的重要一環(huán),具有了讓意義迸發(fā)的重要作用。寫作者們爭先恐后地進行各種各樣的藝術實踐,引入新鮮的知識與經驗,對“現(xiàn)實主義”進行梳理與轉化,使得“現(xiàn)實主義”在1980年代有了新的“變奏”。而不同知識構成、情感結構、美學意識的寫作者,其具體的路徑以及作品本身呈現(xiàn)的審美形態(tài)也略有不同。
現(xiàn)象級小說作為一種與經驗世界保持對話,在敘事與美學(或者說公共性與文學性)之間“思想著”的文學,實際上起著改變認知、重塑情感的作用。它激活了鮮活的“感”,喚醒了民眾自我表達以及表達他者的欲望,使得情緒與感知得到了充分的釋放,培養(yǎng)著個體對自身經驗與思想能力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個體思想的“解放”。這種個體維度上的意義參與了正在生成的社會主要價值秩序,也因此,1980年代現(xiàn)象級小說深深地嵌入時代,成為勘探1980年代文學史、社會史、心靈史的重要刺點。
【注釋】
①朱正琳認為“讀書無禁區(qū)”是直接針對普通民眾的“解禁”。參見朱正琳:《老字號的老》,載王世襄等《我與三聯(lián):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成立六十周年紀念集:1948—2008》,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第87頁。
②關于“現(xiàn)象級文本”的提出及其研究實踐,可參見何平自2022年1月起至今,在《小說評論》主持的《重勘現(xiàn)象級文本》專欄。在專欄中,何平多次強調現(xiàn)象級文本的現(xiàn)實指向性,認為現(xiàn)象級文本強調“文學性”,“但它更重視文本和讀者,文本和文學生活,文本和更廣闊社會生活等等相關聯(lián)的歷史感和整體性”;指認文本的“現(xiàn)象級”,“會綜合考量它所關聯(lián)的——或公共議題、或讀者參與、或審美嘩變的公共性和社會性等等”;“無論怎么說,現(xiàn)象級文本應該是被國民廣泛傳閱,在相當大的讀者群引起反響,成為文學的公共事件的那部分文學作品”。參見何平:《主持人語:時間之流的文本浮標》,《小說評論》2022年第1期。
③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xiàn)代認同的形成》,韓震、王成兵、喬春霞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第25頁。
④36王蒙:《我在尋找什么?》,《文藝報》1980年第10期。
⑤劉心武:《班主任·后記》,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第254頁。
⑥盧新華:《要真誠,永遠也不要虛偽》,《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
⑦王蒙:《漫談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載彭華生、錢光培編《新時期作家談創(chuàng)作》,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第350頁。
⑧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創(chuàng)作之初》,《北京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期。
⑨高曉聲:《且說陳奐生》,《人民文學》1980年第6期。
⑩鐘錫知:《小說〈傷痕〉發(fā)表前后》,《新聞記者》1991年第8期。
11古華:《閑話〈芙蓉鎮(zhèn)〉:兼答讀者問》,《作品與爭鳴》1982年第3期。
12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趙月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第161頁。
13德里達:《文學行動》,趙興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5-6頁。
1420何平:《主持人語:改革開放時代文學的欲望表達》,《小說評論》2022年第3期。
15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王爾勃、周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第141頁。
16張灝:《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高力克、王躍、許殿才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5-6頁。
17何平:《主持人語:時間之流的文本浮標》,《小說評論》2022年第1期。
18劉心武:《讓我們來討論愛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82-83頁。
19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載《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09、208頁。
21劉復生:《為什么非得是〈傷痕〉?》,《小說評論》2022年第1期。
22諶容:《寫在〈人到中年〉放映時》,《大眾電影》1983年第2期。
23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的生活賬》,載《不惑文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第52頁。
2425馮驥才:《激流中》,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第2、5頁。
262728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載《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第5、7、7頁。
293031馮驥才:《下一步踏向何處?》,《人民文學》1981年第3期。
32劉心武:《寫在水仙花旁》,《人民文學》1981年第6期。
3334劉心武:《我是劉心武》,團結出版社,1996,第123、183頁。
35王蒙:《王蒙致高行健》,《小說界》1982年第2期。
37努斯鮑姆:《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生活》,丁曉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47頁。
38這種“新”,并非進化論意義上新舊之新,更傾于是有著區(qū)別性特征的“新”,套用馮強的話來說這種“新”側重于“更新感知”,“只要有助于更新感知,它完全可以激活舊傳統(tǒng)”。參見馮強:《文明論“文學性”發(fā)微》,《當代文壇》2023年第5期。
39馮驥才:《中國文學需要“現(xiàn)代派”!——給李陀同志的信》,載《我心中的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第41頁。
40查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第22-23頁。
41杜威:《經驗與自然》,傅統(tǒng)先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第26頁。
(陳娟,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