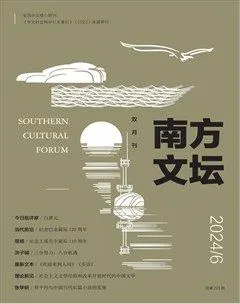越界的想象力
2024年8月20日,萬眾矚目的國產游戲《黑神話·悟空》正式發售。很巧,就在兩個月前,拙著《英雄變格:孫悟空與現代中國的自我超越》有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增訂再版,距離初版已有七年時間。仿佛是一種回聲,這迫使我再度思考作為個人學術起點的孫悟空形象研究。
當孫悟空形象從古典文學名著中翻騰而來,并再現于20世紀中國的種種媒介,一種越界的問題意識隨之浮現,即古典文學與當代文化的互動關系。古典文學形象如何被當代文化重塑?古典文學傳統能否在當代語境中轉化新生?媒介激變是否導向“形式的意識形態”?基于階級、性別、民族國家、媒介、非人類/后人類等文化研究坐標,我們如何建構一種關乎“古今之變”的批判性思想視野?如果說,文明的穩定性在于包容性,那么,對五千年中華文明而言,越界早已發生,且早已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
與“妖仙”孫悟空相似,文化研究在當代學院體制中的位置也是越界的。這是一種彈性的身份處境,它游走于種種壁壘之間,貌似沒有專屬領地,卻也因此“七十二變”,靈活機動。我想,文化研究的花果山或許不在某處具體根據地,而是生成于不同學科的交叉邊界處,層巒疊嶂,郁郁蔥蔥。文化研究帶領我們從邊緣處望向中心,激活交界地帶的想象力,以期翻轉地圖,逆讀世界。把“跨越”(trans-)作為方法,意味著走出研究舒適區,主動向不那么熟悉的領域跋涉,進而從他者處反觀自身,這或許也是《西游記》的精神遺產。
因此,在孫悟空形象的延長線上,哪吒、青蛇或故宮等選題,都是在“古今之變”的意義上展開討論,我嘗試跨越物種、性別、地域、文明等分界,尋找原發的、間性的、古為今用的批判性思想資源。一切形象學終將通往自我形象學,這些不斷翻新的經典形象皆是當代中國人想象自我的話語裝置。“當代”的誘惑力也在于這里:無論“故事講述的年代”幾何,“講述故事的年代”必然朝向當下。
我曾經在讀書時決絕逃離那些“失卻轟動效應”的小說,并以“公共性”之名,對脆弱的作品發起了一次次“墜落的審判”;可走上講臺之后,當我不斷遭遇不同學科背景的師友們,我竟如此強烈地意識到,正是文學塑造了我的思維方式與情感立場。如果成長小說可以劃為“分離、考驗與回歸”三個階段,那么,我近年來漸漸感受到了回歸母體的親切。對文學研究者而言,文學當然是對象,是“庖丁解牛”的賓語,但文學也是狀語,是用文學的方式思考問題,是用文學塑造的情感結構與更廣闊的世界相連。唯其如此,文學研究才能真正抵達莊子筆下“游刃有余”的美感體驗: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我理想中的文學研究應是具有想象力和可讀性的,它帶著研究者本真的口音、語氣與修辭,通往一種身體在場的劇場效果,以“越界”的勇氣擊穿“第四堵墻”,給新時代的觀眾帶來深切情動體驗。
用解構主義批評家杰弗里·哈特曼的名言來說,正是“作為文學的文學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