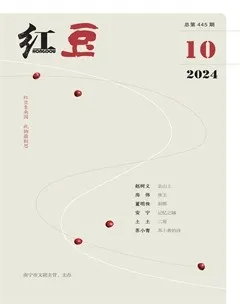兩把溫柔的剪刀
四個(gè)韓國籍工人跑高走低忙活了一周,房子粉刷一新,啞光的蛋殼白,細(xì)膩,干凈。在洛杉磯的冬日艷陽下,無論誰經(jīng)過望一眼,都會不由得面露歡喜的微笑。房前屋后走一圈,欣欣然清點(diǎn)物品,我發(fā)現(xiàn)側(cè)院墻角下,我種的黑金剛多肉被攔腰截?cái)嗔耍⒙湓诘厣希駪?zhàn)場上士兵的殘肢。房東杰伊把那幾根斷枝插進(jìn)花盆,說新的根須不久會生出來。杰伊是個(gè)細(xì)心的人,他把臨時(shí)借給工人的梯子、水桶歸位,說:“那把剪刀不見了。我媽的剪刀,不見了。”他說得很輕松,也很失落,但那失落輕得像一片雪花,只夠讓他灰藍(lán)色的眼睛暗淡了幾秒。“一定是那個(gè)韓國籍工頭拿走了!昨天他跟我借過。我這就打電話要回來。”我急急地說,并不完全因?yàn)轫n國籍工人是我找來的,還因?yàn)榻芤翆λ赣H的感情令我不敢掉以輕心。
這個(gè)五十歲的單身大男人,其實(shí)只是個(gè)長著成年人體型和外表的大孩子。大學(xué)畢業(yè)那年,正忙著四處找工作,他母親患腦瘤去世了。不同于滿不在乎的弟弟,他被失母之痛擊倒——他答應(yīng)母親,掙半年錢,帶她去歐洲看她祖先生活的牧場。子欲養(yǎng)而親不待。失眠讓他失掉了一頭濃密的金發(fā)。他某天開車上班途中犯困撞上了公路護(hù)欄,被警察以兒時(shí)有癲癇為由扣留了駕照。他不得不單程花兩個(gè)小時(shí)倒三次公交車通勤,他失不起業(yè)。他父親和弟弟拿走了家里所有的值錢之物,那把剪刀還是他從車庫的一個(gè)破帆布袋里撿到的。他記得母親在廚房忙碌的身影,常有這把橘色剪刀的陪伴。
做軟件工程師的他現(xiàn)在收入頗豐,可儉樸的生活和他的微笑一樣,似乎刻在基因里了。他特別喜歡穿的兩件T恤,下擺和袖口都破了洞,我問他為什么不扔掉,他笑笑不答。后來才聽他弟弟說,那是當(dāng)年他母親買給他的圣誕禮物。而那個(gè)藍(lán)白條紋舊枕頭套,也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物件——大學(xué)離家時(shí),他母親追出來塞進(jìn)他的行李箱,說:“你帶著,放臟衣物用。”
其實(shí),那只是一把很普通的剪刀,在任何文具店都能找得到,橘色的塑料刀柄,天長日久褪色了,一側(cè)臨近刀刃的地方還有一道裂痕,上面貼著一條顏色發(fā)黑的白膠布。
追查的結(jié)果是,那把剪刀果然被那個(gè)黑瘦的韓國籍工頭隨手裝進(jìn)工具箱帶走了。第二天,來領(lǐng)工錢,他順便歸還。“我的剪刀比這可好多了。”那人呵呵地笑著道歉,放著光的眼神,有一絲不加掩飾的不屑。
我很欣慰這物件回到杰伊的車庫工具架上。在一片金屬色的鉗子、板子、鋸子中,它顯得過于光滑亮眼,像我在黑白照片上看到的那個(gè)安靜而略有些自負(fù)的美婦人,那是杰伊的母親著婚紗的玉照。另一張彩色照片上,她已經(jīng)面帶中年滄桑,只有側(cè)臉面對鏡頭,因?yàn)樗唤芤劣姹饋恚嘀碾p腳懸空,但那笑容顯然比婚紗照里多了煙火氣和做母親的暖意。
有些東西跟人廝混久了,會突然失蹤。也不知哪天,與莫名其妙消失的塑料勺子、水果刀子一樣,這剪刀又不見了!我常為這樣的不告而別懊惱。都不是什么值錢的東西,從經(jīng)濟(jì)角度考慮并沒有太大損失,可那物件偏偏又是常用且用順手了的,突然失蹤,像家人或?qū)櫸镓?fù)氣離家出走了一般,讓呆在原地的人頗有措手不及的沮喪。“沒什么,找不到就算了。”杰伊仍是輕而淡地說。話雖這么說,他仍跟我一起,瞪著大眼睛找遍了這兩層樓房的每個(gè)角落,唯一的希望就是某天它又突然冒出來。
三年過去了,那把剪刀的下落和它的故事徹底斷了。像斷成兩截的繩子,有一半墜下深不可測的懸崖,另一半空留在人的腦海,再也無法接續(xù)。我只發(fā)現(xiàn),杰伊?xí)抗褡由希赣H的照片似乎比以往更加一塵不染。
幾天前的北京,另一個(gè)剪刀的故事上演,短促得像一出未經(jīng)彩排的獨(dú)幕劇。
初夏的早晨,我醒來在床上發(fā)呆,接到兒子的電話:“我今早有點(diǎn)不舒服,到單位測了一下,兩道杠。我別傳染給你,想找個(gè)旅館住幾天。” “你還是回家來住,我找地方去。”我不由得提高了聲調(diào),心里想的卻是,還有三天,就是我的新書分享會的日子,我不能有半點(diǎn)閃失。兒子立即接收到了我的負(fù)面情緒,說:“媽,對不起。我病得真不是時(shí)候。”已經(jīng)開始發(fā)燒的他坐在車?yán)锏认ⅰN掖蛄巳齻€(gè)電話,終于得到一個(gè)退休女友的首肯,我可以去她家住一陣子,她正在南城照顧她九旬的父親。“家里太亂,下不去腳。也就是你,我可以給鑰匙自暴家丑。”
兒子的心似乎也落了地,回到家直奔自己的臥室。我煮了簡單的早餐,把門開個(gè)縫,把食物放進(jìn)房里。關(guān)門。身后是他帶著咳嗽的責(zé)備:“你怎么不戴上口罩?!別管我,趕緊走。”好像他隨身攜帶的是隨時(shí)可能爆炸的火藥。可能實(shí)在燒得難受,吞下幾粒連花清瘟膠囊后,他問正在收拾行李打算出逃的我能否找一下體溫計(jì)。我兩年外出采訪不在家,對諸物已經(jīng)像在陌生人家里一般生疏。“在你臥室的床頭柜上。”他的聲音已經(jīng)沒了剛才的底氣。體溫計(jì)壞了,我下樓去藥店買回一支。他測了,三十九攝氏度。所幸家里藥箱有他去年躉下的藥。
“我訂了一些試劑,馬上就送到,你走前也測一下。” 兒子在單親家庭長大,早熟得比我這個(gè)母親更像個(gè)成年人。當(dāng)年我們同去美國大峽谷旅游,忘情拍照的我離懸崖近一步,十五歲少年的心就懸高一寸,最后實(shí)在害怕了,他一把把我拽回來。我乖乖地測了,試劑上顯示一條紅杠。聽到我拉著行李箱離開的聲音,他又囑咐:“帶上幾份試劑。活動(dòng)前勤測著點(diǎn)兒,有潛伏期的。”我依言拿了三份裝進(jìn)背包。
事實(shí)證明,這個(gè)大姐說的一點(diǎn)也沒夸張,那十年前我去過的兩居室曾窗明幾凈,隨著主人的落魄完全淪落為一個(gè)倉庫,只進(jìn)不出的倉庫。唯一能讓人容身的地方就是那張大床,上面至少有一半沒有被物品覆蓋。
沒有無線網(wǎng)絡(luò),我可以應(yīng)付,用手機(jī)流量與主辦方交流會議的細(xì)節(jié)。可睡眠質(zhì)量太差,實(shí)在讓人沒底氣。房子在那十五層樓的東頭把角兒,躺在床上,一墻之隔,頭頂正對著那每幾分鐘就有呼嘯而過的列車的城際鐵路。墻的一半是落地窗,不到凌晨五點(diǎn),天光就隔著那層薄薄的紗簾敞亮地照進(jìn)來。好不容易剛睡著的我猛然睜開眼,望著四周堆放的雜物,愕然以為自己躺在露天的舊貨填埋場。
每天睡三個(gè)小時(shí),耗了三個(gè)晚上,活動(dòng)終于搞完了。 “看完了,兩個(gè)小時(shí)的直播,很不錯(cuò)!”第一條祝賀微信,是兒子發(fā)來的。發(fā)著燒,刀片嗓,頭疼著,他居然還隔空關(guān)注著那個(gè)他放心不下的媽。“既然可以換到陳伯伯郊區(qū)的書房,那就換過去住幾天吧,只當(dāng)度假。我每天都在測,想早點(diǎn)去上班。要不每天扣五百塊錢呢。”聽說我的借住條件太差,他啞著嗓子出主意。他很珍惜好不容易找到的這份工作,周末不加班似乎才是不正常。我心疼又難過,想發(fā)幾句牢騷又閉了嘴。
我依言搬到了密云。每天給兒子發(fā)個(gè)信息算盡母責(zé)。不時(shí)聽聞這個(gè)友人煲了湯閃送給兒子,那個(gè)鄰居放了西瓜在門外。想到我這個(gè)躲出去的母親,心中凄然難過。“活動(dòng)結(jié)束了還沒回去?要是我,早回家照顧孩子了。”那大姐心直口快,更讓我自責(zé)落淚,打算搬回去。
“你千萬別回,最多還有兩天,我相信我就轉(zhuǎn)陰了。你雖然得過一次,也不要再冒險(xiǎn),這病還是挺讓人難受的!對了,有幾個(gè)你的快遞,我都收好了。”我答應(yīng)去看看司馬臺長城,他窩在床上回信息:“挺好,這才是生活!”
回到家那天是周五,剛轉(zhuǎn)陰的兒子已經(jīng)上班去了。玄關(guān)處堆著一堆我網(wǎng)購的衣物,還有幾本雜志。我們這普通的百姓之家沒什么家規(guī),可凡是外來的東西,寫誰的名字誰才能打開,在父親健在時(shí)家庭成員間就默認(rèn)了這種對彼此隱私的起碼尊重。當(dāng)年我駐外工作,每年回國休假一次,明知是最普通的印刷品如《作家通訊》,父親都一本本收好,連同其他信件原封不動(dòng)地交給我。這份默契也被我和兒子保留著。
我走進(jìn)廚房,拿出那把總在刀架后立著的黑柄剪刀,劃開紙箱上的塑料封。是急于把紙箱連同廚房的幾個(gè)塑料水瓶清理掉嗎?我比往日的開箱速度快許多。
中午約了朋友吃飯,下樓時(shí)匆忙把那堆大小紙箱丟到樓下分類垃圾箱中。下午想用剪刀剪掉衣物上的商標(biāo),我才發(fā)現(xiàn)各屋找遍,也找不到那黑柄剪刀。懊惱之情油然而生,陡然間想起杰伊那把再也沒了下落的剪刀。毫無疑問,我把它隨手放進(jìn)紙箱,丟進(jìn)垃圾箱里了。
那只是一把剪刀,比杰伊母親那把“名貴”一點(diǎn),因?yàn)閬碜缘聡莾鹤赢?dāng)年在國外讀書時(shí)往返飛行,用航空積分為我換的“雙立人”牌剪刀。那個(gè)少年如今已經(jīng)是胡茬滿腮的成年男子。每次來了快遞,他亦如我,直奔廚房,取出那把伴隨這個(gè)家十年的剪刀,劃開塑料膜開箱。那把剪刀像一個(gè)不會說話卻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員。沮喪加自責(zé)。我知道唯一的彌補(bǔ)方式就是上網(wǎng)再買一把。京東果然有,果斷下單買下。心中似乎好受了一點(diǎn),雖然明知它已不是那一把。
黃昏時(shí)分去公園走路,仍想著那剪刀的下落,只盼著它和杰伊的那把一樣,得到某個(gè)身心干凈的人珍惜善待。回來時(shí)順便去院門口拿在小區(qū)群里預(yù)訂的葡萄和老玉米。經(jīng)過垃圾箱時(shí),在路燈下依稀認(rèn)出坐在三輪車上的女人,正是我不久前給過許多舊書和舊衣物的收廢品女人。“你……有沒有碰巧看到一把剪刀?我中午丟了幾個(gè)紙箱子在這兒……”我知道小區(qū)不止一個(gè)人頻繁地翻找可回收物品換錢,絲毫不抱希望地問。
“剪刀?我看到了呢。我知道是你的,因?yàn)槟羌埡猩嫌虚T牌號。我還在想,這么好的剪刀咋就不要了呢。”快人快語地說罷,她從三輪上一偏腿下來,在放著一堆紙板和繩索的車斗里一通翻找,遞給我一把。“不是這把?這也挺鋒利好使,要不你先拿去用?”她一臉耐心的笑。“不。我就要我那把。你再找找好嗎?”我突然有些慌亂,生怕歡喜落空。
被楊樹的枝葉濾過一遍的燈光很暗淡,她擰開一把小手電筒,繼續(xù)低頭翻找了一會兒,忽然張大嘴巴仰起笑臉,手中舉著我的那把黑柄剪刀。半天的離別,這剪刀回到它的家,似乎經(jīng)歷了一生的流離。我用酒精濕巾仔細(xì)地擦拭它,一寸一寸,像擦拭著我自己的手腳。
我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杰伊,隔著浩瀚的太平洋,傳來的他的聲音,依然輕柔如雪花:“Fascinating(奇妙)!一把剪刀,原來也可以有這么溫柔的故事。我上周剛?cè)ツ沟兀o我媽添了一個(gè)小天使銅像……”
【作者簡介】淡巴菰,女,本名李冰。現(xiàn)供職于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上海文學(xué)》專欄作家。在《人民文學(xué)》《中國作家》《北京文學(xué)》《江南》《飛天》等發(fā)表小說、散文若干。出版散文集《下次你路過》,紀(jì)實(shí)隨筆“洛杉磯三部曲”,小說《寫給玄奘的情書》,紀(jì)實(shí)文學(xué)《人間久別不成悲》《聽說》等十二部圖書。《聽說》被譯為英文出版。
責(zé)任編輯 練彩利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