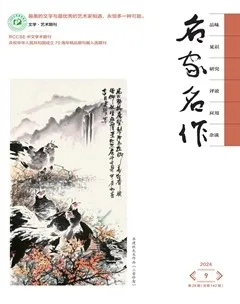花鳥畫創作的寫生與寫心




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提道:“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朱光潛在《談美》一書中也曾提道:“主觀的藝術家在創作時也要能‘超以象外’,客觀的藝術家在創造時也要能‘得其環中’。”自然界中的意象是生生不息的,人的情感也是,換一種意象就是換一種情感,反之亦然。即景可以生情,因情也可以生景。朱光潛講道:“詩人于想象之外又必有情感,那畫者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從姚最的“心師造化論”到張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再到宗炳游歷高山大川的“身所盤恒,目所綢繆”,從寫生到內化于心、以心寫神,這似乎是中國畫家一致認同的繪畫原則,這一原則歷經朝代的更迭,直至今日依然是指導藝術創作的準則。
客觀寫生對繪畫創作具有重要作用,很多時候那些生活化、情緒化的表現,光靠腦中的構建是無法完成的。面對自然物象時的欣然命筆,為畫面增添了些許的生動之氣。那些往返于戶外寫生的時光,對于我創作中的畫面構建起到很大的作用。我每次寫生都是辛苦、疲憊的,背著沉重的畫材翻越鄉間田野,吃不習慣的飯菜,睡不習慣的床,偶爾還會在山野中倚山背水,草草解決一頓午飯,每天接受烈日的灼曬與風沙的洗禮,這些聽起來似乎是不太美好的。但當真的看到自然界恣意生長的植物,將那些生動扭轉之姿即刻表現在自己的畫面中時,那些不適感又會瞬間煙消云散。每次寫生結束,整理作品是一個漫長又美好的階段,那些夾雜著山野氣息的紙張,總是會在悠長的藝術探索道路上成為見證成長的印記。
清代惲南田曾在《南田畫跋》中記述:“寫生先斂浮氣,待意思靜專,然后落筆,方能洗脫塵俗,發新趣也。”寫生是表現生活中的尋常景物,繪畫表達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繪對象也隨處可見。因此,以什么樣的方式表達能去除塵世俗鄙,不落畦徑地創造新趣味,又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了。幾年前我畫蜀葵,一整個夏天都在宋莊的胡同里,每天對著那一大片長勢旺盛的蜀葵花寫生。看得太久,以至于注意力全集中在客觀對象的細節:葉片是如何疊搭、枝干是如何扭動、花朵是怎么翻轉,甚至連花瓣上的脈絡也細心地記錄到了。我反復畫了很多張蜀葵的稿子,記錄了每朵花的姿態,糾結于表現細節和色彩關系的變化,卻唯獨忽略了畫面的構圖與取勢。花鳥畫構圖中大的布局須有一個大的趨勢,小的起結必須服從于大的趨勢,才不顯得雜亂和對沖。雖然我最終也沒有畫出理想中的滿意作品,但積累了大量寫生素材,也為寫生向創作轉化奠定了基礎。
花鳥畫寫生,既是形的描摹,又是意的感悟,同時也是物我交融的情感體現。潘天壽在其論畫筆錄中說:“自然界中的一切形象與色彩,是沒有思想性的,例如一棵樹或一朵花,本身是沒有思想性的,但是畫畫的人是有思想的,因此,無思想的對象經過畫家的眼及腦的觀察和想象,也自然有了思想性。”去年秋天,我偶然發現宋莊胡同口的一大片野姜花。暮秋時節,多數花卉已近衰敗,唯有這一大片野姜花落落欲往、矯矯不群。我觀這生長旺盛的野姜花,因為有了我的情感綜合,筆下的野姜花便是生生不息的希望,是成長于困境中的清新生命。但情感又是往復低回的,你憂,則看寒鴉、枯樹皆是慘淡悲涼;你懷揣憧憬,則看寂寥寒冬也是孕育著勃勃生機。面對相同的物象,一千個繪畫者或許有一千種處理方式,但技法層面的變化卻始終脫離不開傳統繪畫“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美學追求。自然界中花草的生生之氣,通過畫筆被再創作,平添了一份繪畫者的思想與審美情趣。
面對自然景物時,是物性與心性的交融。到自然中,看看那些頑強生長的花草,聽聽那些婉轉悠揚的鳥鳴,將對自然的感受“呈于象,感于目,會于心”,才能在心里滋長一些美好的繪畫情感。我想,繪畫始終是在追尋一種平衡,寫生時面對自然物象的取舍在追求平衡,繪畫時構圖是力求平衡,色彩也是追尋平衡。拋開技法層面,大抵是繪畫者對這些分寸的把控了,在芥子須彌的畫紙上呈現大千物象,不能過也不可不及,這恰好也暗合了中國傳統美學的“中庸之美”。尋常景物以丹青之筆表現,或許是繪畫者獻給生活最浪漫的不語詩。
王燕楠,山東青島人,2022年碩士研究生畢業于中國藝術研究院,導師陰澍雨。
2021年7月,作品入選“丹青寫光輝——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書畫展”(深圳泓嶺美術館)。
2022年3月, 作品入選“春暖——青年女性藝術家作品展”(北京華亞藝術基金會)。
2022年5月 ,作品《紅絲石拓片題跋》入選“靈氣所鐘——山東臨朐紅絲硯歷史文化展”(北京大學圖書館),被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
2023年3月, 作品入選“芳華——女性藝術家作品展”(北京華亞藝術基金會)。
2024年3月,舉辦“同硯——謝孜菡、王燕楠書畫作品展”(北京華亞藝術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