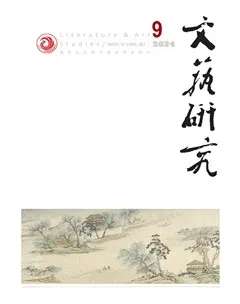“寫宋人詞意”:晚清民國詞意圖蔚興的歷史情境與內在理路







一、由林紓“寫宋人詞意”談起
1902年,林紓據姜夔《杏花天影》詞句寫意,并請人刻制墨盒,題贈王劭廉曰:綠絲低拂鴛鴦浦,想桃葉,當時喚渡。少泉仁兄同志大人屬,弟林紓寫宋人詞意。
八年后的一個北京雪天,林紓對雪起興,一天之內畫了十幾幅宋人詞意小品,隨后被榮寶齋制成箋紙,是為《宋人詞意箋》(圖1)。林紓之所以好寫宋人詞意,這自然與其詞境喜歡取法南宋詞蕭疏荒寂的畫境有關,也是其對“詞中亦有畫”觀點的踐行。林紓《宋人詞意箋》頗具象征意義,如若將其“寫宋人詞意”之舉視作一種文藝活動予以前溯后延,可以發現宋詞詞意圖的創作是晚清士林一個蔚為風氣的特有現象,并且至民國時期也流風未歇。
從通代視域來看,晚清之前的詞意圖創作整體上具有隨機性,一是未形成自覺的“寫某某詞意”之特定畫題,二是并不專主于圖寫宋人的詞意。宋至清中期的詞意圖,大都是據詞句構圖設色,畫題中并無“詞意”字樣,而是如通行畫題那樣“四字短語+圖”的制題模式③。例如,宋王詵《江山秋晚圖》系據孫浩然《離亭燕·一帶江山如畫》而作,“盡寫浩然詞意”,卻不題作“浩然詞意圖”。從詞句取材來看,繪圖者有取唐五代詞句之例,如元末王蒙自題李白《秦樓月》詞意圖卷;有取同時代人詞句之例,如元末陸行直《碧梧蒼石圖》繪友人張炎詞意,文徵明畫竹之詞意圖兩度用高啟《水龍吟·題朱竹畫卷》;也有先自作詞,然后據以畫圖之例,如沈周《漁家傲》《柳梢青》之詞意圖。總體而言,清中期以前詞意圖既對詞句取材的時段比較隨意,也沒有出現地域、流派或某個時段集中涌現的情況。
清代前中期的二百多年間,宋詞詞意圖可考者僅十余種;而至晚清民國時期,無論詞意圖的作者、數量還是類型,都遠遠超過之前二百年的積累,呈現出宋詞詞意圖蔚興的現象,尤以海上畫派最具代表性。茲部分列表如下:
列表之外,民國時期尚有呂鳳子《蔣捷詞意圖》《斷腸點點飛紅(辛棄疾詞意)》《數流螢過墻》、姚茫父《煎茶詞意圖》、劉毓盤《斷夢離痕圖》、唐怡瑩《繪謝池春慢詞意》、高炳華《秦少游〈浣溪沙〉詞意》、徐燕孫《李清照詞意圖》、熊秉三《辛稼軒詞意》、徐宗浩《李清照詞意圖》、卜孝懷《李清照詞意》《周美成詞意》、朱玉麒《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詞意》、陳從周《一絲柳一寸柔情(宋人詞意)》、吳藕汀《宋人詞意圖冊》等,皆專從宋詞取材。
近年來,隨著學界研究的“物質性轉向”,圖像與文學的關系成為學術前沿,而融詩畫為一體的詩意圖尤受關注。學者在古已有之的詩畫關系研究基礎上,引入西方圖像理論,甚至關注到南宋杭州、晚明蘇州詩意圖對東亞文化圈的影響。稍顯遺憾的是,學界迄今的詩意圖研究往往默認詞意圖僅是詩意圖中無甚特出的一支,忽視二者差異性;另有研究則明確指出“宋詞構成了另一種紛繁復雜的文學圖像系統”,故而在研究詩意圖時將詞意圖摒除不論。無論哪種情形,都導致詞意圖在圖像與文學關系這一研究譜系中的“門前冷落”。
當然,也有部分學者關注到了詞意圖內在具有的特殊性,并對明刻《詩余畫譜》展開專題研究;王曉驪連刊兩文,提取了詞意圖以詞作為中心和以繪畫為中心兩種闡釋方式,并指出詞意圖通過造型藝術的特殊話語,創造了文人詞接受的新方式。吳企明、史創新《題畫詞與詞意畫》,魏新河《詞學圖錄》,趙憲章主編《中國文學圖像關系史》等著作則在詞意圖匯集方面頗有貢獻。在詞意圖的起源及流變方面,張克鋒、魏亮亮等注意到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是詞意圖興盛、鼎盛的兩個時期。不過,問題是:晚清民國詞意圖具有明顯的專主宋詞的特點,形成了“寫宋人詞意”的風尚,那么其興起的歷史情境與內在理路是什么?本文即從此出發,探究晚清民國詞意圖的“內”“外”相關問題。
二、晚清以來“好宋”歷史情境與詞意圖之“憂患”
在談及清代中期以后詞意圖的創作土壤時,有學者總結了三重因素,即嘉道年間的奢靡之風、晚清時期上海商業經濟的繁榮以及“國學”“國粹”思潮的影響。不過,這三重因素似乎都難以解釋為什么晚清詞意圖喜歡“寫宋人詞意”。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需要深入到當時士林的文化風習以及審美趣味。
在親歷晚清民國學術思想風氣的薰染后,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論定式地總結說:“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陳氏所論“新宋學”,自具卓識,而其明確將考古、歷史、文藝、思想史列舉為學術變遷的顯著領域,也正得其實。晚清的學術風氣確實已然呈現了“宋學轉向”,“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個基本風氣”。至于文藝層面,尤與本論題正相關,可析分為繪畫與文學兩個維度加以探考。
就畫史來看,既往研究從“正統”眼光出發,認為19世紀宮廷畫派和隱逸派同時式微,“畫壇便入蕭索的局面”。但也有學者予以撥正,認為19世紀畫史屬于“并非衰落的百年”,大凡所歷觀念變革、社會轉型、市場主導以及西畫的沖擊皆為背景,而非“中國繪畫傳統的內部在審美意識和時代風格上的變革”的主因,實際乃是“‘筆墨藝術深化’在中國描繪物象的繪畫語言限制中形成一種解脫的創造性傳承”。每當一種藝術傳統處于變革之際,身處其間者倘欲有所突破,一方面要復古以為新,另一方面則要開拓新的畫境。對于晚清的畫家而言,復古至宋代,從詞文類中去挖掘繪畫題材,便是學術史演進規律的題中應有之義了。清中期以后,江浙一代已經出現了一些不拘于時風的畫家,其表現之一便是“繼承明代吳門畫派的傳統并上溯宋人而獨辟蹊徑”。至于晚清崛起的海上畫派,更是遠紹宋風,尤其吳昌碩畫面之中蘊有南宋詞人一般的憂患意識,畫旨作苦調。高爾泰將這種憂患意識看作為中國傳統藝術的一個特色,“產生于憂患意識的情感,必然是深沉的和迂回的”,在藝術表現上就顯得“含蓄”“意在言外”。隨著社會危機的加深,繪畫中的憂患意識也不斷生長,甚至后來轉換成美術領域的“救亡圖存”。
至于文學領域,其軌跡更為明顯。道咸年間詩壇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宗宋風氣,宋詩派、桐城派、經世派共同推闡,形成晚清的“宋詩運動”,典型表現則如簁邰唱和、門存唱和等。19世紀初期所繁興的壽蘇會、壽黃會、壽歐會等,通過“為宋人壽”的儀式化集會,主持風雅,追慕前宋,“匯成奔涌向前的宗宋浪潮”。具體到詞學方面,“清人對宋詞的研究從輯佚詞集、辨析版本到考證詞人、評述風格,從校勘文本、編選詞選到推求韻律、分析結構”,充分顯示出清人治宋詞的豐富內涵與宏闊規模。平心而論,晚清民國詞面對著唐五代詞、宋詞兩大傳統,自然不可能整體性、一邊倒地偏向一側,比如為了矯正浙派標舉南宋、推崇姜張之弊,常州詞派便有意識地回返唐五代詞,推尊詞體,尋繹比興寄托。因此,本文無意、實際也不可能證成晚清民國詞一律皆帶“宋氣”。具有“宋氣”的文人詞,其特點概括言之:寫景、敘事、抒情皆返歸于對士人格調的呈現,風格既蕭散又超越。談及宋詞與清詞關系,姚椿有“詞之義至南宋而正,至國朝而續”之論,亦是直以清詞接南宋詞。晚清詞壇之風氣,或學周邦彥,或學吳文英,這一風氣的末流,便是文廷式所謂“以二窗為祖禰,視辛、劉若仇讎”。不過,諸家在“尊體”這一層面有著近乎共識的價值判斷。晚清在詞學領域的尊體,則是基于對比興寄托傳統的重新發現。而比興寄托要求詞體關注社會現實, 寫社會憂患, 即周濟所說“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后人論世之資。詩有史, 詞亦有史, 庶乎自樹一幟矣”。
于是,晚清繪畫與詞體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詞意圖,其憂患意識更加明顯,這也是晚清社會群體心理的另一種折射。在19、20世紀之交的時代,面對歷史巨變,士大夫群體普遍懷有沉甸甸的“落花”心事,或如陳寅恪所說的“辛有索靖之憂”。在這樣一種群體心理下,文人畫家在憂患意識所投射的宋詞尤其南宋詞中,找到一種“不同時代的同時代性”。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吳昌碩的《復堂填詞圖》(圖2),畫上題署“煙柳斜陽填詞圖”,寫辛棄疾《摸魚兒》“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復堂填詞圖》之所以在晚清被多家題跋且反復提及,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便是“煙柳斜陽”的意象戳中了士人敏感的憂患意識——憂心華夏文化的淪替。
晚清以后,宋詞詞意圖形成了兩個作品眾多的公共詞題,即柳永《雨霖鈴》的“楊柳岸,曉風殘月”和蔣捷《虞美人·聽雨》。“楊柳岸圖”有鄭文焯《楊柳岸曉風殘月》(圖3)、湯貽汾《雨霖鈴詞意圖》、倪田《宋人詩意圖軸》等,“聽雨圖”則有張墨池《僧廬聽雨圖》、改琦《少年聽雨圖》等。在這兩個詞題的畫作中,我們一方面可以體會到人類情感的不同載體跨越時空所達到的共鳴,另一方面則更能通過詞境、畫境的疊加,感受到晚清民國士林所獨具的以“疏離”“飄零”“凄涼”為底色的身世之感。實際上,晚清民國詞意圖明顯體現出了吳宓所說的“危亂貧弱文物凋殘之中國之人所特具之感情”。
三、“書卷氣”與“小品”特質
回到林紓的《宋人詞意箋》掌故,我們發現鄧云鄉的一則評議很值得關注。鄧云鄉《〈北平箋譜〉史話——魯迅先生逝世五十年祭》曰:
畏廬老人(林紓——引者注) 所作是近代境界極高的文人畫,師法南宗,用筆蕭疏有致,所選都是山水小品,寫宋人詞意,高古處如倪云林。如一幅吳夢窗之“竹箋燈窗,識秋娘庭院”,畫面左方幾枝秀竹,竹下小室軒窗,構圖十分簡潔,而章法筆法,極為高妙。秋情滿紙,只此數筆,便把觀者引入詞境了。
鄧云鄉認定林紓的詞意圖屬于南宗文人畫,且多小品尺幅。無獨有偶,張旭、車樹昇《林紓年譜長編》引林紓贈王劭廉“寫宋人詞意”后,即認為“該作系典型的文人寫意畫”。如果再向前追溯,可以發現“文人畫”的這一定位在清王文治為潘恭壽《寫柳永詞意圖》題跋中即已有比較明確的“自覺”:“柳屯田《雨淋鈴》詞情景入畫,然畫家畫景易,畫情難,非文人濡毫,不能得詞中三昧也。”強調了“文人”在畫面情致表現中的長處。該詞意圖今藏天津博物館,疏柳陂塘,小舟橫泊,筆墨疏朗,設色淡雅,確實是典型的文人畫。這自然就衍生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只有文人小品畫才能畫得出“詞中三昧”?
我們的回應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無論是詩意圖還是詞意圖,皆有文字所指涉、聯想的意境相映發,故而“書卷氣”成為詞意圖的應然水準;第二個層面,小尺幅、小局部的“小品”特質是詞意圖在所有“文-圖”中最具識別度與區分度的特質。先從第一個層面看,清代畫家查禮在《榕巢題畫梅》中說:“凡作畫須有書卷氣方佳。文人作畫,雖非專家,而一種高雅超逸之氣,流露于紙上者,書之氣味也。”俞劍華論文人畫曰:“唯以其人品高尚,文學豐富,詩意優長,書法超逸,故所作雖不精工,亦自有一種秀逸高雅之氣,撲人眉宇……所謂文人畫,所謂士氣,所謂書卷氣,所謂無縱橫習氣,俱屬此類。”復考陳師曾《文人畫之價值》曰:“何謂文人畫?即畫中帶有文人之性質,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畫中考究藝術上之功夫,必須于畫外看出許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謂文人畫。”這一闡釋有著兩個向度的要求。在內在向度方面,要求畫圖之“文人”具備人品、學問、才情、思想等素養。在陳師曾看來,文人之能事,無非文辭詩賦;而“文辭詩賦之材料,無非山川草木、禽獸蟲魚及尋常目所接觸之物而已。其所感想,無非人情世故、古往今來之變遷而已”。文人基于自己的素養,面對自然、人世、歷史會生出幽微的感想,此即詩心(具體到詞,即是詞心)。況周頤《蕙風詞話》云:“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詞意圖的可貴之處,即將此獨具的詞心在紙墨上予以具象化,“首重精神,不貴形式”。在外在向度方面,則是通過布局、設色,將心中之性靈與感觸在小幅畫卷中傳達出來,營造荒率、質樸、瘦硬、簡渾、雅淡的文人畫神韻。
從第二個層面看,前舉宋詞詞意圖文獻,多為小品畫,這留給畫藝的施展空間頗為有限,對其品鑒則頗需詞心感想的參與,這恰能佐證陳師曾“不在畫中考究藝術上之功夫,必須于畫外看出許多文人之感想”的論斷。潘恭壽曾在《寫柳永詞意圖》題識中有所自陳,從中可探知他在作詞意圖前與王文治探討的并非技法,而是如何使詞意圖“得纏綿宛轉之情”,而他得情的載體仍是一柳岸空舟的局部特寫。林紓作詞意圖,也是在“感想”上下功夫。王沂孫《齊天樂·贈秋崖道人西歸》開篇有“冷煙殘水山陰道,家家擁(壅) 門黃葉”之佳句,晚清陳廷焯曾評價曰“一起令人魂銷”。林紓據以繪制《宋人詞意圖》(圖4),且題識曰:
閩中秋后,草木黃落,諸山咸有蒼赭之色。此宋人詞所謂“家家壅門黃葉”者也。每一山行,輒嘆古人體物之肖。頌眉先生大雅之屬,畏廬林紓識。
這一題識寫出了自己以親身經歷的情境去印合古人的歷史情境,正與里爾克所論“詩是經驗”異域同轍。實際上,這樣的以小幅呈現截句,確能給異時異地者以“心有戚戚”的共情感,“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詞意圖喜“截句入畫”,尤其是詞作中的警策之句,比如顧鶴逸畫張先詞意就著重寫其“張三影”三句,“以畫詞之影也”。晚清民國時期,逐漸形成了小品畫、截句題的模式,畫面與詞句相得益彰,最得雋永之妙。啟功嘗論:“畫上的幾個字的題辭以至題詩,都起著注明的作用……可因圖名而喚起觀者的聯想,豐富了圖中的意境,題詩更足以發揮這種功能。”此語正可移評詞意圖。
萊辛認為,最能產生繪畫效果的并不是情節或情感的“頂點”,而是“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頃刻”。為了呈現“頃刻”,尤其適合進行小幅、冊頁或扇面等小品畫的創作,來表現寥寥一二“截句”,詞意圖如是,乃至清代風行的填詞圖亦有著相近的規律。清蔣寶齡論陶懷玉曰:“山水得法于翟云屏,尤長小幅。曩曾見其繪宋人詞意一冊,用意精微,點染入妙,覺古人片語單詞,彌有不盡之致。”詞意圖的“小幅”化,與詞體的內在質性有關。與詩作不同,詞作取景往往注目于庭院樓臺的小景,或山水一角,而很少去描摹山河壯闊,宇宙星野。橫向比較來看,以唐詩為素材淵藪的詩意圖注重深遠的空間營構,即便畫面為小幅,詩意圖也追求“氣勢開闊”“小中現大”;而以宋詞為素材淵藪的小品詞意圖,則多注重近景和特寫。
詞意圖的“小品”特質還體現在對詞句的細微改造。畫家創作詞意圖時會將其心神領會的“詞中三昧”加以創造性設計,有時不惜改變詞意、本事甚至詞句,而不會像畫工那樣謹守句意, 亦步亦趨。吳企明、史創新在《題畫詞與詞意畫》中總結詞意畫的兩個美學特征,一是遴選前人詞句時,擇取全詞中的關鍵詞句;二是畫家根據需要,往往轉換詞意,轉換詞中主人公。比如晏幾道《臨江仙》“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本為小山自況,而余集繪詞意圖,則轉換主角為看花少婦,將這一詞境引入到仕女畫的譜系之中。在任熊的《荷塘仕女圖》(圖5)中,款識嵌入畫圖,題于欄桿之上。核查詞句原文,可發現畫圖所據姜夔《念奴嬌》詞原為“翠葉吹涼,玉容銷酒,更灑菰蒲雨”。姜夔原詞意象繁密,取境幽廣,任熊則將圖景轉移到閨閣書房,描繪兩女子聽雨納涼,于是畫題也便修改成了“繡屋招涼,更灑菰蒲雨”。可見文人濡毫,最切要處在于構思獨出機杼,不落窠臼。結合前文所論,我們也更加精準地理解林紓的這段論畫名言:“作畫須書卷氣,非文人自高聲價也,亦構思著筆,不落俗耳。”在詞意圖創作中,選取佳句、性別改換、意境轉移都是作畫者在視覺化過程中對文學文本的一種重新解讀,是貼切詞作抒情本質的再創作,如此文圖關系不僅折射出“文人意趣與審美風尚,更為古典詩詞的文學內涵注入了新質”。
四、“秀”與“詞畫一律”
詞意畫的發展,離不開士人對詞畫相通藝術原理的把握,清人多借用畫理說詞,如“寫意”“皴劈”“勾勒”“開闔”“點染”等,于是也指向一條伏線:詞意圖之所以成為可能,其本質可能是基于兩種藝術門類內在的“詞畫一律”。關于“詩畫一律”,論之者頗多,但詞與畫的一律性少有人加以論列。那么,詞與畫的共通點何在?饒宗頤曾一言以蔽之曰:
詞與畫在本質上有共通點,即是一個“秀”字。
“秀”范疇的提出,可以看作對近代諸家有關詞、畫相通性的總結。其實,這也不是饒宗頤的一家之言,畫史中對“秀”的強調,自晚明董其昌以來便已成風氣,而清人畫品更是多將“秀”字納入,如潘曾瑩《紅雪山房畫品》有“幽秀”,秦祖永《桐陰論畫》有“秀潤”“秀嫩”“秀淡”“秀挺”“文秀”“古秀”“蒼秀”“高秀”“松秀”“森秀”“疏秀”“韶秀”“娟秀”“風秀”“秀逸”“秀潔”“雅秀(秀雅) ”“靈秀(秀靈) ”等十多種品目,屢以“筆情松秀”“墨法松秀”“清疏秀逸”來論文人畫,范璣也認為“文人作畫多有秀韻”是因為有“卷軸之氣發于楮墨間耳”。更有意味的是,范璣之言更是將詞意圖之“秀”與上文所言“書卷氣”建立了聯系。也就是說,“書卷氣”關乎學深識廣,氣韻閑雅,呈現在詞意圖上,便是意境、格調層面的“秀”。關于詞之宜“秀”,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多有闡發,“以松秀之筆,達清勁之氣”,“信手拈來,自成妙諦。以‘松秀’二字評之宜”。與之呼應的是,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論“皴”法亦曰“松秀長韌”(云頭皴)、“筆筆松秀”(牛毛皴) 。
由此可見,在談藝者的視域中,“秀”往往與“松”“疏”聯類,主要體現為整體性的疏朗沖淡。落實到詞意圖上,則是需要將詞境款款徐引,注入到詞意圖的簡淡曠遠之中。吳湖帆《清真詞意》題識曰:“周清真詞云‘風嬌雨秀’,此圖略具姿態。湖帆隨筆。”顯然,周邦彥《玉燭新》抓住了梅花“照水一枝清瘦”的精神,且將梅花在風中“嬌”、雨中“秀”的神韻點了出來。吳湖帆之所以要根據周邦彥詞意畫梅,是因為他極意營造的正是這種“嬌秀”的姿態在畫圖上的顯現。
當詞與畫融合為詞意圖時,秀韻往往更能顯現,而精于品鑒者也能獨具只眼,將此一律性拈出。詞評家認為“耆卿秀淡幽艷”,據方濬頤《夢園書畫錄》卷一著錄,宋王谷曾畫“楊柳岸,曉風殘月”詞意,方氏的評價為“船頭一人,仰觀明月,岸旁疏柳掩映,柔條拂處,秀韻無雙”。所謂“秀韻”“雅秀”,可以說是對詞意圖境界造詣的精準提取,也與饒宗頤所提煉的“秀”字遙相印證。
“秀”這一風格定位,無論對于詞還是對于畫,都具有一定的篩選作用。它要求畫作須為文人畫,而非畫工畫;而畫作所取資的詞句也須為文人詞(士大夫詞),而非側艷之詞(伶工之詞)。也就是說,以“秀”論,則唐詞、南唐詞、西蜀詞皆不與焉;宋詞之中,哀感頑艷之作,也非其選。“秀”是立足于“書卷氣”的一種境界,如果一首詞純托性情,大開大闔,奇崛變化,則難以用“秀”來形容。因此,“秀”的評價多加諸疏松、淡遠、清媚的詞作,近于這一風格的詞人如晏殊、歐陽修、秦觀、李清照及姜夔等,意象工巧,風格疏淡,呈現出“于方寸中見高標”的藝術效果,動人心曲。
那么,在詞意圖層面的“秀”,其范疇究竟蘊含哪些層面呢?首先,從前揭詞論“秀”往往與“松”聯類可見,作為文人畫的詞意圖往往令人心胸疏瀹,霽月光風,盡管圖中似有無限心緒,但很少呈現出悲戚哀絕之態。在《蕙風詞話》中,況周頤有如下對話:“問:填詞如何乃有風度。答:由養出,非由學出。問:如何乃為有養。答:自善葆吾本有之清氣始。”錢載《寫玉田詞意》刻畫的是張炎“一片松陰外。石根蒼潤,飄飄元是清氣”三句。以詞句入畫,畫家須在文本中選擇可以入畫之物象。此處張炎《湘月》一詞上闕僅此三句有具體物象可以入畫,“清氣”無法刻畫,這里所著力表達的實際上是以蘭花飄蕩的葉片來喻“清氣”。“清氣”一語,既關涉文人氣質,也與“秀”的范疇意脈相通,可以看作“秀”的第一層闡釋。
其次,改琦《玉田詞意仕女圖》(圖6) 誤題“屯田”作“玉田”,實際是畫的柳永“楊柳岸,曉風殘月”詞意。畫中主人公為一少女倚柳而望,董耀題跋贊曰:“風姿婉麗仿佛于柳煙月色之間。”陸儼少評吳湖帆之詞意圖為“婉約的詞境,風韻嫣然的嫻靜美”。“婉約”“風韻嫣然”“嫻靜”等詞,皆道出詞意畫與詞作本色相通的風格,正如學人所指出的,“詞長短參差的特殊體式和婉約深曲的藝術風格,又給繪畫增添了委婉的情韻和錯落的美感。”“婉”之一字,可以看作“秀”的第二層闡釋。
最后,于源為計光炘撰《守甓齋詞序》謂:“去射襄城二三里為雁湖,橋上有亭曰‘冠鰲’,一名‘野水’,又有僧舍曰‘小滄浪’,曦伯消夏于此。風帆沙鳥,煙波渺然,此畫境,亦詞境。”“風帆沙鳥,煙波渺然”之境,并非萬籟俱寂的靜美,而是天機靈動卻不喧囂,有一種活潑潑的萬物運化之象。馮班嘗曰:“秀者,章中迫出之詞,意象生動者也。”“氣韻生動”在傳統畫論中被看作繪畫品評的最高標準,“生動”一詞,可以看作“秀”的第三層闡釋。
不同的藝術具有“某種共同的聯系,某種互相認同的質素”,詩歌和繪畫的一律性在東方和西方都是傳統觀點,而具體到詞意圖中的“詞”和“畫”,這種認同的“質素”究竟為何是本節所要追問的。“詞畫一律”在詞意圖層面有其成立的內在理路, 那就是基于“秀”這一藝術范疇在詞學和畫學層面的本質共通點——清、婉以及生動。唯其詞句有清氣,遷移到圖畫上則有清明的觀感;唯其詞句憂患于中、哀婉而不傷,遷移到圖畫上則有克制絜矩的人、物以寫遠意;唯其詞句有飽滿生動的生命意識,遷移到圖畫上則滿紙生機、包涵希望。龐德認為:“每一個概念,每一種情感,都以某種元形在我們活活潑潑的意識中呈現。”在晚清民國寫宋人詞意圖的世界里,各種風神氣韻運行其中,而“秀”是理解其融通精神的“元形”所在。
余論
詞意圖是詞的視覺化形態,它作為對詞作文本的摹寫,或者詞意的圖像再現,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宋代以來人們對于詞體與繪畫共同的身份認同是“詩余”,作為“詩人之余事”的詞和蘇軾筆下“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余”的畫,“詩余”固然是在詩本位思想下對其身份的邊緣化,但正是在這樣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窺得詞和畫內在的實質性聯系。在藝術批評中,詞和畫有著諸多共同的審美標準、概念和范疇,比如意境、意趣、氣象、氣韻等,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詞意圖是詞畫關系體系的審美實踐。
詞作在豐富的長短句式中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境界,往往是通過揀選的意象對人生實境進行詩意化表達。相比較于詞句,詞意圖則是又一度的創造。詞句中的意象表現為具體的物象實景,詞意圖的創造旨在復現原本僅僅存在于詞句中的場景,本質是一種可視的“幻境”。“截句入畫”類型的詞意畫創作在晚清勃興,這種類型的詞意畫力圖最大限度地完成意象安置和詞意抒發以呈現“頃刻”,實現了詞作內涵的增殖。誠如法國漢學家羅思德所論,“因為文人重視文學,繪畫所選擇的題材也因此變得相當重要,常常涵蘊深刻的文學意義,有時甚至變成一種文學的詮注,體現當時文人的文學觀念和對文章的想法,從而給畫作多加了一層含義”。詞意圖在視覺上的呈現不僅是簡單的文圖結合的畫面,更是注重表現詞之外的詞人和畫作者的情感體驗,其詞畫融通的精神內涵與傳統文人的生命品格不無關系。
晚清士林的“好宋”之風、商業的發展以及“國粹”思潮的流行,詞畫共享的社會背景和藝術精神綜合孕育了詞意圖發展的社會文化土壤。高居翰說:“畫家讓自己投入畫中,成為其中理想文人的角色。”投入其中的文人,通過與詞作共生的意象和意境營造來實現對于“不可說”的詞意的表達。晚清文化史上的“寫宋人詞意”是對宋詞的一次回望和致敬,拓展了宋詞時間和空間的限度,具有“經典”的意義和價值。隨著晚清時期宋詞詞意圖影響的擴散,詞意逐漸溢出文人畫,在多種物質性載體上得到表現。民國時期流行一種被稱作“黑白畫”的藝術形式,融版畫、剪紙等藝術元素,頗適合報刊的黑白印刷,當時黑白畫的代表性作者黎朔便創作了多幅宋詞詞意畫作品。甚至某些建筑的天臺石窗,也通過石刻造型表現歐陽修的名句“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后”。從中皆可看到一種文化風氣所浸潤的文化心理,而古典也正是通過文本形態、物質性載體的遷移延展,最終成為文明幕布上的一層底色。
作者單位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學院
責任編輯 高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