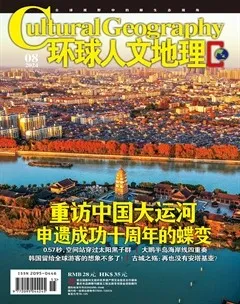南長灘,北長灘
2024-10-10 00:00:00唐榮堯
環(huán)球人文地理
2024年8期
黃河流過黑山峽中的小觀音后不久,兩岸對排的群山像兩個商量好即將要決斗的摔跤手,身子向下稍微一彎——山勢稍微減弱了一下,各自朝后退了半步——給兩岸各自騰出了一片狹長的灘地。隔河相望的兩片狹長河灘,南長灘是黃河流入寧夏的第一個村,南長灘對面的村民所稱呼的《景泰縣志》中標注的“北長灘”,則是甘肅省轄內(nèi)黃河最東邊的一個村。
南長灘是寧夏迎迓黃河的第一村,如果從沙坡頭區(qū)前往那里,得沿著騰格里沙漠南緣的338國道往西而行,至甘肅省景泰縣草窩灘鎮(zhèn)轄內(nèi)的十里溝溝口,再順著這條干溝往里走,兩邊的山坡因為煤礦開采而裸露著廢棄的煤渣,讓人恍如進入一個黑色世界。沿途會依次經(jīng)過由幾戶人家構成的翠柳村一組、二組,直到河邊的翠柳村六組,這里就是當?shù)匕傩战械摹氨遍L灘”。我趕到河邊時已是黃昏時分,兩岸群山猶如雙唇,一河濤音自那雙唇間流淌而出,吹奏著一曲古老而神秘的歌謠。
從小在黃河邊長大,我知道面對大河該有的敬畏與禮數(shù):晨不越山,暮不過河!于是便在暮色中的北長灘臺地上尋找扎帳篷的地方。河流是有口音的,并能將這種口音灌輸給流經(jīng)地區(qū)的村子。黃河在甘肅省境內(nèi)流經(jīng)哈思山后,至下游100多公里的長灘一帶,被兩岸百姓稱為“下河”。這一帶人說話基本保持著和上游地區(qū)不一樣的“語言孤島”,我的鄉(xiāng)親和這里的村民說的就是“下河話”。
鄉(xiāng)音是一臺拆除聽力交流之墻的推土機,我用下河話一張口,就消除了和村民們對話的障礙。……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