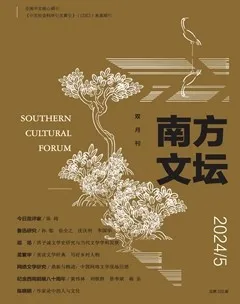讓人生充滿愈發豐盈、遼闊的可能
我的朋友兼同事“濤哥”陳濤是個神人。他寫過小說,寫過散文,寫過評論,而且是中國作家協會職工里少有的在作協三個主要辦公區域(東土城的機關、芍藥居的魯迅文學院、長虹橋的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都工作過的人。他的散文我讀過,就是那本前幾年曾經在圈里風靡一時的《山中歲月》(修訂后的新版換了個書名叫《在群山之間》)。他的評論我讀過,雖然數量不多,但每篇讀過之后都讓人印象深刻。他的小說我沒讀過,大概屬于“悔其少作”的那種,想必他也不好意思拿出來讓我們拜讀或批判;不過《山中歲月》里有那么一小截文字,以“我”的視角寫一個名叫“寧”的女孩子,文字空靈,從“寧”的身上甚至能看出《聊齋志異》里嬰寧的影子,很有些小說的味道。只可惜出版社在出修訂版的時候認為此篇與全書主題不搭界,硬生生給拿掉了。對于這種焚琴煮鶴的做法,我非常不以為然。最近濤哥又告訴我,他正在醞釀一篇研究柳青佚作《在曠野里》的學術論文。這部小說發表在他擔任副主編的《人民文學》雜志上,是《人民文學》2024年開年的兩記“重炮”之一(另一記是《人民文學》登上“與輝同行”,是董宇輝第一次在直播間里為文學期刊“帶貨”),所以當我問他此舉算不算“職務行為”時,他笑而不語。
濤哥最著名的事跡是曾以“第一書記”的身份在甘肅臨潭駐村兩年,并且榮獲了“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山中歲月》就是他這兩年間駐村見聞和思考的記錄。翻開這本書,第一句話便是“2015年7月27日,我離開北京奔赴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冶力關鎮池溝村開始為期兩年的‘第一書記’生活”。初讀這句話,我先是有些驚訝,繼而百感交集:我畢業后到第一個工作單位中國現代文學館報到是2014年7月8日,從此在文學館地下室的集體宿舍一住就是五年,當時濤哥還是魯迅文學院的一名老師;文學館和魯院同在朝陽區芍藥居文學館路45號,也就是說我們兩個人曾經在那個大院子里共事整整一年,但在這一年里我們幾乎沒打過交道。我至今還記得,剛參加工作時的我每天下班后無聊地在院子里轉圈,經常能看到一群人在籃球場上鏖戰,里面應該就有濤哥,只是當時我們還互不認識;而真正熟絡起來,還要等到幾年后他從甘肅駐村歸來在作協機關工會組織青年職工活動,甚至要等到我們先后調入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之后。十年時光一晃即逝,不知現如今的大忙人濤哥已經遠離籃球場多久了。套用讀書時某部無厘頭網劇里的著名臺詞,大概可以感嘆:我想起那天夕陽下濤哥的奔跑,那是濤哥逝去的青春。
正是因為有過住地下室、靠在院子里轉圈打發孤獨無聊時光的經歷,我才能對濤哥《山中歲月》里的那些細節感同身受。說實話,剛看到這個書名時,我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小時候讀過的那本曾經獲得國際安徒生獎的同名童話(作者有個拗口的姓“克萊格海德”Craighead);其次想到的是“山中宰相”的典故,還跟同事開玩笑說,濤哥不會在書里自比隱居茅山的陶弘景吧?直至讀罷掩卷,復雜的情感在心中糾結,一種如嚼青橄欖似的苦澀久久不能散去,我才第一次對“第一書記”這個特殊的任務、對“生命中的二十四個月”(濤哥駐村的時間,也是《山中歲月》最后一章的標題)有了感悟。而當我拿到已經更名為《在群山之間》的修訂版時,我會心一笑,因為我記得曾經有一位著名的智利詩人在《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中大聲吟唱“從群山中我將為你捎來幸福的花束/風鈴草,黑榛樹的果實/以及一籃籃的吻”(巴勃羅·聶魯達《你每天都同宇宙之光嬉戲》),而濤哥在群山之間寫下的這本書,就是他為我們捎來的世間最美麗的花束。
中國作協歷來不缺少掛職干部,但是以“第一書記”身份到最基層的貧困村駐村、親身參與脫貧攻堅這一歷史偉業的,濤哥是第一個。我們都對他能夠做出這個決定佩服得五體投地。《在群山之間》的書前、一般用來安排作者“獻詞”的位置,摘錄了此書《后記》開頭的那句話:“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會有無數個決定,但總會有那么幾個決定,將你引向難以預知卻又充滿獨特魅力的旅途。”這句話總能讓人想起路遙在《平凡的世界》開頭所引的柳青的那句名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2015年,濤哥36歲,應該還算得上年輕。就在這一年,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邁出了人生中最緊要的一步,走上了赴甘肅扶貧的旅途。從此,他將與窗外的那棵核桃樹日夜相伴。他曾經在多篇文章里提到那棵樹,它似乎成了濤哥駐村兩年時間里的精神寄托。它高大,孤獨,每當風吹過,鮮亮的葉子輕擺,簌簌作響,“閉眼傾聽,只覺天地間最美妙的聲音也不過如此”。樹亦人,人亦樹,一時間竟分不清誰是樹,誰是人。
許多人是因為濤哥去駐村才第一次聽說了臨潭冶力關這個地方。在這一點上,我也許比大家知道得都早。大約從2011年開始,甘肅省每年都會在7、8月間舉辦“絲綢之路國際旅游節”,從第一屆起,冶力關就是被重點推介的旅游目的地。2013年暑假,我曾經打算在動筆寫博士論文前去闊別20年的西北窮游一番,冶力關也被納入了計劃之內,可惜旅程剛剛開啟就因為各種原因而草草收兵。所以,幾年后當我聽說濤哥要去臨潭冶力關駐村,第一反應并不是感動或者欽佩,而是腹誹——怎么會有人跑到景區去扶貧?讓我去我還巴不得呢!印刷精美的《山中歲月》和《在群山之間》里也有許多冶力關的“美照”,據說有一些還是出自濤哥之手,看那藍天、白云、碧水、森林、麥田、經幡、晚霞,簡直就是都市人夢寐以求的“香格里拉”。可是讀罷全書我才知道,盡管池溝村也位于冶力關景區內(或者可以說,整個冶力關鎮就是一個巨大的景區),但這個被游客們視為“避暑天堂”的地方,一年之中也只有夏天的兩三個月可以開門納客,其余時間則要與冰雪、寒風或凍雨斗爭,因為這里“只有兩個季節:冬季或者大約在冬季”。這里的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自黑”是:這里啥都不產啊,真是個神奇的地方!當一個人只能通過去飯館里吃包子里星星點點的菜葉才能一解對青菜的渴望,我想,再美麗的風光都留不住遠方的來客。
書中寫道,駐村任務結束后,濤哥曾經多次回到冶力關,回到池溝村,但曾經的同事小尤每一次都會在半醉半醒之間斷定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這里,“我當然是否認,但是他總是堅持,一邊飲酒一邊說我將會忘記這個地方”。他身邊眾多的80后干部們,身負重擔又升遷無望,每天需要面對的是填不完的表格和不時冒出的突擊檢查,還要應付《山上來客》里戴土黃色頭巾的女人和《芒拉鄉死亡事件》里羊得才夫婦那樣令人訝異的鄉民,只能靠喝酒來排遣自我愁緒,“有的人喝著喝著就醉了,有的人喝著喝著就哭了,是飲酒幫他們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內心的平衡與調和”。按理說,一本“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品里出現《山上來客》《芒拉鄉死亡事件》《困境的氣息》《小鎮青年、酒及酒事》這樣色調灰暗的章節,多多少少有“違和”之嫌;他甚至把這些青年基層干部們常用的一個比喻“瓶子里的蒼蠅”——前途一片光明,卻不知出路——寫進了書里。他毫無顧忌,只是如實地記錄下他們的心態和所作所為,酒喝干,再斟滿,一場宿醉醒來之后仍然要面對像小鎮天氣一樣冷酷的現實。無論如何,人生道路上的決定是自己做出的,“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這正如他乘車在臨潭的盤山路上顛簸時得出的感悟:“一個個的拐彎,有著相同的樣貌,一個個的高坡,有著相似的坡度,看似很近的路,卻需要向相反的方向行駛,再迂回前行,如同人生。”所以,他抄沈從文《給志在寫作者》里的話自勉:“一個偉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種博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難,在極端貧困艱辛中,還能支持下去,且能組織理想(對未來的美麗而光明的合理社會理想)在篇章里,表現多數人在災難中心與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數人浸潤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輝里,能夠向上。”
在池溝村的兩年是無比艱苦的,當地流行的兩種“高原病”——痛風和膽結石,以及外人無法想象的酒風,都給濤哥的身體帶來了不小的傷害。他大學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青島,那是一個以啤酒著稱的海濱城市。他曾經多次向我們回憶自己當年在青島的生活:每天下班后在路邊用塑料袋打上兩斤鮮啤酒,回到宿舍以后喝啤酒吃蛤蜊,簡直就是神仙日子!然而,從高原回來的濤哥再也不能喝啤酒了。與身體的痛楚相比,心靈的折磨或許更為難熬,所以我才會在前文提到“因為有過住地下室、靠在院子里轉圈打發孤獨無聊時光的經歷,我才能對濤哥《山中歲月》里的那些細節感同身受”。“孤獨”大概是這本書里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在小鎮的日子里,我始終在學習如何獨處”,“在這段歲月中,我獲得了與孤獨和諧共處的能力”……剛到池溝村的濤哥,在斗室里“時常手插口袋低著頭來回踱步”,計算著從入門處的書柜到窗臺的距離,“正常六步走完,走得慢些則需八步”——我不知道他是否讀過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但這個細節像極了《二六七號牢房》那一章“從門口到窗戶七步,從窗戶到門口七步”的著名開頭。也許拿駐村與坐牢相類比太不合適,但是遠離北京、遠離單位甚至遠離文學,被拋到早已習慣的日常生活軌道之外,看人來人往,聽眾聲喧嘩,穿行于其中卻又與己無關,倘若沒有一點修為,是很難挨過這人生中的24個月的。書中有一篇題為《修道》,寫的是濤哥在村里修路的事情,但我總覺得他是一語雙關,修的不僅是現實中的“道路”,也是在修心中之“道”。時下流行“松弛感”,但是在飛速運轉的都市生活中,“松弛”往往是千金難買的奢侈;只有從固化的生活軌道中抽離,讓我們習以為常的精確、秩序、規則等一一退場,才能體驗到那種自由和不在乎時間觀念的“散漫”中難于人言的妙趣。在《“浪山”》中記錄了一個頗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濤哥和一個專門做羊肉的鄉間廚師“老穆薩”閑聊,在聊到一種叫“林自草”的、似乎只應該存在于《山海經》《搜神記》里的植物時,老穆薩的手機響了,有人找他回去。他一邊說著“就來了,就來了”的口頭禪,一邊掛斷了電話,跟濤哥繼續閑聊。直到對方等不及了,再次把電話打來,老穆薩才再一次說著“就來了”,怏怏離去。濤哥寫道:“我回到房間后看了一下表,在兩個‘就來了’之間,整整隔了一個小時,但是我卻第一次感受到‘一個小時’帶給我的一份莫名的復雜。”現如今,大概也只有在冶力關、在池溝KhvydmeY5rJXfJZhJnehY09K2H6A2AvGRGqeahHAVOw=村這樣遠離塵囂的地方,才會有像老穆薩這樣“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的“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存在吧。所以,濤哥才會將這種核桃樹下的“日漸松弛”視為生活的一種恩賜。我想,他真是把“道”修到家了。
以平常心看待駐村生活的艱辛,看待工作中種種不合理之處,以“理解之同情”去對待村里、鎮上的鄉親和同事們,在“量力而行,盡力而為”這八個字的微光引領下為村小建圖書室為村里修路、安裝路燈,不讓自己的激情被現實中的種種困難與無奈消磨干凈,這是濤哥駐村兩年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和精神財富。他做的事情絕非轟轟烈烈,卻件件都是實打實,這也印證了“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這塊獎牌質地的純正。
我想,這既是源于他血脈里流淌著的山東人的質樸血液,也與他曾經深入研究過山東籍文學評論家李長之的學術和心路歷程有很大的關系。李長之是山東東營利津人,是我的純老鄉;他幼年時隨父母遷居濟南,住在南護城河畔的司里街和南關一帶,也離我從小生活的地方咫尺之遙。我一直認為這位25歲時就寫出了《魯迅批判》的老鄉沒有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因此,當我偶然得知濤哥的碩士論文題目是《論李長之的評傳藝術——以歷史人物傳記為核心》時,我跟他開玩笑說,我要代表220萬東營人民感謝他。王富仁先生曾經評價說,李長之以一個普通人的心態,深入了魯迅的心靈,“像兩顆心靈接通了電路一樣”“迸發出思想的火花,有著不隔不離的特征”;而他研究李白,研究司馬遷,研究韓愈,都是采用“評傳”這種獨特的文體,頌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旗幟鮮明地踐行他所主張的“感情的批評主義”——以“跳入作者世界里,為作者的甘苦所澆灌的客觀化了的審美能力”,去“深入于詩人世界中的吟味”。所以,他寫《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是因為“在我的心目中,李白是有一個活潑潑的清楚的影子在那里的。把這一個活潑潑的影子寫下來,就是這本書”。他寫《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在初寫時,最不滿意的是關于李陵案的一章,誰知在重校時,我卻為這一章哭了,淚水一直模糊著我的眼”。因為在他看來,批評者要用作者的愛的情感來體驗愛,用作者的恨的情感來體驗恨,寫到司馬遷身陷李陵案,就像自己也被拘于囹圄一樣。“知人論世”“推己及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而要將文學批評立場推廣擴展為人生態度,則更是難上加難,可是濤哥做到了。他在《困境的氣息》里說:“我真切地覺得文章里的鄉村與農民既不僅僅是緬懷的載體,也不僅僅是批判的靶子,我們的文字應該是扎根鄉村這片土地生出來的燦爛之花,是懷著痛與愛、懷著敬畏的生發。”來小鎮之前,他知道他將會有很多的迷惘,也注定要帶著這些迷惘離開這里,但現在看來,他的大部分“迷惘”都已經因為“理解之同情”而煙消云散,就像等太陽出來,大地上、山腰上的白雪都會悄然融化,仿佛從未落過雪,只有墻角陰冷處的小塊積雪提醒自己它真的來過。
濤哥的文學評論文章并不多,我能想起的大多是他關于“城市文學”的看法。他曾經專文論述過的作者,例如張楚、喬葉、次仁羅布等,似乎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鄉土文學”作家。有趣的是,盡管駐村生活讓他“遠離文學”,但他仍然在《困境的氣息》里提到了海外華人作家陳謙的中篇小說《望斷南飛雁》,并且通過對作品的解讀得出結論:“在展示人生的困境方面,城市文學似乎比鄉土文學更全面而深入。”不知道那刻骨銘心的“生命中的二十四個月”是否會動搖他的觀念?他自己的困境、他身邊的干部和鄉民們的困境未必就會比城市人少多少,因此他在一篇關于“精準扶貧背景下鄉村書寫”的文章里簡短地復述了《芒拉鄉死亡事件》里的故事:“我曾親身經歷過一些類似的事件,有的農民因為扶貧點的建設占用了一點自己的耕地,在補償金的索要中獅子大開口,并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面前,寧愿損害大多數村民利益,也要得到不合理的補償,并且在欲望得不到滿足后持續上訪,強調自己的受侵害;有的村民因為生活條件明顯好轉后,享受的低保標準被降低,他就會在寒夜中將自己的父母扔至鄉鎮政府院內,不管不顧,揚長而去。母親過世后,又去大吵大鬧,索要賠償。”我想,倘若不是親自來到最基層的鄉村,接觸到最鮮活的鄉村生活,濤哥斷然不會見識到人生中會有如此的困境。正如那篇文章的題目——《寫什么與怎么寫——精準扶貧背景下鄉村書寫的兩個問題》——所糾結的,中國文學界已經為此爭論了一個多世紀,勢必還將繼續爭論下去。但是在我看來,當我們連“寫什么”都不能完全確定,以為自己在城市中、在辦公室里看到的就是生活的全部,就無從談起“怎么寫”。
拉拉雜雜寫了這么多,在結尾之處還要插播一個小花絮:2020年底,我剛接手《長篇小說選刊》不久,策劃將來年第二期定為“決戰決勝脫貧攻堅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專號,邀請濤哥為天津作家王松的脫貧攻堅題材作品《暖夏》寫一篇評論。彼時濤哥尚未榮獲“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而當刊物已經付梓,卻傳來了他將去人民大會堂受中央領導接見并領獎的消息。我當即決定將這一喜訊通過刊物微信公眾號向讀者傳播,并得寸進尺地要求濤哥除交稿之外,還要手寫一段扶貧工作感言,作為給讀者的“寄語”。于是,這則題為《喜報|我刊2021年第2期作者陳濤喜獲“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榮譽稱號》的推文便在網上廣為流傳。濤哥看到后給我打電話說:“你們起這樣的題目不太合適吧?”我反問他:“你是不是叫‘陳濤’?”答曰:“是。”我又問:“你是不是‘我刊2021年第2期作者’?”答曰:“是。”我再問:“你是不是獲得了‘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榮譽稱號?”答曰:“是。”于是,我哈哈大笑:“你懂得!”濤哥也無話可說。
花絮歸花絮,玩笑歸玩笑,但濤哥的那段感言,寫得真是情真意切。我要再次占用《南方文壇》寶貴的篇幅將其抄下,與大家共勉——
以個體微薄之力投身時代發展,親身經歷并見證這段奇跡與歷史,是一件幸運的事。在這段歲月中,我從未如此融入人群,也從未如此貼近自己的內心。很慶幸在自己的生命中有這樣一段刻骨銘心的時光,淬煉青春,磨礪品格,讓人生充滿愈發豐盈、遼闊的可能。
(宋嵩,《長篇小說選刊》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