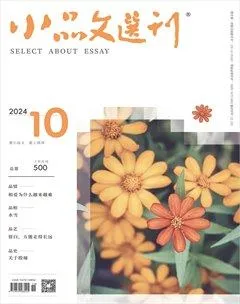陽光水暖好田螺
我有一次問石田叔:“田螺,是不是它走得慢,才做了人家盤中的好菜?”
石田叔揪了我的小鼻子,說:“小兔崽子,你是不是在拐著彎說你石田叔呀?”
我說我真的是講田螺哩,我們都好田螺!我狡黠地一笑。
田螺在我們家鄉太常見,太普通。在田里,在塘里,在小溪,在井沿……到處都能遇見,只要是個人,就是一個三歲娃娃,也隨手可取,不像一條活泥鰍,滑溜滑溜的,總是難以捉住。
所以在陽光把水照暖的時節,我們一幫小孩子總愛纏著石田叔帶我們去摸田螺。石田叔若有空,立馬說:“要得,跟我去撿。”說是撿,一點兒不假,石田叔選的地方,田螺多得是,齊腳踝深的水,白花花的陽光照得清楚,俯拾皆是。我記得我們收獲最大的一次是一頓飯的功夫,家里的腳盆堆成了一座小山。
田螺大如梨、橘,小如桃、李,人人可煮而食之。別看它外殼堅硬,內肉豐厚、柔軟而細滑。尤其吸起來的感覺極好,嗞溜一聲,肉直入嘴里。所以我現在吃起田螺來,便是這番真功夫,讓旁人稱羨。倒是我見旁人吃田螺時用牙簽一下一下地撬出來,既費事又殘忍。
關于田螺,石田叔最為詳熟。他不僅能把田螺煮出十二個花樣,讓誰都贊不絕口,而且是田螺到他手里,就有千百種用處千萬個妙方。譬如哪個眼睛痛,他立馬煮出田螺汁,取少許注眼中,那種漲痛感立馬便消。又如哪個久醉不醒,他去水中摸來田螺,加蔥、豉,煮汁灌下,即解。又如疔瘡惡腫,用田螺入冰片,化水點瘡上,不日就愈。還比如止瀉、小兒急驚風,田螺殼燒成灰,水灌服之即止。
當然,石田叔用田螺作藥用還有許多許多方子,我現在已記不得多少了。但是,石田叔用田螺殼做玩具,做樂器,我印象很深。特別是用田螺殼吹出的那首《梁祝》,我至今認為那是我一生中聽到的最好的旋律。
石田叔其實是讀過一點書的,在我們村子里應該算一個聰明人。但怪就怪在他并沒有成起一個家。其實,這怪不得那些乖態(湖南武岡洞口一帶的方言,指漂亮、美麗、好看)的女子,要怪只怪石田叔自己。任憑那些個乖態的女子走斷腳后跟,石田叔就一句話:要娶也得哥先娶!
他哥水田做什么都無勁,唯一是摸起紙牌來勁,不論忙季淡季,不論天光夜暗,不管呷,不管睡。他哥很難找到媳婦。但石田叔還是央不少媒人到處去說。也有很多人上門來看,卻總是來過一回,再沒來第二回了。
大約是石田叔賣了一欄豬的那年,他fiPX9CwsAFjPPvzqQp/9dQ==哥水田終于娶上了媳婦。娶上媳婦的水田叔仍然沒什么兩樣,做什么都無勁,唯一是摸起紙牌來勁。
石田叔人高馬大,田里地里,農活是一把好手,家務活也能抵得上一個女人。后來,他哥生了一兒兩女,他就更忙了。
這樣一忙一忙,就忙到了四十歲。四十歲那年的一天,他在耙田時,一向聽使喚的老牛忽然發瘋般地亂躥亂踢,踢中了石田叔的右腿。從此落下了腳疾,走起路來不利索了,但他還是緩緩地走在山川田野。
他哥一生從不勞累,也從不發病染疾,有一日竟安安靜靜地去了。
這時,石田叔卻和嫂子分了家。石田叔說侄兒侄女都大了,該是分家的時候了。有好心人勸,還分家?應該是你和你嫂子合家的時候了。石田叔曉得這個“合家”是另一層的意思,他第一次發了脾氣。
據說,這些年,石田叔一個人過得很孤單,常一個人拿起田螺殼吹曲子。
我想,明年清明回到鄉下,我一定要下塘摸些田螺,再用香樁樹葉和紅辣椒爆炒上一盤田螺肉,和石田叔喝上幾碗米酒。邊喝邊聽石田叔用田螺殼吹《梁祝》,聽他一生情感的訴說。
盡管我酒量不大,會喝高了,但是不打緊的,反正石田叔會用田螺給我解酒。
陽光水暖好田螺。我仿佛看到我們一幫光屁股的孩子,嘻嘻哈哈地,一個個下到齊腳踝深的水里,白花花的陽光晃得我們一臉一身……田螺是好東西,我們都好田螺,我們都愛石田叔!
選自《海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