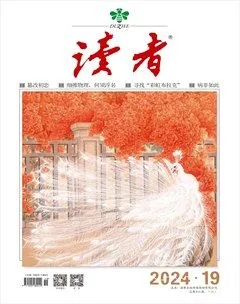從拔尖的陷阱到掌控的反噬

在今天,我們對“精英的傲慢”和“精致的利己主義”有許多檢討。與其用這些詞來批評年輕人,不如去看看背后造就這一現象的制度邏輯。
與此同時,教育的“成功學”現象或者被熱情追捧,或者被激烈批判,但我更愿意探尋這些成功學如何在教育場域里被制造出來,又如何侵蝕、改寫、異化著教育的實踐。
搶跑的代價
我們都愿意相信天賦異稟者存在,也樂意塑造神童。第一位出場的同學楊搶跑,就被視作神童。
3歲時,楊搶跑的媽媽就給她買了第一本字典,并教會她怎么查字典。4歲前,她學會了10以內的加減法,誤打誤撞做對了奧數題。小學二年級她開始系統學習奧數,三年級學習初中英語,五年級學習初中數學,六年級學習初二物理,在小升初的暑假背完了中考必背的古詩詞。
搶跑讓她能獲得很強的正向反饋,她嘗到了搶跑的甜頭。因為成績好,她深得老師的信任,獲得各種榮譽,甚至有批改同學作業的特權。
但是,領先的優勢是因為超常的學習能力,還是因為超前的學習節奏?
搶跑有甜頭,也有代價。初中畢業后,楊搶跑進入一所重點高中的實驗班。她發現,在高中,“搶一步、贏一路”不再是她個人的制勝秘訣。實驗班里的多數同學按下了超前學習的快進鍵。老師將學生已經學過一遍默認為基礎水平,會直接在課堂進行拔高與拓展訓練。校外培訓成了“生存”的必需——不提前學,很難跟上常規的學校課程進度。
楊搶跑們為什么普遍地超前學習?因為中小學正在經歷中國基礎教育的課程改革。
新世紀開始的第八次課程改革,出發點是學業減負,改變過去課程中繁難的知識傳授,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用學生自主學習替代老師的教授。老師從講臺上的知識的講解者,變成激發者、輔導者、各種能力和積極個性的培養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檢查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上。
這一改革背后是一套新自由主義的教育理念,是一套解放的邏輯,它建構了一個自主的學習者的意象——好像只要學校松綁,學生就會自主地學習。
學生看起來是在自主地學習,但是,校內減負與學業外包,自主學習與校外培訓,多元選擇與項目超市、成長賽道,構成了一個復雜的教育生態——學生在校外系統地學習知識,在校內輸出能力,體驗碾壓別人的快感。
這種復雜的教育生態背后是名校壟斷。一個學生的成就取決于學校所擁有的資源:賽道是否多元?學生有無在競賽中獲獎?對考試規則是否熟悉?其中,教育中最優質的資源其實是那些拔尖的學生。
有拔尖就有掐尖,學生考試的名次與學校的排名直接對應,學校究竟是在對人進行增值培養,還是僅僅完成了對學生的精準篩選與簡單分層?
此外,課程改革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以前老師是依據教學大綱教知識,而現在老師教學的效果要用學生的學習行為和可表現的能力來衡量。因此,評價體系變得非常重要。
從學業評鑒到指標記錄、發展診斷,再到自我診斷、自我表現鑒定,評價體系不斷迭代優化。“以學生為中心”的自主學習本來是很開放的,卻被套上了嚴格的行為指標的鐵格,形成一個控制細密的指標迷宮,學生在指標迷宮里不斷打卡通關。
學校成了優績主義的實驗場。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學生會有怎樣的心理感受?他們今天的脆弱或者孤獨,是否與此有關?
套路的秘籍與代價
著名數學家陳省身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的題詞是:“不要考第一。”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清時對這句話的理解是,原生態的孩子一般考試就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到100分,需要付出好幾倍的努力,訓練得非常熟練才能不出小錯。要爭這100分,就需要浪費很多時間和資源,相當于要給土地施10遍化肥,最后孩子的創造性都被磨滅了。
為什么學生提不出好問題?因為他們在不斷地練習某種套路。
最早進入套路的是老師。套路的實質就是老師把一些思考型的工作拆解成操作型的知識,將復雜的工作不斷地標準化和程序化,再編成相關的學案和套路,讓學生大量刷題。其背后是泰勒教學模式的盛行。
泰勒模式不要求勞動者具備基本的智力,但是需要其有忍受單調工作的意志。泰勒教學模式源于泰勒模式,也是通過細致的分工,把復雜的知識分解成最小和最簡單的部分,再嫻熟地連接起來,保證攝入知識的速度與準確性。
一個學生告訴我:“尋找標準答案是我在高考以前的人生階段的主要矛盾,為此我可以從早上7點端坐到晚上11點,在做題總結和反思的流程中無限循環。”
他相信一切都有標準答案,都有一個最優解。因為考試總有標準答案,所以沒必要去質疑老師講的結論。他也變得害怕不確定的結果,因為不確定的結果就意味著考試的分數可能會更低,這讓他條件反射地心理恐懼。
可是,不確定、瑕疵正意味著新知識和新經驗生長的可能性。
因此,這一群中國基礎教育生產出的最優秀的學生,其中很多人逐漸喪失了對復雜世界的認識能力——世界對他們而言,只有對和錯、是與非。因此,他們也失去了直面真實世界的能力。
一場自我監控的學習
這群最優秀的學生進入大學后,有些人就陷入了一個“忙、茫、盲”的囚徒困境,彼此之間展開了逐底競爭。
他們被困于“茫”——外部目標缺失,內在價值虛無。于是,他們用群體性的“盲”來回避內在的茫然,又用競爭性的“忙”來提升標準,不愿也不敢正視自己獨有的使命。
在經典的大學理論里,大學是一個人的自我教育時代的開始。從高中到大學,一個人需要茫然又自主地探究,通過知識和學科打開一個“小我”,走向一個更大的世界。同時,他們要和身邊不同的人打交道,閱讀不同的心靈,建立一些可信任的穩定的關系。通過自身的理性和力量駕馭動蕩的人生,不斷地塑造內在生活,形成自己的準則和風格,在一個更大的世界讓自己的內在精神變得更充盈。
可是我們今天的自主教育,更像一種自我調控、自我監控的學習。自我監控的學習意味著學生要知道評價標準是什么,針對這個目標制訂計劃,去看自己和目標之間的差距是什么,要實施什么樣的策略縮小差距,檢查與評價實施結果是否符合計劃,改進不符合計劃的部分,再針對特定情況提出一個新的計劃和新的目標……如此周期性地循環。他們不斷地評價自己的能力,走向一個看似高效能的狀態。
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眼睛始終沒有看向外在的世界。真實的世界中常有斑駁的光影、模糊的色調,他們自幼被訓練習慣于去追求明晰、可達成的目標,來提升自我效能感。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學生,習慣于目標明確、規則清晰的生活。今天,他們離開了一切都清晰、確定的目標鐵格,來到了奔涌的水流里,不知道該怎么辦。
獵手的抉擇
這也是為什么今天的學生如此在意評價和考試。在他們看來,評價構成了目標本身。因為他們從小熟悉的就是學業評價、綜合素質的測評,要清楚地知道賽道,不斷地對標別人,一路打卡通關。評價制度不僅影響著學生的日常學習和生活,還塑造了他們基本的習慣和性情。
一個很聰明的學生說,在大學里,非常重要的是學會學習,策略比知識更重要。做題家總是揣摩出題人的心思,我們要從做題家變成命題者。
穩妥的策略是,成為一個全能型人才,每個部分都要做得最好。那如何做到呢?
這需要一種高階能力,需要的是一種“超注意力”,在多重任務、多個信息來源和多個工作程序之間不斷地轉換焦點,而不是進入一件具體的事情中去。
這種高階能力非常強調靈活性,也就意味著人要機動,要隨時離開,隨時重組。它與專注無緣,具備這樣能力的人不會為一件事情著迷,對任何事情都是沒有差別的投入。
因此,今天更多的學生變成了“獵手”。獵手既要追蹤獵物,也要警惕四周,還要監控自己,更要出手果斷迅速。因此,他們講適應性,適應性讓他們變得非常靈敏和機警。
他們不能深度投入,在人和事之間都要強調邊界,輾轉于得失之間。他們對獵物的熱情有限,選定的獵物是精心算計過的,是可置換的對象。獵物可以是績點,也可以是學分,還可以是賽事與證書。因此,他們要把自己訓練成一個靈巧的元素,以便隨時自由地嵌入,又能輕易地脫嵌、移動。于是,他們采用一種“選而不擇”的策略,這也讓他們陷入選擇的悖論。
而人的真正成長需要一種否定性的力量。選擇意味著選擇完成后的承諾、付出和責任、契約。選擇作為一種生命實踐,正需要“有所不為”的內在堅定性,“有所不為”恰是“終有所為”的前提。你只有有所舍棄,才可能真正獲得一些東西。
這也影響了他們與人的關系。這一代人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搭子——飯搭子、酒搭子、運動搭子……他們只在某件具體的事情上共事,不是朋友,彼此之間不再是深刻的、持久的、信任的關系。
一位教育學教授這樣描述他們的狀態:“所有的人都是橋,可以幫助他們過河的橋。老話說‘過河拆橋’,而現在都不存在拆橋。他人的橋都可以是浮橋,一只腳踏上去,另一只腳又離開。”
“高效掌控”的反噬
另外一個同學,我把他稱為達,因為他總是能達到目標。達是高效掌控管道中的高手,掌控塑造了他日常生活中的習慣,讓他活成了一臺高效且封閉的機器。一旦離開這個管道,他的生活也將隨之崩塌。
達說:“其實在成長過程中我一直在升級打怪,升級打怪本身就非常刺激。你一定要問我意義,這個意義會讓我困惑,它會逼迫我去想,我到底要做什么,這讓我很惶恐。”
達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最優解。他沒有談過戀愛,因為他沒時間,他說:“愛情常常是不受控制的事情,但我要做的是控制我自己。”
他將日常生活理性化的能力超強,內心很少起波瀾,很少受到觸動,甚至逐漸失去了對生活的感覺。沒有人可以進入他的內心,他將自己完全封閉了起來。
自我負責的陷阱
像達一樣的獵手成長于一個真實的制度空間,在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下,他們被要求對自己的學習結果高度負責,這一能力關系到他們未來的職業素養、工作能力,乃至在一個快速變動的世界中的可遷移能力以及終身學習的能力:置身奔涌的潮汐中,如何掌控自己,成為不敗的“弄潮兒”。
非常有意思的是,整個世界也發生了這樣的變化。
很多年前,X一代(出生于1964—1975年的人)從科層制的機構里走出來,享受著流動的好處,他們不愿意也不想追求終身制的工作,但渴望終身學習。但是,到了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紀,在21世紀初成年的一代人),我們看到,他們的獨立變成了漂移,對穩定重復的工作的感受從無聊變成不斷的焦慮。而且他們非常強調彈性。彈性背后是能伸能縮,能夠不斷地適應不同的機構、不同的文化。這種適應要求你像變色龍一樣。更為關鍵的是,你不需要有內在的原則、內在的堅持。
我們還會看到“斜杠青年”的流行,在多重經驗背后,他們不斷地進行自我塑造、自我定義,面目模糊。在自律與自我塑造中,這些和潮汐一起奔流的弄潮兒,常常通往深深的倦怠。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獵手,他們的眼睛被訓練得既靈敏又盲,他們永遠把目光盯著目標,對其他東西視而不見。他們看不到更大的世界。他們輾轉于得失之間,奔波于動蕩和風險之間,直到他們的獵手生涯終結,或者自己成為一個獵物。
他們在一個孤零零的自我頭腦里面,構建了一個高度形式化且體系化的全球定位系統,砍斷了一切聯系。這個定位系統把他們拉向遠方,把他們和身邊具體的他人、近處的世界完全割裂。
那么他們到底是離世界更近,還是更遠?
(哈哈鏡摘自微信公眾號“一席”,本刊節選,勾 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