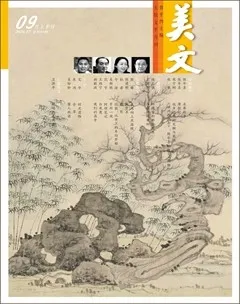手電筒【時光遺物】
2024-09-06 00:00:00艾華
美文
2024年17期
呲的一聲,火柴劃燃,一雙手捧著火苗移向一根煙。但煙躲開了,叼煙的嘴吹滅火苗,黑暗中有話冒出來:
“先給艾華點。”
呲一聲,火柴又劃燃了,火苗湊過來。我把煙塞到嘴里,對準火苗吸燃,忍不住咳嗽起來。
“Sorry!慚愧!”
火苗晃熄。我已咳完,聞到一絲松木的清香,吸吸鼻子,煙草和火藥的味道有濃有淡。
“鼻子通了吧?”
“通了。”
1979年,小鎮夏夜,是一支煙治好了我的感冒。我第一次抽煙,給我煙的是“長發彭健”。給我點煙的是彭春,大我一歲。彭春喜歡把剛學的英文掛嘴上,緊接中文,比如“Sorry”加“慚愧”,比如“Spring 彭”。夏天了,彭春又突然給自己改了名:
“夏季我就叫Summer 彭。”
抽完煙,三人走到變壓器圍墻邊,都抬頭看電桿上的路燈,看赴火的飛蛾。看得無聊了,就跟往常一樣翻進圍墻,單腿落地,是為了防備變壓器有電漏至地面。我歇口氣,然后單腿順時針跳半圈,扶著墻聽一會兒變壓器的噪音。
“嗡嗡嗡的。”唐西兮每次都說,“好多蜜蜂!”
她的聲音被蜂鳴吞沒,再也不會響起。彭春跟我一樣聽一會兒,迅速換條腿,順時針再跳半圈。彭健這回沒有扶墻,也沒有換腿,一口氣跳完一圈,翻墻出去了。
等我最后一個翻出來,三人就坐在圍墻的陰影里,屁股下是周瞎子擺攤用的磚頭,多出的一塊從前是屬于唐西兮的。
春天變成夏天,唐西兮回到童話里去了。鎮上的人再也看不到她踮腳走路,也看不到她坐在彭健的單車上。她不是坐三角架橫杠,就是反身坐后座,坐姿叫人看不順眼,后來慢慢看習慣了,也就習慣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