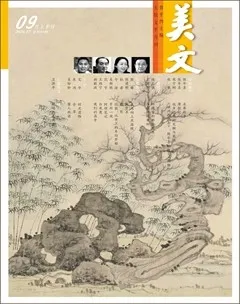阿壩筆記
雨落草原空
從紅原醒來,輕盈的雨,落在窗外無垠的草原上,一片蒼茫。
摸黑來到紅原時,星光下的草原,早已進入夢鄉。我們在縣城與草原的邊界線附近,隨意找了一家旅店住下,說好次日清晨早起看草原升紅日的盛景。誰承想,滿天的星光里竟藏著幾朵不安分的烏云,它們于夜深人靜時分悄然結成了聯盟,要在黎明抵達之前醞釀一片云雨。
心里不免生出幾分失落。
不能在草原與朝霞構筑的夢里醒來也就罷了,還要和潛意識里天高云淡的草原擦肩而過,雨中的涼意就一陣陣涌上心頭。在丘區簡陽長大的我,從沒有真實地置身過草原,電視和網絡上的構圖,詩詞和歌曲里的吟唱,構成了我對草原的全部想象。天該是藍的,云該是淡的,草該是青的,牛羊該是散淡的,牧人該是奔放的,從未想過清新明麗的草原闖入一陣朦朧煙雨,會是怎樣一番光景。
按計劃,我們要在紅原縣城周邊的草原上牛羊作伴、騎馬馳騁,感受天地的遼遠與歷史的壯闊。這一場雨半點要停的意思也沒有,我們只好把九曲黃河第一灣的日程提前。然而有些醉心的風景,有些難忘的故事,總是在計劃之外,闖進我們的生命。
公路在廣袤的草原伸向遠方,好似在宣紙上拉了長長一筆,那青青的草原就是大片的留白,那若有似無的煙雨就是淡淡的墨痕,簡單幾筆的潑墨畫境卻給人以無限的遐想。驅車在雨霧籠罩的草原上,腦海里突然蹦出一個字來——“空”。空空如也的“空”,空山不見人的“空”。沒有流動風景的草原是空的,成群結隊的牛羊在低洼處躲雨,牧民也回到帳篷喝起了青稞酒,只有那些雨滴不停地敲打著車窗。心仿佛也是空的。妻子把頭靠在車門上打起了盹,而我則懶心無常地踩著油門、聽著老歌,只有女兒伊伊不停地擦著車窗上的霧氣,好奇地打量著窗外的一切。
蘇軾寫過一種“空”,是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空”。在他的眼里,“水光瀲滟”是極致之美,“山色空蒙”也別有一番韻味,反倒成全了“淡妝濃抹總相宜”的千古絕唱。生長在阿壩的藏族作家阿來也寫過一種“空”,是長篇小說《空山》里的“空”,是古老村落在歷史山谷中久久回蕩的“空”。在伊伊的世界里,這草原的“空”,是否也是水墨暈染開來的幽遠古意,亦或是歷史長河響起的文明回聲呢?年僅三歲的伊伊沒有過多的聯想,也沒有落入俗套的標準審美,只在幼小的心靈上一遍遍著上煙雨草原的原始底色。
或許,此時此景的草原,將成為一種干凈而純粹的意識,潛藏在腦海,交匯在血液,成為伊伊一生的詩意源泉。
雨漸漸小了,風在草原上吹著。慢慢有牛羊闖入我們的視線,有的埋頭吃草,有的低頭喝水,有的打量遠方,有的成群遷徙。“快看,羊群!”妻子從睡夢中醒來,惺忪的雙眼瞬間充滿神光,不停地搜索著羊群的蹤跡。空空的草原,終于有了一些流動的風景,這讓人瞬間來了精神,飄蕩在車內的旋律似乎也悠揚起來。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當伊伊突然背誦出北朝的民歌時,我猛地一怔——年幼的伊伊,背誦過《敕勒歌》,但歌中景、詞中意未必能深刻領會,那么她是怎樣做到見景生情的,又是怎樣做到精準抒發的呢?
我從后視鏡分明看到妻子的臉上難掩激動,緊緊地把伊伊抱在懷中,不停地撫摸她的頭發,親吻她的臉頰。我甚至看到妻子的眼中。有些熱淚在打轉,渾身上下都散發著一位母親對孩子的深情溫度。人與人、人與萬物之間的情感聯系,有時用不著過多地詮釋與解讀,它往往在歲月沉淀抵達之前最自然地流露在某個美好的瞬間,最終定格成人生最可貴最恒久的記憶。
我們在長大的過程中,天真慢慢被侵蝕,感知漸漸被風化,往往偏執地認為最好的風景是外化的內心,而非內化的山川。面對雨中的草原,我和妻子發現、感知和抒發美的功能,都遠不如伊伊,似乎我們早已失去了欣賞“空山新雨后”“清泉石上流”的那份閑適與恬淡,難以抖落身上的塵埃。
日常里,妻子喜歡擺弄花草,剛開始在陽臺上放了幾盆君子蘭、紅掌、綠蘿,錯落有致,十分愜意。可后來,妻子不斷添置各類花草,直到把陽臺塞得滿滿當當的,原本養花的意境也就全然沒有了。我以中國畫講究留白來營造氣韻和靈動給妻子打過比方,倘若陽臺是一張中國畫,是否也該為它適當留白,讓我們的生活多一點空間和意境呢?當然,更多的時候,我們意識不到“空”的詩意與悠遠,反而不停地用各種喜歡或不喜歡的事物來填滿我們小小的心房,以至于有一天不堪重負,活脫脫變成一個成天抱怨的“怨婦”。
或許,曾經的我們也和伊伊一樣,空得像一張白紙,世間萬物輕輕一落筆,都是最美好最動人的湖光山色。站在彼岸的我們,多么希望,成長的風浪不要無情地摧毀伊伊內心純粹的堡壘,讓她這一生,都擁有雨落草原的這份空。
雨落草原空,空出一首詩,空出一幅畫,空出一份美,也空出一份愿,無疑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
永恒阿媽樹
在四姑娘山,最讓我感到震撼的不是連綿的山、秀美的景,也不是雪山下古老美麗的傳說,而是那些不知在某年某月某天枯掉的樹。它們或在刺骨的雪水中靜默屹立,或倒在路邊抽出了新枝,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山上,被郁郁蔥蔥的森林包圍,反而成為一道直抵人心的生命風景。
我是在上山的路邊發現這些枯樹的,盡管景區專門為它們立了說明牌,但在一棵棵參天的樹和一叢叢茂密的草構成的浩瀚林海中,它們仍然顯得形單影只、聲希味淡。絡繹不絕的游客從它們身旁經過,有的漫不經心地瞄了兩眼,有的則完全沒有留意到它們的存在,很少有人駐足打量,仿佛與一棵棵枯掉的樹對視,毫無視覺上的美感可言,更無現實選擇的內心沖動。面對遠道而來的客人們,它們似乎早已習以為常,以格外自我的姿態保持著一份獨有的矜持。只有真正停下來走近它們,聆聽它們內心獨白的人們,才有可能從千年時光的積淀中發現美的存在,讀懂生命的頑強與偉大,領悟到內外明澈的愛的輪回。
幸好,我在滿目蒼翠中發現了它們。
幸好,我在亦步亦趨的人群中停下了腳步。
或許,它們是在千百年前的某個風雪天里倒下的,清脆的嘎吱聲,在空曠的大山里并未引起冬眠動物們的驚覺。很快,積雪將它們嚴嚴實實地覆蓋起來,仿佛誰也不知道,白茫茫的一片之下,還有幾棵惶恐的枯樹期待著來年的陽光。春暖花開時,積雪慢慢融化,它們重新探出腦袋,伸了個懶腰,仔細打量著周遭的一切,鄰家的樹、鄰家的草、鄰家的花及熟悉的動物朋友們,正在陽光下迸發出朝氣蓬勃的生命活力。這時,它們才猛然間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已經干枯,風華早已不在。在鄰居和朋友們眼中,它們已是風燭殘年,哪怕一陣風過,都隨時可能嗚呼哀哉。
坍塌的生命,將就此終結了么?
“不!”它們用微弱的氣息講出這個“不”字時,卻十分鏗鏘,目光中是歷經千年風霜雨雪的篤定。這份篤定來自極端氣候條件和惡劣生存環境中的千年淬煉。正因為有這份篤定,今時今日,我們才有幸在陽光與雨水交織的季節里,看到枯樹干上抽出一根根新枝,孕育出一簇簇希望。
想到這里,我不由得對它們生出幾分敬畏來。越是敬畏,越讓我無法挪動腳步,越讓我抱以生命思考走近它們,面對它們,甚至嘗試著讀懂它們。枯掉的樹干無序地橫亙著,新長出來的枝條早已在它們熟悉的陽光下,構成一派枝繁葉茂的新氣象。枯榮之間,仿佛向有緣人傳遞著生生不息的生命啟示,又像是對天與地訴說著天道輪回的生命哲學。
它們在歷史縫隙間的低吟淺唱,正好被我聽見了。
在景區所立的說明牌上,它們有個好聽的名字——阿媽樹。我毫不掩飾對這個名字的喜歡,并不僅僅是因為好聽,而是因為它十分貼切地對枯榮之間體現的生命之偉大進行了深刻而凝練的詮釋。我內心的這點歡喜,從說明牌上書寫著的這樣一句話,似乎也不難看出端倪——“力竭干枯之際,用殘存的生命力托起無數個新生命,深根連枯干,枯干育幼枝,把偉大的母親形象體現得淋漓盡致。”
對此,我深以為然。那些枯掉的樹,就像是一個個行將就木的阿媽,往往在面對來日方長的孩子時,它們總恨不得將自己身上僅存的一點燭火燃燒殆盡,以此照亮孩子的前路,心底多么希望孩子不曾在每一個人生的三岔路口迷失方向。阿媽樹,其實映照的是作為孩子的我們與父母之間的生命傳承,折射的是作為父母的我們與孩子之間的生命許諾。當我們讀懂了阿媽樹,也就讀懂了我們自己的人生。人生如樹,枯榮之間,盡顯愛與偉大。
佇立在阿媽樹前,我想起了詩人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詩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那些枯掉的樹不正是詩中的“落紅”么?那些新綠的枝條不正是詩中的“花”么?或許,有一天,枯掉的樹干也會在歲月的風化中徹底腐爛,化作一堆堆黑褐色的泥土,但它們的生命卻并未因此終結,那些枯樹上的枝條早已茁壯成長,并將根深深地扎進腳下的土地,從此踏上了阿媽曾經走過的漫漫人生路。生命不就是在這樣周而復始的傳承中,走向堅韌,走向偉大,走向永恒的么?!
阿媽樹,為了傳承,將生命的戰線無限拉長。而我們,則同樣為了傳承,盡情燃燒著生命的燭火。終有一天,我們會在另一個世界與那些阿媽樹相遇,那時,似曾相識的我們與它們相視一笑,揮手致意,彼此道一聲“阿媽”。
這聲“阿媽”,讓生命繼續走向永恒。
云上蘿卜寨
云在天邊,時而定格成夢里的樣子,時而在湛藍色的綢布上緩緩移動。蘿卜寨就在云上,它是云朵上的街市。我們行駛在一圈又一圈的盤山公路上,向著天邊的云朵駛去,向著夢里的蘿卜寨駛去。
云仍在天邊,蘿卜寨已在眼前。
寨門口三兩羌族阿媽支著售貨攤,叫賣著具有濃郁羌文化元素的小飾品、服飾、布鞋、墊底等小商品,手頭也沒有閑著,一針一線地繡著花或納著鞋底。在她們溝壑縱深的臉上,烙著深深的歲月痕跡,可當她們把笑容送給初來乍到的我們時,歲月在她們眼中卻又如此云淡風輕。千年時光流轉,一個民族的豁達,仿佛能夠愈合所有曾經撕裂的傷口。至少,在她們樸素的笑臉上,我洞見的不僅是歷史的厚重與滄桑,更是災難過后的堅韌與豁達。
沿著斑駁的泥墻,走在狹長的巷道中,隨處可見橫生的野草和朽掉的木門。尋跡于此的游客們談論著這里的過往,感嘆著眼前的光景,無不為一個民族的傷口、一個寨子的命運感到疼痛與惋惜。輕輕推開一道門,吱吱呀呀的聲響在耳邊回蕩,眼前是七零八落的廢墟,廢墟之上生長著野草與野樹,有些樹已經高過了院墻,郁郁蔥蔥,向陽而生。每一陣風過,眼前的野草與野樹都向我們揮手致意,仿佛向我們訴說著一個關于生死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折射著生命的頑強與生活的智慧。
廢墟是毀滅,是葬送,是訣別,也是選擇。解讀眼前這些廢墟,不得不將時間的指針撥回到十多年前的200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地震,打破了蘿卜寨的寧靜,一間間房屋在搖晃中坍塌,一個個生命在廢墟中消失,一個個美夢在剎那間破碎。蘿卜寨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黃泥羌寨,大約三四千年前就有人類活動的痕跡。一個歷史如此久遠、文化如此厚重、特色如此鮮明的古寨,就這樣在猝不及防中倒下了,倒在一簇簇熟悉的云中。蘿卜寨離震中僅5公里,這樣的毀滅性打擊,對一座千年古寨而言,是不可逆的。
廢墟成了蘿卜寨千年時光的終點。
向陽而生的野草、野樹,卻是羌寨人下一個千年時光的起點。
穿過一片廢墟,向東眺望,一片全新的寨落是汶川大地震后重建的蘿卜寨。寨子里幸存下來的人們,大多都搬到了新寨生活,在那里他們重新建立起生活秩序、生活習慣,以及對未來生活的信心。時間無法在廢墟之上重構坍塌的古老寨落,卻能在撕裂的傷口上撫慰受傷的心靈。藍天之下,白云朵朵,日子就像十多年前一樣平靜,羌寨人在習以為常中堅守著千年文化的固執,也適應著全新時代的潮流。
這是一個古老民族的現代生存哲學。
站在岷江大峽谷之巔,舊寨與新寨在回望與眺望中形成極大的反差,心靈的羅盤在這里感應強烈。一片廢墟就是地理之上的一段歷史,一片新寨就是走向未來的一段征程。這些年,廢墟之上開始有一些修繕的痕跡,羌寨人試圖還原一些過往的生存跡象,給廢墟重新注入文明的重量。對此,我喜聞樂見。期待有一天,羌寨人能在這里摸索到回家的路,而作為過客的我們也能在這里找到更愿意憑吊的理由。
古寨與新寨周圍生長著難以計數的車厘子樹,枝繁葉茂,枝葉間長滿了青綠色的車厘子。綠色象征著生命,象征著希望。凝視著漫山的車厘子,就像看到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它們向著陽光瘋狂生長,向著成熟勇敢前行,周而復始。羌寨人說,再過個把月,這些“大櫻桃”就成熟了,歡迎屆時再來做客品嘗。羌寨人,把車厘子喚作“大櫻桃”,從他們口中說出來,仿佛自帶著一份甜蜜、一份珍視。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道,一定再來。
這是蘿卜寨強大的生命磁場帶給我深深的心靈召喚,讓我無法抗拒。
陽光西斜,天空湛藍,白云飄飄。我們從蘿卜寨驅車離開,下山的路輕松了許多,心情像天上的云一樣輕盈。當我們重新來到山下,再回首蘿卜寨時,古老的寨子又回到了藍天白云之間。那些隨風變幻的云朵,仿佛堆積成一只飛天的鳳凰,騰飛在蘿卜寨,歌頌著一段浴火重生的傳奇。
后來我才知道,蘿卜寨又叫鳳凰寨。不錯的,蘿卜寨就是一只云上的鳳凰,演繹著一段浴火的悲壯故事,也昭示著一個涅槃的深刻寓言。
(責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