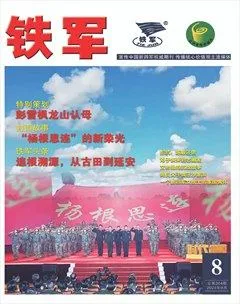八一吟唱《媽媽的吻》
八一建軍節來臨,耳畔又響起了那首熟悉的歌:“媽媽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每每吟唱這柔情似水的歌曲,記憶中的那位白發蒼蒼的大媽總會從云端輕步走來。
大媽的獨生子從郭村參加新四軍后到了江蘇鹽城。新中國成立不久后,他又去了朝鮮。最后在那年八一的黎明時分,他倒在了異國他鄉的炮火硝煙中。
“在那遙遠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親愛的媽媽/已白發鬢鬢/過去的時光難忘懷,難忘懷……”歌聲中,鄉親們在訴說,大媽是個苦命女人,幼時沒了父母,做了夫家的童養媳。幸虧男人對她好,幾年后有了一個兒子,生活雖然清苦卻也滿足。不承想,日軍進了泰州城,大媽的男人被抓去修工事,因策動集體逃跑被日軍一刺刀捅死了。噩耗傳來,滿身血性的兒子氣得咬破舌頭,手指沾血在墻上寫下“報仇”二字,留下一句“我要當新四軍”,話音未落便沖出家門。大媽踮著小腳追上去一把抱住愛子,吻干他沾血的食指,又吻干他滴血的嘴角。最后,大媽雙手托著兒子腮幫子好一陣端詳,一字一頓地叮囑:“兒啊,去吧,殺敵,報仇!”兒走了,媽哭了。從此,夜深人靜時,孤苦伶仃的大媽經常獨自翻看兒子留下的衣物,一件一件地吻過。她在尋找衣物上兒子的體味,排解母親內心思兒的惆悵。
“媽媽曾給我多少吻,多少吻/吻干我臉上的淚花/溫暖我那幼小的心……”歌聲中,鄉親們告訴我,大媽的兒子不僅是個英雄,還是一個孝子。兒子打仗不怕死,立功喜報曾讓大媽笑逐顏開。新中國成立后,已是連隊指導員的兒子來信說很快回家探望母親。那一刻,大媽高興得熱淚盈眶地吻著兒子的書信,仿佛愛子到了眼前。可是,不久之后的一天,大媽等來了兒子跨過鴨綠江的消息。大媽信佛,從此天天焚香祈禱,讓上天保佑兒子和所有的志愿軍戰士都能平安歸來。
“遙望家鄉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可愛的小燕子,可回了家門……”大媽仿佛在歌聲中泣訴。她沒有等來可愛的兒子,等來的卻是政府送上門的一紙烈士證明書。那一天,大媽顫抖著雙手接過裝有烈士證明書的玻璃匾,突然間跪伏在地,把那冷冰冰的玻璃吻了個遍,淚水順著口水,把玻璃匾弄得濕乎乎的。那情那景催人淚下,在場的鄉親哭了,連政府來人也流淚了。政府的人走了以后,大媽把這塊玻璃匾擺上家神柜,天天燒香,日日親吻,直至終老。
《媽媽的吻》的歌聲原本是甜蜜的,可聯想到大媽的遭遇,心頭卻平添了不盡的傷感。哎,兒子和那些來不及與母親告別便慷慨赴死的烈士們,永遠沒機會也不可能為母親擦干思兒的淚珠了。
戰場上,倒下多少干部戰士,就有多少默默流淚的母親;陵園里,矗立起多少烈士墓碑,就有多少無法侍母奉親的赤子遺憾。作為生活在烈士用熱血換來的歲月靜好時代里的人們,有責任有義務用一顆感恩之心去吻干烈士母親思兒的淚花,讓她們重獲兒女的孝敬與關懷。
黨的十八大以后,“讓軍人成為全社會尊崇的職業”已成為新時代的實踐要求。今年這個八一,再度吟唱《媽媽的吻》,我們曾經的傷感已被信心替代,相信不久的將來,擁軍優屬將有更好的制度保障。
軍人甘愿犧牲與奉獻,是“為了母親的微笑”。一個敬仰英雄的民族,一個尊崇軍人的國家,必然擁有一支所向披靡、戰無不勝的軍隊;一支受到社會尊崇的軍隊,定能擔當起護國佑民的神圣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