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變音的合音后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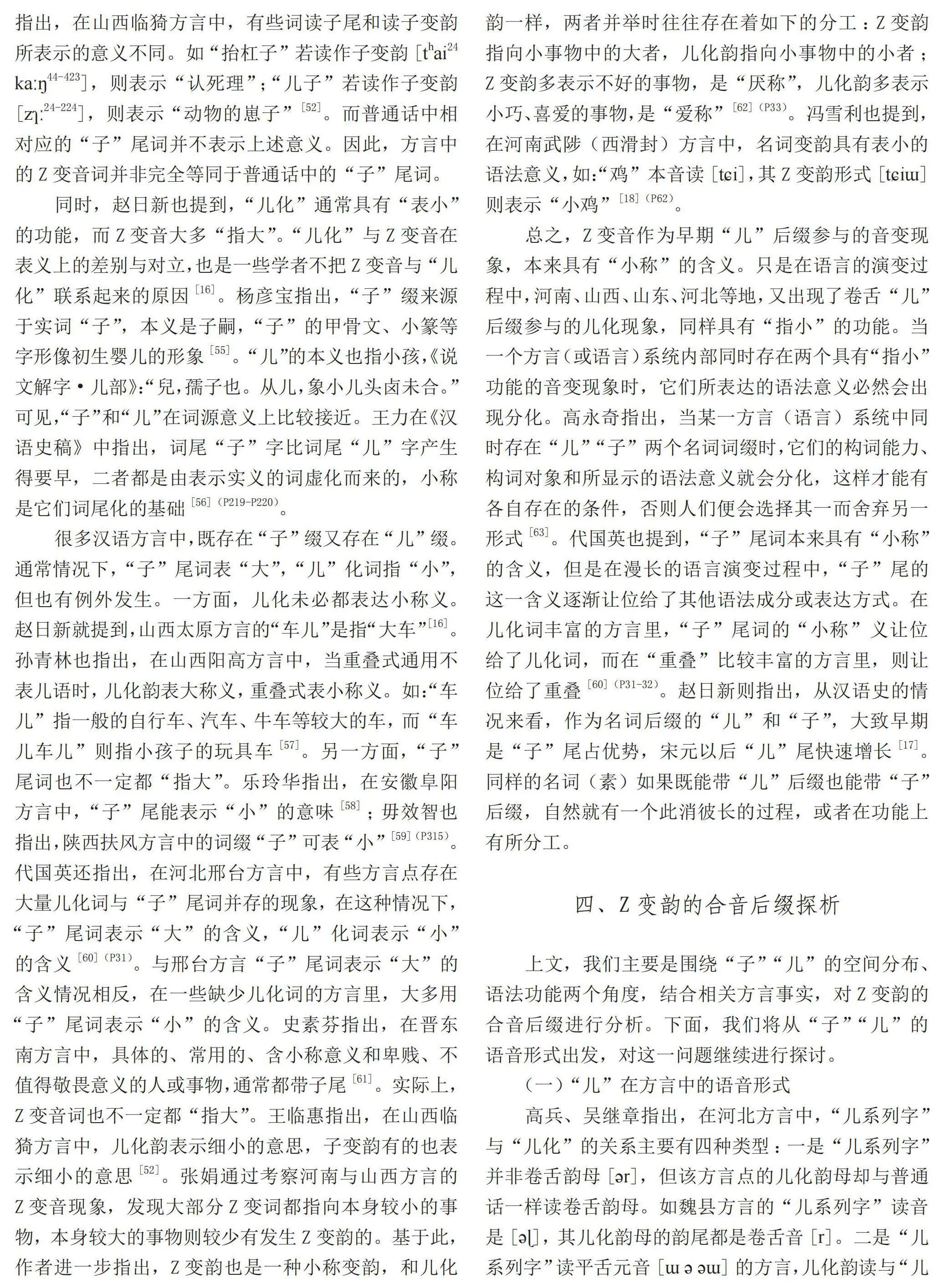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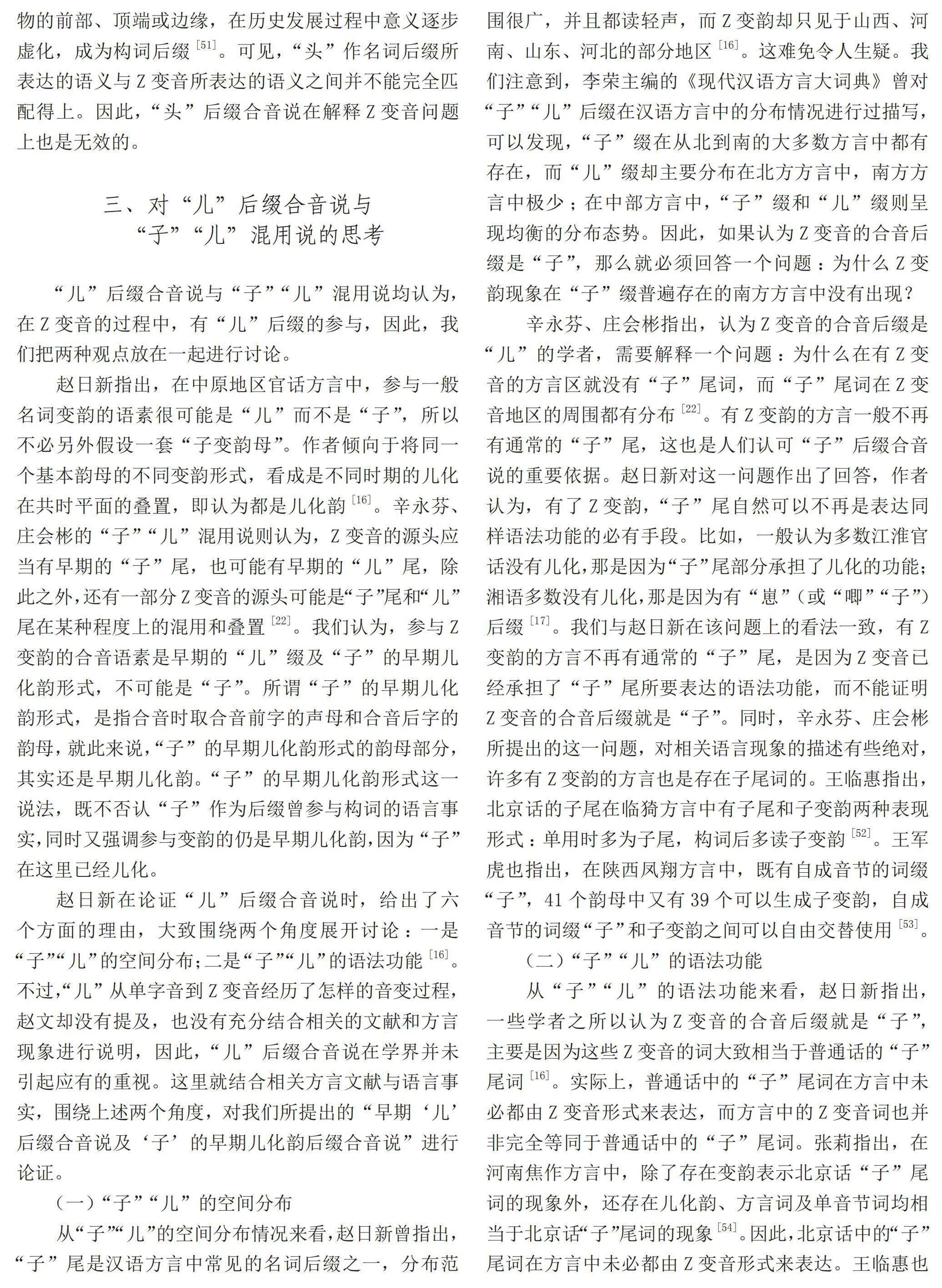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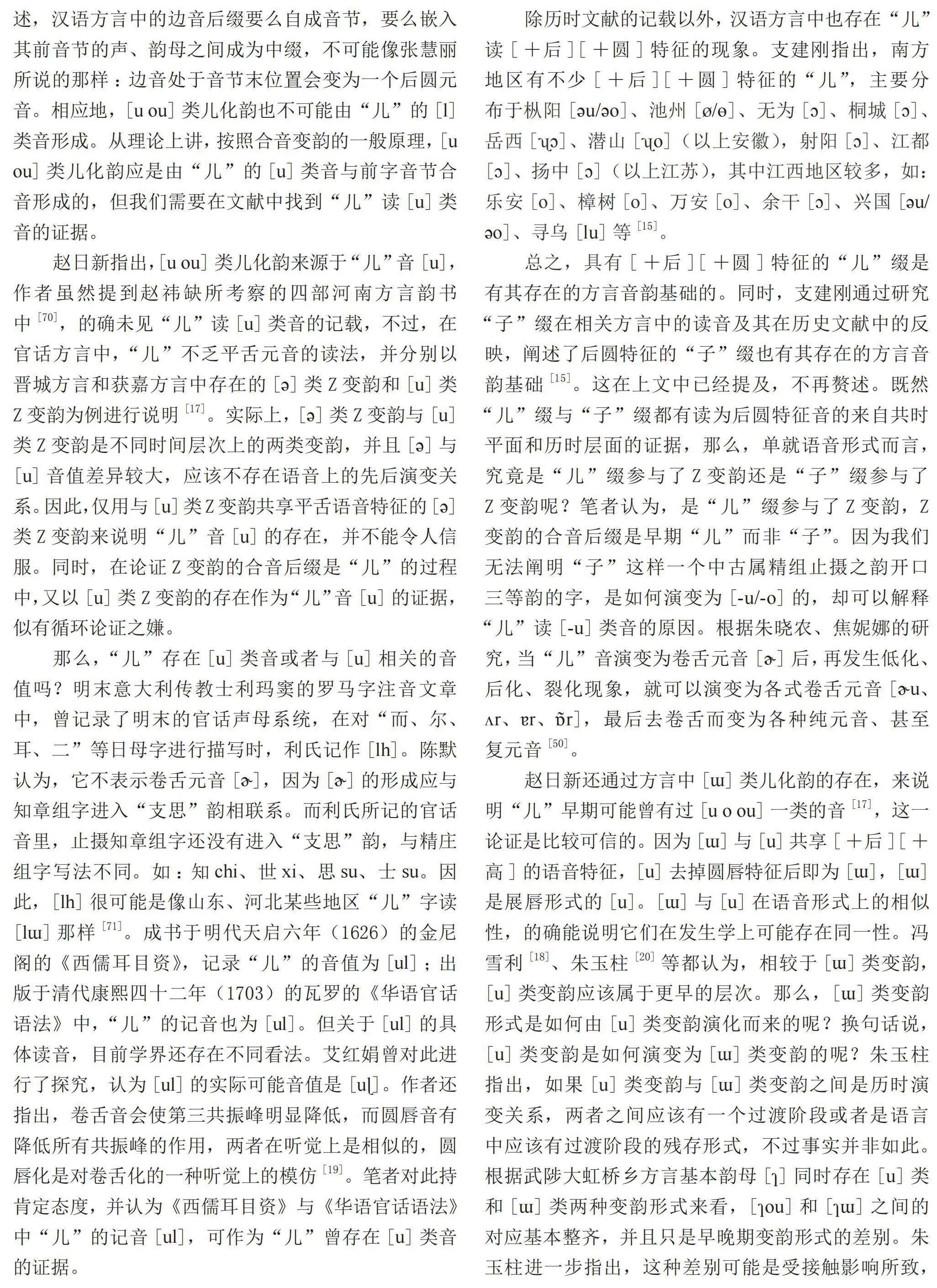




摘" 要:關于Z變音合音成分的本源字問題,學界仍未達成共識,主要有四種觀點:“子”后綴合音說、“兒”后綴合音說、“頭”后綴合音說、“子”“兒”混用說。對這些觀點進行理性反思和簡要評述,闡明它們在論證過程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此基礎上,結合相關方言文獻與語言事實,從后綴“子”“兒”的空間分布、語法功能、語音形式等方面,對Z變韻的合音后綴進行分析。研究顯示,Z變韻的合音后綴應是早期“兒”及“子”的早期兒化韻形式,而不是“子”,更不是“頭”。
關鍵詞:Z變音;合音后綴;兒化韻;“子”后綴
Z變音是漢語方言中以韻母或韻母和聲調的變化,表示與普通話“-子”后綴名詞相同語法意義的音變現象。自20世紀50年代漢語方言普查以來,學界發現,Z變音現象大量存在于河南北部、中部及山西南部、東南部地區;同時,在山東、河北、陜西的方言中也零星報道有Z變音的存在。隨著Z變音現象的不斷發掘,其形成和來源問題也備受關注。雖然學界普遍認為Z變音是由合音形成的,合音后綴是一個具有[+后][+圓唇]特征的成分[-u/-o],但在合音成分的本源字問題上仍缺乏統一認識。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學界主要存在四種觀點:第一,“子”后綴合音說[1]-[15];第二,“兒”后綴合音說[16]-[20];第三,“頭”后綴合音說[21];第四,“子”“兒”混用說[22]。下面,我們將結合相關語言事實,對上述觀點逐一進行評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
一、對“子”后綴合音說的思考
呂枕甲指出,子變韻系詞根音節基本韻母與“子”后綴合讀而成[1](P11-13)。王福堂也認為,其中的構形語素目前基本上可以認為是“子”,因此,仍然把這部分變韻叫作子變韻[2](P136)。認為Z變音是由詞根語素與“子”后綴合音而成的觀點,對學界影響深遠,大多數學者都認同這一說法,但也有學者對此持審慎態度。李榮認為,我們還不能斷定[-u]就是從“子”來的,只能說[-u]尾相當于“子尾”就是了[23](P142-147)。王洪君也指出,目前發現的方言中Z變詞的演變鏈還缺少一些環節,因此,我們還不能完全確定它的本源字就是“子”。盡管從語法意義來看,它很可能是“-子”:出現在名詞詞根之后,沒有明顯的小稱義;從語音上看,是“-子”似乎也說得通,但演化鏈沒有全部銜接上[24](P215)。
如果認為Z變音的合音后綴是“-子”,那么,必須首先解決“子”這樣一個中古屬精組止攝之韻開口三等韻的字,是如何演變為[-u/-o]的問題。即便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子”尾也只是形成了聲母塞擦音→塞音或擦音→流音、韻母趨央的弱化鏈[24](P213)、[16](P225)。
“子”尾的這些不圓唇的前或央元音形式,似乎無論如何也與具有[+后][+圓唇]特征的成分[-u/-o]扯不上關系。后續持“子”后綴合音說的學者,也都在從多個角度嘗試將“子”的語音形式與[-u/-o]銜接起來。
(一)陳衛恒的“子后綴”合音說
陳衛恒從早期漢語之幽兩部交涉的現象出發,認為古韻之幽交涉與今方言的子變韻現象在音變原理上具有共通性,體現了兩類相距遙遠或相互對立的音位之間轉化的可能[4]。但正如陳衛恒所言,之幽兩部交涉的音理解釋,也還只是一個討論中的問題,并且古音不同于今音,我們不能簡單地拿今音去比附古音[4]。
陳衛恒在論證“子”尾到[-u/-o]為韻尾的子變韻母的轉變過程中,給出的一個重要的語言事實是:在河南林州南端的臨淇話中,音素特征為高的某些詞根音節后的子尾,在該片不再讀[??],而有轉讀為[?u]的跡象,如“柿”“姨”“李”等止開三等字,“梯”“(鞋)底”等蟹開四等字等。在此基礎上,陳文指出,“子”尾可能首先弱化為[-?]類音,然后再變為[?],進而變為[-o/-u]這樣的子變韻形式[4]。那么,接下來就需要討論陳衛恒提出的子尾“??→?u”的轉變是否符合音理及語言事實。
通過查閱相關文獻,筆者發現,漢語方言中的入聲韻在語音演變過程中確實存在“??→?u”的音變現象。栗華益指出,主元音為較低、較前元音的入聲韻容易增生[u]類元音作韻尾,其中就包括“??→?u?”這一音變類型[25]。入聲韻因主元音與塞音尾相互作用而增生了一個元音,這樣一來,入聲韻就有兩個韻尾。栗華益進而指出,一個音節存在兩個韻尾違反了漢語音節單位只能由一個音素組成的音系規則,違反音系規則就會造成音系結構的不平衡。這時,增加了元音尾的入聲韻有兩種方式能使音節結構符合漢語音系規則,一是消失元音尾,一是消失塞音尾。消失元音尾的完全回頭演變幾率較低,而消失塞音尾卻符合漢語音系響音化的發展方向。也就是說,在“??→?u?”后,“?u?”會繼續脫落塞音尾從而演變為“?u”[25]。由此可見,在漢語方言入聲韻的演變過程中,確實存在著“??→?u?→?u”音變現象。那么,“子”尾弱化為“??”后混入入聲韻,并跟隨入聲韻進行演變,增生[u]類元音后再脫落塞音尾變為“?u”,也是有可能的。但栗華益同時又指出,入聲韻主元音與塞音尾相互作用而增生[u]類元音的現象,主要出現于宕江通三攝,以通攝為主,并且主要分布在吳語、贛語、徽語、客家話等南方方言中[25]。可見,“??→?u?”的音變現象,不僅只出現在特定的韻攝中,而且分布區域也很有限。上文中,陳衛恒所列舉的幾個變韻例字都不屬于上述韻攝,同時,根據橋本萬太郎的觀點,晉語也沒有元音尾化現象[26]。因此,筆者認為,林州南端臨淇話中,“子”尾出現“??→?u”的音變現象應是不大可能的。
回到問題本身,我們繼續分析臨淇話中“子”尾不再讀[??]而轉讀為[?u]的變韻例字[4]。通過查閱描寫漢語方言Z變韻現象文獻,可以獲知,“柿”“姨”“李”“梯”“底”等基本韻母為前高元音單韻母[i,?,?]的字,后綴[u]與其進行合音,一般會生成[?u]類拼合型Z變韻母。其中,[?]為從前高元音[i,?,?]到后高元音[u]滑動過程中的過渡音。因此,準確來說,陳文中所列出的[?u]類讀音,應該只能稱得上是上述幾個字的Z變韻形式,而非“子”尾轉讀形式。如果認為它們是“子”尾[??]的轉讀形式,就說存在“??→?u”的音變,則屬于循環論證。那么,“子”尾音如何演變為[-u/-o]的問題,仍是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趙日新通過研究河南獲嘉方言D變韻的語音表現,指出D變韻主要是小地名中的“家”等和動詞后的虛成分,如“在、地、得、到、著、了、過”等,在弱化過程中主元音央化,以近央[?]的語音形式合入基本音節,從而形成[?]類變韻,它與[u]類Z變韻的語音形式是不同的[17]。那么,這就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如果名詞變韻是子變韻,是“子”后綴變來的[?]繼續演變為[u ou]的,為什么由“家、著、在、到”等變來的[?],沒有隨著一道變化從而形成[u]類D變韻?因此,通過與語言系統中的其他變韻現象作對比分析,趙日新也認為,[?]類變韻是不可能演變為[u]類變韻的[17]。
(二)張慧麗的“子后綴”合音說
據張慧麗[8]、[9]及賀巖、張慧麗[27]調查,在河南南部和湖北西北部地區,“子”尾讀作一個自成音節的邊顫/閃音或邊音,從這一角度出發,作者闡述了Z變韻形成的一種可能途徑:從邊音到圓唇。張慧麗指出,“子”尾會弱化為邊音尾,這時,邊音在音節末位置上會與圓唇元音混同,這從發音生理和聲學參數上都可以得到解釋。音節末邊音在聲道中的收縮點靠后,從而引起F2下降,而后圓元音典型的聲學表現也是F2下降[8](P34)、[9](P60)。同時,張文也指出,邊音在音節末會變為一個后圓元音,這樣的音變在多個語言中都已發生。在法語中,這樣的音變已成為事實;在標準英語中,邊音在某些復合詞中第一個成分末的位置已經書寫為圓唇元音。這說明在某些條件下音節末邊音已經變為圓唇元音[8](P34-35)、[9](P61)。
邊音在音節末的位置上會變為后圓元音,的確是符合音理的;音節末邊音在法語、英語這樣的多音節詞語言中會演變為圓唇元音,也的確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們關心的是:在漢語這樣的單音節詞語言中,音節末邊音也會演變為后圓元音嗎?邊音韻尾在漢語方言中確有存在,考察邊音韻尾在漢語方言中的語音特征及發展趨勢,或許能為上述問題提供解決思路。
根據一些學者的觀點[28]-[34],漢語方言中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邊音作韻尾的現象,對應于中古的某些入聲韻。也就是說,入聲韻塞音尾[-p,-t,-k,-?]在一定條件下經過相關演變過程后,會弱化為邊音韻尾。其中,董為光[28]、王世華[30]、栗華益[33]等學者,都描寫了相關方言點邊音韻尾的發音特征。董為光指出,在湘鄂贛三界方言中,典型的[-l]韻尾的發音特征是:舌尖略微卷起,與上腭形成較松的接觸,與此同時,聲帶振動,氣流經由舌頭兩邊流出,發出一個清晰的[-l]。從旁觀察,可以明顯地看到舌尖的卷曲動作,猛然聽去,甚至會有一種特殊“兒化”的現象[28]。
王世華指出,在江蘇寶應方言中,韻尾[-l]的發音是用舌尖抵住上齒齦,氣流由兩邊出來,并且收[-l]尾的音節可以延長,延長時的音值能很清楚地聽出是邊音[l]持阻階段的音值,而收喉塞尾[-?]的音節則無法延長[30]。栗華益指出,改變[-t]尾的成阻方式即可形成邊音韻尾,發[-t]尾時,舌尖前伸抬高抵住上齒齦,而當舌頭下降緊抵齒齦形成阻塞的舌尖放松、兩側的舌葉打開形成裂縫讓氣流逸出時,就形成了邊音尾[33]。
我們知道,在英語中,音素/l/存在兩種發音:當出現在音節首位置時,如在英語單詞“leave”“follow”中,它是齒齦邊音[l]。發音時,舌尖抵住上齒齦,氣流從舌頭兩側流出,此時,[l]被稱作“clear l”,可譯為“清晰/l/”。當出現在音節韻尾位置時,如在英語單詞“ill”“cold”中,它是軟腭化了的齒齦邊音
[?]。發音時,伴隨著舌體的后縮,舌頭后部升高抬起,就像發[u]或[?]音時一樣[35],被稱作“dark ?”,可譯為“模糊/?/”。可見,在英語中,音素/l/出現在音節首和出現在音節尾時的發音是不一樣的。但通過上文描寫的漢語方言邊音韻尾的發音特征,可以知道,當漢語中的齒齦邊音/l/出現在韻尾位置時,并沒有像在法語、英語中那樣發生軟腭化現象變為“dark ?”,而是繼續保持“clear l”的發音特征不變。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各位學者對入聲塞音韻尾到邊音韻尾演變過程的構擬略有不同,但大都認為邊音韻尾會繼續發展而演變為喉塞韻尾[-?],即入聲韻尾存在著“-l→-?”的音變現象。由此可見,無論是在發音特征上,還是在演變趨勢上,漢語方言入聲韻的邊音韻尾都與后圓元音無關。
有學者可能會發現,上述考察的都是漢語方言入聲韻邊音尾的語音特征和發展趨勢,而張慧麗及賀巖、張慧麗研究的則是湖北地區邊音“子”尾的發音和聲學特征。下面,我們也來嘗試分析因單音節化而使得邊音可能處于韻尾位置的情況下,邊音的語音狀況及其發展趨勢。
徐通鏘對山西平定方言及其他相關方言的兒化現象進行了考察,在此基礎上,作者指出,漢語方言中的邊音“兒”要么只能自成音節,無法達到“化”的結果,如杭州方言中的“凳兒”發音為[t?? l?]等;要么就像平定方言一樣,使“兒”在“兒化”時嵌入聲母和韻母之間而成為一個中綴,如“豆兒”在該方言中發音為[t??u]。因為“兒化”后為實現單音節化而使邊音處于韻尾的位置,與漢語的音節結構相矛盾。在現代漢語方言中,除了從入聲[-t]尾轉化來的[-l]韻尾,還沒有因復合的音節的單音節化而形成以邊音(特別是卷舌的邊音)收尾的音節[36]。所以,漢語方言中的邊音后綴要么自成音節,要么嵌入其前音節的聲、韻母之間成為中綴。山東高密方言的兒化現象也證實了這一觀點。董紹克指出,高密方言的兒化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兒化后出現復輔音,即聲母+[l];二是兒化后出現雙音節,即輔音+介音(i,y)+輔音(l)+兒化韻韻腹;三是兒化后的韻母結構同普通話的兒化相同[37]。
徐先生站在理論的高度,對漢語方言中邊音后綴的演變趨勢作了預測,使我們對隱藏在相關音變現象背后的機制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董紹克還指出,在山東聊城陽谷方言中存在“?”型兒化現象。所謂“?”型兒化,就是在原來的韻母(有的則是主要元音)之后加“?”或韻母“?”變為“?”。“?”型兒化韻母主要對應[?,i,y]作主要元音的基本韻母,如在陽谷方言中,“字兒”讀作[ts?],“衣兒”讀作[i?],“魚兒”讀作[y?]。陽谷方言“?”型兒化的生成機制及相關語言現象顯示,邊音后綴“?”在上述情況下確實是直接加綴在前字韻母之后的。那么,此時處于韻尾位置的“?”的語音特征是怎樣的呢?董先生明確指出,“?”型兒化只是就韻尾的特點而言的,如果就音節結構形式來看,它也具備“雙音節型兒化”的某些特點。其中,“字”的兒化韻形式[ts?]為聲母[ts]和“兒”后綴[?]直接拼合形成的復輔音[38]。由此可見,在漢語方言中,即使邊音確實加綴在韻母之后,也不會發生軟腭化現象變讀為后圓元音,而是依然保持其輔音性。從這個角度來看,陽谷方言的“?”型兒化與杭州方言中的兒后綴一樣,也是自成音節,從而進一步證明了徐先生關于邊音后綴論斷的正確性。
總之,張慧麗等闡明了從邊音到圓唇的Z變韻形成途徑,作者認為,“子”尾弱化為邊音后,處在音節末尾位置上的邊音會演變為圓唇元音。該觀點為探究Z變音圓唇特征的由來提供了新的視角,但是并未結合漢語的實際情況來展開討論,其結論在漢語中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如果認為Z變音的合音后綴是“子”,那么,Z變音的圓唇特征如何由“子”尾演變而來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三)史艷鋒的“子后綴”合音說
史艷鋒指出,在子變合音時,“子”尾韻母的音值是多元的,同一方言內的子變韻母,也可能是由不同“子”尾韻母合音而成的[10](P151-184)。以孟州方言為例,該方言中的大部分陰聲韻Z變音的合音后綴是具有[+后][+高][+圓唇]特征的[-u]類成分,而[an]類基本韻母的合音后綴則為[-?]。作者進一步指出,孟州方言[an]類基本韻母在Z變韻過程中增生的[i]介音,是源自韻頭[?]與韻尾[?]的異化作用[11]。史艷鋒的論證雖然環環相扣,但其論證過程得以展開的立論基礎則需要商榷。筆者認為,一個方言點在共時層面上不可能同時存在兩類表達同樣語法意義的合音后綴,如果存在兩類不同的表達同樣語法意義的合音后綴,那必然是在不同的時間層次上形成的。因此,我們的觀點是:如果認為方言中Z變音的合音后綴有多個,必須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不同的合音后綴是在不同的時間層次上與基本韻母進行合音形成Z變韻的。支建剛也在該問題上與我們觀點一致,他指出,就單個方言來說,合音時“子”尾韻母的音值并非多元的,很多Z變音的特征是合音中與合音后繼續演變的結果[15]。
陳衛恒指出,從韻腹為央元音的“子”到“-o/u”為韻尾的子變韻的轉化過程中,[?]處于重要的過渡環節,它可以兼顧-u和-i兩個演變方向[4]。同時,關于萬榮方言中的“-子”,吳建生記作t?0[39](P32-40),吳建生記作t?0[40],吳云霞則記作t?u0[41](P81)。史艷鋒以此為理論依據和事實支撐,認為“-子”存在t?0>t?0>t?u0>?u0>u的弱化過程[10](P152)、[11]。首先,陳文中提出的[?]在從“子”到“-o/u”的Z變韻的轉化過程中起著橋梁作用,只是一種猜測,我們在漢語方言中并未發現成系統的-?作韻尾的Z變音現象。其次,史艷鋒根據萬榮方言的“子”在不同的時間段被記作不同的讀音,就認為“子”的三種讀音之間存在語音的先后演化關系,即“-子”是從t?0發展到t?0,再由t?0演變為t?u0,這個語音演化鏈還需要進一步的論證。我們認為,萬榮方言“子”的幾種讀音之間不一定存在先后的演化關系,也可能彼此之間是替代與被替代、覆蓋與被覆蓋的關系。
(四)支建剛的“子后綴”合音說
支建剛指出,河南林州桂林鎮方言的“子”尾有[?]和[l?]兩種語音形式,均讀輕聲,“子”尾究竟讀[?]還是[l?],則受前字韻母末位音素的影響。當前字韻母的末位音素具備[+高]特征時,“子”尾讀[?];當前字韻母的末位音素具備[-高]特征時,“子”尾讀[l?]。在此基礎上,支建剛又從方言間的系統對比和方言內的功能擔當上,判定林州桂林鎮等地的名詞后綴[?]和[l?]就是“子”的具體存在形式[13]、[14]。
我們認同支建剛所提出的桂林鎮等地方言的兩種語音形式[?]和[l?],就是“子”而不是其他名詞后綴(如“兒”“頭”)變體的觀點,但不認同桂林鎮等地方言的“子”尾讀音[?]和[l?]是[u]類Z變韻合音成分的現實來源。
首先,雖然桂林鎮方言“子”尾的主元音[?]與Z變音的合音成分[-u]共享[+后][+圓]的語音特征,但二者在舌位高度上存在差異。那么,“子”尾的韻母[?]有沒有可能是Z變音合音后綴[-u]的語音變體呢?我們認為這個可能性不大。根據侯精一、溫端政的觀點,山西聞喜話子尾大都是念輕讀的u,由于受前一個音節元音韻尾的影響,有時也念成輕讀的o。例如:“盤子”在聞喜方言中讀作[pha?21-31 u],“瞎子”則讀作[xa51 o][42](P88-95)。王洪君也指出,Z變韻中的u只代表收向后、高、圓的方向,實際上往往達不到u那么高,特別是在低元音的后面,音值上更接近于o[43]。由此可見,即使Z變音的合音成分[-u]存在較之舌位稍低的語音變體,那么也只會低到中高元音[o]的位置。
同時,在其他存在圓唇型Z變韻形式的方言中,也沒有找到相關證據的支持。夏俐萍在分析河南封丘趙崗方言的Z變韻現象時指出,從[i? i u y]的子變韻形式中應該可以推斷出Z綴的基本形式,因為[i? i u y]在子變韻中充當了介音,而Z綴則充當了子變韻的主元音[44]。因此,當基本韻母為前高元音單韻母時,會生成拼合型Z變韻母。從拼合型Z變韻母的語音形式中,我們能清楚地離析出合音后綴的語音成分。觀察河南及山西相關方言前高元音單韻母所對應Z變韻母的語音形式,以基本韻母[i]為例,它所生成的圓唇型Z變韻母有[i?u]、[i?u]等,卻沒有[i??]、[i?]。雖然方言中普遍存在以[?]為主元音的Z變韻母,但[?]類Z變韻母屬于融合型,融合型Z變韻母不同于拼合型Z變韻母,不能簡單地將[?]從Z變韻母中分離出來作為Z變韻的合音后綴。因此,桂林鎮方言“子”尾的主元音[?]與Z變音的合音成分[-u]有關,是沒有相關語言事實證明的。
那么,桂林鎮等地方言“子”尾的兩種語音形式[?]和[l?]與什么有關呢?筆者認為,主元音為后圓元音[?]的“子”尾語音形式應與[?]類“子”尾形式屬于一類,[?]是[?]的語音變體。首先,[?]與[?]具有語音上的相似性,發元音[?]時,舌頭往前同時往高稍作移動就會變為[?]。其次,[?]類“子”尾與[?]類“子”尾存在系統性的對應,它們分化為兩種讀音的音韻條件也相同。陳衛恒指出,林州城區的“子”尾讀[??]還是[l??],也是以詞根韻母中最后一個音素語音特征的“高”“低”而定,“低”的(-?,-a,-?,
-?)為l??,“高”的為??[45]。陳衛恒還指出,林州方言中相當于普通話的“的”“得”“著”等助詞,也有類似的讀音分界現象:在-?、-a、-?、-?后讀l??,其他韻尾后讀??[45]。[?]類“子”尾形式與[?]類“子”“的”“得”“著”等,不僅具有語音上的相似性,在讀音分化的語音條件上也相同。因此,[?]類“子”尾形式與[?]類“子”尾形式應屬于一類。再次,喬全生指出,晉語區子尾的讀音與官話區不同:北京話及整個官話區讀[ts?];晉語區讀音雖然多樣,但主要韻母多讀央元音[?]是其一大特色[46]。就此而言,將[?]類子尾與[?]類子尾歸入一類符合晉語區的方言特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最后,林州桂林鎮方言“子”尾的語音形式與Z變韻形式之間存在較大差異。雖然表面上看兩者都讀[?]韻,但桂林鎮方言的[?]韻是以詞尾的形式存在的,并未與其前音節發生合音現象,而Z變韻形式中的[?]韻卻是由合音后綴與基本韻母的主元音和韻尾合音形成的,屬于融合型Z變韻形式。因此,桂林鎮方言的“子”尾是本身就讀[?]韻,而[?]類Z變韻母并不說明Z變韻的合音后綴即為[?]。王福堂[2]、[3]及王洪君[24]、[47]在分析河南獲嘉方言Z變韻的語音形式時都曾指出,[?]類Z變韻母是由[u]類后綴與基本韻母的主元音和韻尾拼合后,又單元音化而形成的。實際上,漢語方言中的[?]類“子”音也是以詞尾的形式存在的,這進一步說明了[?]類“子”與[?]類“子”應屬一類。總之,我們認為,支建剛所描寫的林州桂林鎮等地方言的[?]類子尾,實質上是[?]類“子”尾的語音變體,屬于[?]類“子”尾,而與Z變音的合音后綴[-u]沒有關系。
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支建剛還從語音形式入手,發現Z變音分布區周邊方言有后圓特征的“子”綴,卻沒有后圓特征的“兒”音,并且后圓特征的“子”綴有其存在的方言音韻基礎。因此,參與Z變音的合音成分不是“兒”“頭”,而是“子”,Z變音即子變音[15]。
支建剛詳細羅列了具有[+后][+圓]特征的“子”綴的方言材料,并充分論證了具有[+后][+圓]特征的“子”綴的音韻基礎。從表面上看,既然“子”韻具有[+后][+圓]特征,Z變韻也讀若[u/o]形式,“子”變韻與Z變韻不僅在語音形式上重疊,在表達的語法功能上也基本一致,認為Z變韻就是子變韻確實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把“兒”綴的相關材料也一并進行對比論證,則會發現Z變韻到底是不是子變韻并不能立即斷定。
首先,在支建剛所列舉的豫北方言中,“子”綴讀[?]和[l?]的現象在上文中已作分析,我們認為,[?]類子綴實際上就是[?]類“子”綴。至于一并羅列的晉南、山東方言中的讀為[u、ou]類音的所謂“子”,我們關心的是:怎么確定這類讀作[u、ou]類的音就是“子”,而不是“兒”?筆者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疑問,是因為筆者發現,在自己的母語河南新密方言中,如果問當地的母語者:“孩子”在新密方言中怎么說,我們的回答是[x?r]。難道我們就能據此認為“子”在新密方言中具有卷舌特征?因此,在兒化韻比較發達的方言中,會采用兒化的形式來表達與普通話“子”尾相同的語法意義,從而造成方言中“子”與“兒”在音義上錯綜復雜的對應現象。就此而言,如果說晉南、山東方言中讀為[u、ou]類音的詞綴就是“子”,那么,必須給出足夠的證據來證明這些后綴不是“兒”。其次,支建剛在論證Z變音就是子變音的過程中,曾引用侍建國的觀點[48],認為在尋找具備[+后][+圓]特征的后綴形式時,需要注意“求近”與“廣泛”。求近就是尋找周邊毗鄰方言,廣泛就是不限于一個周邊方言。支建剛認為,雖然南方地區的不少方言中存在具有[+后][+圓]特征的“兒”,但不符合“求近”原則,對證明“兒”參與Z變音是無用的[15]。我們知道,兒化韻在漢語方言中的分布非常廣泛,由于“兒”本身語音形式的復雜多樣,在各個方言區中呈現出的合音結果也不盡相同。方言的共時分布狀況往往反映方言的歷時演變過程,“兒”復雜多樣的語音形式之間是存在先后演化關系的。李思敬[49]、朱曉農與焦妮娜[50]
等學者,對“兒”語音演變史的重建,也都是從“兒”的各種鼻音形式出發進行的,而“兒”的鼻音形式在南方方言中很常見,與“兒”的中古音值接近。比如,按照蒲立本的擬音,“耳二兒而”等字的中古音即為[?i][50]。筆者認為,此時不能照搬“求近”原則。對“兒”這樣一個在漢語方言中分布非常廣泛的詞綴而言,是需要參考它在各個方言區的讀音形式,來考察它在歷時階段上的演化進程的。因此,南方不少方言中的“兒”音具有[+后][+圓]特征,對探究“兒”音是否參與Z變韻應具有重要價值。
上文分析了前人在將方言中“子”的語音形式與Z變音的合音后綴[-u]聯系起來的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對此,我們與趙日新持同樣的觀點,即“子”弱化為詞綴后,語音亦相應弱化,的確有變為[?]的可能,但變為[u]或[o]則幾乎是不可能的[16]。王臨惠也認為,“子”后綴與Z變音之間不能建立合理的演變鏈,因而大致可以排除參與Z變音的后綴是
“-子”的可能性[21]。趙日新在分析方言中的名詞變韻與D變韻時指出,即使“子”尾可以變為[u ou]一類的音,也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名詞變韻和D變韻既然都經歷了[?]階段,名詞變韻的[?]會變成[u ou]類音,那么,獲嘉方言的D變韻母為什么不是[u]類變韻?[17]除非能夠證明名詞變韻與D變韻不是同時發生的音變,否則很難解釋二者之間的不同。
二、對“頭”后綴合音說的思考
王臨惠認為,臨猗猗氏鎮(城關)方言的Z變音,是語流中后綴“都”的逐漸弱化造成的,基于這一語言事實,作者指出,猗氏方言Z變音的整個變化鏈應當是:詞根音節+“都”[tou]→詞根音節+[ou]→詞根音節與[ou]合音,音節變讀長調→詞根音節主要元音變讀長元音,音節變讀長調。王文還從構詞能力、語音演變、語義特征等方面綜合考量,認為“都”后綴應是“頭”后綴無疑,Z變音的合音后綴是“頭”而不是“子”[21]。
支建剛針對王臨惠所報道的語言現象,提出一系列問題:這個“都”綴到底是什么,它與“頭”綴是何關系,它們是不同的歷史層次還是不同詞匯條件下的變體等;只有清楚回答這些問題,才能有效討論“[tou]→[ou]→合音變調”弱化鏈條現象[14]。支建剛進一步指出,如果認為長治的[t??]、萬榮的[t?]/[t?]、內黃的[t?]、平順的[l??]、林州的[l??]等后綴,都是由“頭”綴演變而來的,那么,這些周邊方言將會形成兩個“頭”綴并存的局面。如此大面積成系統的跨語音語法層面的疊置,在漢語中并不曾見[15]。可以說,“頭”變詞與頭綴詞、兩個“頭”綴之間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并不容易解釋清楚。因此,Z變音不可能是頭變音。
筆者認為,雖然“頭”后綴合音說可以彌補Z變音演化鏈中缺失的重要一環,使Z變音的語音演化鏈得以銜接,但“頭”后綴在豫北、晉南方言中的使用頻率太低,只在“石頭”“磚頭”“木頭”“鋤頭”等極個別詞語中出現,與“子”后綴、“兒”后綴在使用頻率及構詞能產性上毫無可比性可言。趙日新也提到,除非能在文獻中找到“雞頭、獅頭、鋸頭、盆頭、絲頭、字頭、事頭”等最初具有小稱義的“頭”綴詞的實際例證,否則“頭”綴說很難成立[17]。還需指出的是,“頭”后綴與Z變音所表達的語義是存在一定差別的。在現代漢語方言中,Z變音一般用來表大。而《說文解字》對“頭”的解釋是:“頭,首也。”王麗娟認為,“頭”的本義是指“頭部”,后來引申指事物的前部、頂端或邊緣,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意義逐步虛化,成為構詞后綴[51]。可見,“頭”作名詞后綴所表達的語義與Z變音所表達的語義之間并不能完全匹配得上。因此,“頭”后綴合音說在解釋Z變音問題上也是無效的。
三、對“兒”后綴合音說與
“子”“兒”混用說的思考
“兒”后綴合音說與“子”“兒”混用說均認為,在Z變音的過程中,有“兒”后綴的參與,因此,我們把兩種觀點放在一起進行討論。
趙日新指出,在中原地區官話方言中,參與一般名詞變韻的語素很可能是“兒”而不是“子”,所以不必另外假設一套“子變韻母”。作者傾向于將同一個基本韻母的不同變韻形式,看成是不同時期的兒化在共時平面的疊置,即認為都是兒化韻[16]。辛永芬、莊會彬的“子”“兒”混用說則認為,Z變音的源頭應當有早期的“子”尾,也可能有早期的“兒”尾,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Z變音的源頭可能是“子”尾和“兒”尾在某種程度上的混用和疊置[22]。我們認為,參與Z變韻的合音語素是早期的“兒”綴及“子”的早期兒化韻形式,不可能是“子”。所謂“子”的早期兒化韻形式,是指合音時取合音前字的聲母和合音后字的韻母,就此來說,“子”的早期兒化韻形式的韻母部分,其實還是早期兒化韻。“子”的早期兒化韻形式這一說法,既不否認“子”作為后綴曾參與構詞的語言事實,同時又強調參與變韻的仍是早期兒化韻,因為“子”在這里已經兒化。
趙日新在論證“兒”后綴合音說時,給出了六個方面的理由,大致圍繞兩個角度展開討論:一是“子”“兒”的空間分布;二是“子”“兒”的語法功能[16]。不過,“兒”從單字音到Z變音經歷了怎樣的音變過程,趙文卻沒有提及,也沒有充分結合相關的文獻和方言現象進行說明,因此,“兒”后綴合音說在學界并未引起應有的重視。這里就結合相關方言文獻與語言事實,圍繞上述兩個角度,對我們所提出的“早期‘兒’后綴合音說及‘子’的早期兒化韻后綴合音說”進行論證。
(一)“子”“兒”的空間分布
從“子”“兒”的空間分布情況來看,趙日新曾指出,“子”尾是漢語方言中常見的名詞后綴之一,分布范圍很廣,并且都讀輕聲,而Z變韻卻只見于山西、河南、山東、河北的部分地區[16]。這難免令人生疑。我們注意到,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曾對“子”“兒”后綴在漢語方言中的分布情況進行過描寫,可以發現,“子”綴在從北到南的大多數方言中都有存在,而“兒”綴卻主要分布在北方方言中,南方方言中極少;在中部方言中,“子”綴和“兒”綴則呈現均衡的分布態勢。因此,如果認為Z變音的合音后綴是“子”,那么就必須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Z變韻現象在“子”綴普遍存在的南方方言中沒有出現?
辛永芬、莊會彬指出,認為Z變音的合音后綴是“兒”的學者,需要解釋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有Z變音的方言區就沒有“子”尾詞,而“子”尾詞在Z變音地區的周圍都有分布[22]。有Z變韻的方言一般不再有通常的“子”尾,這也是人們認可“子”后綴合音說的重要依據。趙日新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答,作者認為,有了Z變韻,“子”尾自然可以不再是表達同樣語法功能的必有手段。比如,一般認為多數江淮官話沒有兒化,那是因為“子”尾部分承擔了兒化的功能;湘語多數沒有兒化,那是因為有“崽”(或“唧”“子”)后綴[17]。我們與趙日新在該問題上的看法一致,有Z變韻的方言不再有通常的“子”尾,是因為Z變音已經承擔了“子”尾所要表達的語法功能,而不能證明Z變音的合音后綴就是“子”。同時,辛永芬、莊會彬所提出的這一問題,對相關語言現象的描述有些絕對,許多有Z變韻的方言也是存在子尾詞的。王臨惠指出,北京話的子尾在臨猗方言中有子尾和子變韻兩種表現形式:單用時多為子尾,構詞后多讀子變韻[52]。王軍虎也指出,在陜西鳳翔方言中,既有自成音節的詞綴“子”,41個韻母中又有39個可以生成子變韻,自成音節的詞綴“子”和子變韻之間可以自由交替使用[53]。
(二)“子”“兒”的語法功能
從“子”“兒”的語法功能來看,趙日新指出,一些學者之所以認為Z變音的合音后綴就是“子”,主要是因為這些Z變音的詞大致相當于普通話的“子”尾詞[16]。實際上,普通話中的“子”尾詞在方言中未必都由Z變音形式來表達,而方言中的Z變音詞也并非完全等同于普通話中的“子”尾詞。張莉指出,在河南焦作方言中,除了存在變韻表示北京話“子”尾詞的現象外,還存在兒化韻、方言詞及單音節詞均相當于北京話“子”尾詞的現象[54]。因此,北京話中的“子”尾詞在方言中未必都由Z變音形式來表達。王臨惠也指出,在山西臨猗方言中,有些詞讀子尾和讀子變韻所表示的意義不同。如“抬杠子”若讀作子變韻[thai24 ka??44-423],則表示“認死理”;“兒子”若讀作子變韻[z??24-224],則表示“動物的崽子”[52]。而普通話中相對應的“子”尾詞并不表示上述意義。因此,方言中的Z變音詞并非完全等同于普通話中的“子”尾詞。
同時,趙日新也提到,“兒化”通常具有“表小”的功能,而Z變音大多“指大”。“兒化”與Z變音在表義上的差別與對立,也是一些學者不把Z變音與“兒化”聯系起來的原因[16]。楊彥寶指出,“子”綴來源于實詞“子”,本義是子嗣,“子”的甲骨文、小篆等字形像初生嬰兒的形象[55]。“兒”的本義也指小孩,《說文解字·兒部》:“兒,孺子也。從兒,象小兒頭鹵未合。”可見,“子”和“兒”在詞源意義上比較接近。王力在《漢語史稿》中指出,詞尾“子”字比詞尾“兒”字產生得要早,二者都是由表示實義的詞虛化而來的,小稱是它們詞尾化的基礎[56](P219-P220)。
很多漢語方言中,既存在“子”綴又存在“兒”綴。通常情況下,“子”尾詞表“大”,“兒”化詞指“小”,但也有例外發生。一方面,兒化未必都表達小稱義。趙日新就提到,山西太原方言的“車兒”是指“大車”[16]。孫青林也指出,在山西陽高方言中,當重疊式通用不表兒語時,兒化韻表大稱義,重疊式表小稱義。如:“車兒”指一般的自行車、汽車、牛車等較大的車,而“車兒車兒”則指小孩子的玩具車[57]。另一方面,“子”尾詞也不一定都“指大”。樂玲華指出,在安徽阜陽方言中,“子”尾能表示“小”的意味[58];毋效智也指出,陜西扶風方言中的詞綴“子”可表“小”[59](P315)。代國英還指出,在河北邢臺方言中,有些方言點存在大量兒化詞與“子”尾詞并存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子”尾詞表示“大”的含義,“兒”化詞表示“小”的含義[60](P31)。與邢臺方言“子”尾詞表示“大”的含義情況相反,在一些缺少兒化詞的方言里,大多用“子”尾詞表示“小”的含義。史素芬指出,在晉東南方言中,具體的、常用的、含小稱意義和卑賤、不值得敬畏意義的人或事物,通常都帶子尾[61]。實際上,Z變音詞也不一定都“指大”。王臨惠指出,在山西臨猗方言中,兒化韻表示細小的意思,子變韻有的也表示細小的意思[52]。張娟通過考察河南與山西方言的Z變音現象,發現大部分Z變詞都指向本身較小的事物,本身較大的事物則較少有發生Z變韻的。基于此,作者進一步指出,Z變韻也是一種小稱變韻,和兒化韻一樣,兩者并舉時往往存在著如下的分工:Z變韻指向小事物中的大者,兒化韻指向小事物中的小者;Z變韻多表示不好的事物,是“厭稱”,兒化韻多表示小巧、喜愛的事物,是“愛稱”[62](P33)。馮雪利也提到,在河南武陟(西滑封)方言中,名詞變韻具有表小的語法意義,如:“雞”本音讀[t?i],其Z變韻形式[t?i?]則表示“小雞”[18](P62)。
總之,Z變音作為早期“兒”后綴參與的音變現象,本來具有“小稱”的含義。只是在語言的演變過程中,河南、山西、山東、河北等地,又出現了卷舌“兒”后綴參與的兒化現象,同樣具有“指小”的功能。當一個方言(或語言)系統內部同時存在兩個具有“指小”功能的音變現象時,它們所表達的語法意義必然會出現分化。高永奇指出,當某一方言(語言)系統中同時存在“兒”“子”兩個名詞詞綴時,它們的構詞能力、構詞對象和所顯示的語法意義就會分化,這樣才能有各自存在的條件,否則人們便會選擇其一而舍棄另一形式[63]。代國英也提到,“子”尾詞本來具有“小稱”的含義,但是在漫長的語言演變過程中,“子”尾的這一含義逐漸讓位給了其他語法成分或表達方式。在兒化詞豐富的方言里,“子”尾詞的“小稱”義讓位給了兒化詞,而在“重疊”比較豐富的方言里,則讓位給了重疊[60](P31-32)。趙日新則指出,從漢語史的情況來看,作為名詞后綴的“兒”和“子”,大致早期是“子”尾占優勢,宋元以后“兒”尾快速增長[17]。同樣的名詞(素)如果既能帶“兒”后綴也能帶“子”后綴,自然就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或者在功能上有所分工。
四、Z變韻的合音后綴探析
上文,我們主要是圍繞“子”“兒”的空間分布、語法功能兩個角度,結合相關方言事實,對Z變韻的合音后綴進行分析。下面,我們將從“子”“兒”的語音形式出發,對這一問題繼續進行探討。
(一)“兒”在方言中的語音形式
高兵、吳繼章指出,在河北方言中,“兒系列字”與“兒化”的關系主要有四種類型:一是“兒系列字”并非卷舌韻母[?r],但該方言點的兒化韻母卻與普通話一樣讀卷舌韻母。如魏縣方言的“兒系列字”讀音是[??],其兒化韻母的韻尾都是卷舌音[r]。二是“兒系列字”讀平舌元音[? ? ??]的方言,兒化韻讀與“兒系列字”相應的平舌元音尾韻。如淶源話中“點兒”讀作[ti??],遷西話中“把兒”讀作[pa?]。三是“兒系列字”讀平舌元音[?]的懷安一帶的方言,兒化韻的形式比較復雜:有讀平舌元音尾韻的,有讀卷舌尾韻的。四是“兒系列字”的讀音是[?r],但兒化韻卻不一定是卷舌韻母[64]。
學界一般認為,兒化韻的語音形式主要由“兒”的讀音形式決定[65](P83),兒化韻由“兒”后綴與前字音節合音而成[24](P201),邏輯上也應該是這樣的。但如上所述,在河北一些縣市的方言中,兒化卻并非如此,在這些方言點中,從共時平面來看,兒化韻不是“兒系列字”與前一韻母融合的結果。上述四種情況中,就有三類不是這樣或不完全是這樣。就此而言,我們不能因為“兒”的單字音在某方言點中不讀[u]類音,就斷言[u]類名詞變韻不可能是兒化韻。上述兒化韻與“兒系列字”讀音之間并不完全對應,也說明即使解決了“子”這樣一個中古屬精組止攝之韻開口三等韻的字如何演變為[-u/-o]的問題,仍不能證明“子后綴合音說”就具有正確性。
上文,我們曾提到,“子”這樣一個屬于精組止攝的字,是無論如何也與具有[+后][+圓唇]特征的成分[-u/-o]扯不上關系的。接下來,我們將嘗試運用“兒”在方言中出現的語音形式來證明Z變音的合音后綴就是早期“兒”及“子”的早期兒化韻形式。
趙日新從豫北方言名詞變韻與D變韻的區別、“侄兒”一詞的讀音、明清時期河南方言“兒”和“子”的讀音、邊音[l]的性質等方面,闡明了豫北方言的兒化韻具有三個層次:[u ou]層、[? ?]層和[?]層面。其中,[u ou]類兒化韻由“兒”的[u l]音形成,[? ?]類由“兒”的[?]類讀音形成,[?]類由卷舌的“兒”音形成[17]。
[?]類兒化韻由卷舌的“兒”音形成很容易理解,普通話的兒化音變現象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在普通話中,“兒”的音值即為[?],那么,它與前字音節合音形成卷舌兒化韻也是十分自然的。
[?]類兒化韻由“兒”的[?]類讀音形成,也是顯而易見的,漢語方言中就存在普遍的[?]尾兒化韻現象。趙日新曾列舉了河南洛陽方言的[?]尾兒化韻和武陟西滑村方言、焦作市區方言[? ?]類兒化韻的并存現象[17]。裴澤仁指出,在豫西方言中,除了偃師之外,其他各個縣市的兒化韻都是[?]尾[66]。可見[?]尾兒化韻現象在豫西方言中的普遍性。同時,趙日新還舉例介紹了河北部分方言點中的[?]尾兒化韻現象[17]。
[?]尾兒化韻不僅存在于河南、河北的一些方言點中,在山西、陜西、甘肅的部分方言中也有發現。據《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記錄,山西的洪洞、壽陽、清徐、太谷等縣,均存在舌面元音兒化[?]。孫立新指出,部分陜南方言如城固、白河城關話的老派等,也存在[?]尾兒化韻現象[67]。高曉虹指出,蘭州、神木的平舌兒化韻母都是-?尾韻母[68]。那么,存在“兒”的單字音讀[?]韻的現象嗎?答案也是肯定的。根據馮雪利的研究,“兒”讀[?]的情況在武陟西滑村的臨近方言中大量存在,如洛陽[??]、靜樂[??]、戶縣[?]、神木[??]、遷安與遷西[??][18](P76)。劉麗麗指出,在安徽休寧溪口方言中,“兒”讀作[??54],雖然該方言的兒化形式主要表現為基本韻母加[n]尾[69]。
既然“兒”存在讀[?]韻的現象,那么,方言中普遍存在的[?]類兒化韻,在音理上自然就可以解釋得通。
趙日新還提到,[?]類兒化韻也是由“兒”的[?]類讀音形成的[17]。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首先,雖然[?]類與[?]類音都屬于平舌兒化韻,但[?]與[?]音值差異較大,認為[?]類兒化韻由“兒”的[?]類音演變而來,在音理上講不通。其次,一些語言現象說明,[?]類與[?]類兒化韻應是在不同的時間層次上形成的,并且[?]類比[?]類兒化韻出現的時間早。根據張莉的研究,近些年來,在河南焦作方言中,“籃子”的發音由[la?312]轉變為[lan13 ts?],“房子”的發音由[fa?13]轉變為[fa?13 ts?][54]。馮雪利也指出,在[u]類、[?]類與[?]類兒化韻并存的武陟西滑村方言中,[u]類變韻應該屬于最早的層次,[?]類次之,[?]類應該屬于最新的層次,[u]類、[?]類變韻的“表小”功能衰亡,在新起的[?]類中得到更新[18](P76)。朱玉柱指出,在河南武陟大虹橋鄉方言中,相較于[u]類和[?]類名詞變韻,[?]類變韻是該方言中的最新變韻層次[20]。趙日新亦指出,條條道路通央[?][16]。因此,“兒”作為合音后綴,音值演化為[?]后再與其前音節合音為[?]類兒化韻是水到渠成的。也就是說,[?]類兒化韻是由“兒”弱化為[?]類音后與其前音節合音形成的。
(二)“兒”的[u]類語音形式
趙日新曾提出[u ou]類兒化韻是由“兒”的[ul]音形成的[17],下面就對這一觀點進行剖析。如前所述,漢語方言中的邊音后綴要么自成音節,要么嵌入其前音節的聲、韻母之間成為中綴,不可能像張慧麗所說的那樣:邊音處于音節末位置會變為一個后圓元音。相應地,[u ou]類兒化韻也不可能由“兒”的[l]類音形成。從理論上講,按照合音變韻的一般原理,[u ou]類兒化韻應是由“兒”的[u]類音與前字音節合音形成的,但我們需要在文獻中找到“兒”讀[u]類音的證據。
趙日新指出,[u ou]類兒化韻來源于“兒”音[u],作者雖然提到趙祎缺所考察的四部河南方言韻書
中[70],的確未見“兒”讀[u]類音的記載,不過,在官話方言中,“兒”不乏平舌元音的讀法,并分別以晉城方言和獲嘉方言中存在的[?]類Z變韻和[u]類Z變韻為例進行說明[17]。實際上,[?]類Z變韻與[u]類Z變韻是不同時間層次上的兩類變韻,并且[?]與[u]音值差異較大,應該不存在語音上的先后演變關系。因此,僅用與[u]類Z變韻共享平舌語音特征的[?]類Z變韻來說明“兒”音[u]的存在,并不能令人信服。同時,在論證Z變韻的合音后綴是“兒”的過程中,又以[u]類Z變韻的存在作為“兒”音[u]的證據,似有循環論證之嫌。
那么,“兒”存在[u]類音或者與[u]相關的音值嗎?明末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羅馬字注音文章中,曾記錄了明末的官話聲母系統,在對“而、爾、耳、二”等日母字進行描寫時,利氏記作[lh]。陳默認為,它不表示卷舌元音[?],因為[?]的形成應與知章組字進入“支思”韻相聯系。而利氏所記的官話音里,止攝知章組字還沒有進入“支思”韻,與精莊組字寫法不同。如:知chi、世xi、思su、士su。因此,[lh]很可能是像山東、河北某些地區“兒”字讀[l?]那樣[71]。成書于明代天啟六年(1626)的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記錄“兒”的音值為[ul];出版于清代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瓦羅的《華語官話語法》中,“兒”的記音也為[ul]。但關于[ul]的具體讀音,目前學界還存在不同看法。艾紅娟曾對此進行了探究,認為[ul]的實際可能音值是[u?]。作者還指出,卷舌音會使第三共振峰明顯降低,而圓唇音有降低所有共振峰的作用,兩者在聽覺上是相似的,圓唇化是對卷舌化的一種聽覺上的模仿[19]。筆者對此持肯定態度,并認為《西儒耳目資》與《華語官話語法》中“兒”的記音[ul],可作為“兒”曾存在[u]類音的證據。
除歷時文獻的記載以外,漢語方言中也存在“兒”讀[+后][+圓]特征的現象。支建剛指出,南方地區有不少[+后][+圓]特征的“兒”,主要分布于樅陽[?u/?o]、池州[?/?]、無為[?]、桐城[?]、岳西[??]、潛山[?o](以上安徽),射陽[?]、江都[?]、揚中[?](以上江蘇),其中江西地區較多,如:樂安[o]、樟樹[o]、萬安[o]、余干[?]、興國[?u/?o]、尋烏[lu]等[15]。
總之,具有[+后][+圓]特征的“兒”綴是有其存在的方言音韻基礎的。同時,支建剛通過研究“子”綴在相關方言中的讀音及其在歷史文獻中的反映,闡述了后圓特征的“子”綴也有其存在的方言音韻基礎[15]。這在上文中已經提及,不再贅述。既然“兒”綴與“子”綴都有讀為后圓特征音的來自共時平面和歷時層面的證據,那么,單就語音形式而言,究竟是“兒”綴參與了Z變韻還是“子”綴參與了Z變韻呢?筆者認為,是“兒”綴參與了Z變韻,Z變韻的合音后綴是早期“兒”而非“子”。因為我們無法闡明“子”這樣一個中古屬精組止攝之韻開口三等韻的字,是如何演變為[-u/-o]的,卻可以解釋“兒”讀[-u]類音的原因。根據朱曉農、焦妮娜的研究,當“兒”音演變為卷舌元音[?]后,再發生低化、后化、裂化現象,就可以演變為各式卷舌元音[?u、?r、?r、??r],最后去卷舌而變為各種純元音、甚至復元音[50]。
趙日新還通過方言中[?]類兒化韻的存在,來說明“兒”早期可能曾有過[u o ou]一類的音[17],這一論證是比較可信的。因為[?]與[u]共享[+后][+高]的語音特征,[u]去掉圓唇特征后即為[?],[?]是展唇形式的[u]。[?]與[u]在語音形式上的相似性,的確能說明它們在發生學上可能存在同一性。馮雪利[18]、朱玉柱[20]等都認為,相較于[?]類變韻,[u]類變韻應該屬于更早的層次。那么,[?]類變韻形式是如何由[u]類變韻演化而來的呢?換句話說,[u]類變韻是如何演變為[?]類變韻的呢?朱玉柱
指出,如果[u]類變韻與[?]類變韻之間是歷時演變關系,兩者之間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或者是語言中應該有過渡階段的殘存形式,不過事實并非如此。根據武陟大虹橋鄉方言基本韻母[?]同時存在[u]類和[?]類兩種變韻形式來看,[?ou]和[??]之間的對應基本整齊,并且只是早晚期變韻形式的差別。朱玉柱進一步指出,這種差別可能是受接觸影響所致,并且[?]類變韻采取的演化策略是直接占據[?ou]中[ou]的位置[20]。對此,我們期待能夠發現更多語料,來說明[u]類變韻與[?]類變韻之間的關系:它們到底是歷時的先后演化關系,還是共時的替換與被替換的關系。
需要指出的是,漢語方言中也存在所謂“子”讀鼻音的現象。辛菊指出,在山西翼城城關及附近,“-子”讀?0,其他地方則念n??0[72]。賀巍也指出,在河南濟源方言中,陰聲韻和入聲韻基本韻母[y,y?]Z變韻后,成為長音型的[-?]尾陽聲韻[73]。我們知道,高元音單韻母或主元音為高元音的入聲韻基本韻母,所對應的變韻韻母為拼合型,從拼合型變韻韻母的語音形式中可以提取出合音后綴的語音特征。因此,濟源方言Z變韻的合音后綴除了[u]類音外,個別詞也存在合音后綴為[-?]的情況。史艷鋒也曾對“子”變鼻音/鼻化韻母進行了解釋[10]。我們認為,最好的處理方式是將[-?]視作“兒”,而不是想方設法證明它為“子”,在讀音上,“子”與[-?]是沒有關系的。而“兒”無論是在語音演變史上,還是在現代漢語方言中,都存在讀作[-?]的現象。王力指出,詞尾“子”字與詞尾“兒”字都是由表示實義的詞虛化而來的,小稱是它們詞尾化的基礎[56](P219-220)。也就是說,早期“子”與“兒”在語法功能的表達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將[-?]視作“兒”,不僅在音理上講得通,在語義上也相匹配。方言中的陰聲韻和入聲韻基本韻母Z變韻后讀作陽聲韻、以及“子”尾讀作[-?],這些現象進一步證明了Z變韻的合音后綴是“兒”而不是“子”。
綜上所述,“子”“兒”的空間分布、語法功能、語音形式等,都充分說明了Z變韻的合音后綴是早期“兒”及“子”的早期兒化韻形式,而不是“子”,更不是“頭”。王洪君指出,在山西聞喜方言中,一般子變韻在先,兒化韻在后。如果一個單字有文白兩種讀音,則兒化一般是該字文讀音的兒化,子變一般是白讀音的子變[43]。史艷鋒也指出,在豫北晉語中,兒化韻是比較晚起的變韻現象,如果某單字有子變、兒化兩種變音現象,子變韻往往老年人相對使用較多,兒化韻中青年人使用較多。例如:鳳泉話中的“成年雞”,在60歲以下人群叫“小雞兒t?i?r23”,60歲以上人群仍有“小雞t?i:u23”的叫法[10]、[74]。
因此,我們也可以將“子變韻”或“Z變韻”稱為早期兒化韻。
參考文獻:
[1]呂枕甲.運城方言志[M].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1.
[2]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M].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3]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修訂本)[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5.
[4]陳衛恒.古韻之幽交涉與今方言子變韻現象音變原理的一致性[J].殷都學刊,2004,(2).
[5]陳衛恒.豫北方言和漢語的變音[D].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6]陳衛恒.音節與意義暨音系與詞匯化、語法化、主觀化的關聯:豫北方言變音的理論研究[M].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1.
[7]辛永芬.河南浚縣方言的子變韻[J].方言,2006,(3).
[8]張慧麗.漢語方言變韻的語音格局[D].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9]張慧麗.官話方言變韻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10]史艷鋒.豫北晉語單字音與變音現象研究[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11]史艷鋒.漢語開口一等字中的j介音考察——以孟州方言為例[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
[12]史艷鋒.子變韻和子變韻的形成構擬——以孟州方言為例[J].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013,(5).
[13]支建剛.河南林州桂林鎮方言子尾的讀音[J].方言,2015,(2).
[14]支建剛.論官話方言中子變韻的合音成分[A].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語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輯)[C].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
[15]支建剛.試解Z變音之謎:語音篇[A].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語言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輯)[C].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
[16]趙日新.中原地區官話方言弱化變韻現象探析[A].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語言學論叢(第三十六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17]趙日新.豫北方言兒化韻的層次[J].中國語文,2020,(5).
[18]馮雪利.武陟(西滑封)方言的名詞變韻[D].北京:北京語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19]艾紅娟.山西聞喜方言子變韻來源研究[J].學術論壇,2014,(1).
[20]朱玉柱.試析河南武陟(大虹橋鄉)方言的名詞變韻[A].馮勝利,馬秋武主編.韻律語法研究(第三輯)[C].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8.
[21]王臨惠.晉豫一帶方言Z變音源于“頭”后綴試證[J].中國語文,2013,(4).
[22]辛永芬,莊會彬.漢語方言Z變音的類型分布及歷史流變[J].中國語文,2019,(5).
[23]李榮.漢語方言調查手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24]王洪君.漢語非線性音系學——漢語的音系格局與單字音[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5]栗華益.試析漢語方言入聲韻元音分尾現象[J].語言科學,2013,(3).
[26][日]橋本萬太郎.西北方言和中古漢語的硬軟顎音韻尾——中古漢語的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的不同作用[J].語文研究,1982,(1).
[27]賀巖,張慧麗.從邊音到圓唇——Z變韻形成的一種可能途徑[J].現代語文,2016,(5).
[28]董為光.湘鄂贛三界方言的“l”韻尾[J].語言研究,1987,(1).
[29]楊自翔.安徽桐城方言入聲的特點[J].中國語文,1989,(5).
[30]王世華.寶應方言的邊音韻尾[J].方言,1992,(4).
[31]吳波.江淮方言的邊音韻尾[J].語言研究,2007,(1).
[32]石紹浪.漢語方言邊音韻尾的兩個來源[J].語言科學,2010,(6).
[33]栗華益.試析漢語方言入聲韻尾邊音化[J].方言,2013,(4).
[34]馮青青.蘇北方言的邊音韻尾[J].語言科學,2014,(1).
[35]Gusssenhoven, C. amp; Jacobs,H.Understanding Phonology(3rd ed.)[M].London:Hodder Education,2011.
[36]徐通鏘.山西平定方言的“兒化”和晉中的所謂“嵌l詞”[J].中國語文,1981,(6).
[37]董紹克.高密方言的兒化[J].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1).
[38]董紹克.陽谷方言的兒化[J].中國語文,1985,(4).
[39]吳建生.萬榮方言志[M].太原:《語文研究》編輯部,1984.
[40]吳建生.萬榮方言的“子”尾[J].語文研究,1997,(2).
[41]吳云霞.萬榮方言語法研究[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9.
[42]侯精一,溫端政.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R].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3.
[43]王洪君.從山西聞喜的小方言差異看Z變音的衰敗[J].語文研究,2004,(1).
[44]夏俐萍.河南封丘趙崗方言的子變韻[J].方言,2012,(3).
[45]陳衛恒.林州方言“子”尾讀音研究[J].語文研究,2003,(3).
[46]喬全生.晉方言語法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47]王洪君.漢語非線性音系學——漢語的音系格局與單字音(增訂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8]侍建國.歷史語言學:方音比較與層次[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49]李思敬.漢語“兒”[?]音史研究(增訂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50]朱曉農,焦妮娜.晉城方言中的卷舌邊近音[?]——兼論“兒”音的變遷[J].南開語言學刊,2006,(1).
[51]王麗娟.《國語辭典》和《現代漢語詞典》詞綴比較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52]王臨惠.臨猗方言的子尾與子變韻母[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1).
[53]王軍虎.鳳翔方言的子變韻和D變韻[J].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2,(3).
[54]張莉.焦作底層方言的“子”尾——談“子”字綴的變韻及其相關問題[J].焦作大學學報,2009,(2).
[55]楊彥寶.漢語方言名詞后綴“子”“兒”的地理分布差異分析[J].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7).
[56]王力.漢語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7]孫青林.山西陽高方言的子變韻[J].現代語文,2014,(12).
[58]樂玲華.阜陽地區方言“子尾詞”的初步考察[J].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1).
[59]毋效智.扶風方言[M].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5.
[60]代國英.邢臺方言的“子”尾詞研究[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61]史素芬.晉東南方言的“子尾”研究[J].語文研究,2012,(3).
[62]張娟.河南和山西方言中的Z變韻研究[D].北京: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63]高永奇.河南浚縣話中的子變韻及其功能[A].天津:天津市語言學會年會論文[C].2000.
[64]高兵,吳繼章.河北方言中與兒化有關的問題[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
[65]施向東,陳默.再探漢語“兒”音的演變[A].馬慶株,石鋒,王澤鵬主編.劉叔新先生七十華誕紀念文集[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
[66]裴澤仁.明代流民與豫西方言——河南方言的形成(二)[J].中州學刊,1990,(4).
[67]孫立新.陜南方言略說[J].方言,1998,(2).
[68]高曉虹.山東方言的平舌兒化韻[A].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語言學論叢(第五十三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69]劉麗麗.安徽休寧縣溪口方言的兒化現象[J].牡丹江大學學報,2008,(8).
[70]趙祎缺.明清河南韻書韻圖所反映汴洛地區古止開三日母字的演變[A].開封:第四屆韻律語法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C].2017.
[71]陳默.兒音演變之我見[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6).
[72]辛菊.翼城方言“子”尾的特點[J].語文研究,1999,(1).
[73]賀巍.濟源方言記略[J].方言,1981,(1).
[74]史艷鋒.豫北晉語的兒化[J].語言研究,2017,(1).
The Suffix of the Z Rime Alternation Phenomena
Wei Mengy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ingboTech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There is still no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issue of the suffix of the Z rime alternation phenomena, and there are mainly four viewpoints: the suffix of the Z rime alternation phenomena is “zi(子)”; the suffix of the Z rime alternation phenomena is “er(兒)”; the suffix of the Z rime alternation phenomena is “tou(頭)”; the suffix of the Z rime alternation phenomena is a mix of “zi(子)” and “er(兒)”. On the basis of pointing out the problems exist in these previous opinions through rational reflections and brief comments on them,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s the suffix of the Z rime alternation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the phonetic forms of the suffix “zi(子)” and the suffix “er(兒)” combined with the related dialect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 facts. And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suffix of the Z rime alternation phenomena is the earlier phonetic form of “er(兒)” and the earlier phonetic form of the retroflex final of “zi(子)”, not “zi(子)”, let alone “tou(頭)”.
Key words:Z rime alternation phenomena;sound combination suffix;retroflex final;the suffix “zi(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