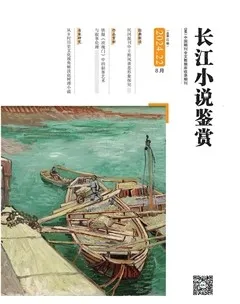身份的偏移與人性的矛盾
[摘要]作為京派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沈從文向來以“鄉下人”自居,并在其作品中構建自己理想的鄉土社會,以此來表達對城市化進程中工業文明異化的深深排拒。在《丈夫》中,沈從文通過描寫丈夫對自我身份認知的變化來展現人性的矛盾,并從丈夫身份的回歸中,表達對原始人性的贊揚,以“歸向自然”的原始主義傾向建構起其鄉土文學獨特的審美價值。
[關鍵詞]沈從文 《丈夫》 身份偏移 人性書寫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2-0017-04
沈從文的小說《丈夫》問世于1930年,作家以冷靜樸實的風格,講述了一個關于湘西船妓的故事:年輕鄉村女子“老七”因家境貧寒被迫在城市的花船上當船妓,用出賣身體賺取的金錢來補貼家庭開支,她的丈夫則留在鄉下耕地種田。在黃莊,“賣妻為妓”不僅是極其平常的事,這種丈夫也成為一個群體。
盡管《丈夫》這部作品在題材上略顯邊緣化,但是沈從文并未沉溺于表面的情色場面描寫,反而將筆墨聚焦于丈夫到城中探望妻子時心境的微妙變化。作家從城鄉對峙的宏觀視角出發,深刻揭示身為“鄉下人”的丈夫與“城里人”的妻子之間家庭地位的轉換,以及丈夫在自我身份認知上的偏移,這種轉變不僅展現出人性的復雜與矛盾,更凸顯出沈從文對自然、淳樸人性的熱切呼喚。
一、身份認知偏移背后的社會根源
《丈夫》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湘西的黃莊。黃莊是一個極度貧窮落后的小村莊,“一點點收成照例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1],無論人們多么省吃儉用、吃苦耐勞,還是連吃飯這種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都解決不了,甚至“一年中四分之一時間,即或用紅薯葉和糠灰拌和充饑”[1]。為了生存,這些家庭中的年輕妻子只得出鄉討生活,在大河碼頭邊的船上賣身以貼補家用,而這些女子的行為竟是丈夫默許甚至逼迫的。于是,來到城里的妻子成為賺錢養家的“頂梁柱”,顛覆了傳統家庭結構中丈夫的經濟地位,并且丈夫成為留守在鄉下需要被供養的人。然而,這種異地的生活方式不僅導致夫妻之間情感的疏離,更加劇了傳統家庭結構的瓦解。在此背景下,夫妻雙方的家庭角色發生明顯轉變,丈夫的定位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家庭責任承擔者,妻子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丈夫的附庸。隨著家庭內部生活方式的變遷,丈夫再也不敢將妻子視為出氣筒而隨意打罵,原本溫柔賢淑的妻子在婚姻關系中逐漸擺脫被動與依賴,與原本在家庭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丈夫之間的身份界限開始模糊,甚至發生一定程度的轉換。這種身份變換并非偶然發生的,而是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經濟實力一定程度上決定家庭地位。來到城市的妻子逐漸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在自給自足的同時,還能為家庭提供經濟支持。相較之下,鄉下的丈夫務農所得就難以支撐家庭開支,再加上受到上層勢力的壓榨,經濟狀況更是捉襟見肘。物質基礎的提高帶來家庭的安全感,妻子自然會獲得更高的地位和尊重。其次,城里的妻子們不僅收入提高了,而且由于接觸了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物,見識也有所增長。而留在鄉下閉塞環境中老實本分的丈夫,重新面對妻子時自然產生了一種落差感和自卑心理。在《丈夫》中,鄉下的男子面對城里的妻子時有兩次復雜的心理活動。第一次是再見面時,妻子已然擺脫鄉下人的姿態,不論是氣色、穿著,還是說話的神態,已完全與鄉下時不同。第二次是手中的煙管被妻子換成香煙,這引起丈夫內心極大的震動。對于鄉下的丈夫來說,香煙是他所觸及不到的新鮮事物,一根香煙增強了丈夫與妻子間的疏離感和不對稱的社會地位。于是,傳統家庭中的男女地位發生置換,即原本在家庭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男性被邊緣化。在城市空間中,丈夫的邊緣化地位被進一步強化并產生了雙重性,即不僅在小家庭中處于被動地位,在城市嚴格的階級秩序之下更是成為社會的底層。丈夫以“鄉下人”的身份進入城市,面對陌生的事物和人際關系自然呈現出一種不適、茫然無措和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導致丈夫身上“男性氣概”的消失,在大方自信且已經適應城市生活的妻子面前,丈夫的復雜心理進一步外化為主導地位的喪失,丈夫便不成“丈夫”了。
傳統鄉土社會的結構是十分穩定的,但是由于農村經濟的困境,民眾對于基本物質需求的渴望愈發強烈,鄉下人紛紛涌入城市以尋求生存之道,不可避免地導致傳統家庭倫理的瓦解和重構。《丈夫》中,將不急于生養的妻子送進城里當船妓,在當時鄉下人眼中是一件并不與道德相悖的事情,并且成了一種“生意”,成了一種合“禮”的行為,而夫妻雙方為了物質的豐裕,也只能忍受這種扭曲變異的家庭倫理觀,這是傳統道德秩序對城市異化文明的服膺。在商業文明的作用下,以親密情感為紐帶的兩性關系被商品買賣的關系替代,工業異化文明對自然原生文明的侵襲已經深入到傳統家庭的內部結構之中。
可見,在生存這一基本需求的驅使下,鄉土社會中的道德準則并非一成不變或嚴格穩定。為了生命的延續與生存權益的保障,人們往往會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自身的道德判斷和行為準則。沈從文通過細膩的筆觸,深刻剖析男子對自我丈夫身份認知偏移背后的社會根源和心理動因,為我們理解鄉土社會同都市文明的沖突與融合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二、人性呼喚中傳統身份的回歸
盡管城市的文明與繁華對鄉村的淳樸人性帶來不小的沖擊,傳統的家庭結構和夫妻關系也在這種沖擊下發生深刻的變化。然而,在沈從文的筆下,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人性的美好與溫暖并未被完全磨滅。在《丈夫》中,是人性的原始本能和妻子的牽掛喚醒了年輕男子身為丈夫的意識的覺醒,于是在探望妻子的過程中丈夫迷失的身份得以漸漸回歸。
丈夫身份從迷失到重拾的過程反映出人性的多變與復雜。這首先體現在男子對水保的態度由尊重到憤怒的轉變上。最初,男子對水保持有深深的敬意,而這種尊重源于水保所代表的權威和地位。作為鄉下人的男子來到城里,面對的是陌生的環境、冷漠的人際關系還有不熟悉的生活方式,內心自然而然產生了局促感。基于二人社會地位的顯著差異,男子在面對水保時,原先的局促不安情緒逐漸深化為自卑自慚的心理狀態。然而,水保這位所謂的“大人物”竟展現出傾聽的姿態,使得年輕男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于是,男子孤獨寂寞的心理短暫地被水保療愈。另外,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丈夫對妻子的嫖客如此“大度”,甚至因為自己和大人物說了話而洋洋得意,體現出男子內心深處強烈的自卑感,而這種自卑感一方面來源于丈夫來到城市后一直所處的被忽視的境遇,正如阿德勒提出的,人在被忽視時容易產生錯誤的認知觀念[2]。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境的變化,男子開始逐漸感受到水保所帶來的壓力與束縛,這種壓力源于對家庭角色、社會角色的期待與自我實現之間的沖突。直到饑餓的原始本能喚醒他的自然人性,作為丈夫應有的嫉妒和羞辱終于從他的身體里噴薄而出,點不燃的濕柴引燃他內心的怒火,他對水保的態度發生顛覆性的轉變,水保不再是他尊敬的大人物,他對水保的印象變成了“一個用酒糟同紅血所捏成的橘皮紅色四方臉”[1]和“極其討厭的神氣”[1],對水保的尊重逐漸轉化為憤怒和不滿。對現狀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的迷茫使男子開始質疑水保的身份地位,甚至開始反思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選擇。經過一系列的掙扎和思考,男子最終實現身份的回歸,重新找回自己角色的定位和方向。由此,在男子的丈夫身份從迷失走向回歸的過程中,人性的復雜體現得淋漓盡致。
作者通過描述男性面對水保時的態度變化,生動展示了年輕男子重新接受丈夫身份的心理過程。而這對年輕夫妻之間的愛也是丈夫身份意識和理性回歸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可以看出,即使傳統的夫妻關系已經被商品化的物欲侵襲,老七與丈夫之間仍然互相關心和關愛,兩性之間的感情正是家庭和睦的強大力量。丈夫一個一個地挑出圓而發烏金光澤的大板栗帶給城里的妻子,自己卻不舍得吃,又“背了整籮整簍的紅薯糍粑之類,趕到市上來”[1]。妻子記得丈夫喜歡口含片糖的習慣,也記得丈夫拉胡琴的愛好,并在街上為丈夫尋來一把好琴討丈夫歡心。夫妻之愛使我們看到他們對物質財富的追求背后所隱藏的美好本性。他們彈琴歡唱,感受到久違的和睦與幸福。但是好景不長,美好的氛圍被醉酒的士兵們打破,久別重逢的夫妻再次被外力沖散,而身為丈夫的男子卻無能為力,異化的社會身份與自然人性的矛盾就此浮出水面。
在深入分析男子所經歷的復雜情感和心理變化時,我們發現,當男子面對妻子時,原本存在的性沖動本能受到外部多重因素的強烈抑制。這種抑制不僅加劇了他對自我身份的焦慮感,更促使他不得不重新審視“送妻為妓”這一決策的正當性。喝醉的士兵、巡官、酒保,這些人都在剝奪男子身為丈夫的權利,使他不僅無法與妻子同房,甚至連與妻子說話的權利也被剝奪。這一系列外在因素的干預,對男子的心理造成極大的沖擊,迫使他不得不面對現實,重新思考自己的處境與未來。于是,在妻子將士兵給的五張票子塞到男子手中時,一向沉默的男子忍不住哭了起來,這哭是內心矛盾、壓抑情緒的釋放,更是自然人性和原始本能的徹底回歸。這哭,不僅讓男子開始反思當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也讓妻子更加深刻體會到丈夫的無奈與辛酸。于是,夫妻倆第二天主動告別城市回到鄉下的結局,不僅意味著夫妻二人傳統身份的徹底回歸,更象征著自然美好人性突破重重枷鎖的重新展現。
通過《丈夫》這部作品,沈從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充滿矛盾與掙扎的世界,同時也表達了他堅信人性之美好與溫暖。他讓我們看到,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人性的光輝依然閃耀,并溫暖每一個心靈。
三、牧歌外衣下的啟蒙選擇
沈從文在其作品中深入剖析了城鄉對立情境下人性的紛繁復雜與內在矛盾,而這些作品的結局往往透出濃重的悲劇色彩。在凄美的挽歌中,沈從文不僅批判了城市工業文明對自然本真人性的扭曲,更揭示了落后國民性所導致的人生悲劇。
不同于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中對“丑”的深刻揭示,沈從文在文學作品中傾向于通過“美”的描繪與“丑”的對比,引導讀者對傳統文明的不合理之處進行反思。丁帆評價這種藝術手法反映出沈從文“‘擇美’而‘遮丑’的美學觀念”[3]。從這個角度來看,沈從文的鄉土小說并沒有摒棄“五四”時期的啟蒙傳統,而是開創了一條嶄新的啟蒙道路。他巧妙地將批判的鋒芒藏匿于鄉村純樸原始的道德風貌之下,轉而頌揚那些美好、原始、自然的人性,并對鄉村的人物與景致進行美化處理,形成一種更為含蓄的批判方式,既保留了批判的力度,又增添了藝術的美感。學者張清華曾指出,沈從文在繼承“五四”作家啟蒙使命的同時,在文化策略上卻與前輩作家大相徑庭,他堅守的是傳統(湘西)的價值觀念[4]。然而,這種堅守也帶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因為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
不同于《邊城》和《蕭蕭》,沈從文在《丈夫》中為這對年輕夫妻設置了一個溫情的結局。但事實上他并沒有放棄“血和淚”的書寫,而是將悲苦掩藏起來。因為他認為“神圣偉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攤血一把淚,一個聰明的作家寫人類痛苦是用微笑來表現的”[5]。
《丈夫》的開放式結局激發了讀者的無盡想象。返鄉的夫婦命運將會如何?這看似溫情的結局是否一樣蘊含著悲情呢?答案是肯定的。離鄉又返鄉的妻子,她已經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城市的熏陶,這種熏陶涉及了方方面面,不僅生活習慣被改變,連精神也遭到城市商業文明的浸染。她們嘗到了獨立自主的甜頭,賺錢的快感使她們將道德拋之腦后。那么,當她們再次面對鄉村的落后與貧困時,又能否重新適應與接納呢?同時,丈夫又能否毫無芥蒂地接受“從良”的妻子呢?可以看出,雖然作者有意在構建烏托邦般的鄉下世界,想要用自然的“力和真”來與矯揉造作的“城市人”情感相抗衡,但他逃避了時代和經濟等因素下的集體無意識對人思想的異化。于是,夫妻一同返鄉的結局,也變成了城鄉沖突之下的權宜之策。
值得關注的是,面對城鄉對立時的復雜心境在京派鄉土作家的寫作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現象。除了沈從文,廢名、蕭乾、凌叔華等京派小說家在面對城市現代文明與農村傳統文明的沖突時,也展現出復雜而多元的心態。他們的作品不僅反映這一時代的社會變革,更深入挖掘人性在這一變革中的掙扎與蛻變。他們和沈從文一樣,試圖從日漸沒落的傳統文化中挖掘出用以抵抗西方文明的民族美德。但是,在當時民族矛盾的嚴峻現實之下,他們的文化立場顯得虛浮無依,宛如海市蜃樓,難以在現實中穩固立足。
四、結語
面對“新”與“舊”的文化沖突時,沈從文選擇回歸人類的原始狀態來消解文化所造成的人的困頓,在古老的文明中來尋找“避難所”,體現出他對原始主義的探索。沈從文將覺醒的丈夫作為自然生命力的象征,寄托了他重塑美好人性與民族品質的深切期盼。特別是年輕夫婦最終選擇回到鄉下的情節,不僅展現了沈從文回歸自然、返璞歸真的原始主義情感傾向,更揭示了他對于人性復歸的渴望。在《邊城》《蕭蕭》和《三三》等小說中,沈從文一再彰顯湘西鄉民雄壯的生命力和溫情的人際關系,“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將這分野蠻氣質當作火炬,引燃整個民族青春之焰”[6]。可見,沈從文的原始主義并非對西方原始主義理念的簡單回溯,而是一種獨特的東方探索。他期望通過重新闡釋傳統文化,探索其中可供參考之內容,從而制定對民族復興有益的策略。
在《丈夫》這部作品中,沈從文在追求美好人性回歸的同時,也在積極尋找療愈尊嚴喪失、人性沉淪的良策。他提出的這劑良方,便是回歸自然,尋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道。在社會激蕩、階級矛盾尖銳的時局下,沈從文原始主義之下的啟蒙路徑選擇顯然是理想化的,也必然走向“悲劇”的命運,但這種“悲劇”或許正是沈從文及其他京派文人的價值所在。沈從文以其獨特的文學風格和深刻的人文關懷,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他通過細膩的筆觸和豐富的情感,描繪了一個既真實又充滿詩意的文學世界,令讀者感受到人性的美好與純真,引發讀者思考現代化進程中如何保持這些寶貴品質。科技的飛速發展、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人們常常忽略人性的美好與純真,忽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沈從文的作品正是提醒人們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保持對人性、自然和社會的敬畏和尊重。
參考文獻
[1] 徐俊西.海上文學百家文庫(沈從文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2] 阿德勒.自卑與超越[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
[3]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4] 張清華.抗拒的神話和轉向的啟蒙——對沈從文文化策略的一個再回顧[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4).
[5] 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1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
[6] 蘇雪林.蘇雪林文集(第3卷)[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
(特約編輯" 張" "帆)
作者簡介:宋涵,河南理工大學文法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