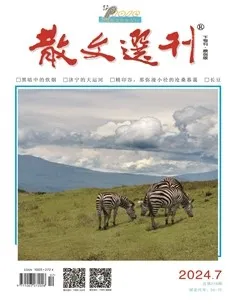往事,咸咸
那是一段瘦骨嶙峋的光陰。
冬天,很冷。日子,很慢,如果沒有晝與夜的交替,我以為它按下了暫停鍵。帶著沙塵的風總是纏著我,怎么也擺脫不了。如果說在那枯燥、乏味的冬天里,還有什么味道,那便是母親做的咸菜。
時間進入十月份,天氣一天比一天冷,地里的白菜正在經歷著霜降。母親說,葉子紅了的時候,就可以腌漬咸菜。
大山里的葉子全紅了,村子里家家戶戶院子堆滿了白菜。母親將白菜一擔擔挑回來,在院子里撿,一瓣一瓣掰下來,然后用笤帚清掃蟲子、蟲屎。那時候沒有農藥,白菜葉全是小洞洞,飽餐后的蟲子胖乎乎的,躺在葉片間休息,在那貧窮的年月里,長著嘴巴的所有動物都在餓著肚子,唯有這些蟲子未曾嘗到饑餓的滋味。母親笤帚所到之處,蟲子紛紛落在院子里,先是蜷縮成一個“0”形,假寐三五秒鐘,便一縱一縱地四下逃跑。離開了白菜的保護,它們怎么可能逃脫老母雞那圓乎乎、賊溜溜、一直在覓食的小眼睛呢?
清掃過的白菜,母親再用抹布擦干凈根部的泥土,然后洗。洗過的白菜得晾干后才能入缸。咸菜的味道在最后一道工序——兌鹽水。鹽多了會苦,菜色發黑,鹽少了會酸,會腐爛。四嬸等好幾個阿姨都掌握不好鹽和菜的比例,每每都是母親幫她們兌鹽水。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后,再用一塊大石頭壓在菜上面,鹽水得漫過石頭,然后封缸。一個月后,菜缸解封了,似乎村子里到處亂竄的風、煙囪里冒出的炊煙都帶著咸菜的味道。
母親腌漬的咸菜不僅可口,色澤更是一絕,菜心呈姜黃色,菜股奶白色,葉子翠綠色。就這色澤,足以讓人饞涎欲滴。村子里那些懶婆姨家里沒有咸菜,記得隔三岔五,總有人拿著缽缽到我家要咸菜,特別是張阿姨,嘴上抹了蜜似的,使勁地夸母親做的咸菜有多么好吃,母親笑笑算是回應。只要來我家要咸菜的,母親都會滿足他們的要求。看著他們抱著缽缽、罐罐滿意地離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們拿一罐,我們就少一罐,還未到春天的野菜長大,我家的咸菜缸就見底了,年年如此。
往事,咸咸,裝滿我心靈的谷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