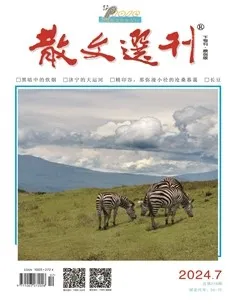故鄉的初夏
初夏,故鄉迎來了一位令人動容的歌唱家:“快快布谷,快快布谷!”是布谷鳥在催促農民播種呢。
此時,大地開始做擴胸運動,種子們到處滾動,開啟新的生命歷程,輝煌地奔赴各自的前程。時間讓種子與初夏緊緊相擁。有種子的日子,時間走得很穩,很安詳,也很放心。種子曾與無數個暗夜較量,終于在初夏的某個黎明被牛脖子上悠揚的搖鈴聲叫醒,迎著朝陽,在父親豐碩的種子袋里一路高歌,朝圣般的走向田野,又一次成為故鄉的原風景。
父親站在黃土地里,用嗅覺感受著大地的恩賜,他一手揚起牛鞭,在空中啪啪作響,一手扶著鐵犁,嘴里對牛吆喝著:噠噠咧咧——那聲音在田野里隨風飄得很遠,甩鞭子的聲音更是響徹天空。田野因之震動,土地因犁的深入而生動。但是,父親從未把鞭子落到GlX20zEtOFAq8XXwXAl9st7AerrW1pH/1MZ0Tl9w6b8=牛身上,他總是稱牛為老伙計。
播種的琴弦奏響,大地注入瓊漿,著色墨的芳香,用歌聲書寫一音一符,種子整齊地排列著,編織著父親夢想的樂章。那些有節奏的旋律,譜寫了一曲曲關于勞動的動人歌謠。母親在地里一邊撒玉米的種子,一邊祈禱,遇上一顆有思想的種子,“我——要——發芽”,她喜上眉梢。“天光露水白洋洋,寧可日夜曬太陽”,有一顆唱“懶漢哥”的種子,逃落到地沿兒,她破口大罵,“你這個懶鬼,滾回來!”然后把種子扯回到地里。
狹長的田壟宋詞一般抒情地低吟著,飽滿的種子仿佛唐詩中走來一位位豐腴華貴的侍女。母親撒一顆種子,彎一下腰,好像是給大地行著一種古老虔誠的謝禮。她的老繭掠過復蘇的土層,那些帶著她體溫的種子沾滿了泥土的芬芳。土坑彌合眼瞼的剎那,她的嘴角掛著一輪微笑的圓月。
看著那深入泥土的種子,父親靜默不言,大漠孤煙似的雄渾氣勢里,種子在土地上翻花沸騰,嫁接著美麗的琴音,勇敢飛翔。當所有的種子紛紛落入地里,一場盛大的勞動場面宣告結束。父親舍不得將犁放在牛身上,怕累壞了牛,怕磕壞了犁。一張犁,只有扛在自己肩上,他才踏實。他覺得自己就是一頭牛,一頭永不停息犁地的牛,他彎腰的身影,早已和牛重疊在了一起。
河兩岸青春期的楊柳樹,樹葉密集,像伸開雙手的大傘,被高高地舉在空中。它們由嫩綠色變為深綠色,拂動著新生的柔枝,倒映在河面上,河水被染上綠色,仿佛一河翡翠向東流去。水草被水推著,搖著,悠閑地扭動著纖細的腰肢。“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響,跳下了山崗走過了草地來到我身旁。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唱著歌兒彈著琴弦流向遠方……”小蝌蚪含情脈脈地唱給流水,“最是流水留不住”,它知道流水心有遠方。只有經過高山、險谷,水聲才能張揚個性,充滿靈性。流水忽左忽右,或拋物線,或曲線……前面越有障礙物,它越有激情。
回家的路上,父親去河邊掬一捧水,洗去滿身的疲倦。他先是把農具往地上輕輕一放,然后挽起袖子,把手伸入河水的懷抱,多么有儀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