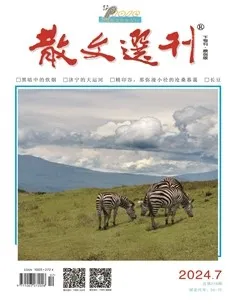歪脖子樹會講故事
小時候坐在爸爸自行車的后座上,從縣城到鄉下一路顛得屁股疼。視線越過爸爸的后背,不時遠眺,就盼望著一棵歪脖子樹的出現,那代表了這段顛簸的路程終于抵達了終點。
歪脖子樹就站在老家村口,它的樹冠張開龐大的懷抱,隨便一伸肢腰,便遮住了奶奶家的半個院子。歪脖子樹是棵老槐樹,傳說它有百余歲的高齡。它曾經被雷電從頂端劈開過,根基不穩,便成了傾斜的姿態。每年春天四五月份,是歪脖子樹最受矚目的時刻。一串串雪白的花穗掛滿枝條,流蘇般飄蕩,輕觸微風,美得很不真實。那些花兒,仿佛是大地的呼吸,被塵封在泥土里的香氛,從小小的花蕊里釋放出來。花香一徑穿行,越過池塘、羊腸小道、碧野和春山,忽而緊窄、忽而開闊。
槐花落了,歪脖子樹就變成了翠綠色,滿樹都是被陽光染成金邊的橢圓葉子,遠看像一塊晶瑩透亮的翡翠。
上小學之前,我的大部分童年時光都是在奶奶家度過的,住個把月,再接回縣城,如此往復。
我是喜歡住在奶奶家的,自由的鄉野向來是孩子們的樂園,更何況還有一個與我年紀相仿的玩伴——堂妹,每天早晨她會從村東頭出發,跑到村西頭奶奶家,大喊一聲:“爬樹去!”我們便攜手出門了。
歪脖子樹是村里孩子們的攀爬架,大點兒的孩子會爬到樹頂,離地近十米高。我和堂妹膽子小,爬上第一層枝丫便滿足地坐在樹上看風景。
如果把歪脖子樹擬人,我想,它一定是拄著拐棍的白胡子老頭兒形象,慈祥又寬厚。我們在它身上爬上爬下,從來沒有一個孩子從樹上掉下來摔傷過。
有一次,村里一個老人還佐證說,小時候他從樹頂滑落,心想:完了,要摔地上了。誰知恍惚之中,竟安穩地落在底層軟綿綿的樹枝上,仿佛有一只大手接住了他。除了被樹枝上的刺兒劃破些小口子,沒受半點兒傷。聽到這個故事時,我們都驚得張大了嘴巴。
村里偶爾會有賣貨郎挑著擔子經過,他總是停在歪脖子樹下面賣貨。遠遠地看到手拿撥浪鼓的賣貨郎,孩子們會迅速地從樹上溜下來,將他圍住。那撥浪鼓仿佛被賣貨郎搖出了語言的感覺,聲音聽起來似在說:“不來?等等!”
孩子們的小腦袋聚攏成一個圓圈,圍觀著賣貨郎如百寶箱一般的竹籮Pkpni8lkkODBJ99u2pkjWpagz7lcYhEZdSaDVpsNNZw=筐,里面有針線、玩具、花布、陶瓷等等商品。奶奶曾經很奢侈地給我和堂妹買了小鳥形狀的哨子,還用繩子穿起來,掛在脖子上,從此我倆在村子里行走便有了伴奏,時不時要炫耀地吹響它。
夏天吃完晚飯,村里的人們喜歡聚在歪脖子樹下乘涼,奶奶一手拿一把扇子,左右開工,為我和堂妹驅趕著蚊子,我的耳邊陸續響起大人們七嘴八舌的聊天。在樹下,你會毫不費力地獲悉村子里一天發生的所有事情。
一個叫聾子的老漢,開始細數家里幾個兒子的飯量,孩子們都已長成壯年,一頓飯要吃掉一籠屜饅頭。聾子老漢在戰爭年代當過民工,一個炸彈震聾了他的耳朵。一個包頭巾的媳婦開始數落她的男人又發脾氣,男人因為旋耕機操作失誤,被切掉了雙腿,整日郁郁寡歡。一個禿了頭頂的男人朝地面上叩了一下煙袋鍋子,說起他去山溝溝里摟草時遇到狼的經歷。那狼披了一身油亮亮的黑灰色的毛,他一邊大喊道:畜生,走開!一邊揮舞著鐵锨喝退了狼。他描述的場景驚心動魄,一人如何英勇大戰惡狼的畫面呼之欲出。然而坐在一旁的媳婦卻撇撇嘴,咧開嗓子喊:“瞎說,那天你回來時都光著腳,嚇得鞋都跑丟了。”當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版本被抖了出來,眾人哄笑,男人也跟著尷尬地嘿嘿笑著。
大人們的聊天聲在我耳邊由近而遠,直至被歪脖子樹葉子搖晃的沙沙聲覆蓋,它一定聽過很多故事吧,怕忘了要趕緊記下來,沙沙聲就是筆劃過紙面的聲音。
我仰頭看著與漫天星辰融為一體的歪脖子樹,月光順著它粗糙的樹皮滑落,它伸展著灰色的枝干,由攏至散,把墨色的天幕襯托得越發得高。
我不知道多少人從樹下仰起面龐,承接這命運無聲的飄落。時間悄然地穿過每一個人,究竟會留下怎樣的痕跡呢?
歪脖子樹下的往事還有一幕讓我記憶猶新,那就是每到我回縣城的日子,堂妹總是不舍我離開,雖然她和爸爸都非常民主地說,讓我自己決定,但是他們倆的動作都擺出了要拔河的架勢。堂妹站在歪脖子樹一頭大哭,企圖用眼淚將我挽留,爸爸則站在樹那頭,扶著自行車單腳站地,隨時等待出發。
這種選擇對一個五六歲的孩子來說太殘酷了,我站在歪脖子樹下左看右看,難以作出決定。直到現在,我回望那個場景,依然覺得十分為難,站在樹兩頭的情感都讓我難以取舍。
這些是我兒時對歪脖子樹的一些記憶片段,瑣碎而深刻。
后來,我回到縣城讀書,再到城市里工作。這期間,爺爺奶奶相繼離世,那個小村莊便從我的視線中漸漸淡去。只是每年春天,在市場里看到被當作野味售賣的槐花,會買些回來,學著記憶里奶奶的樣子,開水燙一下,做槐花肉餡兒包子、槐花窩頭或者槐花面糊湯。唇齒間綻放的香味是熟悉的味道,歪脖子樹的影子便由遠及近,與故鄉的回憶重疊。
去年中秋,我特意找了機會返回家鄉。村莊富了,瓦房代替了土屋,智慧農業代替了傳統的農耕方式。老樹旁還建起一座紅瓦白墻的小學,附近幾個村子的孩子都在這里上學,堂妹是這所小學的校長,她每天站在老樹下,目送放學后的孩子們奔跑在回家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