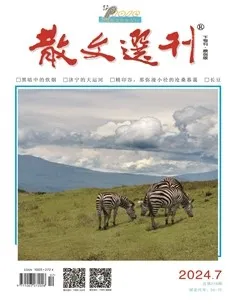沿途經(jīng)過扎尕那
草原上有孩子奔跑,野花灼人。它們無數(shù)次熄滅又被無數(shù)次點(diǎn)亮,這些未來的記憶,沿河流兩岸向上攀緣。
好長時(shí)間了,我的眼睛沒有在高原的天空下啄食到這么多野花和青草。那時(shí),我時(shí)常把窗臺(tái)上的水仙花從一間屋子移到另一間屋子;抑或到庭外的玫瑰園坐一會(huì)兒,聽鳥語,聞花香,但從沒有踏進(jìn)這樣深遠(yuǎn)的草原和樹林,也從未延伸出沒有樓宇、商場和城市道路的風(fēng)景。
這樣,我熟悉的陽光就像一張巨網(wǎng)的留白——在扎尕那路邊的小餐館,變得生澀起來。
從陽光里灑下的雨水,好像就是沖著我來的。我躲在一棵冷杉樹下,聽——那些被敲打的針葉明顯帶有寺院的鐘聲。
一個(gè)小男孩兒在車子里,用衣袖擦拭著玻璃上的水霧,他好像有充足理由證明我是從洮河的彼岸過來的。一群披紅戴綠的女子,被一陣大雨從草叢里趕了出來,但并沒有躲雨的跡象,她們?cè)谝煌敉羲叄从甑螖噭?dòng)鏡子里的云朵。
這清新的空氣,兩只鷹從我的頭頂飛過,一只野兔正離我越來越近。
一棵樹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暗語,懸崖上的瀑布就很難與之交流了。暮色中的千年紅豆杉不是這樣的,它有足夠的能力去理解我仰望時(shí)的疑慮。系在樹上的彩帶,算起來可以牽動(dòng)至某年某月某日的某個(gè)山外人——內(nèi)心的痛處。那時(shí),沒有多余的形式,也沒有告別的說法,圍緊的柵欄好像也不能阻隔對(duì)于外界的念想。
游人走遠(yuǎn),留下各種顏色的彩帶在晚風(fēng)中輕輕飄起。只有紅豆杉自己,依然故我,堅(jiān)守著腳下的泥土。
這讓我想起了山下的一池清泉,涼風(fēng)中,波光不停地晃動(dòng),好像要晃出更多的紅豆杉來,并與水邊的三角槭一起,等候著陌生人的經(jīng)過。
山林中有異鄉(xiāng)人的口音,而他們的腳步卻混雜在一起。黑色的背包裝有食品和雨傘,但他們?cè)陲L(fēng)景中好像已經(jīng)忘乎所以。
崖壁上的水與暮色正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落下來。我認(rèn)識(shí)前方那個(gè)穿長裙的女子,淺藍(lán)的短袖衫繡著金色的邊條,而胸前的那朵蓮花更讓西邊的埡口和深灰槭有了醒目的目標(biāo)。
我是光著腳涉過溪水的,卻很難徒步歸來。然而,這里的確有過一隊(duì)人馬,在黃昏的襯托下,將十個(gè)腳趾頭的印記留在了一塊石頭上。至此我發(fā)現(xiàn),有一只纏著繃帶的草鞋還浸泡在水底——它的生動(dòng),像一串不朽的字符。許多草絮黏著它在水底飄動(dòng),我在想——還是不要驚動(dòng)它吧;也不要驚動(dòng)它身邊的月色和星光。
夜晚,天氣有些冷,但在草地與雪山之間依然有燈火,有回蕩的聲音。
野花讓草原沒有盡頭,它們一路向前,大面積演繹扎尕那的場景。這讓矜持的女子于水邊——不再掩飾本真的面目。她們撩起裙擺,挽起衣袖,讓細(xì)膩的肌膚被陽光與溪水肆意摩挲,好像這樣就能以加速的方式貼近草原的內(nèi)心。
幾只灰鼠并不在我的考察范疇,它們從洞穴中探出頭來,沒有一點(diǎn)兒儀式感,其肢體只會(huì)將草原上的花草弄得悚然顫抖。
而那些慵懶的羊群,也只會(huì)用路來陳述——蠕動(dòng)的白云。它們旁若無人地堵在文明的傷口,讓更多的車輛不得不停歇下來,于無聲處歷練著等待者的性情。唯有牧羊人甩出的鞭子,才能還原出前方的道路和岔口。
暮色降臨,拉桑寺金頂依然熠熠生輝。對(duì)于我——一個(gè)趕路的人,那些拔地而起的石峰并不能賦予我更多的意義。
一群男女將車輛停靠在樹林邊上,好像這樣就能隱匿旅途的秘密。他們?cè)噲D享受山中的寧靜,但跌宕的清流并不會(huì)輕易讓疲憊的身體停歇下來。即便到深夜,前方的山坡依然會(huì)有曖昧的月光,柔軟的花草和對(duì)流的夜風(fēng)。
有時(shí)我也會(huì)站在風(fēng)口——想遠(yuǎn)方;抑或冥悟著于深山入眠之后的感覺。但導(dǎo)航持續(xù)提醒——前方還有許多路程,正等待著我去追趕。
夕陽,把光蓋山的石峰點(diǎn)燃,就以為天空不會(huì)再孤獨(dú)了。
一只灰鸛以燒紅的石壁為背景,以鷹的姿態(tài),欺騙了我的視覺,以及山那邊性格溫和的牦牛和羊群。
被石峰環(huán)拱的扎尕那,我以為是幸運(yùn)的。光潔的山坡,錚亮的石壁,依然存續(xù)著冰川的遺跡—— 它們活得艱難,也很浪漫。從透明的穹頂灑下的雨水,好像還會(huì)故意讓我產(chǎn)生幻覺:樓群、廣場、高鐵和賓館,眨眼間就被山嵐霧成了雪山、圣湖和村落;霧成了色彩斑斕一碰就會(huì)成為碎片的藍(lán)、白、黃和粉紅色的小花。
此刻,沿途的黃昏漸漸消失在彼此看不見的峭壁,消失在洮疊古道的必經(jīng)之路。不用多久,我就會(huì)熟悉這里的樹木與村莊,河流與草地;我的骨骼也會(huì)沾染上崖巖的氣質(zhì)。
當(dāng)風(fēng)在暮云中停下來,我的身影已進(jìn)入了旅途的回溯之中。
給一個(gè)埡口起個(gè)名字是不難的,而我的思路總會(huì)被東西兩側(cè)的山峰遮擋著。無論早晨或傍晚,那片灰白的影子,總會(huì)讓我進(jìn)入隧道似的聯(lián)想到冰川的變遷和沉積。
能在如此有靈性的地方走走看看,已經(jīng)是非常幸運(yùn)的事了。延續(xù)的傳統(tǒng)一直在堅(jiān)持著,不愿被現(xiàn)代文明重新打理。因而,我也不能使用被污染過的詞,去觸碰百萬年以前的圣潔。
雪在融化,雪水從高處流下來——既然不愿公開,就讓它們保留那份神秘,然后靜靜地流過每一塊石頭或每一片草地。
與一棵古藤接觸的時(shí)間很短,就讓我與對(duì)面的山峰產(chǎn)生了某種契合。它的藤蔓像成人的胳膊,而藤條和葉子卻毅然生長到了懸崖邊下。
我是在陽光的正南面,拽著它——眺望著對(duì)面的峭壁,以及峭壁上的佛洞與佛像的。在眾佛的目光下,我的心也擁有了一片寧靜。
而古藤卻在一棵大樹的陰影中,用力向沙石的深處延伸,仿佛自己一定能抓到底層的泥土與水分。裸露在山徑上的根須,早已被進(jìn)山人踩踏到了骨頭,而我在祈禱時(shí)卻忽略了它的疼痛。
扎尕那的山路有許多相似的性格,它們螺旋式上升,又彎曲著下降。這樣的路——有人要走上一輩子。
我認(rèn)識(shí)的那個(gè)藏族女孩兒,黝黑的臉、眼睛、鼻子和睫毛,是那樣地像自己——相信生活。這讓我感覺到,山里仿佛有自己的親人。她肩上的背簍,縫合著一塊破舊的麻布,像文物照亮了她背簍中新鮮的蘑菇、蕨菜和黑木耳。她的每一次轉(zhuǎn)身或抵達(dá)都與山路、流泉和崖壁有關(guān)。但她從未因險(xiǎn)峻而滯留在山外。
白天山下熱浪撲面,夜晚山上寒氣逼人,但有一點(diǎn)她是清楚的:陡峭、懸崖——會(huì)隨時(shí)擋在前方的路上。
光蓋山與洮河都被說成是一面鏡子,而我說天空才是。它的藍(lán)——浸透了我的肌膚和骨骼。我誤以為自己已經(jīng)在鏡子里融化了。
河水沒有山峰的定力,身體也缺少鐫刻的文字,但它們躺在大地上的時(shí)候,已將草原和山峰攬入了懷里。在與倒影的凝視中,它們搖晃著大山、搖晃著云朵。有時(shí)因?yàn)榇笥甑募尤耄鼈冞€會(huì)流淌出許多條河流。在它們的影子里,天空永遠(yuǎn)屬于飛鳥的翅膀。
河水清澈靜流,讓岸變成了虛擬的線條。浣衣的村婦像花草,把自己的影子揉碎在鏡子里。唯有捶衣棒的聲音,讓河水充滿激情,讓大山與草原有節(jié)奏地回響。
夜晚,在山里行車,頭上的山峰和山下的流泉,會(huì)讓我在猶豫中——忽然打起精神。
前面就是諾爾蓋草原了,隱藏在草甸下的沼澤有著不可忽略的細(xì)節(jié)。從這里徒步的人,都是對(duì)草地的懷念。
作為見證者——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親眼看見過,在一支疲憊的隊(duì)伍中,有許多人在不知不覺中消失的情景,但偽裝在草甸下的沼澤并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只有野花和青草年復(fù)一年傾吐著它們的氣息。
我是這片草地的向往者,我確定要從這里走過去;抑或把感動(dòng)托付給草地或沼澤。假如我也成了這里的風(fēng)景,那就在往后的日子里幸福地回望——每一棵小草和花朵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