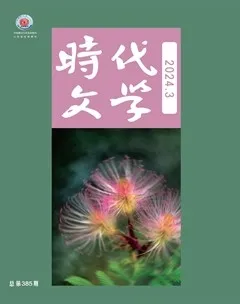老鴰
1
那時候,天氣很好,省城這條一直繁華無比的小街浸泡在正午的陽光中。往西不足二里,過了尚平坊,過了省政府,又過了護城河,鈴鐺街上的居民老關,竟然沿著四眼潭墻根開挖出一溜寬不足半米,長卻有八十多米的菜田。
菜田里種植有多樣蔬菜:茄子、西紅柿,還有辣椒和黃瓜。
對了,老關還順帶種了幾棵玉米,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已經往外伸展著了,長勢喜人。
老關正在那里侍弄那一溜菜田,他弓著腰,一勺一勺地把糞水澆到每一棵菜的根上。
老關很仔細,侍弄菜田比侍弄孩子還要上心。當然,這是他老婆的話,也是他的酒友老栓的話。老關和老栓都住在鈴鐺街上,住房很逼仄,都是老城區的樣子。正因為是老城區的樣子,便有規定不允許拆建了,也不允許隨意改變狀態,說是省城的老城區必須要保持原貌,否則外地人來這北方有名的省城,看什么呢?那些新的高樓大廈和其他城市里的高樓大廈又有什么兩樣呢?很多時候,老關和老栓喝著小酒,聊著這惱人的情狀,一點辦法也沒有。
“出事了,老關,出事了!”
老栓急匆匆跑過來,一邊說著,一邊拉住正侍弄菜田的老關的胳膊。
“老栓你個王八羔子,俺老關啥時候出事了?咒俺?”
老關抬起頭,瞪著眼睛,惱怒地望著老栓,口氣里透著不滿。
老栓不管老關如何惱怒,滿頭汗水顧不上擦,一口氣將鈴鐺街上來了一只變色老鴰的事說了。老栓本來結巴,性子又急,說起事來更結巴。說到后來,老關才聽出是鈴鐺街上飛來了一只鳥。
“飛來一只鳥,值得大驚小怪嗎?”
“不是鳥,是……是一只……老鴰呢。”
老關聽過老栓一番結巴著的說道,不再惱怒了,而是把糞勺的把撐在下巴上,有些不以為意。老關知道,在這個樹綠水清的城市里,因為生態環境好,隨便從哪里飛來一只鳥,或飛來一只老栓說的老鴰,那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有啥大不了的呢?
“變色,變色……的呢!”老栓說。
“變色的又怎樣?不就是一只老鴰嗎!”老關說。
“不……就是……一只老鴰?知……知道老鴰的降臨……和老鴰的叫……是啥征兆嗎?”老栓說。
“啥征兆?都是瞎說,你也信?”老關說。
“咋……就是……瞎說呢?”老栓說。
“咋就不是瞎說呢?”老關說。
“你呀,你呀……”
老栓沒再和老關說下去,他跺了跺腳,沖老關甩了一下手,走了。
老關望著一甩手走掉的老栓,搖了搖頭,苦澀地笑笑,想說啥又沒有說。他發現不遠處沿著菜田走向的一截長滿蒿草的土埂上,有一只顏色雪白的寵物狗,正在使勁地用爪子刨挖著什么,黃土被揚起來很高,蒿草的白色根須也被翻露了出來。不大一會兒,狗的主人走了過來,一個穿著時髦、臉上涂脂抹粉的女人,望著依然還在奮力刨挖的狗,她大驚失色地喊道:“俺的個娘哎!露露啊露露,就不嫌臟嗎?咋就愛刨挖這臟兮兮的泥土呢?不知道昨天晚上剛剛給你洗了澡嗎?回家還得再洗一回。”
老關搖了搖頭,再一次苦澀地笑笑,嘆出一口氣,輕聲說道:“泥土咋就臟兮兮了呢?沒有泥土,你吃啥呢?”
老關不再看那女人和狗,轉眼望向長勢旺盛的各種菜秧,臉上爬滿喜悅。
老關知道,即便是這樣一溜不足以稱之為菜田的菜田,也足夠他一家人吃了,而且很多時候他還把采摘下來的茄子和辣椒分送給鄰居們。每每拿到老關送的新鮮蔬菜,鄰居們都會嘖嘖夸上一番,說偌大一個城市,都買不到老關種出的這種有機蔬菜呢。而每到這時候,老關一準兒會補上一句:“空氣質量不好,咋能種出有機蔬菜呢?只不過沒有農藥殘留而已。”
“而已?”
“是啊,可不就而已呢。”老關說。
老關發現,沒有農藥殘留的新鮮蔬菜還是挺受鄰居們歡迎的。他在鈴鐺街上走著,總會有人親熱地和他打招呼,說你這人好哩,有了好東西總想著街坊鄰居們,厚道。
“變色?老鴰?”
“是啊,變色,老鴰。”
老關侍弄完菜田回到鈴鐺街上,見老栓又在和小蒙說道變色老鴰的事。
似是老栓把不祥征兆那套話說了,小蒙聽得滿臉驚恐,大睜著眼睛望著老栓,不住地問:“不祥?啥不祥呢?”
老栓情緒已經平穩,也不怎么結巴了:“聽過一句話嗎?”
“啥話?”小蒙說。
“‘老鴰頭上過,無災必有禍。’這……老鴰來了,沒啥好事呢。”老栓說。
“不是變色的嗎?變色的應該不是老鴰。”小蒙說。
“無論咋變色,老鴰依然……是老鴰。”老栓說。
老關站在不遠處,聽著老栓在那里和小蒙瞎扯。
老栓告訴小蒙,老鴰就是烏鴉,根據人們的生活經驗分析,這是一種不祥的鳥,落在誰家樹梢上,或在誰家附近叫個不停,誰家就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老栓說:“要不咋會有‘烏鴉嘴’一說?”
小蒙說:“烏鴉一叫,或者一落,準會有壞事發生,對嗎?”
老栓點了點頭:“對嘍……”
老關有些聽不下去了,走到老栓和小蒙跟前:“對你個頭!咋和個孩子說這事?”
老栓又結巴了,想必是怕老關罵他:“咋,咋……就不,不能說呢?”
“不能說,就是不能說!”
老關真是想要罵幾句了,罵啥呢?
老關望望老栓,又望望小蒙,啥也沒罵。
2
鈴鐺街上飛來一只變色老鴰的消息不脛而走。當然,老栓那張結巴嘴也在四處宣揚,人們不可能不知道。于是,人們對這只變色老鴰的認知中,或多或少地摻雜了些許情緒。
情緒與風俗有關,與傳說有關,通常的老鴰總穿一身黑色外衣,是個不受歡迎的角色。而且它們經常出沒于陰森恐怖的墳地或深林,據說是以腐尸為食物,所以被人認為是兇鳥。但是,飛來鈴鐺街的這只老鴰和尋常的老鴰不一樣,是變色的。既然是變色的,怎么會是兇鳥呢?然而,在鈴鐺街這樣一條有頗多風俗講究的傳統老街上,人們認準了的事,無論“變色”還是不“變色”,那都是改變不了的。比如王小蒙,這樣一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聽了人們的說道,竟然也有了情緒,而且被攪和得不知所措了。
王小蒙的不知所措,更多是來自老栓,是老栓最先和他說的,而后便是老栓的老婆三嬸。三嬸學了老栓的口氣告訴王小蒙:“不得了,飛來一只老鴰,天天晚上落在不遠的樹上叫幾聲,不吉利,說不定誰家要出事呢。”
“出事?”王小蒙說。
“老鴰沖著人不停地叫,咋能不出事?”三嬸說。
對了,老栓弟兄三個,他排行老三,所以他老婆被人喊作“三嬸”。三嬸的話嚇了王小蒙一跳,他也看到了那只變色老鴰,老鴰叫的時候正沖著他住的格子間。那一刻,他感覺格子間的窗子都被震動了,便想,一只鳥兒,咋叫得如此響亮呢?
“不得了,不得了呢!”王小蒙說。
“當然不得了,多少年沒有過老鴰叫了。”三嬸說。
王小蒙是兩年前畢業的大學生,在報社找到工作后租下老栓在鈴鐺街上的格子間。因為喜歡喝兩口,便與老栓老關成了忘年交,有事沒事湊在一起,弄兩瓶白干,配一盤油炸花生米或三根面筋,聊著,喝著,有時一個下午,有時一個晚上,好不樂呵。
“晚報上說的目擊者,是你嗎?”小蒙問。
“不是俺。”老栓回答。
“怕就是他呢,只有他喜歡對一只老鴰瞎揣測。”老關說。
“看你,看看……你呢……”老栓說。
那個傍晚夕陽還沒完全消失的時候,三個人已經喝上了。小蒙頭天回老家,順帶把老爹的兩瓶存貨老酒捎了過來。老栓笑笑說,不怕老爹揍你?老關也笑笑說,兩瓶酒,老爹值得揍兒子嗎?老栓說,你兒子那次偷了你的酒,不也挨了你兩巴掌?滾!小蒙聽著老關沖老栓吼,笑得前仰后合,順便端起酒杯,一口干了。
“咋哪壺不開提哪壺呢。”老關說。
“知道,知道。不開的壺呢,對吧?”老栓說。
小蒙怕兩人再爭執,便再次端起酒杯,與兩人的酒杯碰了碰:“敬您,敬您!”
“還是小蒙懂事。”老關說。
“就是,小蒙……懂事。”老栓說。
小蒙依然笑著,問老栓:“老鴰會不會再落在旁邊樹上?”
老栓抬頭望一眼旁邊的樹:“不好……說呢。”
老關很不屑:“落就落唄,一個飛禽,咱能管得了?”
其實,關于變色老鴰飛臨鈴鐺街的事,這幾天弄得人心惶惶。無論是上年紀的還是小年輕,都把這當成了一個事,想著鈴鐺街上會不會真就發生點啥啊!
還是老關清醒,說:“這記者沒事干了,咋就把這樣一件不足掛齒的事報道出來呢?如果晚報不報,如果老栓還有三嬸不到處瞎嚷嚷,怕是啥事也沒有呢。”
“老關叔,園林部門的鳥類專家來過了,說要調查是只怎樣的老鴰呢。”小蒙說。
“看看,上級部門也來人了。”老栓說。
“為啥?”老關說。
“是珍禽呢,整個省城都沒有過。”小蒙說。
“可那叫聲?”老關說。
“人家不管叫聲,只管變色老鴰是珍禽,要保護。”小蒙說。
小蒙沒說錯,下午確有鳥類專家來過,無論人們如何討厭那只老鴰,但因為老鴰能夠變色,也就成了稀有鳥類。據說,這樣一只變色老鴰的價錢,恐怕買得下半條鈴鐺街呢。
“不然,晚報也……也……不會報道。”老栓說。
“無論多么值錢,老鴰落……老鴰叫……不祥啊!”老栓喝酒喝得舌頭有點硬了,卻依然感嘆著,端起酒杯,干了。
那些天,老關沒睡好,也沒吃好。
老栓與老關一樣,沒睡好,也沒吃好。
住在鈴鐺街上的很多人,似乎都與老關和老栓一樣,總在想著那只老鴰的叫聲和那只老鴰落下的事。誰都怕老鴰會落在自家院子的樹上或房頂上,更怕老鴰沖著自家的方向叫幾聲。漆黑的夜晚,老鴰沖著自家方向野貓一樣地叫幾聲,瘆人不?對了,也許因為那只老鴰會變色,和通常的烏鴉不一樣,其叫聲特別像貓,又比貓聲音大,尖利、陰森、凄涼。所以,聽到過變色老鴰叫聲的人,都相信了老栓的話:“老鴰頭上過,無災必有禍。”
“是俗語,是俗語呢。”老栓說。
“大家沒聽過俗語,只聽過你說。”老關說。
“那是不知道……有如此之……俗語。”老栓說。
“所以,你就別再喝點酒就胡咧咧了,胡咧咧得鈴鐺街上人心惶惶,圖啥?”老關說。
“圖……圖吉利。”老栓說。
“吉利好,吉利好。”小蒙說。
老關、老栓和小蒙把兩瓶酒喝光后,夜已經深了。而這時的鈴鐺街上依然燈火輝煌,街上的人有南來的,有北往的,但南來北往的人不知道有一只變色老鴰飛臨,更不知道飛臨鈴鐺街的這只變色老鴰像一根奇粗無比的棍子,攪動了一池清水。
3
一連幾日,鈴鐺街上很多人都在意起了這只變色老鴰,鳥類專家也在意起了這只變色老鴰。有鳥類研究專家來到鈴鐺街,問誰看到了“先呈黃色,后呈綠色,再呈斑斕七彩”的變色老鴰。雖然報紙上說變色老鴰離去的“方向正西,四眼潭一帶”,但每到夜間,便會有人聽到老鴰的叫聲,那聲音時近時遠,但不怎么好聽,像發情的老貓。
“都是在夜里叫,專家咋不來?”老栓說。
“夜里看不到老鴰的顏色。”老關說。
“能聽到老鴰的叫呢,盯上一夜,說不定還能看到顏色。”老栓說。
老關和老栓的身影,那幾天總出現在鈴鐺街上。他們原來不這樣,沒事的時候貓到哪里下個棋,或打個牌,從不在鈴鐺街上亂走動。老關更是,有那溜菜田,每天他都得去忙活。在鈴鐺街上開店的人,也時不時會走出門來,與鄰居議論一番變色老鴰的事。世上稀有,并且能值買下半條鈴鐺街的價錢,就成了一個很誘人的話題。而再靜下心來思考一番,問題的嚴重性便一下子攤開在面前了。一只能換走半條鈴鐺街的老鴰,對,就是老鴰,不怎么討人喜歡的兇鳥,卻比鈴鐺街上任何一家店鋪都值錢,怪不得鳥類研究專家跑來調查。
其實,比起變色老鴰到底能值多少錢,鈴鐺街上的人更關心“老鴰頭上過,無災必有禍”的事。變色老鴰會給鈴鐺街帶來怎樣不可預知的變故呢?
老關在想,老栓在想,三嬸在想,王小蒙也在想。
如此之怪事,誰能不想呢?
其實,在人們議論來議論去的時候,首先坐立不安的還是老栓。小孫子出生以后,老栓家在鈴鐺街上的幾間房子住起來也就擁擠了。三嬸讓他把王小蒙攆走,說格子間不租了,收回來老兩口住,把大房間讓給兒子和兒媳,有了孫子,就得讓孩子們住得寬敞一些。但是老栓不同意,王小蒙已經租住了兩年,而且成了他和老關的酒友,房東和租客相處得如此融洽,怎能說攆就攆呢?再說了,一個八平方米不到的格子間,每個月租金八百塊,對于老栓一家來說,這是一筆可觀的收入。把王小蒙攆走了,再去哪兒弄這八百塊錢呢?
“咋就光想著那點錢?”三嬸說。
“過日子,不想錢想啥?”老栓說。
“有了孫子,一家人擠著住,行嗎?”三嬸說。
“不行。”老栓說。
“咋辦?”三嬸說。
“有辦法。”老栓說。
一個周末的上午,老栓跑到自己退休的化工廠,將幾個徒弟喊了過來。老栓脾氣好,對徒弟也好,雖然退休了,還會經常喊徒弟們來家里喝上兩杯,所以他一招呼,徒弟們呼啦啦都來了。
只用了一天,老房子門口十幾平方米的空地就被徒弟們用鋁合金和玻璃罩了起來。這一罩不要緊,老栓家多出了一間房子,寬敞了許多。這事居委會知道了,說老城區怎能隨便搭建呢?那十幾平方米是公共區域,不可私人占有,非要老栓拆掉。好在兒媳叔叔人脈廣,三打點兩打點,暫時不讓拆了,罩起來的十幾平方米也就成了私有房產。但老栓心里不踏實,知道自己有違規定,哪天居委會領導換了,再讓兒媳叔叔幫著打點?所以他怕,怕變色老鴰深更半夜沖著自家叫上幾聲,誰知道會發生啥事?
老關同樣有心事,也是因為變色老鴰。老關比老栓豁達,但也隱隱為老鴰的叫聲和老鴰的落腳心生忌憚。沒人的時候,他會嘆幾口氣,埋怨老栓:“咋會有‘老鴰頭上過,無災必有禍’的說法呢?胡扯!”然而,老關心里依然不踏實。在四眼潭邊上費勁開出的一溜菜田已經種了兩年多,期間有領導找過他,說怎么能在四眼潭邊上開荒種菜呢?弄掉,必須弄掉!
老關幸運,讓他“弄掉”的領導與兒子的老丈人有交情。也許兒子的老丈人吃了老關的辣椒或茄子,對了,還有紅彤彤的西紅柿和粒粒飽滿的玉米棒子,給領導遞了個話說合了一下,領導再沒來找,老關那溜菜田也就一直種著了。
即便如此,老關心里依然不踏實,想著半夜老鴰落到旁邊的樹上,又伸著脖子叫上幾聲,領導會不會又要堅持原則?
老關怕呢。
那溜菜田成了他的心頭肉。
老關退休后,身體之所以沒出問題,多半因為開荒種菜田。沒了菜田,沒了自己種的有機菜,血壓會高嗎?血糖呢?這個年紀的人據說不干活大都會得上各種病。還有,在工廠上班時他有過胃下垂的毛病,沒了菜田種,會不會再復發?
在王小蒙看來,因為老鴰飛臨鈴鐺街,老栓和老關便各懷鬼胎起來。然而,即便他年級輕輕,似乎也踩著老關、老栓的腳步,有些心慌。原因很簡單,小蒙生在農村,老家一帶對老鴰的忌諱更多,鄉間到處流傳著關于老鴰的不祥之說。小蒙記得,讀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奶奶給他講過二大娘的事,那事一直種在他心里,如今他回到老家都不敢去祖墳上看一看,哪怕是清明節上墳的日子,也只是遠遠觀望著祖墳上繚繞著的青煙,心里七上八下。
奶奶說:“知道嗎?老鴰成精了。”
小蒙不解:“老鴰咋會成精?”
奶奶說:“老鴰就是成精了,半夜里,你二伯家房頂落了只黑老鴰,伸著脖子,‘哇哇’叫了三聲,你二大娘就……”
小蒙說:“咋了?”
奶奶說:“上吊了,舌頭伸著,臉面發紫,嚇人著呢。”
小蒙說:“為啥?”
奶奶說:“老鴰叫了唄,老鴰叫,你二大娘就上吊。”
讀過大學后,王小蒙知道奶奶說的是迷信。可迷信歸迷信,鄉里人都信,沒聽誰說過不信的話。而今鈴鐺街上變色老鴰的出現,又讓王小蒙想起了二大娘,想起了鄉間里的黑老鴰。
“變色老鴰和黑老鴰,一樣嗎?”王小蒙說。
“咋不一樣?都是老鴰。”老栓說。
“鳥類專家沒注意黑老鴰,卻來調查變色老鴰。”王小蒙說。
“變色老鴰,世界稀有呢。”老關說。
王小蒙兩次聽到過老鴰的叫,三次看到過老鴰落在旁邊樹上。老鴰很好看,真如報上所言,其狀似鴨,羽毛先呈黃色,后呈綠色,再呈斑斕七彩,漂亮著呢。而且,翅膀拍得很響,狀似鴨,卻比鴨小,胸脯上還有一撮白毛,尾梢呈紅色。如此漂亮的一只老鴰,伸開脖子一叫,卻老貓一般瘆人。于是,老栓說過的“老鴰頭上過,無災必有禍”,便在王小蒙腦際縈繞不去。
能有啥禍?王小蒙想了半天,突然想起了小梅,對了,小梅會不會離自己而去?
乖乖!變色老鴰飛臨鈴鐺街,莫不是沖著自己與小梅?
那些天,王小蒙腦子亂得很,他真怕中了老栓說過的話。于是,他去天橋底下買來兩包老鼠藥,說要放到樹杈上,變色老鴰再來,說不定會吃下去。老關、老栓知道后,似是被嚇著了,沖著王小蒙吼:“不可作孽,絕對不行!”
4
王小蒙與吳小梅已經相戀很久。
吳小梅在銀行工作,人長得漂亮,家庭條件也優越。每一次出去吃飯,王小蒙都囊中羞澀,而吳小梅卻不管那么多,總沖他喊:“吃,姑奶奶有錢呢。”
吳小梅越這么說,王小蒙越怕,他怕被吳小梅看不起,怕吳小梅說他是個“窮光蛋”。當然,這詞吳小梅沒說過,吃完也從不讓他結賬。但王小蒙很忐忑,忐忑吳小梅熱情似火,忐忑吳小梅冷若冰霜。盡管吳小梅表示絕不離他而去,他依然拿不準這是福還是禍。于是,他去問老栓。老栓一杯酒下肚,嘆出一口氣,拉著長長的調兒說:“不看好哦……”
老鴰又叫了,王小蒙又聽到了。
是午夜。
王小蒙看看表,打了個哆嗦,又想起老栓的話:“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是福,還是禍?”王小蒙想問吳小梅,又怕問吳小梅,只能祈求老鴰別來,別叫。即便是變色老鴰,如老栓所言,也是老鴰,老鴰來了,能有好事嗎?
這個時候,月亮很好,天上星星稀少,老栓喊了王小蒙,又去喊老關,要到鈴鐺街上的老槐樹下燒紙,祭拜。王小蒙說:“管用?”
老栓說:“老輩傳下來的方法,管用。”
王小蒙搖搖頭,老栓拿眼睛瞪他:“啥樣的老鴰,聞到燒紙味兒,就再也不會來了,來了也不會叫。”
王小蒙說:“這么神奇?”
老栓說:“世上神奇的事,多著呢!”
老栓和王小蒙沒能喊來老關,老關正躺在床上發汗。一連幾天,老關都在發高燒,說是得了不好對外說的什么病,下面的某個部位,先是疼得要命,后來小便就撒些又稠又黏的東西。妻子讓他去醫院,他說啥也不去,稱沒大事,扛幾天就好了。兒媳比兒子孝順,堅持去找大夫來家里看,老關更是不允,想著大夫來了,這病也不好說出口呢。
“養幾天就好,沒大事。”老關說,“俺心里有數,長這么大還沒看過大夫。”
兒媳依了,但為了退燒,將兩床被子給他捂在身上。老關出了一身大汗,從床上下來,似是有些虛脫的樣子,頭暈目眩。這時候,老關聽到窗外的嘈雜聲,便+oMZ61V9tXh0QduC9r2QjQIAbTHiD6NBXDkIXgUL/t8=又想起自己那溜菜田幾天沒燒水了,會不會蔫了呢?
“安心養著,其他別管。”妻子說。
“好像有人在罵?”老關說。
“罵老鴰。老鴰來了,叫了,不安生呢。”妻子說。
“乖乖,咋能罵老鴰呢?”老關說。
老關嚇著了,有人罵老鴰,怎么得了?
過了幾天,老關病好了,去看菜田,便生出意氣風發的感覺。
菜田真好,老關與其難以分離。
經過一場病,老關性子溫和了許多,感覺陽光、風,還有天上的鳥兒,像是都成了新的。于是,他臉上掛著笑,想把這溫良的世界抱在懷中。后來,老關看見管四眼潭的領導走過來了,便忙忙地打招呼,領導也和他寒暄著,顯得比過去客氣了許多。
“聽說你病了?”領導說。
“小毛病,沒事。”老關說。
“這把年紀,別累著。”
“是啊,年紀一大,身體就差。”老關說。
領導說著,走了過去,沒再望一眼那溜長勢良好的菜田。
老關很感激這番搭訕。想著,如此搭訕了,菜田一準兒沒事。
“多么和藹可親。”老關說。
“多么禮賢下士。”老關說。
老關是在心里對自己說的。而領導對他身體的關心,讓老關在感激之余又有些不好意思了。也許,妻子,或者兒媳,把自己那不好對外說的病告訴別人了,別人再和另一些人說了,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嗎?老關想著,有些慌,便在心里埋怨妻子,埋怨兒媳,不曉事的婆娘們,僅僅是尿路炎癥而已,為啥要對別人說?
“唉!不曉事的婆娘們啊。”老關嘆著氣,又抬眼望望那溜長勢良好的菜田。
菜田還真好,綠色的蔓兒已把田壟擠得滿滿了,這季的蔬菜一定會有個好收成。老關這么想著,發現頭頂上飛過一只鳥,鳥有些大,很像那只變色的老鴰,心里便又不踏實起來。
“咋又來了呢?”老關眼睛盯著飛過的鳥,想著它會不會又飛去鈴鐺街。
對了,聽老栓說,他和王小蒙昨夜燒過紙了,老鴰咋還會來呢?
這一天的晚些時候,老關回到鈴鐺街上。還沒進家門,就聽附近傳來一陣嘈雜聲。循聲過去,見執勤人員正訓斥一個無視禁令下水游泳的年輕人。年輕人不服,執勤人員便按規定進行處罰,年輕人動了手,把執勤人員打了。有人報警,警察很快趕到,沒說幾句,就將年輕人帶上了警車。
“拘留!至少七天。”有人說。
“還得承擔執勤人員的醫藥費、誤工費、營養費……”有人說。
不知是誰提醒,昨兒夜里,年輕人家門前樹上有老鴰落下來,還叫了三聲。聲音刺耳,恐怖。
三聲啊!
“真的?”有人說。
“一早,年輕人就說給人聽了。”有人說。
“乖乖,這是咋了呢?”老關嘆口氣,想著,咋啥事都與老鴰有關。
“鳥類專家不是說了嗎,價值萬金的好鳥呢!”老關說。
5
又過了一些時日,老關身體好了,遇到老栓,老關問被警察帶走的年輕人咋樣了。
老栓說:“老鴰……門前……叫了,能有好?”
老栓又喝酒了,舌頭還硬著。老關無語,望一眼老栓,又轉頭向西看,想著過了尚平坊,過了省政府,又過了護城河,還有他的一溜菜田呢。而此刻的老栓似是覺得不應該那樣說,沖著老關笑笑:“誰年輕時沒有打過……打過‘黑碗’呢?”
老關不解:“啥‘黑碗’?”
老栓說:“你……沒有過?”
老關突然明白過來,笑了,老栓也笑了。的確,誰年輕時候沒作過事呢?
這時候,吳小梅挎著王小蒙的胳膊,滿臉幸福地走了過來。見老栓和老關在說話,王小蒙抬手打一個飛指,繼續往前走了。望著吳小梅和王小蒙的背影,老栓的舌頭沒再硬:“老鴰,沒再叫?”
王小蒙回過頭來:“叫了,好鳥呢!”
第二天,老關忽然動了觀光的念頭,便拉著老栓去了動物園。在珍禽館的那些網壁前面,他們流連了很久。他們竟然看到了那只變色老鴰,其狀似鴨,羽毛先呈黃色,后呈綠色,再呈斑斕七彩……
“好看。”老關說。
“是啊,好……看呢。”老栓說。
他們發現,好多人都圍攏在那里看那只變色老鴰,并談論著變色老鴰這些天的經歷。他們聽了一會兒就明白過來了,說是變色老鴰根本不是老鴰,而是一只變色的怪鳥。不久前,怪鳥撞破網籠,失蹤了好些天,害得鳥類專家們著急了好一陣子。后來,在大家找得幾乎要絕望的時候,變色怪鳥竟然從珍禽管理員的床下飛了出來……
“不是啊?唉!”老關不覺生出感慨。
“是啊,不……是呢!”老栓同樣生出感慨。
那一刻,老關老栓都在想,一只漂亮的變色怪鳥,能買下半條鈴鐺街呢,要是被人當成老鴰打死了,或者在樹杈上放了老鼠藥毒死了,那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