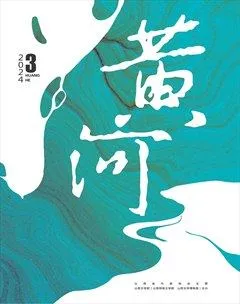舊我、新我與捉拿生活
編者按:“新時代文學晉旅”,是山西繼“山藥蛋派”“晉軍崛起”與“三晉新銳作家群”之后涌現的又一文學群體,是由山西中青年作家共同建立起的文學地域坐標,獲得文學界的廣泛關注。本期對話立足“新時代文學晉旅”的精神內核,邀請本省知名詩人、散文家、小說家、編輯及評論家,就“新時代文學晉旅”的本質、發展、創新展開討論,相信他們的深度對話能給讀者帶來更多有益的啟示,也相信“新時代文學晉旅”定會為中國當代文學增添獨特且寶貴的光華。
1.時下,能夠提出“新時代文學晉旅”這個具有指向性的命名,說明在山西,已經有諸多中青年作家脫穎而出,他們亟需一個噴發的出口。請你羅列幾位比較熟知的山西作家,并講講他們的創作特點。
張二棍(詩人,以下簡稱“張”):對同輩甚至更年輕的山西作家們,我不敢輕易置喙。我們這一代寫作者,既生活在現實主義寫作的土壤之上,也呼吸著各種新鮮而迥異的空氣。甚至每個人的經歷、閱讀、性格都大為不同,我們關注什么或者寫下什么,諸多時候并不是自我的抉擇,而是我們擁有的生活,童年記憶,正在遭遇的境況與日常,念念不忘的瞬間……等等這些,促使“新時代文學晉旅”麾下的每個青年作家,都形成各自獨立的風格。比如楊遙、克海對鄉土中國的深刻洞察,在普羅大眾的柔弱中,尋找見堅硬的真理。比如浦歌、呂魁對人心和人性的深邃理解,于繁復莫測的日常里,刻畫了非典型的愛恨情仇、生老病死。比如白琳、蘇二花、陳年等等竭力探索和建構著新的女性意識與慈愛情懷,并借“我”的口吻,自在袒露出人世間潛藏的大善與小惡,歡愉與憂傷。我想,每個寫作個體的出口都不太一樣,他們百花齊放的模樣也讓人欣喜。我看到,大家奔赴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即寫下不可忽略的作品,成為那個各自理想狀態的作家。
手指(小說家,以下簡稱“手”):我密切聯系,感到親切的一些小說作者,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看重這件事,認同“寫出好小說”的價值,他們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創造上,放在作品上的,他們試圖去發現。
陳克海(小說家,編輯,以下簡稱“陳”):從2004年開始在《山西文學》當小說編輯,可以說見證了一大批山西小說家的成長和變化。大概談一點印象。比如出生于1975年的楊遙,他的小說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既有對童年記憶的深情回憶,也有對日常遭遇的準確記錄,不能因為他書寫的題材,就簡單歸類為底層敘述,事實上在他豐富且龐雜的文本中,始終埋藏著一種倔強的精神,那就是對復雜人性的探幽索隱,對偏離公正與平等等社會現象的執拗校正。讀他的小說,總會想起《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孩子,總有一種純粹的天真,那就是對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嚴肅追問。比如出生于1981年的手指,早年他的小說關注青年人的精神狀態,講述他們面對世界進入社會這個龐然大物時的種種反應,充滿激情的敘述里,文本不乏戲謔、調侃,甚至帶有一種狂歡精神。近些年,隨著閱讀和思考的深入,早期作品里的憤怒、激烈情緒消隱,作品越來越開闊,同樣是書寫普通人的日常,他打量世界的眼光帶了更多的溫情和理解。比如出生于1975年的李燕蓉,她的小說若從題材上區分,寫的多是都市男女,故事談不上大的起伏,她常常能從看似尋常的生活狀態中洞幽燭微,發現不正常之處。得益于女性獨有的審視目光,現代人生活的精神困境常常在她縝密的邏輯推演之下,逐漸成形,呈現出耐人尋味的質地。比如出生于1974年的浦歌,他的小說好像就是要打破現實與夢境的區隔,在那些幾近變形的世界中,他饒有興味地做著試驗,現代社會究竟是怎樣影響著人,那些不可思議的遭遇在他的耐心敘述下,變得越來越像寓言和神話。比如出生于1972年的楊鳳喜,他的小說至少從題材上看都不離奇,全是些家常之事,但在他簡潔、近乎樸素的敘述下,仍然能看到他對人心的精妙捕捉。這樣的小說家,還可以舉出很多,因為出身和閱歷不同,性格迥異,他們的小說風格也大不一樣,如果非要找尋相近之處,可能是他們正好置身在這塊土地上,又迎面撞上了這個火熱又生機勃勃的時代。
董曉可(評論家,以下簡稱“董”):2020年,我很榮幸成為山西文學院第七屆簽約作家,簽約的課題名稱為“山西中青年作家研究”。截止目前,我已對21位山西中青年作家的代表作品進行了相對細致的考察。現簡要列舉幾位小說作家:
楊遙小說的主人公大都是有著善良底色的小人物,在大時代列車的呼嘯前行中經歷著不為人知的希望與絕望、隱忍與逃避、侮辱與損害、爆發與復仇。他通過對毫不避諱的社會矛盾與公平失卻的尖銳書寫,給人帶來了真切的痛感意識與現實反思。總體而言,歷經20余年打磨與沉淀,楊遙的創作愈發深刻,正朝著小說大家的方向進發。
陳克海很擅長書寫底層女性,如果將其與畢飛宇、張楚兩位女性書寫高手對比,他往往更側重將這些蝴蝶般柔弱的女子置于“自我”與“世界”加劇割裂的現代文明境況下,書寫她們失卻的本真、天然的感傷與托舉美好希冀沉重起飛的點點鱗片。從寫作手法看,他的作品很少有絢爛的技巧展示與離奇的情節設置,更多的是尋常“慢故事”的耐心細致推移,采用類似于白描的生活細部構筑文本。
張暄的作品往往聚焦于人的肉身需求,通過看似瑣碎的生活煩憂與愛情失落,展現現代人生存的缺憾。如同他最喜歡的電影《大話西游》那樣,他作品中有諸多看似不太沉重、實則無能為力的獨屬于現代人的愛情荒誕、親情隔膜與生存迷惘所構筑起的現代人殘缺的“維納斯之臂”,且往往通過一些美好的“闖入者”(女性居多)形象,來賦予文本輕盈與微妙,并以此點亮抵御現代桎梏的微弱星光。
白琳,是山西作家中近年來成績斐然而引人矚目的存在,她的作品近年來頻頻出現在《收獲》《當代》等大刊。她本人走得很遠,從三晉大地一直走到了歐洲羅馬,而她的主人公也隨著她有了更多漂泊感。就從她今年在《收獲》第二期發表的小說《支離的席勒》來看,一種表面光鮮而內心荒涼的離亂感,一種用孤傲保護孤獨的貝殼似的軟體心靈,是她鐘情的文體感受。這,讓人不由想起郁達夫、張愛玲等有異域經歷、有羈旅愁苦的文學大家。如果擴展開,以白琳為典型,或許其代表了山西“走出去”作家中更為龐大的隊伍,就目前來看,這支隊伍至少涵蓋了笛安、孫頻、顧拜妮、武茳虹、舒吾、王譯彬等一串名字,他們不惟有著晉土異地生活的特殊經歷,有更多新質文學血液的融入,這也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新時代文學晉旅的厚重基座。
2.你認為,和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及“晉軍崛起”“三晉新銳作家群”相比,“新時代文學晉旅”這個被命名的新群體有什么新質素和新向度?
閆文盛(散文家,以下簡稱“閆”):很顯然,新的命名強調了時間性。這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無論是主觀需求,還是客觀呈現,都集中地體現出的新的洞察。“山藥蛋派”及“晉軍崛起”,都以小說為重,“三晉新銳作家群”開始涵蓋一些別的文類的作家,“新時代文學晉旅”則無疑更突出了“百花齊放”的特征。而且,從我們山西的文學源流看來,近百年以降,小說達到一定的高度后,在散文、詩歌、評論甚至類型文學的范疇,都涌現出了實力頗為不俗的創作者。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現象。各個文體之間可以相互補益,無需自設藩籬,更應去除壁壘,則時日一久,山西文學曾有的榮光便會重現,甚至更可有新的期待。因為“江山代有才人出”“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立意高遠,謀之于實事,血液自會更新,青壯老幼也大可以互相師事,舊我、新我都在成長———足以充實我們整個陣容。
董:在此,請允許我引用新近發表在《都市》第4期《浦歌的敘事魔盒》一文中的一段話:“任何時候最優秀的文學都是一種造山運動,一種叛逆性的災變革命,這在文學被讀者邊緣化或娛樂媒體征用而變為‘無限的少數’接受受眾的今天尤為突出。從這個意義而言,浦歌所接續的自呂新而來的文學的災變革命,顯得尤為可貴。或者說,正是以浦歌的敘事魔盒為標志之一,同時涵蓋了張二棍的草莽刺殺、閆文盛的主觀王國、手指的暴力先鋒等一批青年作家的異質突破,才使得山西文學有了通向未來、對接新生的無限可能。”
這,是我對“新時代文學晉旅”這個新群體的新質素與新向度的整體判斷,即不自我遮蔽于所謂山西“傳統文學手法”,追求一種更具先鋒意識,更為大膽探索,更顯明的融合與突破為一體的“造山運動”與“災變革命”。
張:時代洪流之下,我們都是摸索著石頭過河的人。每一代作家都像一條河流,有自己的浪花與漩渦,都有呵護著自己的兩岸,都有自己流經的疆域,滋潤的人群,匯入的海洋……老一輩“山藥蛋派”作家們深挖洞廣積糧,對素材精益求精的沉著,值得我們學習。“晉軍崛起”與“三晉新銳作家群”,一位位優秀的作家,他們都擁有生活的深度與視野的廣度,自然也形成了各自作品中的先鋒、多元、異化,甚至與主流寫作格格不入、背道而馳、另起爐灶,他們仿佛一面面鏡子、一枚枚法器、一張張明信片,以此來映照時代、捉拿生活、傳達愛意。到了我們“新時代文學晉旅”這一代作家,許多人有著更好的學業背景,甚至知識和見識的來源也遠非前輩作家可以比擬。但我們的苦惱是,在這樣一個碎片、急躁的網絡時代,無法做到對生活和生命的沉潛與深入,凝視與審視。所以,如果大家安靜下來,一定也會與我們的前輩一樣,取得不可估量的成績。
3.最近很流行一個概念,叫“新南方寫作”。據這個概念的首倡者楊慶祥說,“新南方寫作”是對漢語主權的預先書寫和確認。那么你是如何理解新南方寫作的?我們的“新時代文學晉旅”與其有沒有相通之處?我們又如何增強“新時代文學晉旅”的辨識度?
手:最主要的還是寫出好作品吧。
張:我是個比較懶惰的人,很少關注其他地方,其他群體,甚至其他個體的寫作。總覺得,不管南方北方,所有的寫作終究都是個人的、隱秘的、不可預測的。我們“新時代文學晉旅”所能做到的,就是用好我們山西本土紛繁復雜的寫作資源,真正承接前輩們十年磨一劍的意志,汲取外省乃至國外的寶貴經驗,以嚴謹規范、一絲不茍的態度,寫下不斷摒棄、時刻陌生、永遠無依無靠卻活色生香的作品。
董:“新南方寫作”,以及“新東北作家群寫作”“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甚至包括“文學新浙派”等等提法,其背后本質而言是一種文學話語權的地域性爭奪。當然,這種地域性研究本身可對鐵板一塊的文學秩序解構與地方經驗總結起到一定作用。就此層面而言,我們的“新時代文學晉旅”與以上術語并無二致。
在增強“新時代文學晉旅”的辨識度上,更多的工作需要省作協和文學研究者去實施。在此層面,我們已經在做諸多扎實的活動,如去年推出的“新時代文學晉旅”叢書與活動策劃、在《小說選刊》上同時對山西70、80、90后作家展覽,今年與山東省作協合作,在《青島文學》上開辟的“魯軍·晉旅”欄目對于山西作家的集中推出等。
如果說還有短板的話,目前我們在文學評論的集中推送方面存在欠缺。就“新南方寫作”而言,廣東在《廣州文藝》《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有專門的、高強度的話題討論,并與《當代作家評論》合作推出了“新東北·新南方”的針對性欄目,而在山西,該方面的工作無疑是缺失的。
4.你作為“新時代文學晉旅”的成員之一,在日常寫作中,都有哪些困惑?可試舉幾例。
陳:日常寫作中,困惑太多了,也非常具體,就是每一篇小說剛開始動筆的時候。以前好像打開文檔,就可以信馬由韁,想怎么寫就怎么寫,現在會想得更多,總要等到有一種強烈的愿望,確實有話要說的時候,才會坐下來。
當然,因為生活環境的局限,或者說受制于想象力,好多時候看見別人寫普通人的生活,寫日常,難免也會受影響,跟著“底層寫作”,結果難免陷于同質化的尷尬境地。
我也經常在想,在如此便捷的互聯網時代,小說怎么能給人提供陌生的經驗?小說肯定還是大有作為的。說是信息時代,實則受制于算法,每個人看到的世界,可能更像是自己愿意看到的幻境,結果就是更多的人活在舒適的信息繭房里。好多時候會悲嘆,小說想寫出新意來似乎很難,但好在每個人接受的信息千差萬別,或者說在前人歷盡千辛萬苦才能獲得一點體驗,而今天的人得益于新技術,瞬息間就能享用幾百年來的文明成果,這些巨大的刺激,興許是現在的小說家挖掘不盡的寶藏。只要滿懷熱情,葆有一顆好奇的心,仍然大有作為。
手:寫作的困惑很多啊,寫什么啊,如何寫啊,為什么要寫啊,重要的是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一度你以為自己解決了,結果過段時間你又回到了一些基本問題上。現在我覺得,生活的困惑和寫作的困惑密切相關,之所以有困惑,肯定是因為“不滿”,不滿是寫作的前提。
張:困惑一直都存在著,甚至喜歡困惑像一條條藤蔓般將我纏繞。我想,我終其一生,也不過是用自己手中的文字,當成和這個世界交換秘密的信物,我們用這一個個的方塊字,與這個世界不停兌換著。一首詩,就仿佛是一次交易。而一本詩集,大概就是一個人很多年的積蓄,我們用盡這心中的籌碼,才換來了一頁頁白紙黑字。是的,我們都是困頓于大地上,奔波在塵埃間的人,我無法讓自己的肉身超脫與蝶變。但我們擁有文字一如擁有魔法,而我,渴望自己就是那個站在人群中,變魔法的詩人。可事實上,我的淺薄與無能,讓我寫下許多并不高明,當然更談不上完美的作品,甚至有一些不堪卒讀,漏洞百出的作品,我不能避諱它們的存在。我常常在寫作時陷入無力與掙扎,既做不到李白的豁達無邪,也做不到杜甫那樣的深沉厚重。我一直活在愚鈍和遲疑中,我的詩歌也更多是一個人精神世界里的無法自拔和有所期待。我從來不是個白云悠悠的寫作者,也成不了一個心如止水的詩人。我知道,正是我的局限與狹隘,我的顧慮和膽怯,催促著我去寫下這些自我的反思與掙扎,愛與悔意。我希望我說出的這些情緒和心境,能夠抵達某些讀到它們的人。我希望,我們能夠在一首詩歌里,尋找、分享到彼此共有的那部分生而為人的歡喜與憂患。所以,我在自己寫東西的時候,就是用一種接近匍匐的方式,靠近著……總的來說,我淺陋的學養,有時候讓我面對重大題材時力有不逮;我古舊的小農思想,讓我無法寫出擁有純粹當代性甚至超越性的思考;我經年累月的懶惰,使得我一直沉浸在詩歌的舒適圈子里,自以為是。
5.跨界寫作現在已成為一種趨勢或新動向,你是如何看待跨界寫作的?跨界在跨過文體界限的同時,還跨過了什么?
閆:跨過了一些本不該有的障礙和限制。跨界會使創作者的心靈面貌更為自由。這本來就是一個汲長補短的時代。信息快捷,記憶迭代,都使文學一途體現出了更大的包容性。而且,追根溯源,文學在細分之前,本就各類兼通,沒有太多的自我設限。況且,文史哲不分家,文學與其他領域的藝術品類,也各有交融。現在既然有了“跨界”一詞,我覺得只是正本清源罷了。讓創作者既能落地生根,又能讓其筆下的文字長出翅羽,各諳飛行之道,則文學的領空就不會過于單調和落寞。形形色色的創造力,會誕生各負其重、各展其能又雜糅各類菁華的新成果。
陳:羨慕那些能對這個世界滔滔不絕發言的人。面對這碎片化的世界,怎么融合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考量的不單是一個人的認知水平,對這個世界的觀察和判斷能力,更考驗一個人有沒有去參與、建設的激情。換句話說,去中SpZo163KMPo32jKRyL2W3k3TKf9a+lPmRnXQqM77gzQ=心化的互聯網體時代,正在重塑人的思維方式,也在生成、創造新的表達可能。在我的理解中,跨界其實就是對話,就是打破信息繭房的一種渴望。說到底,還是因為確實有話要說,并且能恰到好處地表達出來,至于文體界限,不過是為了表達心中意圖,一個合適的選擇而已。
張:跨界寫作是應該的,也是必然的。每個有抱負或者有野心的作家,都該有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寫作。但術業有專攻,如果我們并非通才,也不能一味以己之短,來與別人之長爭鋒。尤其到了這個時代,萬紫千紅的生活,處處在消磨我們作為詩人、小說家、散文家的“使命感”。跨界可以嘗試,比如小說家可以偶爾去做一次編劇、導演,詩人也可以寫幾篇小說、歌詞……我們需要警惕的是,得魚忘筌,竹籃打水,最后使得我們寫什么都不倫不類。
手:我沒有關注到這種趨勢,有人寫出了個東西,這個東西好還是不好,我覺得跟跨界不跨界沒什么關系,主要還是看他說了什么,有沒有創造性,有沒有感染力……主要還是看“產品”本身吧。
6.我們都知道“晉旅”中的“晉”代表山西,但每一個真正的作家又不想受制于地域,那么我們將如何“突圍”?或者說如何在晉地作家的“裝置”內,找到抵達文學高峰的必由之路?
董:所謂地域性寫作,更多的是為了抱團取暖,有些吾道不孤的意思。我認為就作家個體而言,不必刻意去追求“晉旅”,要堅持自己的路子,堅守自己的個性和聲音,其寫作本就會如鹽在水地體現“晉地”特色。
在晉地作家的“裝置”內,找到抵達文學高峰的必由之路,更多的是探索共通性的文學升華路徑。我認為,就作家整體而言,山西目前從60后至90后的作家梯隊在全國范圍內是相當健全的,但從文學大家來看,相對江蘇、河南等文學大省又明顯落后。這無疑在提醒我們,走向更為高遠文學遠方的雄心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從來就沒有“浙江作家魯迅”“湖南作家沈從文”的提法,這反而要求我們的作家,在內心深處不畫地為牢,以全國一線作家甚至世界一流作家為對標對象,通過大批量世界經典作品與國內優秀作品閱讀、艱辛浩繁書寫與舍我其誰的魄力創作出無愧于自我、也無愧于文學的優秀作品。
陳:如何出作品、出人才,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在我的理解里,“晉旅”和其他文學概念一樣,更多的是為了一種概括的方便,事實上作家從來都是個體的,創作也是多樣化的,所謂的集群,近似于共同體的想象,都是人為制造的浪漫。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真有所謂突圍一說,一定是作家個人的作品得到了更多讀者的認可。當然,外部有一個更好的環境,可能會刺激鼓勵更多有才能的人進行創作,出現好作品的機率可能也要大增。
對創作者而言,除了外部的環境,還是得靠作品說話。沒有作品,一切都是虛妄。怎么突圍呢?一個人的學識、素養、想象力,似乎都足以構成障礙。簡單從創作習慣來說,更多的需要一個人的自律、自覺。有句話怎么說來著,自律就是自由。只有嚴格地要求自己,在寫出大量作品的基礎上,才有更多言說的可能性。
閆:我確實不想僅僅在一個區域之內談論文學。因為真正的文學必然超越時空。我們目前界定了這樣一個概念,是因為我們身在“山西”、“21世紀”這樣具體的時空點上。這是一個行經之事。但我們一直在往前,所以“突圍”“抵達文學高峰”就是應有之義。行高望遠,你的視野會真正打開,那么過于具體的指涉會淡化。如何做?我覺得首先需要將時空的意識更為凝練、抽象而無需太過拘泥,只有站在地域之外、時間之外來做判斷,才能更加清晰地返顧我們的“晉”元素。譬如,作為一個中國作家來寫作,作為一個地球人來寫作,作為一個人來寫作,這和僅僅作為一個山西作家來寫作,就有大區別。再者,我覺得在解決了時空定位之后,來為自己的寫作生涯謀篇布局,就需要精準和審慎,大意就是需要明確自己的優劣所在,不貪大求全,而務求準確和精深———只要足夠清晰地知道你能夠寫出什么,而又足夠努力地將之予以完成,則你的面目就不會被淹沒于蕓蕓眾生。不需要太多的妄想,只要將你的作品置身在萬卷———如你作為一個“人”置身在人群之中,你能夠確保做到:你的視線不會受到任何阻隔,就足以說明一切問題了。
張:山西是我們的根脈所在,我們熟悉它,只要做好一個耐心的觀察者,一個細致的傾聽者,我們只要不是游離于故鄉的局外人,就會看到與理解一個嶄新的土地,一個經過自我意識改造和私有化的山西,另一種版本的山西。那么,一片宏大的土地,一代代生老病死的人,一段段可歌可泣可書寫可回憶的故事,就可以組成一個如謎般深邃的世界,它會等同于馬爾克斯的南美、托爾斯泰的俄羅斯……所以,我個人以為,在這里的寫作,與任何地方的寫作,都需要面對一樣的突圍。一個有準備的寫作者都應該正視和接納我們的環境與身份,挖掘好“我”的山西,就會如魚得水如虎添翼,就會寫出具備異質與多維的作品。
手:對于我來說,最主要的還是寫這件事,如何能掌握它,如何讓自己保持創造力,如何能讓自己“享受”這個創造過程,如何靠近那些好的藝術品。
7.從詩歌、小說、散文、紀實文學、評論等,到編輯、發表、出版,你認為怎樣做才能達成一種良性的互動或互應,才能讓“新時代文學晉旅”真正成為一支中國文壇的勁旅?
張:說老實話,編輯、發表、出版這幾點上,我們山西許多作家比較內斂和被動。我們常常處于一個等待召喚的狀態。當然,這個狀態也可能不是什么壞事。但在這樣一個信息更迭頻繁,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時代,它一定也是有局限的。要想獲得主流期刊、主流批評家的肯定,我們不能只是注重拘囿于本省、本地區、本圈子的發表、出版、研討會等等。如何突破圈層,讓“嚴肅文學”成為熱點、重點、賣點的文學,大概是我們都需要思考的。在傳統模式之外,我們不妨把大家的作品,通過一些非典型性的、跨界的,甚至街頭巷尾的方式,去接觸和宣傳我們的優秀作品。
閆:既然是“中國文壇的勁旅”,則不能關起門來做事。需要定位高標,與國內最優秀的詩人、小說家、散文家、評論家等等交流互通。山西作品,要有大影響,不可能僅僅在山西層面上叫好便成,需要經受更廣泛的考驗。所以,得大刀闊斧地走出去。還有一點,我覺得可能尤為重要,即對那些真正有潛力的、尚待發掘的作家和作品,我們得有伯樂之眼。步別人后塵肯定不成,得舍得下大力氣投入和挖掘。因為任何一條道路都不會重復,所以僅僅停留于“想”這個層面是一回事,真正地去做就是另一回事。需要不拘束于陳規,需要破舊立新,加大培育人才的力度,在“舍”和“得”之間找到大平衡。
8.是什么讓你的寫作得以存續,難道僅僅是情懷嗎?
陳:走上寫作這條路純屬偶然。當熱情消退,或者說對寫作真正祛魅之后,仍然能控制不住,繼續去寫,一定還是因為有話要講。面對這個復雜豐富的世界,我們表達的聲音雖然微不足道,但總算沒有完全失語不是?套用索爾·貝婁的一部隨筆集的名字,這個世界實在是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也可以借用王小波的話,他的幾本雜文集雖然講述的多是常情常理,但處處都閃現著《思維的樂趣》。當萬千碎片,經過自己的拼貼、重組,變得像模像樣,原來毫無邏輯的一切,似乎都有了新的秩序,這樣的時刻應該是寫小說最為美妙的時刻吧。
手:已經寫了二十多年了,之所以還在繼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相信它,認為在這件事上耗費時間是值得的。
張: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一直斷斷續續寫著。寫作,如此接近于一場漫游,甚至像極了一場回溯。我太喜歡“漫游”和“回溯”這兩個詞了,它們有一種讓人身心愉悅的感覺。漫游,帶著某種解脫和釋放的感覺。而回溯,則有一些使命與天性的意識。是的,漫游能讓人忘了肉體的疲倦,而回溯則讓人帶著疲倦不斷超越肉身的極限。寫作,也是憑借著內心對世界的感覺,來締造著另一處田疇、家園、異域,也或是另一個肉身,有著創世般的欣喜。我喜歡被文字包裹在巨大而神奇的磁場里,感受它們的瑰麗與奇特,所以才緩慢寫下去。
閆:我覺得,我的寫作對我來說只是日常呼吸,與其他無關。當然,寫作久了,因為借此也可以安身立命,所以就比較順暢地走了下來。但是,在最開始的五年甚至十年之內(大約在1995—2005年間),寫作帶給我的東西極少(包括經濟上的支撐、精神層面的收獲等等)。我只是發現通過寫作這個行為,逐步地找到了一條介入人世的通道。我為什么寫作?可能無法具體地談論其真正的動因,但差不多三十年了,我至少發現了一點,即寫作的存在強化了我與他人、世界,更重要的是與思考的聯接。思考重要嗎?對我來說是這樣的。我的寫作脈絡———在很久之后,我才意識到,可能與普魯斯特、佩索阿、昌耀、卡夫卡都有近似之處,但作為個體,又在更大的層面上實有大不同。“情懷”與“文學”的關系,若是若非,若即若離,對我而言,換成別的詞或許更合適。是熱愛、存在、命運、呼吸嗎?但也不完全是。可能就是一種行為本能吧,沒有刻意的外物的添加,是一種內在的、精神方面的需要,這似乎更妥貼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