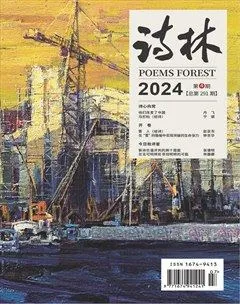為文字接通36℃體溫
2024-07-02 11:29:37陋巖
詩林 2024年4期
陋巖
山西人形容煤礦工人的工作環境有點“東北風”的氣質,非常形象和直接——四疙瘩石頭夾著一塊肉。這塊“肉”就是礦工。再準確點講就是“四疙瘩石頭夾著一塊‘帶骨肉”,因為礦工兄弟都是“帶骨”的。他們的鈣質,他們的骨氣,叩之有金屬的清越,望之有山岳的偉岸,常常讓我肅然起敬乃至淚流滿面。
我寫詩幾十年,筆尖好像鑲嵌著掘進機的鋒利,眼睛好像佩戴著鉆探黑暗的礦燈,一不小心就會進入八百米深處,用煤的黑測量礦工的明,用煤的冷測量陽光的暖,在煤的硬中尋找生活的軟。我力求讓那些橫豎撇捺彎折鉤……組成的文字,接通36℃體溫,組合成一架架詩歌的梯子抑或一段段長城,來表達我對礦物、礦工、礦嫂和礦山的熱愛、尊敬。
我出生的地方叫石卜咀村,坐落在一塊巨大的煤田之上,是拿一把鐵鍬向下隨便挖一下子,就能看見“錢”的風水寶地。所以,煤礦隨時都會讓我有觸電的感覺,隨時都會打開我情感的閘門和詩歌的開關。
井口的桃花、電線上的麻雀、頭燈房的女工、掌子面的割煤機等等物象,都曾攜帶著36℃體溫進入我的詩歌,與我稱兄道弟、勾肩搭背、推杯換盞、同頻共振。
詩歌的高度來自詩歌的深度。在我的眼睛里,每一位礦工都是天才詩人,他們深入八百米深處,挖出了能發光、發熱、發電的詩句。詩歌也是一種煤炭。我固執地認為:不管你是什么“派”的詩人,黑色字體里的能量,能否溫暖、點亮讀者的眼睛乃至心靈,是一首詩成功與否的度量衡之一。
每次與詩友們站在太行山巔,我的眼前都會幻化出這樣一個遙遠的鏡頭:冰雪覆蓋大地的冬天,一列列火車載著煤炭,載著披著黑色戰袍的遠征將軍,從太行山的腹地出發,邁著鋼鐵般鏗鏘的步履,正向與寒流短兵相接的戰場開拔。這黑與白的對比呀!能把空氣化作烈酒,點燃在胸膛里窖藏了萬年的春天。
他們是復活的陽光,去修補忽冷忽熱的人間。
猜你喜歡
中學生天地(A版)(2022年9期)2022-10-31 06:36:28
好日子(2022年3期)2022-06-01 15:58:27
故事作文·高年級(2021年10期)2021-10-23 13:21:26
動漫界·幼教365(中班)(2020年7期)2020-07-14 03:07:21
中學生數理化·八年級物理人教版(2019年9期)2019-11-25 07:33:02
中學生數理化·八年級物理人教版(2019年3期)2019-04-25 06:20:54
中學生數理化·八年級物理人教版(2018年3期)2018-05-31 08:52:45
數學小靈通(1-2年級)(2017年10期)2017-11-08 08:39:45
涼山文學(2016年6期)2016-12-05 11:51:42
少兒科學周刊·兒童版(2016年1期)2016-03-14 03:5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