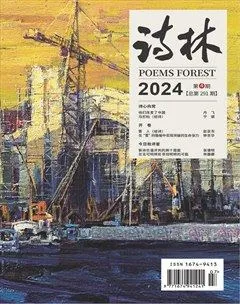雪人(組詩)
趙亞東

留下來的人依然潔凈
這寂靜還在敲打你的心嗎?巨大的轟鳴
在發炎的喉嚨里滾動
當年我一無所有,現在依然如此。
那在大雪中默默點燃燈盞的人,早已轉身離去
而那火光還在照亮,
我曾“謬誤百出的生活”。
這生活的曠野里,早已經沒有野獸出沒
只有一只奮力飛起的麻雀
它如何振翅,也高不過那晃動的樹梢
索菲亞教堂的鐘聲絲絲縷縷,化作雪煙
——鬢角上的白發。早晚有一天
我們也會離開這里,就像剛剛醒來的夢中
漫天大雪突然停在半空
堆積成無盡的山巒,又轟然而落
在被掩埋的一刻,我們依然祈禱著
那些留下來的人依然潔凈如初。
為冬天準備好荒原
如果牙齒背叛了舌頭,在一場大雪中
我們該相信誰?為迷路準備好永無盡頭的荒原
為灰燼準備好柴草。眼睛的深淵
雪將永遠不能填滿。我們沒有準備好愛情
就生下了冬的孩子,他正用睫毛上的冰山
修補我們的額頭。烏鴉停止了朗誦
而關于我們的傳說還在繼續。誰會毫無保留地
為我們做證。雪最終可以辨認我的樣子
作為一根蘆葦,我已滿頭白發,不再會是
敵人,只能和其他的蘆葦簇擁在一起
連綿的雪山傾瀉而下,我們還沒有倒下去
月光的碎片種在骨頭里。
用你的手指作為樹苗
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樹木
……還有哪一棵是活著的?它們是否真的會死去
你一棵一棵地擁抱,耗盡自己所有的溫度
直到你自己結滿冰霜,一個再也回不去家的雪人
到底是什么力量才能讓它們活過來?
那些我不能錯過的鳥鳴,每當我想從它們的聲音里
辨別命運的暗示,來自水底的濤聲
就涌上來,穿過厚厚的冰層,而時間的起伏
正在描摹另一個版本的歷史。
我所能給你講述的,也許是我的夢囈
遠方的朋友,你應該種下自己的樹木
——用你的手指作為樹苗。
收集未來的歷史。但它能否證明這一切與你有關?
當更多的星星認領浪花,或者一塊瑪瑙化為
一座火山,我們是否還會依靠這些枝干
它們可能會在下一個季節活過來,但跳動的
注定不再是過去的那顆心,包括時間本身……
自己的大雪
沒有人要求我們必須仰望天空
我的天際線,正由外科醫生用鐮刀慢慢劃開
我的這一場雪,已經不需要從蒼穹借用
遠在南方的兒子,打聽雪的厚度
我竟無言以對。我們自身的成色,由過去書寫
而構成存在的真相,需要記憶
現在雪越下越大,那正被掏空的已無法填補
那還沒到來的,無需祈盼。
我把新寫的詩行讀給兒子聽,那是我們二十年
顛沛流離,被一次次潑冷水的細節
他不回應我,點燃厭倦,眼睛朝向別處
倏忽之間,我的屋檐已經滴水成冰
不離不棄的燕子在焦急地歸攏著車馬
雪不會袒護任何人
蒼穹把一個任務交付給大雪,每一片雪都完成認領
記住這些面孔,鎖線裝訂的賬冊。
我們都在其中,五臟對應五角形,六腑對應六角形
雪不會只落在地上,被風倉皇地追趕
當我默讀兒子從邊關的來信,得知他媽媽的病狀
雪剛好被裁縫們制成涼薄的冬衣
這些年,我忽略了身邊的親人,甚至沒有多看他們一眼
那雪的賬冊里,又會記錄下什么?
雪不會袒護任何人。
我會不會又欠下新的債務,再無力償還
半夜起來,爐膛的火焰早已熄滅,醉酒的友人
你不知道我是惡疾纏身的人,雪在追問
我還不知道如何敘述我的病情,過去的罪責
燭光在雪中戰栗著
我們也是有過好日子的,三五個日落
河邊的舢板船倒扣在雪地上,有這幾天就足夠幸運。
可以靠著這點回憶,這些羞澀的布袋里
叮當的硬幣,為剩下的時間結清花費。
端坐在風中,仍有些驕傲,斷槳尖銳的刺扎進食指
這只是一個意外,并不值得害怕。
我們討論這世間到底什么是最公平的
時間,死亡,太陽的光?暗夜的雪地里
燭光在風雪中戰栗著。我們因此暴露在群星下
到底是什么呢?從食指流出的血染紅了雪野
不!是染成了黑色,月光也被涂抹
不予判決的罪人,雪地上的腳印無法抹去
在找到這個答案之前,我們先要找到容身之所
呼蘭河被蕭紅輕輕披在肩上,我們趔趄著躲進風中
我們不能再小了
過了這座微微拱起的鐵橋,雪就停下來了
我不停地咳嗽,南方的朋友背對著我
橋的另一邊,雪還在下……
我是該重新回到茫茫白雪中
還是再往前走?在無垠的雪野上
把自己縮小成一個黑點兒。還要怎么樣呢?
雪不能再大了,我們不能再小了
我不知道你為什么突然淚流滿面
我們沒有孤舟,沒有斗笠,嚴寒中的飛鳥
依然在飛。這就足夠了
不管認識不認識,不管貧窮還是富足
這世上畢竟還有許多人
……被大雪遮擋著,被大風催促著
雪人是會說話的
早晚有一天,你會說話的
但是現在你沉默,假裝微笑的樣子
騙過了所有的人
他們仰頭看著你的臉和通紅的鼻子
冰涼的手指試探你皮膚的溫度
“比冷更冷,只有凜冽地活著
才能保全自己的命。”我理解你存在的方式
甚至也模仿你的方式——
始終默不作聲,假裝什么都沒有看見
在漫長的嚴寒中,你寬厚的臂膀始終張開著
而我是瑟縮的,不僅僅是因為徹骨的冷
……樹林里一只鳥都沒有
而每一個角落里都擠滿了人。
這首詩的最后一行
這條江可能已經死去多年了
它的流淌是多么無辜,那些隱忍的波浪
多么無助。我在努力寫一首詩
在你眼瞼存留的夜色中,風纏繞著指尖
只需微微轉過身子,就能躲過月亮的碎片
但你沒有。作為一個雪人,你只要轟然倒下
就能填補我寫不出的最后一行
——但你沒有。
被春風掏空的心
很多人說走就走了
死神詮釋了無常,突然松開的手
詮釋了決絕。我們剛剛送走的朋友
掌心還有余溫,用來和活著的人握別
雪白的床單溢出消毒水的味道
每一次告別都讓人沮喪
但又要返回到人海中——
一邊感嘆著生命的脆弱
一邊暗自慶幸自己還能活下去
我們總是這樣:恐懼死,而又厭倦生
當你被一層層地堆起來,被雕刻出
人的輪廓,挺直的脊背,有力的大手
……睜開的眼睛和緊閉的嘴
大雪是你的父親,寒風是你的母親
萬物懼怕嚴冬,而你懼怕春天。
沒有人看見你在春風中流下的淚水
緩緩地坍塌,慢慢把自己殺死。
——沒有人會來和你告別
你被春風掏空的心,到底有沒有生離死別的疼痛
凡是被雪人看見的
古人投出的標槍還在雪中飛翔
我們忙著把滑雪板塞進汽車后備廂
天氣一天天變暖,世間的孩子
都在長高,只有你一天天矮下去
我怕冷,而你恐懼灼熱的心
死亡以溫暖的方式
掏空你的肺腑。慢慢倒下的
偉岸的身軀,沒有恐懼的人生
就沒有任何意義。人們匆忙逃離
雖然躲過了古人的標槍,但還是來不及
躲過你睜開的眼睛。凡是被你看見的
都將成為你,或者你的影子
緘默才更可信
在一個雪人的背后,是從山林中移植來的白樺
它們規規矩矩地站立著
仿佛被施了某種魔法,其實在這世上
沒有一只眼睛是空的
只是假裝看不見而已
……我們寫下的,大多不夠真實
而你的緘默才更可信,即使被那么多眼睛盯著
即使被尖銳的枝椏頂住蒼白的肋骨。
你能不能聽見我大聲歌唱
有些人不會再來了,腳印已被新雪覆蓋
紅色圍脖被風越拉越緊
只有一個獨自飄蕩的氣球
圍繞著你。防波堤把我們帶向遠方
而江水從不會倒流。我努力踮起腳尖
卻依然看不清你的眼睛
遠在西雙版納的兒子沒有接聽我的電話
微藍的薄霧發出清脆的響聲
寒意不知不覺刺進胸口,我想面對你
大聲歌唱,不管你是否能夠聽見
我在詩歌中把自己打掃干凈
我們更容易迷失于自身的濃霧
——寫詩,是為了拆掉內心的籬笆
釋放那個白發蒼蒼的孩子
其實活著也不是多么痛苦的事
……當我在一首詩中把自己打掃干凈
雪人高高佇立在原野。
隔著一場大雪的距離
你所認識的白樺眼睛都朝向別處
而枝椏斜斜地伸進雪中
在這原野上,我們之間隔著一場雪的距離
蘆葦起伏著,但是并沒有發出沙沙的響聲
雪包容了這一切,而唯獨你還在試探著
一枚裂開的銅錢……
一半深埋在雪中,另一半卡在凍僵的眼瞼
我厭惡這秩序,繞不開的路人
腳印沒有很快就被遮蔽,就像這半生的辯解
你凍僵的手指,此刻指證了烏云的戾氣
藏起你的雙手
我無數次地奉勸你,藏起你的雙手
或者其中的一只。我們亮出的太多了
……雪仍然無可奈何。
天空交出了它的混沌,人類坦白了自己的滄桑
我們的孩子,昨晚還出現在夢中
一個無比愧疚的父親,把所有的大雪都抱在懷中
卻仍然是那么輕。膽小的男人
羊毛圍巾結滿了冰霜。沒有人承受過
真正的苦難。“只要我們還活著就好啊……”
風這樣說,風在替我修改這怯懦的詩行。
冷是一匹烈馬
我們對冷的理解不一樣,我曾經說過:
冷是一匹烈馬,在我們的身體里咀嚼著寒冰。
在冰封的松花江上,南方的朋友問我
那些水到哪里去了?這被幽禁的河床
沉默著。我沒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
半跪在冰面上,不停地擦拭,我們的眼睛
沒有力量看得更深,更遠。
耳朵背叛了傾聽,進入更遙遠的寂靜
日子全都凍僵了,過去的,將來的……
包括我們的淚痕,皺紋里的嚴寒
仔細想想,這樣也是好的,把身軀雪藏在風雪中
再也不需要給這個世界一個理由
再也不用多說一句廢話。
風雪中拜謁蕭紅
“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
大理石的雕像被風抽打著,有病的人,那么不幸
……又是那么幸運。如果你留下來又會怎樣
我在漫天的風雪中凝視你,而你也在看著我
蕭紅。我深信不疑的是:
今天的大雪是從你的心里落下的
那三只流浪的小貓,淚水在眼窩結冰
它們叫一聲,我的心就疼一下,就像被利器所傷
紀念館里,你那些故人都死去了,唯獨你
還在活著。蕭紅,我從沒看見你笑過
呼蘭河被雪埋葬了,沒有人能續寫你的半部紅樓
他們不配。在回城的路上,我安慰遠方的朋友
——那在你的故居忍受饑寒的小貓
身體里一定收留過你的靈魂,哪怕是短短的一瞬
在更大的風中
母親從云南打來電話,囑咐我要多穿,別凍著了
其實我早就被嚴寒所傷,骨頭已成堅冰
不斷地斷裂,刺穿自己的胸膛,風雪肆意穿行
我知道這寒冬的力道,暴風雪在睫毛上起舞
因此我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模糊的
……雪不會降臨給所有的人,寒流只涌向
那些善良的心。我使勁跺腳,讓自己越陷越深。
趁還有勇氣,趕緊把自己握緊,再握緊
直到變成一朵雪花的樣子,在更大的風中
在更深的夢中,無聲無息地飄蕩著。
冰涼的哨音
今天會有哪個詞語出現在這張紙上
白樺林中一條烏青色的狗,靜靜地看著我們
被深埋的腳踝,仿佛沉沒的陸地
天空和大地本就沒有任何區別,好人和壞人
都在殘喘著。每一朵雪花的長相都是不一樣的
但你無法長久地凝視它們。
風雪在咆哮著月亮,斧子在等待路過的樵夫
我們沒有柴火,但是也要點著篝火
落日是一顆燒紅的子彈,穿過這茫茫雪原
我的叮嚀,只能由它書寫,用那冰涼的哨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