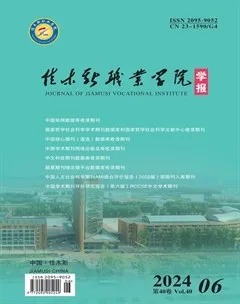《我的父親》中“父與子”母題的三個維度解析
摘 要: 《我的父親》(Хороший Сталин)系俄羅斯著名作家維克多·葉羅菲耶夫(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рофеев)創作的長篇小說。這部被譽為“當代《父與子》”的小說反映了當代俄羅斯文學進程中“父與子”母題的別樣面貌。兒子對原生家庭的矛盾態度、父輩與子輩之間的思想沖突以及造成上述現象的文化空間貫穿小說始終。借助家庭、思想與文化空間三種維度,《我的父親》跳出了建構父子沖突情節的范式,擺脫父子母題小說的中心化思考模式,將人格的形成過程同形成人格的文化空間進行整合,并對“父與子”文學母題進行重構,最終得出:“父與子”的文學母題已突破真實與虛構文本之間的界限,在文本之外得以延續。
關鍵詞: 《我的父親》;“父與子”母題;文化空間;真實與虛構
中圖分類號: I207.67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5-9052(2024)06-0079-03
引言
俄羅斯作家葉羅菲耶夫所著《我的父親》通過描寫一位外交官以及其子對他的看法,勾勒出一幅別樣的“家庭史”。作者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想在這部小說中描寫我家庭中很多年一直存在的父與子矛盾,但名稱不能叫做《父與子》,因為俄國經典作家屠格涅夫已著有《父與子》”。維克多父子沖突框架的構建撐起了整部小說,然而維克多父子之間的矛盾又不同于屠格涅夫創造的原初模式。首先,作為兒子的維克多既享受著原生家庭帶來的種種便利,又對為他帶來便利的父母持批判態度。其次,維克多少年時生活在法國,不同的文化空間塑造了其不同于祖國人的特質。而這些影響最終演化成了維克多父子思想上不可調和的沖突。家庭、思想和文化空間是《我的父親》中的三個重要維度。
一、家庭——“審父敘事”
父輩與子輩是基于血緣關系而建立的倫理關系,亦是具有代表性的社會文化符號,自古以來都是東西方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主題。弗洛伊德將悲劇《俄狄浦斯王》解讀為人類基本的戲劇符號,并認為在家庭的框架中父親作為否定力量的介入(第一階段為主體和母親的二元關系),建構了“父親-母親-我”的三維結構。吳靜在《欲望-生產、配置、反俄狄浦斯:打破裝置化的可能性》的一文中指出:“精神分析理論默認了一種預先被構造起來的、連貫的無意識模型,從而完成了對個體的調教和對欲望的壓抑。[1]”也就是說,在弗洛伊德的視角下,子輩的能動欲望來源是來自父輩的壓抑,是一種“未完成”。顯而易見,弗洛伊德的理論總是仰仗著單一的敘事話語,使得分析視角一直禁錮在家庭中。維克多·葉羅菲耶夫在《我的父親》中塑造了一個家庭空間,包含了父親、母親以及我(維克多)。然而,作者借助對父親和母親的刻薄分析將這個空間解構了。仔細體察《我的父親》的情節后,我們不難發現:父親在維克多的成長過程中沒有做出任何實質上的壓抑行徑,甚至維克多在小說中給自己評價是:“嬌生慣養”。“審父敘事”就是創作欲望在個人心理層面進行投注的實質。
關于《我的父親》體裁,評論家們眾說紛紜。批評界一說是自傳體小說或者是回憶錄,也有人稱之為自傳文學、作者自白或文學隨筆。但根據維克多·葉羅菲耶夫本人在《莫斯科新聞》上的說法,可以確認這是一部長篇紀實小說[2],即基于歷史和回憶的真實資料基礎上對文本進行了某些虛構。所以,回憶片段是研究“審父敘事”的重要切入點。第一,回憶片段中透露著主人公家庭與過往。主人公的思想經歷,其身上的西方影響連通著他對原生家庭的刻薄評價構成了這部小說“父與子”母題的一副面孔。第二,思考自我存在的“特殊性”體現了法國文化空間和存在主義對作者本人思想上的影響。“回憶錄片段”給予我們一種啟示:可以嘗試搭建起文本結構與敘事同文學母題之間的聯系,用以理解文本與創作思想。小說中維克多進行的最為豐富的心理活動就是對父母近乎刻薄的分析。而這種分析最原本的樣貌是對父親基本身份的解析:“父親——外交官”。“我企圖在內心自我解釋,我不再熱愛外交事業,最主要的原因:外交不是別的,而是至今所積累的歷史經驗把我父親的行為變成集樸實忠厚行為之大成。[3]”在《我的父親》中,父親是一名外交官,為祖國的外交事業鞠躬盡瘁;而維克多是一個受到了法國思想影響的人,自詡“先鋒派”,立志于在“停滯”的文藝領域開拓創新[4]。他們都堅定地維護自己的立場,這樣就建構了一個別樣的沖突框架:“我與父親都是理想主義者,以相似的方式捍衛自己的觀點,而這恰恰使我們分道揚鑣”。維克多的母親同父親一起在高級翻譯學校學習,對西方世界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維克多起初以為母親同他是戰友,然而隨著維克多對世界與文化的認識加深,母親開始有意地管制維克多閱讀的書籍,“母子同盟”就這樣瓦解,維克多和母親的文化聯盟由于她為父親的仕途過分擔憂而解體。
《我的父親》的“審父敘事”反映了欲望在個體心理層面上投注的實質,而這種欲望并不是弗洛伊德認為的,受到在家庭中的權威影響而誕生的“被壓迫的”欲望,而是一種積極的、生產的欲望,推動維克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德勒茲和迦塔利認為:拉康的結構主義分析導致了“父親之名”的中心化,讓其成為了某種讓人信奉之物。從“審父敘事”這一維度來看,對父母進行心理上的分析的實質是打破了父輩與子輩的倫理關系,使得父親在維克多心目中的形象不再是偉大的、不可撼動的,而是在心理層面同維克多平起平坐[5]。這導致了心理層面上的家庭解體。維克多在心理層面無法同家庭產生共鳴,繼而表現出對父母事業的不關心與漠然。值得一提的是,對父母的看法集中于維克多的少年時期,也就是說反叛的種子早已在分析父母的過程中種下。
二、思想沖突與文化空間——新人之困境
拉康對弗洛伊德的理論進行了重讀,將父親的權威從個體的無意識拓展為語言文化層面的無意識,從而建立了森嚴的等級制度,將能動欲望的生成緊緊限制在了家庭之中。而德勒茲和迦塔利認為:弗洛伊德與拉康的理論之局限性就在于它具有結構性和等級制特征。代際沖突是人類面臨的永恒問題。它沒有繞過任何一個民族,沒有繞過任何一個時代。每次父親和孩子發生沖突,他們都會找到不盡相同的理由。但這種對抗的本質是什么?在思想觀念的斗爭中,生活條件的變化意味著思維模式的變化。維克多成長在法國,在法國度過的歲月深深影響著他。而他也顯然不具備身邊同事對于這片土地的情感,也正是因此維克多認為自己“不珍惜在祖國的生活”,從而導致了悲劇發生。將思想的誕生與更宏大的社會生產活動結合起來,可以探尋思想同另一文化空間碰撞的本質——創造新人。
欲分析新人形成的原因,首先便是分析塑造維克多人格的文化空間[6]。維克多年少跟隨父親駐法國,來自法國和歐洲的影響融入了維克多的成長之中:“實際上我在法國是匆匆過客,我生活在法國的最表層,但是法國卻把我整個地、完全地吞沒了。”在法國文化環境下成長的維克多人格中逐漸產生了“非祖國性”,文化的“雙重國籍屬性”成了他身上鮮明的標志。在巴黎的密友甚至調侃他:“你去巴黎比去圖拉容易得多” [7]。維克多成長的文化空間造就了他不同于蘇聯人的特性,而這種特性也會必然影響其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
返回蘇聯參加工作后,維克多在文化和藝術上的理解同本國現實的沖突日益加劇。在法國生活的歲月造就維克多的志向——在文藝領域開拓創新,于是他打算制造一枚“文學核彈”——文集《大都會》。令人意外的是,這枚炸彈卻在不諳文學的父親手上爆炸了——由于兒子創辦刊物未經審查,作為外交官的父親被停職。在當時,迫使父親離開外交官的職位就等同于在思想層面上與之了斷。李莉在《反俄狄浦斯視域下論郁達夫小說的欲望敘事》一文中指出:弗洛伊德與拉康的理論把人的動物性看得太高,反而把人的社會性放低,造就了人對批判外界轉向對自我欲望的批判。維克多編撰《大都會》文集是具有法國文化空間印記的“新人”同蘇聯文化空間碰撞的結果。作者葉羅菲耶夫本人曾在隨筆《十年之后》中表示:“《大都會》文集是一次反抗‘停滯的文學創作之嘗試”[8]。然而在堅持自己創作理想的過程中,父親卻意外成為了犧牲品。
維克多的行徑是在一個文化空間下塑造出的人格與思想與另一個文化空間碰撞出的結果。如果堅持將維克多的行徑看做是反抗父親的話,那么父親連帶受到的壓迫便無從解釋。思想與文化空間的維度切實反映了“新人”維克多的困境——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他無法平衡法國文化的影響與祖國文化空間的現實。20世紀70年代被歷史學家稱為“停滯”時期,同時在文學上也造就了“停滯”現象。作家維克多·葉羅菲耶夫曾在論文《追悼蘇聯文學》中嚴厲地指出:作家們長期以來為了生存不得不違背自己的詩學,一石激起千層浪。兒時的維克多同父親駐派法國,之后回到了那個血統上屬于他而文化歸屬感不強的空間。在某種意義上,作為“新人”的維克多的困境與同父親的思想決裂就是注定的,凸顯了“父與子”母題文學悲劇的宿命論感。
三、真實與虛構——再繪“父與子”母題
毋庸置疑,《我的父親》是一部“父與子”母題小說。它既描寫了父親與兒子之間不可避免的思想沖突,又建構了父親同兒子的思想決裂。但經過對家庭、思想與文化空間三個維度的分析之后,我們不難發現,維克多與父親之間的模式不再是單純的沖突,而是呈現出了沖突與理解相互并存的樣貌。隨著來自高層的壓力,維克多被開除出蘇聯作協并面臨驅逐出境的威脅,父親則停職接受審查。在真正的外力面前,維克多才感覺到同父親是共同體。縱使思想上的沖突多么不可協調,當務之急是將“父子共同體”從來自外部的壓力之下解救出來。過去的事實是:父子關系在人類歷史上具有某種恒定的品質,而“父與子”母題也相應地保持著恒定的特性。“父”代表權威與秩序,而“子”代表著發展與創新。在這一層面上,維克多同父親似乎會一直處于對抗模式,永遠不可能相互理解和包容。但是把視角放在更宏大的人類社會活動層面上,來自外部的壓力會激發父輩與子輩的關系中新元素的誕生,促使父輩與子輩之間形成命運共同體,從而展現出“既相生,又相克”的特點,使得“父輩”與“子輩”既對立,又相互統一。
在“父親離職”的情節之中,這種“對立與相互統一”展現地更加淋漓盡致。蘇聯作協要求維克多就《大都會》事件寫出書面悔過書。就此,父親讓維克多先反思自己的錯誤,暫時不要寫悔過書。而父親事實上接受了革職,從而保住了維克多免遭驅逐。甘愿做出犧牲的父親形象在“父與子”母題的小說中十分少見,同時也顛覆了人們以父親為權威的看法。而作為兒子,維克多的做法也沒有令人失望——或許是出于對父親的內疚感,他動用了紈绔子弟時期的舊關系,使父親重返外交比干一份兒閑職,薪水不低。這樣的結局可以看做“父子共同體”對抗外部壓力的一次勝利,給予了悲劇的故事一點點慰藉。
“父子共同體”是父輩與子輩共同面臨外在強力作用下誕生的,而在“父與子”母題之下,父子沖突是必然的。作者葉羅菲耶夫的父親讀過《我的父親》之后,指責這部小說存在對家庭的不公正描寫,要求其作出解釋。盡管作者聲稱《我的父親》是一部虛構小說,但父子沖突早就超越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在小說之外延續。“父與子”母題通過隱喻的方式來暗指現實世界中的現象,是虛構文本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點點映射。而在《我的父親》中維克多與父親的沖突以“父子共同體”得到了暫時緩解,而作家維克多·葉羅菲耶夫同父親的沖突還在真實世界中繼續,這就搭起了一條連接真實與虛構的線,同時也印證了“父與子”母題的永恒性。在德勒茲的視角下,寫作是一個生產的行為,它永遠是未完成態的,永遠在成形之中,并將超越所有已經存在的質料。“父子共同體”的出現以及父子沖突超越真實與虛構的延續可以看做是一種生成的行為,它超越父子沖突的建構模式并且重構了當代文學中的“父與子”母題。
結語
借助家庭、思想與文化空間三個維度,《我的父親》中的“父與子”母題不再將分析視角局限于家庭之中,而是通過分析“審父敘事”,探究家庭在心理層面上的解體過程,總結子輩對父輩事業漠然的成因;整合人格形成過程與形成人格的文化空間,發掘同經典文本相同的要素——新人。而20世紀的新人的困境在于,現代社會的人們可以輕松地跨越不同的文化空間,但無法調和不同文化空間留下的印記,繼而同父輩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三個維度”為“父與子”母題文本提供新的分析視角:小說擁有別樣的建構模式,文學不再看作是“中心化”的慕仿或映射,體現了后現代主義作家創作中的“反總體化”與“去中心化”思想。小說雖是虛構文本,但是運用了自傳——回憶錄性質的語言對父輩進行分析并且探討了子輩自我認同情結的問題。而“父與子”母題沖突的永恒性又可以反映人類文化進程,是社會文化發展的縮影。在這種意義上,只要人類社會還在發展,“父與子”的故事就會繼續發展下去。
參考文獻:
[1] Вик. Ерофеев. Деся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М. Москва: Текст, 1997.
[2]Вик. Ерофеев. Страшный суд: Роман. Рассказы. Маленькие эссе. -М. : Союз фотохудожников России, 1996.
[3]Скоропанова И.С. 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и Наук, 1999.
[4]李莉.反俄狄浦斯視域下論郁達夫小說的欲望敘事[J].寧波開放大學報,2023,21(03):78-82.
[5]汪民安. 文化研究關鍵詞[M]. 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9.
[6]維克多·葉羅菲耶夫著;陳淑賢譯. 我的父親[M]. 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20.
[7]吳靜.欲望-生產、配置、反俄狄浦斯:打破裝置化的可能性[J].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21,(02):216-232.
[8]張建華.家庭、青春、代際鴻溝——屠格涅夫長篇小說《父與子》的三個維度[J].中國俄語教學,2019,38(03):37-43.
作者簡介:于碩望(2000.05— ),男,漢族,遼寧省大連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羅斯當代文學。
基金項目:2023年四川外國語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資助項目“俄羅斯文學中“父與子”母題流變研究——以維克托· 葉羅菲耶夫小說《好的斯大林》為例”(項目編號:SISU2023XK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