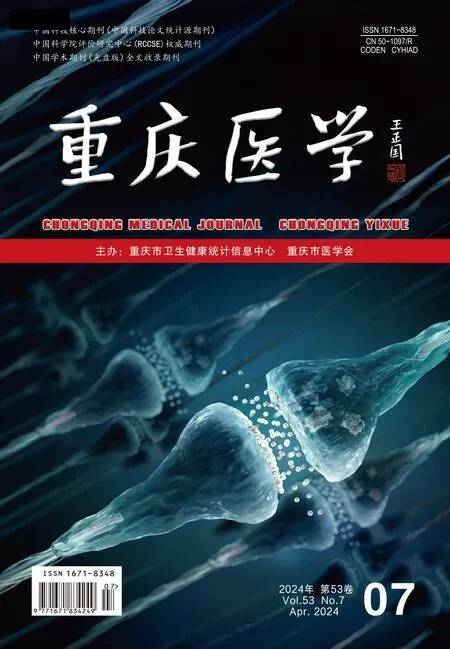免疫炎癥與降低血壓的相關研究進展*
蒙 妮,李文俊,姬燕梅,郭 妮,金醒昉△
(昆明市延安醫院:1.心內科;2.心外科,昆明 650051)
高血壓是指非同日3次測量血壓均≥140/90 mmHg,長期的血壓升高會導致心、腦、腎等靶器官損傷,具有較高的患病率和致死率。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截至2015年,我國約有2.45億高血壓患者[1]。高血壓也是全球致死性疾病之一,2019年全球約19.2%的可歸因死亡來源于高血壓[2]。因此,高血壓患者的血壓控制是全世界的重點關注課題之一。
目前,高血壓的主要降壓方式包括改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控制體重、戒煙限酒、增加運動、減輕精神壓力及藥物治療,常用的降壓藥物有鈣通道阻滯劑(calcium channel blockers,CCB)、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angiotensio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ARB)等[3]。但是,通過傳統降壓方式降壓的高血壓患者中,仍有40%無法獲得滿意的降壓效果[4],即使血壓控制良好,高血壓患者的心血管并發風險也并沒有達到相同血壓水平正常人群的預期流行病學水平,說明心血管并發癥風險并沒有因血壓降低、控制良好而減少。這種不可逆的風險在心腦血管事件中占50%,比較之下,CCB的冠狀動脈事件殘余風險更大,ACEI的卒中風險更大[5]。現使用的降壓藥物都有不同的殘余風險,學者們也在不斷研究新的降壓靶點用于降低血壓。
機體免疫反應是人體抵御外來入侵的一道防線,構成免疫系統這一部分的細胞通常會吞噬并直接殺死病原體,或消化病原體并將病原體特異性抗原呈遞給適應性免疫系統的細胞,激活適應性免疫系統,產生有抗原經驗的或有效的T、B細胞,從而產生強大、高度特異性的免疫反應來消滅病原體[6]。近年來,研究發現高血壓患者中活化的促炎單核細胞和淋巴細胞的比例更高,這些激活的免疫炎癥細胞會滲入靶器官,導致脈管系統和腎功能紊亂,最終影響血壓[7]。雖然在風濕性、自身免疫性和移植患者中的試驗表明,由臨床前研究確定的各途徑特定抗炎藥物可能具有降壓作用,但除了說服力較強的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阻滯劑,其他藥物如羥氯喹、霉酚酸酯等都有自相矛盾的研究結果[7]。了解不同抗炎途徑降壓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免疫炎癥與降壓。
1 高血壓對機體免疫炎癥狀態的影響
高血壓是由脈管系統、腎臟及交感神經系統共同調節的復雜多因素疾病。機體血壓的穩定取決于血管收縮劑和舒張劑之間的動態平衡。血管收縮劑釋放過多會引起血管內皮損傷及其功能障礙[8],而內皮損傷的重要機制是氧化應激和炎癥。高血壓的發生也是機體氧化應激的增加和總抗氧化能力的改變[9],氧化應激是高血壓病理過程的核心,既可以引發機體炎癥發生,也可以是炎癥反應的結果。
高血壓的經典途徑之一是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的激活,增加的腎素可以通過異左旋前列腺素激活先天性免疫系統,由含花生四烯酸的脂質通過異前列腺素途徑被自由基氧化,經過一系列反應產生γ-酮醛,可激活CD4+和CD8+T細胞[7]。在動物模型中,血管緊張素Ⅱ(angiotensin Ⅱ,AngⅡ)增多可增加血管周圍脂肪組織中的T細胞、巨噬細胞和樹突狀細胞[10]。在其他的高血壓動物模型中,單核細胞、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數量與血壓升高呈正比[11]。除此之外,在臨床研究中,分析對比高血壓患者和血壓正常人群的免疫細胞亞群,發現高血壓患者體內的免疫衰老細胞、促炎癥細胞、細胞毒細胞及非經典單核細胞數量均增加[4]。在各種高血壓和高血壓兒童的模型中,發現T調節細胞數量減少[12],T調節細胞減少在高血壓左心室肥厚患者中也會明顯減少,且老年女性比男性更低[13]。
這些活化的免疫細胞在靶器官(血管、大腦、心臟和腎臟)中長期堆積,造成機體的慢性低度炎癥,破壞這些器官的血壓調節能力,進一步升高血壓,加重靶器官損傷[7]。血壓升高改變了機體的免疫炎癥狀態,改變的免疫炎癥狀態又反作用于血壓及其靶器官,故阻斷機體免疫激活、采用抗炎治療可能是降壓的新途徑。
2 非藥物途徑抗炎對血壓的影響
VAMVAKIS等[14]研究督促76例高血壓患者強化生活方式,包括增加水果和蔬菜攝入量、減少鹽的攝入量、減輕體重及定期進行體育鍛煉,在6個月后對患者血管內皮功能、血尿電解質分析和血壓變化等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強化生活組的尿鈉排泄量、收縮壓、舒張壓均降低。另一項隨機對照研究發現,連續12周進行有氧運動和抗阻訓練的高血壓患者日間血壓和24 h平均血壓均下降,并且,有氧訓練組的炎癥標志物(C反應蛋白、單核細胞螯合蛋白-1、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和凝集素樣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受體-1)和內皮素-1水平也出現了下降[15]。
以植物為基礎的膳食蛋白質可能會豐富與抗炎作用有關的細菌種類,肉類消費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炎性腸病的風險[16]。低鹽飲食可以減少促炎癥白細胞和T淋巴細胞在高血壓靶器官組織中的浸潤,減輕微血管的損傷[7],證明控制飲食中鹽的攝入可改善機體的炎癥狀態,影響血壓,促進機體健康。但也有研究呈相反的觀點:食鹽攝入量與預期壽命呈正相關,與全因致死率呈反相關[17]。以上研究都闡述了運動和控制飲食等健康生活方式可以影響機體電解質的排出,降低血壓,減少機體炎癥物質的產生,抗炎的生活方式作為降低血壓的重要途徑不可忽視。
3 免疫細胞對血壓的影響
3.1 T細胞
一般認為,AngⅡ誘導所致高血壓與血管周圍組織的T細胞浸潤、氧化應激、細胞間黏附分子-1、腫瘤壞死因子的表達及內皮依賴性血管舒張的損傷有關[18]。有研究發現,在人源化小鼠模型中,長期輸注AngⅡ導致人類CD4+T細胞在淋巴結、腎臟和主動脈中積聚增加,CD4+T細胞產生的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7A也在人的循環中明顯增加[19]。而IL-17A被多種T細胞亞型產生,可以通過誘導內皮細胞一氧化氮合酶在蘇氨酸495上的磷酸化,導致內皮細胞依賴的血管擴張受損[20],最終導致血壓升高。ABAIS-BATTAD等[21]使用敲除了重組激活基因1(recombination-activating gene 1,RAG1)的鹽敏感高血壓模型小鼠,以高鹽飲食喂養3周后,通過儀器監測血壓并使用外科手段明確腎臟損傷程度,發現RAG1敲除小鼠的血壓升高程度和腎臟損傷程度均較對照組低,證明T細胞在AngⅡ誘發的高血壓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研究顯示[22],表達鹽皮質激素受體(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MR)的T細胞在系統性高血壓中發揮重要作用。MR拮抗劑在臨床上被用于降壓治療,但是T細胞在MR中調節血壓的具體機制仍不清楚。MR是一種核蛋白,與活化T細胞核因子1和活化蛋白1復合,以促進CD8+T細胞產生干擾素-γ,如果特異性刪除T細胞中的MR受體,可以使因血壓升高和AngⅡ引起的腎臟和血管損傷急劇下降。小鼠模型實驗結果顯示,MR敲除減少了AngⅡ誘導產生干擾素-γ的T細胞數量,特別是CD8+T細胞群體在腎臟和主動脈中的積累。相反,如果T細胞中的MR過度表達會加重高血壓,T細胞MR過表達小鼠在AngⅡ輸注后的血壓升高幅度遠高于對照小鼠,而使用干擾素-γ中和抗體可以消除這種差異[22]。
另外,有試驗證明血清和糖皮質激素調節激酶1(serum/glucocorticoid regulated kinase 1,SGK1)依賴性在自身免疫過程中是調節前體和抗炎T細胞發育平衡的關鍵節點,SGK1在體外和體內抑制Treg的擴展和功能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23]。NORLANDER等[24]使用T細胞特異性缺失SGK1的小鼠和野生型小鼠,以AngⅡ誘導其產生高血壓,4周后對比試驗組和對照組的血壓和腎臟白細胞、T細胞數量,發現實驗組平均血壓較對照組低25 mmHg,腎臟浸潤的白細胞和T細胞數量(包括CD4+、CD8+細胞等亞型)遠低于對照組,證明SGK1缺失可以減弱AngⅡ引起的高血壓,減輕腎臟因高血壓產生的炎癥浸潤[24]。
藥物研究方面,學者在鹽敏感高血壓大鼠模型中發現,輔助性CD4和細胞毒性CD8 T淋巴細胞以相同數量浸潤受損的腎小球和血管周圍區域,使用菌霉素或他克莫司,可以使腎小管間質免疫細胞浸潤減少了50%~60%,改善高血壓和蛋白尿情況[25-26]。另外,有研究顯示,霉酚酸酯治療不僅降低了實驗組小鼠的平均動脈壓,甚至抑制了因腎內血管緊張素原引起的巨噬細胞和IL-6水平升高,最終減輕了AngⅡ引起的蛋白尿、腎小管間質擴張和腎小管間質纖維化[27]。
上述研究證明了通過免疫細胞靶點降低血壓是可行的。T細胞中含有眾多與血壓相關的靶點,可分泌與許多血壓相關的細胞因子,隨著實驗技術的拓展和藥理研究的進步,針對T細胞降壓、緩解靶器官損傷進行研究很有前景。
3.2 B細胞
B細胞在哺乳動物的適應性免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能檢測和處理抗原,分化為漿細胞并產生抗體。對于B細胞產生的抗體,不同學者發現,原發性高血壓患者血清中免疫球蛋白G(immunoglobulin G,IgG)、IgA或IgM抗體水平均有增加[4],認為高血壓的發生與抗體水平升高相關。另有研究表明,血清總IgG水平的升高可以作為避免高血壓患者發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獨立預測因素,IgG對于心血管系統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28]。實驗證明,B細胞衍生的抗β2-糖蛋白1抗體IgG的產生和沉積在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hyper homocysteinemia,HHcy)高血壓腎損傷小鼠的腎小球內皮細胞上,引發了鐵蛋白沉著和腎小球硬化,使用抗CD20單克隆抗體和鐵蛋白酶抑制劑Fer-1可以有效地改善HHcy加重的高血壓腎臟損傷[29]。
DINGWELL等[30]認為,原癌基因c-myb不僅可以調節血管平滑肌細胞的增殖和分化,還可以對血壓產生影響。c-mybh/h小鼠為缺乏T細胞和B細胞的小鼠,與野生型小鼠比較,c-mybh/h小鼠基礎收縮壓和心室峰值收縮壓有所降低,其中收縮壓約降低20 mmHg,心室峰值收縮壓約降低10 mmHg。但是,c-mybh/h小鼠在心臟的結構和功能上與野生型小鼠并沒有差別。由于外周血和腎臟免疫細胞群在c-mybh/h小鼠中受到多種免疫細胞缺乏的干擾,該實驗還檢查了骨髓來源的細胞群是否介導c-mybh/h小鼠的血壓降低表型,發現全身性(可能為腎臟)B細胞缺乏癥通過腎臟機制降低血壓。該學者進一步使用僅有B細胞缺失的JHT小鼠接受血壓的侵入性血流動力學評估,發現B細胞缺乏小鼠血壓依舊低于野生型小鼠,進一步證明了B細胞缺乏可以降低血壓。
以上不同靶點均表明,B細胞對高血壓及目標靶器官有一定的影響,但是,B細胞靶點及衍生抗體眾多,B細胞在血壓中的研究尚未完全深入,有待完善與加深。
3.3 樹突狀細胞
樹突狀細胞是專業的抗原呈遞細胞,能誘導/激活幼稚的T淋巴細胞,從而引發適應性免疫力[31]。fms相關受體酪氨酸激酶3配體(fms related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3 ligand,FLT3L)-/-小鼠是一種常用的、具有較少數量經典樹突狀細胞模型,其平均動脈壓和記憶T細胞數量與野生型基線相似。在經過4周的AngⅡ輸注后,與野生型比較,FLT3L-/-小鼠隊列的血壓升高幅度較小,且從輸注AngⅡ的第13~21天,血壓明顯降低,FLT3L-/-小鼠第21天血壓為(166±2)mmHg,而野生型則為(178±4)mmHg(P<0.05)。與血壓反應一致的是,FLT3L-/-小鼠在4周高血壓后,心臟重量也較對照組減輕。該實驗亦證明了經典的樹突狀細胞會增加了高血壓者的水鈉潴留[32]。另一項研究發現,限時攝入食物可以通過降低腎臟部分的先天性免疫細胞數量來降低血壓。實驗組的樹突狀細胞CD45F4/80-CD11c明顯降低,對應其有更低的血壓水平,也證明了樹突狀細胞對血壓的影響[33]。
以上研究模型大多為動物模型,具有局限性,是否能拓展運用至人體仍有較大的疑問。但是,以上研究仍表明通過干預免疫細胞可以影響血壓并減輕高血壓帶來的靶器官損傷。
4 炎癥對血壓的影響
4.1 炎癥小體
炎癥小體是先天免疫反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被證明是高血壓炎癥的驅動因素[34]。炎癥小體是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和內源性宿主衍生的損傷相關分子模式的細胞內傳感器。在多種炎癥小體中,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樣受體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在高血壓中研究較多。
NLRP3一方面通過激活半胱天冬酶-1分泌IL-1β和IL-18[35],另一方面激活細胞焦亡[36],進一步誘導釋放更多的IL-1β、IL-18和其他促炎癥的細胞因子,加重炎癥反應。臨床中發現,IL-1β、IL-18在高血壓患者的血液濃度較高。動物實驗中,誘發NLRP3基因缺失小鼠動脈壓力升高,不會產生IL-1β,也不會有心臟肥大現象;使用親脂性β受體阻滯劑或消融心臟傳入神經可以降低心臟細胞外腺嘌呤核苷三磷酸水平,抑制NLRP3炎癥體的激活,也同樣抑制了IL-1β的產生,避免壓力過高時的心臟適應性肥大[37]。有研究認為,NLRP3可能是唯一對鹽性炎癥反應的炎癥小體[38],鹽敏性高血壓的動物模型中發現有NLRP3亞基的mRNA表達增加,同時腎臟中活性半胱天冬酶-1和成熟IL-1β的蛋白水平增加[39]。NLRP3的激活還與腎臟損傷有關,采用NLRP3活性抑制劑MCC950抑制NLRP3炎癥體的活性,可改善醋酸脫氧皮質酮鹽小鼠模型的高血壓、腎臟炎癥和纖維化現象[40]。
4.2 炎癥基因
基因已經是現代醫學研究疾病病因不可或缺的內容,在高血壓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中,發現97個包含與高血壓相關的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s)基因,其中有81個在炎癥和免疫方面有直接或間接的作用[41]。SH2B3/LNK基因被認為是高血壓發生的關鍵性驅動性因素之一。若SH2B3編碼錯義,則改變了262號氨基酸編碼,使其從主要等位基因的精氨酸變成了次要等位基因的色氨酸[42]。有實驗誘導此項錯義[43],發現與精氨酸/精氨酸對照組小鼠比較,色氨酸/色氨酸小鼠在輸注AngⅡ期間的收縮壓高出10 mmHg,其腎臟損傷和血管周圍纖維化的情況更加嚴重,會產生更多的IL-12。證明淋巴細胞中SH2B3表達增加的多SNPs模型與人類高血壓和高血壓慢性腎臟病呈負相關,rs3184504的色氨酸編碼等位基因與血壓升高和腎功能不全具有因果關系。阻止此蛋白的編碼錯譯可以降低血壓,減輕血壓升高帶來的腎臟和脈管系統損傷,減少炎癥細胞因子的產生。
微核糖核酸(microRNA,miR)是一類內源性非編碼小RNA分子,在減少炎癥降壓方面,miR-214研究較多。在AngⅡ注射后的小鼠體內,miR-214在周圍血管脂肪組織中的表達升高了8倍,連續向miR-214敲除小鼠注射AngⅡ兩周后,沒有監測到血壓的改變,且主動脈周圍膠原積累/纖維化明顯減少,動脈硬化程度明顯下降[44]。
5 小結與展望
雖然實驗、遺傳和臨床證據支持免疫炎癥在降低血壓、減輕腎臟炎癥細胞浸潤、改善腎功能損傷、減輕高血壓心肌肥厚等方面發揮作用,但大多研究成果均來自動物研究,且受限于實驗方法和技術,結果具有局限性。除此之外,通過抗炎機制的降壓藥物,對比與傳統降壓藥物,在頑固性高血壓中降壓效果不明顯。這種全身性的抗炎治療是以增加致命性感染性并發癥的靈敏度為代價[45-46],所以該方法并沒有成為主流,免疫調節方法并不被視為降低血壓和減少心血管疾病的治療選擇。除此之外,由于人體免疫炎癥系統的龐大與復雜,涉及高血壓的不僅有免疫細胞、炎癥小體和炎癥基因,還包括氧化應激、血管重塑、內皮功能、內分泌調節等復雜關系網[7]。因此,今后還需更多的動物實驗與臨床研究探究其兩者關系,發現新的有效的降壓靶點,緩解高血壓治療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