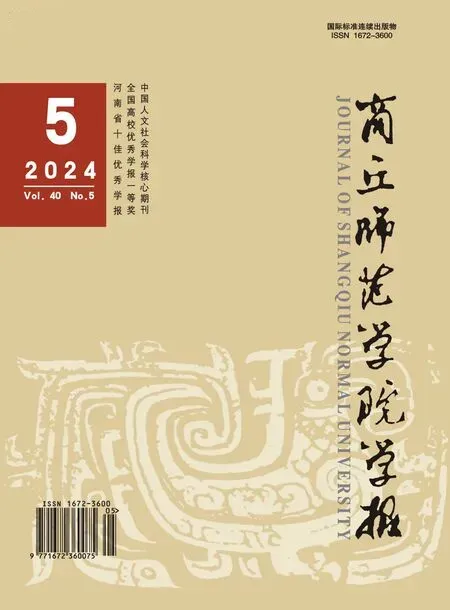明清之際河南書院復興與理學重振
張 清 河
(河南理工大學 中文系,河南 焦作 454000)
書院始盛于北宋河南,以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等尤為人才搖籃。據《宋史》記載,“宋朝興學,始于商丘”;時人稱“州郡置學始于此”,天下學校“視此而興”[1]418。慶歷三年(1043),宋仁宗下旨將應天書院改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到了二程主持嵩陽以及伊洛各書院、邵雍創建百泉書院的時候,河南書院盛極一時。正如胡適《書院制史略》概括的那樣,晏殊、范仲淹、程顥、程頤、邵雍等名宦主持的河南書院,不僅代表了時代精神,而且將講學與議政、自修與研究相結合[2]273。他們心系廟堂講學議政,身在山林自修精研,由此成為兩河碩儒、華夏精英,以其終身踐履創造了中州理學的“源頭活水”。宋末元初,隱逸山林的許衡等受到朝廷重用,暮年致仕后創建“景賢書院”,被孫承恩等稱為“考亭(朱熹)之后第一人也”。而姚樞、姚燧叔侄重建百泉書院等,一度恢復了河南書院的舊制,然這些書院皆毀于元末戰亂,此后河南書院進入近百年較長時期的停滯階段。
天順五年(1461)大梁書院、成化十七年(1481)百泉書院等崛起,與復建的嵩陽書院、應天書院并稱明代“河南四大書院”,加之成化六年(1470)陳州的弦歌書院、成化七年(1471)南陽建成的志學書院、十七年(1481)洛陽伊川書院以及在襄城尚書李敏家塾基礎上改建的紫云書院、二十二年(1486)許州聚星書院以及弘治初安陽北宋韓琦故宅基礎上修建的晝錦書院、正德十一年(1516)懷川再建的許衡祠所在的景賢書院,境內大州基本建有書院。到了嘉靖時期,河南書院實現了由州及縣的遷移;萬歷時期,人口較多的州縣基本上均有書院、義學和社學。至清初康熙時期,全州縣基本實現了書院的覆蓋,正如王洪端所云:“清代是河南書院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在逐漸官學化的同時,以犧牲個性為代價,獲得了它的繼續存在和發展,特別是在數量和分布上有了很大發展。先后設置書院達292所,除南召縣外,全省各個州縣已無一不設書院,基本實現了書院的普及化。”[3]
清承明制,程朱理學再度被確立為官方唯一的正統之學。因陽明后學講學而興盛的書院多半毀于戰亂,尤以河南為甚,諸如大梁、嵩陽、睢陽、南陽等書院皆廢止。隨著北方王學陣營的分化,出現融會程朱理學的知名學者孫奇逢、湯斌、耿介、李來章等。他們復建諸如百泉、嵩陽、大梁等書院;與之相師友的竇克勤父子創建了朱陽書院,形成新的中州“四大書院”。他們在康熙朝被視為理學正統,名列“中州理學八先生”,成為康熙時期理學的重要支柱。河南書院呈現出“中興”的態勢。本文旨在通過書院復興與理學重振的內在聯動關系之梳理,進而探求書院發展的深層次原因,為書院文化之深入研究提供一個可資借鑒的視角。
一、北方王學與河南書院之復興
書院復興是需要外力條件的。明初官方用所謂“性理大全”禁錮人們的思想,理學家難有發揮的空間;與此同時,政府將教育機構專注于州府縣的儒學,因此書院建設也裹步不前。直至成化年間,以河南提學僉事(任滿后又就地升任按察使)吳伯通為代表的官員興建了百泉書院、伊洛書院、汝南書院、大梁書院,“以祀前賢而勵后進”。此后正德十一年巡撫李充嗣重建景賢書院、正德十五年御史汪淵重修百泉書院(成化十七年督學副使吳伯通始建),并廣置田產以保障這些書院的正常教學。當時較有影響的學者,也參與到書院建設中,如正德十一年前后,李夢陽為作《大梁書院義田記》(按:正德間大梁書院遷址繁臺并用此名,天順五年始建時名為“十賢祠”),何瑭為作《許文正公祠堂記》(按:即景賢書院許衡祠),崔銑為作《重修百泉書院記》等等。然而,當時的賢達之士即便是致仕也未曾出任書院的山長。嘉靖初,王陽明傳人張璁、桂萼、黃綰等因“大禮議”崛起于政壇,北方王學在河南迅速傳播,王學弟子開始登壇講學。嘉靖七年陽明弟子劉魁出任禹州知州,在任期間新建了儒林、西溪、白沙、東峰、仙棠等五所書院,(按:除西溪書院為故戶部侍郎任洛所建,其余四所皆劉魁親建。)且不時親自講學。后來,劉魁的得意門生尤時熙成為洛學的掌門人,此時僅洛陽一縣便遍布了十多所書院,分別是狄梁、麗正、奎光、澗西、瀍東、天中、玉虛、敬業、域樸、雪香、望嵩、中山、黃鶴、洛浦、伊川、龍門、洛陽諸書院。至晚明,尤時熙的弟子孟化鯉創川上書院,另一弟子張后覺應羅汝芳之邀赴山東,任愿學、見泰兩書院山長,(《明史》尤時熙傳附:“其門人張后覺,字志仁,茌平人。東昌知府羅汝芳、提學副使鄒善皆宗守仁之學,與后覺同志,善為建愿學書院,俾六郡士師事焉。汝芳亦建見泰書院,時相討論。”)而孟化鯉的其余弟子王以悟、張信民等又出任陜州書院、澠池書院山長,此外,諸如楊東明、董定策、呂維祺、鹿善繼、孫奇逢等,基本上是北方王學的三傳或四傳弟子,他們成為啟禎年間北方儒學的宗師,由此開啟了河南書院的復興之途(1)參見湯斌《洛學編》,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0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522—523頁。。
即便如此,河南書院的復興過程也是一波三折的。明中后期也即嘉靖萬歷年間,朝廷與民間針對書院的博弈十分激烈,可謂屢毀屢建。究其原因,乃因為南北兩京皆有國子監等官學,民間書院對于官學形成了強有力的沖擊,勢必遭到禁毀。但僅就官學而言,無論是規模還是辦學業績,遠遠不能承擔一個超級帝國培養人才的重任,所以等禁毀的風潮過了,書院的建設不僅不會停滯,反而更甚從前。諸如晚年諶若水(1466—1560)致仕后,其所創建的“甘泉書院”毀于嘉靖十七年(1538),嘉靖二十三年(1544),他又在衡岳陳白沙祠堂創建“甘泉精舍”,繼續講學。萬歷七年,張居正奉上諭摧毀天下書院,耿定向、羅汝芳等于南京創設的崇正書院在列。焦竑等學生將書院改造為耿氏祠堂,繼續其學業,十年后高中狀元。自萬歷三十二年(1604)始,顧憲成、高攀龍等“八君子”罷官歸里,在宋代楊時創建的龜山書院舊址上建設“東林書院”。他們利用影響力延請了一批經學大師,而尤以經世實學為根基,東林學子很快在科場占據了優勢,形成了所謂“東林黨”,東林書院也就具備了全國性的影響力,正如柳詒徵曾在《江蘇院志初稿》中所說:“合宋元明清四代江蘇書院衡之,蓋無有過于東林書院者矣。”[4]242清初江陰陳鼎在《東林列傳》卷九《李邦華傳》中認為,晚明政局之轉折,正是從此開始的:“議時眾正淪替,呂坤、鄒元標、顧憲成皆被逐,而王紹徽、徐兆魁等猶目側東林諸賢為朋黨。”[5]4
河南書院之崛起,亦與“東林書院”異曲同工。明中葉以后,黃河兩岸四府(開封府、河南府、懷慶府、衛輝府)書院再度繁盛,尤其在明嘉靖萬歷年間。嘉靖間,僅大梁書院就培養了諸如李夢陽、王廷相等“七子”俊彥,以及沈鯉、高拱、呂坤等名臣。沈鯉、呂坤亦是著名理學家,其教育影響力雖不及東林顧、高,但是在明清書院的發展史上,一樣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們與江夏郭正域并稱為“萬歷三大賢”。沈鯉除了應高攀龍之請而作《東林書院記》,還在丁憂期間與當地官員從無到有興辦了歸德府學,晚年著《文雅社約》,期待鄉賢等置辦義田扶助教育;呂坤與顧憲成共商《東林會約》,他還在沈鯉《學政疏》七條的基礎上增為十二條,并寫有《社學要略》,強調書院建設的社學基礎。而河南府的孟化鯉創建“新安學派”,為河南諸書院培養了一批名師。隆慶五年(1571)孟化鯉建川上書院,其弟子王以悟、張信民、呂維祺諸人亦追隨左右,倡明師說。王以悟被譽為“洛西儒宗”,于天啟元年(1621)建依人書院,鹿善繼出其門。張信民被譽為“河洛真儒”,晚年創聞修堂書院。天啟三年(1623)呂維祺建芝泉書院。天啟五年(1625)張信民在曹端祠的基礎上建澠池正學書院,邀請同門王以悟、呂維祺、張泰宇等前來講學。呂維祺為之作《張抱初傳》云:“嗣是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王惺所、孟宇鍵、許松麓、劉澄遠諸公與予俱大會于正學書院,與先生講《太極》《周易》。”[6]477(同治)《河南府志》卷四十《人物志三·道學》亦載:“呂維祺……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修明廉洛之學。……集郡士立伊洛社,以守先待后自責。 與王惺所(以悟)、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孟守鍵、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于正學書院。”[7]154正學書院,原名穎濱書院,據張信民《抱初先生印正稿》卷首宗人漢序[8]722,因張信民作《正學會語》,乃改名。這是黃河兩岸四府的一次大型的講會聯動,與會者均為當地政要和學者,諸如張泰宇是衛輝守備,劉澄遠是東道主也即澠池縣令等。與正學書院相呼應的是京師首善書院,系以鄒元標、馮從吾、楊東明等為首的官員創建,東林黨人亦廣泛參與共建。而鹿善繼、孫奇逢等加盟首善書院,成為北方王學極盛的標志性事件。
二、康熙時期中州理學與書院的極盛
清初北方王學的代表孫奇逢,與鹿善繼相師友,亦可視為“王守仁——劉魁——尤時熙——孟化鯉——鹿善繼”一脈的學術傳人。四庫館臣彭定求《南畇文集》十二卷提要:“定求之學,出于湯斌;斌之學,出于孫奇逢;奇逢之學,出于鹿善繼;善繼之學,則宗王守仁《傳習錄》。故自奇逢以下,皆根柢于姚江,而能參酌朱陸之間,各擇其善,不規規于門戶之異同。”[9]1658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認為,孫奇逢的王學源自家傳,即“王守仁——鄒守益——孫臣——孫丕振——孫奇逢”一脈,可備一說。前文已述:由明及清,河南書院的發展進程,與理學在中原大地的推進是互為表里的,晚明以寧陵呂坤、虞城楊東明為代表的“北方王門學派”,成為大江以北心學的主導;清初,寓居衛輝的孫奇逢重建百泉書院,更是成為北方王學的重鎮。孫奇逢一改陽明心學侈談心性之流弊,朝實學轉向,契合了上自朝廷、下至廣大讀書人的根本需求。不少官員慕名而來,他們中有的本來中過進士,前往百泉問學,是純粹向著“證道”、求取真學問的目標進發的,比如湯斌、耿介;還有的順治初便考取功名,卻仍然寄學于門下,比如魏一鰲(崇禎年間中舉,順治二年考為平定知州);還有的立志做遺民,比如王余佑、趙御眾(崇禎時諸生,入清絕意于仕進),而王余佑的弟子顏元,開創了清初以實用主義為宗尚的顏李學派。孫夏峰門下甚至還有成為大學士的寄名弟子,比如魏象樞等。正如李留林所言:“他的弟子中既有湯斌、魏一鰲、崔蔚林、耿介這樣的入仕官僚,也有張果中、王余佑、錢佳逸、趙寬夫等不計其數的青衿士人;既多入門弟子,又有魏象樞這樣的私淑弟子;既有默默無聞的鄉間士人,也有費密、薛鳳祚、申涵光、耿極那樣的大名士。”[10]56
孫奇逢的實學轉向,還表現在為理學貼上了“中州”的標簽。他寫下了《中州人物考》,梳理了北方理學發展的源流,其弟子耿介則強調二程夫子以來的道統,作《中州道學篇》。此后“中州理學”作為康熙時期學界的專屬名詞,成為明清理學發展史上較為突出的現象。耿介主持了嵩陽書院的復建工作,為書院特建“崇儒祠”,他與清代八個“文正公”之首的湯斌,并稱“中州理學之冠”,語出沈近思《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清恪儀封張先生墓表》:“我朝前輩湯公潛庵、耿公逸庵,為中州理學之冠,海內學者多宗之。”[11]1030如果說,孫奇逢實現了實學轉向,那么湯斌則實現了由北方王學向正統的程朱理學的回歸,他以“應天府書院”精神為導向,引導“睢州學派”,延續洛學正派,故而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說:“睢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在湯斌的推薦下,冉覲祖、李來章等人皆成為各大書院的山長,陳宏謀在乾隆初巡撫河南,將孫奇逢、湯斌、李來章、耿介、竇克勤、張沐、張伯行、冉覲祖并稱為“中州八先生”[12]945,可謂將中州理學名家作了總結概括,他們不但是理學家,更是書院的建設者。鄧洪波等反復撰文強調中州理學與河南各大書院復興的關聯:“清初中州理學盛極一時,河南地區也涌現出一批理學學者,他們以書院為營地展開理學復興運動……這些學者中如耿介、張沐、竇克勤、冉勤祖、李來章等皆長年從事書院教育活動,故中州理學對清初河南書院教育影響頗大”[13], “展示了特殊時代書院與理學學派在河南地區相結合所達到的高度”[14]。
中州理學在康熙年間的復興,不外乎兩大原因,其一是世道時運,其二是民意人心。就時運而言,從順治到康熙,統治者一直在尋求一種意識形態領域的頂層設計,來緩和國內漢人知識分子階層的敵對情緒并維系社會穩定。在康熙親政后,他將其所受日講公開發行,諸如康熙十年(1671)的《孝經衍義》、康熙十二年(1673)的《大學衍義》、康熙十六年(1677)的《日講書經解義》、康熙十九年(1680)的《日講書經解義》、康熙二十年(1681)的《日講書經解義》等,將這些經籍,由官府刻印贈送至儒學、書院,供師生研習。為了達到督促的目的,康熙親自挑其理學代理人,諸如熊賜履、湯斌等。康熙二十三年(1684),湯斌奉旨督學江南,并調補江蘇巡撫,拉開了康熙以理學改造世風的序幕。其二是民心思順,在康熙二十年平三藩、二十八年雅克薩大捷之后,國內的戰亂告熄,百姓開始重視文教發展生產。自湯斌巡撫江南,七八年間河南各州縣興修或重建書院近30所,分別是:二十三年周師望洧川洧陽書院、張世綬洧川培風書院、衷鹍化密縣檜陽書院、金云鳳新鄉百泉書院、徐登瀛孟縣河陽書院;二十四年陳治策通許進學書院、韓藎中牟廣學書院、郭金璧沈丘求誠書院、馬世英睢州道存書院、高巖孟津平津書院、蔣征猷鞏縣敬業書院;二十五年夏應元密縣興學書院、傅弼西平新建書院;二十六年張思明祥符大梁書院、高明峻滎陽傳經書院;二十七年顧芳宗項城虹陽書院、徐岱林縣黃華書院、申奇彩河陰興文書院、閔子奇商丘范文正公講院、呂士鵕鹿邑真源書院、徐士訥嵩縣鳴皋書院、尤應運濟源尤公書院、楊廷望上蔡顯道書院,二十八年汪楫開封狄梁書院、吳子云登封嵩陽書院,等等。當然,最為著名的還是嵩陽、百泉、紫云、朱陽、大梁諸書院,是因為它們有“中州理學八先生”灌注的心血。今人鄧洪波認為:“清初以嵩陽、朱陽、紫云、南陽等書院為陣地,中州地區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洛學復興運動,耿介、李來章、竇克勤等著名學者都積極投身其中。”[15]23
總之,康熙年間,由于中州理學的盛行,各地書院乘勢而起。以容城孫奇逢、睢州湯斌、襄城李來章等“中州理學八先生”所創百泉、嵩陽、紫云諸書院為標志,河南書院達到極盛。呂民服《大呂書院碑記》曰:“書院之設,倡于宋、盛于明,成于嵩陽、白鹿、大梁、岳麓,而道尊于蘇湖制經義治事兩齋,乃德聞于天子,而取法乎后世。于是在中州者,大梁、嵩陽外,為白沙、為伊洛、為上蔡、為澠池、為百泉、為涑水,中州書院,甲于天下。”[16]卷四十三呂氏所謂“中州書院,甲于天下”,其前提是程朱理學在河南的發展和擴張。如伊洛書院,系二程(程頤程顥)主持;上蔡書院,系“程門四子”謝良佐讀書處;澠池書院,由“明初理學之冠”曹端發起;百泉書院由邵雍創建,清初大儒孫奇逢在其故址重振之;涑水書院為紀念司馬光而建……幾乎可以肯定:明清之際河南書院再度繁盛,與程朱理學在中州重塑權威有極其密切的關聯。正是打著宋明理學家的旗號,河南書院在明清之際才得以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三、康熙時期河南書院崛起的原因探析
在宋初、清初“清平盛世”的背后,主持河南書院的儒學家身體力行成為倫理道德的維系者,繼而得到統治者的褒獎,情形是約略相似的。宋初的“三先生”石介、孫復、胡瑗創建徂徠、泰山、安定諸書院,掀起了儒學的發展熱潮,而清初百泉、嵩陽、紫云諸書院的“山長”孫奇逢、湯斌、耿介、竇克勤、李來章、張沐、張伯行、冉覲祖等,并稱“中州理學八先生”,在全國教育界獨領風騷,“河洛之學”亦轉變成為官方理學的內核。尤其是孫奇逢,因其壽耆德馨、學高望隆,與顧炎武、黃宗羲并稱“清初三大儒”,四庫館臣則以李颙代替顧炎武,亦有所謂“三大學術宗師”之說:“黃宗羲之學盛于南,孫奇逢之學盛于北,李颙之學盛于西。”[9]304那么,清初諸如百泉、嵩陽諸書院崛起的原因何在?固然承平之初國家需要文教人才,這是一大主因,但為什么宋初之學起于山東,而清初之學盛于河南?地緣、學緣、血緣以及業緣,是當時河南較之全國殊勝的另外四大主因。
首先是地緣。明清之際河南書院能夠復興,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州是程朱理學的發源地。孫奇逢曾說:“洛為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黃河蜿蜒,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泄其秘;而渾龐厚樸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是道寄于人而學寄于天。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后之統,關甚矩也。”[17]39沈近思在給張伯行所作《儀封張先生墓表》中亦曰:“中州自二程夫子闡絕學于千載不傳之后,上承洙泗,下啟紫陽,圣賢道統,如日經天。當時及門尹和靖、謝上蔡皆能守其師說,至元而有許魯齋。豈非天地清淑之氣萃于中州,而斯文有厚幸耶。”[12]1030以二程夫子為代表的、以這種“居天地之中”的自豪感為主導的理學家,強調“學以明道”“天人歸一”,成為明清河南理學的自覺追求。他們在維護理學學統、捍衛道統方面,主張言行合一,這種道統的思想一直延續下來。黃舒昺作《勸中州士人學》,結合河南的道學傳統總結曰:“中州鍾天地清淑之氣,帶河溯洛,從古人物之生,于斯為盛。自程純公正公傳道以來,伊洛一堂,直與魯鄒相并,夐乎尚矣。國朝表章正學,蘇門講席,蘊皋毓夔,湯子文正與耿逸庵、冉蟫庵、竇靜庵、張仲誠、李禮山諸公,聯轡而起。”[18]這就是“八先生”并稱的主要原因。河南作為理學的發源地,有良好的地域文化基礎,在合適的時代土壤中就能培育一批理學家和教育家,這是學術界從來就公認的事實。
其次是學緣。黃宗羲《明儒學案》,以孫奇逢為諸儒學案之殿軍,而諸儒又與東林、蕺山學案相鼎足。孫奇逢以北方王學嫡傳自居,晚年贊許黃宗羲為南方王學蕺山學派的傳人,可見其對學緣的重視。黃梨洲云:“歲癸丑(1673),作詩寄(宗)羲,勉以蕺山薪傳,讀而愧之。”[19]1372而徐世昌《清儒學案》將湯斌作為“翼道學案”之首,其次才是顧炎武,可見以“孫奇逢——湯斌”師徒之授受其實承接著明清的理學。湯斌所翼之道,自然是孫奇逢之道。他對夏峰推崇備至,曾手書序,將其與王通、朱熹并提:“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息,人心幾如重昧,賴(孫夏峰)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靡不因運會為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為當代儒者之大宗,其于文中、紫陽何如?”[20]375孫奇逢在百泉書院的影響力,實賴湯斌等一眾高徒而起。紀昀等評:“奇逢雖以布衣終,而當時實負重望,湯斌至北面稱弟子。其所著作,非他郡邑傳記無足輕重者。”[9]527確如紀昀所看到的那樣,中州的這一組師生,非其他郡邑可以比擬。湯斌本為順治九年(1652)進士,在丁憂期間,“渡河執弟子禮于孫奇逢,歸而充養愈邃,屹然推中原巨儒”[16]卷二十一。他在康熙十七年(1678),又獲博學鴻儒科第一,以其理學受到康熙重用。二十三年(1684),圣諭:“朕聞學士湯斌曾與中州孫鐘元(按:孫奇逢)講明道學,頗有實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蘇巡撫。”[21]286湯斌歿后,康熙謚文端,乾隆追謚文正,準從祀泰伯、范仲淹祠,黃宗羲為作神道碑,可見其在全國的影響力。孫奇逢弟子中,如耿介、李來章、竇克勤、張沐等講學于嵩陽、紫云、朱陽、南陽諸書院,皆名列“八先生”,只有張伯行與冉覲祖晚出,創大梁“請見書院”,與孫奇逢沒有直接的學緣關系。
其三是血緣。河南很多書院是在家塾或學舍的基礎上改建的,諸如北宋著名的應天府書院,原本是戚同文創建的睢陽學舍,宋真宗時鄉人曹誠擴建為書院,廷議之后仍歸戚氏之孫戚舜賓主持,曹誠為副。這種情形在明末清初的河南仍是相當普遍的。百泉書院之所以能夠持續下去,便是孫奇逢及其子孫的堅守。孫奇逢移家輝縣,主持興復百泉書院,講學達二十五年之久。其身后,三子望雅與其子孫淦,四子博雅及其子孫潛,以及五子韻雅與其子孫漢等接替經營書院,事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謝國楨先生《孫夏峰李二曲學譜》亦云:“夏峰子六人,立雅、博雅、侄度雅最有名,孫淦能世其學。”[22]685孫淦在康熙二十一年高中進士,官中書舍人;淦之子孫用正為康熙三十五年(1696)舉人,歷官禹州、許州學正,致仕后亦鄉居講學于蘇門,作《百泉書院志》,現存乾隆五年(1740)手稿本、乾隆十三年家藏本3卷6冊,現珍藏于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可以說,百泉書院能夠崛起成為清初的“四大書院”之一,離不開孫氏四世經營。后來,耿介興復嵩陽書院,受其啟發,竇大任、竇克勤父子創建朱陽書院。據竇克勤回憶,“登封耿逸庵先生興復嵩陽既就,謂余曰:四大吾豫居二。前人已往, 后人未來。習此業,公此事。可因則因,不則創以為因,何弗追曩徽也?余大人聞之稱善。因繼先筠峰公未競之志,于邑東門外創建朱陽書院”[23]。此外,李來章也是在祖業的基礎上復建了紫云書院(其六世祖是明初的李敏,紫云書院始建于李敏家塾基礎上)。這種血脈相連的嫡傳,保證了書院辦學的延續性。
其四是業緣(2)所謂業緣,按社會學理論,是指個人在工作中與其他人發生互動而產生的關系。這里主要指辦學。。為迎合康熙理學,連續幾任的河南巡撫大力興學。康熙成年后,表達了對理學的濃厚興趣,其遠房表舅佟鳳彩率先捕捉到這一信號,他于康熙十一年(1672)起任河南巡撫,第一年治理黃河,待水患初定,第二年便在開封城西北隅天波樓舊址興辦大梁書院、傳播理學,可惜康熙十六年卒于任上。他死后,康熙二十二年李元讓在長葛新建“大中丞書院”紀念之。(按:新舊《長葛縣志》“大中丞”所指不一,或謂新任巡撫王日藻。故后來縣志或謂之“王公書院”。)康熙二十二年,巡撫王日藻接連上疏治河、墾荒、辦學,均被皇帝批準。他為嵩陽等書院修建了藏書樓,并將《四書衍義》等經籍賞賜給書院。此舉似乎警醒了河南各地的知縣,在此后以至康熙二十九年的八年之間,河南各州縣興修或重建書院近30所。到了康熙二十九年、三十年,新任河南巡撫閻興邦規范辦學,政績斐然。一方面,他將大梁書院、嵩陽書院等影響全國的書院做成了樣板,延請耿介、李來章等“中州理學八先生”作為山長講學,迎來了中州教育的盛局;另一方面,他改造了河南境內近十所書院,并為各州縣的上百所義學提供了資金保障,使之有了延續的可能。《南陽府志》《祥符縣志》《太康縣志》《扶溝縣志》《長葛縣志》《西平縣志》等《學校志》均有載,后兩者感懷閻興邦的功德,直接興建了大中丞書院、閻公書院。除了巡撫,各地提學僉事、知州知縣也竭力興學。僅嵩陽書院,參建官員即十數人,后來山長耿介特為建“崇儒祠”供奉,設立“原任河南巡撫王日藻、閻興邦興復書院長生位,原任河南提學道吳子云、林堯英嘉意書院之位,特簡翰林院檢討、河南知府汪楫興復書院長生位,原任登封縣知縣張壎、王又旦、張朝瑞、葉封、侯泰、傅梅嘉意書院之位”[24]21。這些地方長官競相辦學、前后相續,促成了康熙中期河南書院的大發展。
綜上所述,清初康熙年間,河南書院迎來了一輪發展的高潮,不僅出現了百泉、大梁、嵩陽、朱陽等全新的“四書院”,而且周圍還興建了大小書院30余所,究其原委,除了海內承平、人心思順,社會上全面興起辦教育的風氣,亦與河南特殊的地緣、學緣、血緣、業緣密切相關。
四、結語
明末清初多數的學者和教育家,按照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歸納,基本上是“陽明學派之余波及其修正者”。誠如梁任公所言,王陽明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束,吐很大光芒”,“陽明死后,他的門生,在朝者如鄒東廓……在野者如錢緒山……都有絕大氣魄,能把師門宗旨發揮光大,勢力籠蓋全國”[25]3。《明史·儒林列傳序》中也曾提到,陽明“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26]7222。對于晚明三大學派,嵇文甫先生視東林為“王學的修正者”[27]97,梁啟超視蕺山為“王學自身的反動”,而對其余一派之“諸儒”,黃宗羲輒視為王學余波。嘉靖、萬歷、啟禎年間國家三毀書院,便是對陽明及其后學興辦講學式書院擴張的壓制。到了清初,大多數書院毀于戰亂。相較于其他郡邑,此時河南書院獲得了持續的發展,理學思潮涌動的主流是其推動力。清初理學是“遺老大師”的天下,無論是南方的黃宗羲還是北方的孫奇逢,他們作為理學秩序的維護者,都是陽明心學的傳人,他們致力于言傳身教,挽回世道人心。孫奇逢開創了百泉書院的繁盛局面,可以說,他是明清之際河南書院的始創者,其實也是理學的承擔者;書院規模化的發展壯大,其實也是宋明理學在封建時代擴張與普及的真實反映。
到了康熙時期,皇帝對于士林侈談心學而不講性理的局面甚為不滿。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玄燁就其理學啟蒙者熊賜履所著《道統》一書的頒行展開“理學真偽論”的大討論,表明其抑王(陽明)揚朱(熹)的思想。至康熙五十二年,他諭令其所欽定的《朱子全書》、“四書”注解“刊刻告竣、可速頒行”[28]608。在此期間,孫奇逢門下的湯斌、耿介、張伯行等成為康熙時期理學的杰出代表。河南書院的興衰,與中州理學活力消長互為表里,孫奇逢開化豫北,湯斌、張伯行等巡撫江南便是河南理學勢力的彰顯。盡管他們被譽為“中州理學八先生”,但其實已逐漸偏離北方王學路徑,尋求與程朱理學的和合,成為官方的程朱理學代言人,他們所復興的百泉、嵩陽等書院,也就成為天下學子翹首的典范。至乾隆初,皇帝駐蹕于此二書院,將百泉作為行宮,且賜嵩陽聯曰,“近四旁惟中央,統泰華衡恒,四塞關河拱神岳;歷九朝為都會,包伊瀍洛澗,三臺風雨作高山”(3)此聯坊間流傳為乾隆御筆,簡東在《鄭州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刊文《清代中州書院的學規與文學教育》,即認為系弘歷所題,然據梁章鉅《楹聯叢話》載,此系嘉慶時期其友人孫慈鶴撰寫。可備一說。,讓人們似乎又看到了宋仁宗賜額嵩陽、應天書院的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