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心動魄”:古詩十九首中的愛情詩論略
戴建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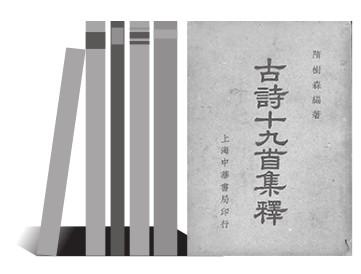
愛欲是人類最強烈的生命沖動之一。
因此,古今中外文學的主題類型中,要數愛欲主題最受作者青睞,也要數愛欲主題最讓人神魂顛倒,因而也最為歷久彌新。
講六朝詩歌,我們得從《古詩十九首》講起,因為它們是魏晉詩歌的濫觴;而講《古詩十九首》,我們首講其中的愛情詩歌,因為這些情詩最能撥動我們的心弦。
《古詩十九首》中有很多作品表現愛欲主題,那一首首熾熱的情詩,或是對愛欲的大膽肯定,或者對愛的強烈渴求,或是對愛的熱情呼喚——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
此前,誰敢放肆地高喊“蕩滌放情志”?誰敢坦承自己“空床難獨守”?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它們讀來照樣“驚心動魄”!
愛的渴求
在聊《古詩十九首》的情詩之前,先和大家侃侃《古詩十九首》。
說起《古詩十九首》,我自己也是一頭霧水。
它作于何時?起于何事?因何而作?何人所作?
這一連串的問題,也許鬼知道,反正我不知道。要是聽到你問這些鬼問題,九泉之下的屈原肯定會馬上坐起,奮筆疾書他的《天問》續篇。
不過,這并沒有影響人們對它的喜愛,更沒有影響大家對它的贊譽。
人世現有的最好形容詞,差不多都堆到了《古詩十九首》身上。
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你們聽懂了沒有?這意思是說,《古詩十九首》是五言詩的珠穆朗瑪峰。順便交代一下,劉勰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文學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最宏偉最系統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著作。他的話古今都極有分量,他對很多作者和作品的評價可謂一錘定音。
南朝梁代另一位著名詩論家鍾嶸,對《古詩十九首》同樣是擊節稱贊,并把它列入《詩品》中的上品:“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不過就是十九首詩歌,竟然讓他“驚心動魄”,而且首首詩都“一字千金”! 我的個天!
更為推崇的是明代胡應麟,可能覺得“驚心動魄”還贊得不到位,他認為《古詩十九首》“真可以泣鬼神,動天地”!(《詩藪》)
對《古詩十九首》研究的歷史,儼然就是贊美大比賽的歷史,評價一個比一個高,調門一個比一個響。王世貞說《古詩十九首》“是千古五言之祖”(《弇州山人四部稿》),話音剛落,陸時雍馬上接過話頭說,它們“謂之風余,謂之詩母”(《古詩鏡》)。
看了陸時雍的評論才知道,五言古詩原來都是《古詩十九首》生出來的!
作于何時
既然知道《古詩十九首》是五言古詩的“詩母”,那誰又是《古詩十九首》的“詩母”呢?《古詩十九首》讓人心醉,人們自然會固執地問:它作于何時?又作于何人?為此爭吵了一千多年,可能還要一直吵下去,至今沒有確切的答案,可能永遠也找不到確切答案。
《古詩十九首》產生的年代及其作者,在南朝時就是一本糊涂賬。徐陵編《玉臺新詠》時將其中九首算在枚乘名下,而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則說:“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鍾嶸在《詩品》中卻說“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枚乘活躍于西漢早期,傅毅屬東漢初期,曹植和王粲又屬曹魏。徐陵、劉勰和鍾嶸同為梁人,對作者歸屬和作品年代,三人雖然沒有同臺吵架,但完全是各說各話,而且他們也是道聽途說,“或”“舊疑”云云,顯然他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后來七嘴八舌就更多了,有的說是張衡,有的說是蔡邕。其實,西晉陸機就不知道這些詩的作者,把自己的仿作稱為“擬古”,梁昭明太子編《昭明文選》,在詩題下注得明明白白:“并云古詩,蓋不知作者。”
《古詩十九首》詩題純屬偶然,剛好這些詩歌都沒有標題,剛好是前代傳下來的“古詩”,又剛好收錄在《文選》中的只十九首,所以人們就隨意把它們稱為“古詩十九首”,久而久之這叫法就成了標題。往雅處說,就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或柴可夫斯基第七號交響樂,往俗處說,就像農村叫大郎八郎三妹一樣,有多少個就叫多少,數字完全是湊巧。
既然“不知作者”,為什么冒出來那么多說法呢?越是人人都沒有證據,越是人人都有膽量,反正每種說法都死無對證,因而每種說法都無對錯之分,即使胡說也不會使自己名譽受損,更不會引起任何糾紛,于是,人手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不過,雖然不能指定它們作于何人,也不能考出它們成于何年,但我們可以根據詩歌內容、風格和情調,大致推斷它們產生于哪個歷史階段。也就是說,依據詩里詩外的“蛛絲馬跡”,來復原或接近事情的真相。一直覺得自己有點福爾摩斯的本事,今天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我正好來小試牛刀——
由于西漢避諱極嚴,不避君諱屬于重罪,東漢則不必諱西漢皇帝。西漢第二位皇帝劉盈,《古詩十九首》中有“盈盈樓上女”“馨香盈懷袖”,可見,這些詩歌大部分或全部不是西漢的作品。
《古詩十九首》第一首說道:
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
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
西漢建都于長安,洛陽不可能如此壯麗繁華,董卓之亂后“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那時洛陽已沒有“雙闕百余尺”的巍峨宮殿,顯然《古詩十九首》不會寫于建安時期,更不會在建安之后。
東漢前期班固《詠史》詩質木僵硬,中期以后五言詩才漸趨成熟,從詩風詩藝的角度看,《古詩十九首》這種“動天地,泣鬼神”的杰作,到東漢后期才可能出現。
《古詩十九首》中“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那對死的恐懼,“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那對生的依戀,“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那對功名的舍棄,“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那對愛情的珍視,“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那對愛欲的肯定,還有“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那及時行樂,在在都指向了人的自覺。《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二者在時間上先后相接,在價值取向與情感體驗上又一脈相承,前者比后者可能早幾十年或十幾年,絕大多數詩歌作于漢靈帝與漢獻帝之間。
它們并非寫于一人,也非寫于一地,又非寫于一時。
《古詩十九首》作于哪個時期,我覺得基本可以結案了 。
作于何人
《古詩十九首》是何人所作?
即使福爾摩斯再世,他也不敢來接這個案子。就算“上窮碧落下黃泉”,也不可能找出半點線索。其實,最正確的提問應該是:像《古詩十九首》這樣的名垂千古的經典,作者為什么不留下自己的大名呢?難道東漢后期的詩人不希望名垂千古嗎?
真是咄咄怪事!
一點也不奇怪。
敦煌詞大多不也都是無名氏的作品嗎?
古代把人分為貴賤,也把文體分為雅俗。
西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說:“古詩率以四言為體……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余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我來給摯虞做一次翻譯吧:古詩都應該以四言為正宗。四言詩才算是雅音之韻。其他的各種體式的詩歌,比如說五言詩,雖然可以寫得委婉曲折,看起來明艷照人,聽起來悅耳動聽,但那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詩體,這就像歌妓生得再嬌艷,打扮得再時髦,也仍然是一名歌妓,也還是登不了大雅之堂。
一直到劉勰還認為“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文心雕龍·明詩》)。劉勰的意思與摯虞大同小異,作為詩歌正體的四言詩,詩風應以典雅溫潤為本,而世俗流行的五言詩,只有清新華麗才能招人喜歡。
劉勰還從語言學的角度,闡述了為什么四言高于五言,聽聽《文心雕龍·章句》是怎么說的:“四字密而不促……至于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四字就是四言,四言詩就是四字詩。他覺得四字句緊湊但不局促,那些莊重宏大的詩體和頌體,用五言就未免過于輕佻,用四言則十分得體。他還說寫五言詩,不過是偶爾的權宜應變之方。寫四言詩可以堂堂正正,而寫五言好像偷雞摸狗。
五言詩在六朝人心中的地位,現在大家看明白了嗎?四言才算“正體”,而五言只是“流調”。所謂“正體”是說四言是詩的正宗,“流調”是指五言詩不過是上不了臺面的流行曲調。摯虞在《文章流別論》說得很明白,五言詩“俳諧倡樂多用之”,唱五言詩的都是一些娼妓舞女。摯虞和劉勰對四言與五言的評價標準一樣,四言詩既然是詩歌“正體”,那寫四言詩才是走正道,寫五言詩即使不是邪門也是旁門。
于是,漢代“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文心雕龍·明詩》)。那時的詩人即使寫了五言詩,誰還敢署上自己的大名呀?倒不是他們感覺寫得太差,而是覺得五言詩的體式太卑。
因此,在當時一個有頭有臉的文人,可能出于好奇偶爾寫寫五言詩,但愛面子又不敢署名,于是就出現了《古詩十九首》這種佚名的名詩。更準確地說,《古詩十九首》不是佚名,而是匿名。
詞也有類似的情況,開始只是民間創作,敦煌詞的作者全屬佚名,開始也只在民間流傳,晚唐五代也只在青樓傳唱,填詞就是為了給“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歐陽炯《花間集序》)。中唐以后才有詩人擬作,如白居易和劉禹錫等人,開始都是寫一些短小的小令:“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晚唐少數失意的詩人才大量填詞,如科場失意的溫庭筠大寫艷詞,無非就是破罐子破摔。
當然,東漢后期那些詩人也不可能長后眼睛,當時根本預料不到越是往后,五言詩越是行情看漲,更沒有意識到自己筆下的五言詩,是流芳百世的不朽經典,致使自己也錯失了流芳百世的良機,可惜!
正因為《古詩十九首》是匿名之作,反正誰也不知道是誰寫的,詩人們用不著端著裝著,敢在詩中毫無保留地敞露真情,所以這些詩歌“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宋陳繹《詩譜》)王國維《人間詞話》也說,《古詩十九首》中有些情感內容,“可為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詩人匿名使得詩歌垂名,真可謂詩人不幸詩歌幸,可喜!
不知道杰作的作者,我們當然非常遺憾;但要是沒有了杰作,那可就是文學史上的災難。可以不知道世有此人,但絕不可以世無此詩。
“空床難獨守”
言歸正傳,我們接著聊《古詩十九首》中的情詩。
就像進入酒店或商場,開門迎賓的都是清一色的美女一樣,一翻開《詩經》,最先迎接我們的就是愛情詩,“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淳樸的小伙子在求愛。
漢樂府中的《陌上桑》家喻戶曉,“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這是心生邪念的使君在求偶。
從《詩經》到漢樂府,愛情都屬于永恒的主題。詩人一寫情詩就來神,大眾一見情詩就來勁。
情詩在哪個時代都十分常見,《古詩十九首》中這首情詩又有什么新鮮之處呢?
上文談到,《古詩十九首》大多寫于漢靈帝和漢獻帝之間,也就是建安前十幾年或者幾十年,時間上是和建安詩緊緊相接。東漢后期,不斷的社會動蕩,加速了王權的崩潰;而隨著王權的迅速崩潰,儒家的價值大廈也隨之瓦解,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又一次“禮崩樂壞”。原先人們遵循的行為規范,轉眼便成了束縛人們的鎖鏈;原先大家崇拜的精神偶像,轉眼就成了人們嘲諷的對象。批判名教成了一種炫酷,反叛孔丘當然更顯派頭。
你們看看阮籍如何挖苦儒生:“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在外裝得冠冕堂皇,一回家便骯臟不堪。剛一露嘴說了幾句心里話,趕緊又滿嘴仁義道德。整天忙于周旋應對逢迎拍馬,那副卑微偽善的丑態叫人發愁。
人們突然發現什么禮義,什么節操,什么勛業,什么盛名,不是欺世盜名,就是轉瞬即逝,只有“年命如朝露”是真的,“轗軻長苦辛”是真的,“與君生別離”是真的,“思君令人老”是真的……
既然這樣,“虛名復何益”?“高節”又有何用?何苦還要“守窮賤”?何苦還要“守空床”?
于是,就有了我們正要講的《古詩十九首》之二《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清初吳淇在《六朝選詩定論》中說:“其興趣全在起首‘青青二句,振起一篇精神。”為什么說“振起一篇精神”呢?
還得從頭道來。
首二句中的“青青”“郁郁”,都是形容植物蔥翠茂盛的樣子,“青青”側重于色調,形容“河畔草”青翠欲滴,“郁郁”則偏重于意態,形容“園中柳”茂密籠煙。這兩句寫景由遠而近,眼光從遠處的“河畔”移到眼前的“園中”。草只有綿綿不盡,才有一眼望不到頭的“青青”之色,柳只有籠煙飄絮,才會呈現出“郁郁”之態,大家平日不妨仔細觀察一下,幾把草不可能一望“青青”,幾株柳也不會滿眼“郁郁”。
在《古詩十九首釋文》中,朱自清先生認為這兩句“是那蕩子婦樓上所見。蕩子婦樓上開窗遠望,望的是遠人,是那‘行不歸的‘蕩子。她卻只見遠處一片青草,近處一片柳”。從第三句“盈盈樓上女”可知,不僅“河畔草”“園中柳”是從詩人眼中看到,連“樓上女”也是從詩人視角寫出,她是詩人要表現的對象。這正是此詩高妙的地方,“分明是從作者眼中拈出,卻從似于女中眼中拈出;分明是從作者眼中虛擬女之意中,卻又似女之意中眼中之感,恰符于作者眼中意中,真有草蛇灰線之妙”(吳淇《六朝選詩定論》)詩人“設身處地”的本領真是到家了,以致騙過了朱自清先生。
我左袒吳淇的說法,“青青”兩句的景象,“分明是從作者眼中拈出”。這首詩并不是代言體,不必假托筆下的“樓上女”之口,詩人直接站在前臺抒情寫意。代言體詩如李白的《長干行》,一起筆就說“妾發初覆額,摘花門前劇”,這樣詩中所寫的一切,都是“妾”耳中所聞,眼中所見。
從寫作手法上看,這兩句既是賦——直描春景,也是興——引起下文。大家看,河畔春草一片翠綠,園中垂柳絲絲飄拂,春歸大地,春意盎然,春色撩人。此時萬物萌發勃勃生機,春日里的少婦同樣也春心萌動,所以說首二句“振起一篇精神”,你們聽懂了沒有?
這樣,自然就過渡到了——“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盈盈”指女子儀態的優雅倩麗,“皎皎”指女子美艷得光彩照人。“窗牖”這里泛指窗戶,在上古,開在墻上的窗叫“牖”,開在屋頂上的窗才叫“窗”,后世因很少把窗戶開在房頂,慢慢這兩個字便都指窗戶了。“盈盈”二句的意思是說,樓上那個美女美得讓人窒息,站在窗戶前明艷動人,誰見了都會神魂顛倒。
詩人進一步描繪“樓上女”:“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娥娥”形容女子姿容姣美,“紅粉妝”是說她濃妝艷抹,“纖纖”當然是指她的纖纖玉指,是形容她雙手修長圓潤,“素手”指女子雙手潔白柔嫩,“出”在這兒是指把手伸向窗外。
“盈盈樓上女”這樣的俏麗佳人,所有男人都夢寐以求,光彩照人更讓男人魂不守舍,春日里“當窗牖”也情有可原,今天的女孩子不是同樣喜歡春游嗎?女子姿容嬌美是上天恩賜,哪個女孩不希望像“樓上女”那樣“娥娥”嬌艷?這一切都沒有什么可指責的,不過,“纖纖出素手”可就有點出格了,“素手”當然十分迷人,“出素手”卻格外驚心,說輕點她是在搔首弄姿,說重點是在招蜂惹蝶。“纖纖出素手”的“另類”舉止,讓我們自然想到了潘金蓮。樓上女為什么會這樣呢?且看下文:“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倡家女”古代指歌舞伎,大多是賣藝而非賣身。“蕩子”,相當于今天的游子,指長期出外闖蕩不歸的男性,不是風流浪蕩的花花公子。“蕩”在這里指游蕩或闖蕩。
要是回家了還算“蕩子”嗎?“守空床”不是“蕩子婦”的宿命嗎?
麻煩的是,今天的“蕩子婦”,偏又是昔日的“倡家女”,讓“倡家女”守“空床”還能不“難”嗎?
讀到最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呵,難怪她要“當窗牖”,難怪她喜歡“紅粉妝”,難怪她“出素手”!不正是由于難守空床嗎?這首詩前后相互照應,讀到后面便明白了前面,回顧前面更理解后面。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這首詩的新意在哪里?
大家還記得“樓上女”“娥娥紅粉妝”的打扮,記得她“纖纖出素手”的招搖吧?中國古代強調“女為悅己者容”,《詩經》中《伯兮》說:“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大意是說,打從丈夫東行之后,我的頭發蓬亂得像草窩,倒不是沒有發油梳妝修飾,可心上人不在自己身邊,打扮得花枝招展給誰看呢?杜甫《新婚別》中,新娘子也對即將從軍的丈夫說:“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丈夫還沒離開便馬上“洗紅妝”,以此來表達對愛情的忠貞專一。南宋詩人徐照《自君之出矣》比喻更新奇:“自君之出矣,懶妝眉黛濃。愁心如屋漏,點點不移蹤。”自從夫君離家以后,娘子就懶得施粉畫眉,她的思念憂傷就像那屋漏,一點一滴都在同一個地方。而“樓上女”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自己的那位“蕩子行不歸”,她的妝飾才那么起勁,她的妝容才那么濃艷,她的行為才那樣招搖。
古代大量的思婦詩,或抒發對丈夫真摯的思念,如曹丕的《燕歌行》:“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或表現對外地丈夫牽腸掛肚的擔憂,如唐代陳玉蘭的《寄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或表現對久別重逢的期盼,如李白的《長干行》:“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但這首詩中的“樓上女”,她關切的重心不是自己“不歸”的丈夫——“蕩子”,而是她自己的煩躁,所以她要濃妝艷抹地裝扮,要急不可耐地“出素手”招惹人,無論是心理還是生理,她都守不住“空床”。
“空床難獨守”是突出的重點,也是讓人刺眼的焦點,更是全詩與眾不同的要點。
清張玉谷《古詩賞析》認為,“此見妖冶而儆蕩游之詩”,他說“既娶倡女”,就不應“舍之遠行”,否則必定家門不幸。這種解釋當然十分可笑,詩歌不能等同于告示,再說太太如果真的“妖冶”成性,蕩子寸步不離也照樣紅杏出墻。不過,張玉谷看出了此女的“妖冶”,她自己不能安分,丈夫又怎能放心?
這首詩真正的與眾不同,不只是寫出了少婦“空床難獨守”,寫出了她不安于室的煩躁,寫出了她“紅粉妝”的嬌艷,寫出了她“出素手”的惹人,更在于詩人對這一切不僅沒有道德的譴責,而且在對她生理渴求的描寫中,表現出對這種渴求的理解和寬容,詩人似乎朦朧地懂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人們對愛情詩的態度,通常判定雅俗的標準是,言情則為雅調,涉性者為俗詞。即使今天談婚論嫁,公開場合,誰都只說是愛情的美好,誰會承認是性的需要?
可是,渴望性的滿足是真切的人性,對“空床難獨守”的寬容,就是對人性的尊重,而尊重人性就是人的覺醒。
過了幾十年以后,三國嵇康才從理論上闡釋,“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縱欲為歡”(嵇康《難自然好學論》)。
正是在這一點上,這首詩引領了時代風潮,是魏晉人覺醒的先聲。
此詩在藝術上的特征十分明顯——
如前面六句連續用六個疊字:“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纖纖”,但絲毫沒有重復單調的感受,讀起來反而一氣呵成。
又如全詩句句宛轉相生,河畔園中草青柳綠,真個是“春色滿園關不住”,自然引得“樓上女”春心蕩漾,一春心蕩漾就會驅使她濃妝艷抹,也會引得她“出素手”勾人。勾人而身邊又無人,自然會想起自家男人——蕩子,既為“蕩子”自然就“行不歸”,“歸”家就不算“蕩子”;既為“蕩子婦”自然只一人在家,因而也就只有“空床”相伴;既為“倡家女”自然習慣了燈紅酒綠,一個人肯定“空床”難守。大家細心體會,就明白什么叫“環環相扣”。
風流夢
對生的依戀,對死的恐懼,是漢魏人覺醒的突出主題。
當突然意識到生命短暫的時候,你會用此后的余生干點什么呢?
饑餓者可能希望大吃一頓,失戀者可能希望大愛一場,有志者可能希望再拼一把,有德者可能希望造福一方……
面臨死亡邊緣時,《古詩十九首》中的人生抉擇可謂五花八門:既然“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后悔“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應趕快建一番豐功偉業;既然知道“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那最好的選擇“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酒要飲美酒,衣要穿名牌,讓人生“瀟灑走一回”;既然看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那“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讓自己非富即貴,不枉一生……
而下面這一首詩中的主人公,當他發覺轉瞬白頭的時候,他的人生選擇尤其不走尋常路——做了一場風流夢: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
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
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
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東城高且長”,首句是說洛陽東面的城墻又高又長。古代的城墻分為里城和外城,此處的“東城”是指里城。里城外面的一道墻叫“郭”,后世常以“城郭”泛指城市。古代常稱東郭先生,南郭先生,現在的城市既沒有里城,也沒有外郭,今天只有東城大爺,西城女孩。“逶迤自相屬”是說城墻綿延不斷,沿著里城繞了一圈,首尾又連在了一起。“逶迤”形容蜿蜒遼遠的樣子,“相屬”就是回環相連形狀。
為什么一起筆就說“東城”呢?洛陽東面城墻有三個門,偏北的叫“上東門”,此詩下一首開關就說“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郭北墓”指洛陽北邙山墓群。可見,從東門北向遠眺,可以望見成片的墓地,為下文人生苦短埋下伏筆。
“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回風”就是旋風,北方的秋天本來就很干燥,自下而上旋轉的秋風,卷起地上的沙土和草葉,滿天沙塵撲面,到處黃葉亂飛。“萋已綠”是“綠已萋”的倒裝,“萋”通“凄”,形容綠草在秋天里變得蕭瑟枯萎。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意思是一年四季不斷地更替變化,一入秋天就一年將盡。中國人俗話說,年怕中秋月怕半,過了月半似乎過了一月,過了中秋就像過了一年。這句是感嘆時光飛逝。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晨風”并不是早晨的風,而是一種鷂鷹類的猛禽。蟋蟀俗稱促織、蟈蟈等。《詩經》中有《晨風》《蟋蟀》篇。連晨風這樣兇猛的飛禽,也對時光流逝十分痛苦,連蟋蟀一入秋天也聲聲哀鳴,悲嘆生命的短促。面對時光流逝,無知的蟲鳥都知道悲傷,更何況多愁善感的詩人呢?
不過,人到底是萬物的靈長,面對生命的無常與短促,蟲鳥只是徒勞地“傷局促”,而人卻懂得如何去放縱:“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蕩滌就是沖洗、清除、洗滌,“放情志”就是開闊心胸,放縱情感,“結束”就是拘束、束縛。這兩句的意思是說為什么不打破人為的禁忌,不沖決精神的囚牢,不放飛自己的情志?為什么要自己捆住自己,自己禁閉自己呢?
這是詩的前半部分,我們來回顧一下詩情的發展脈絡:詩人來到洛陽東面,眼見又高又長的城墻,蜿蜒延伸回環不斷,一陣旋風卷起枯枝敗葉,夏日的滿眼翠綠,轉眼變成一片枯黃蕭瑟。四季轉換好像飛輪,眨眨眼就從年初到了年尾。秋天的晨風鳥也一臉苦相,蟋蟀更是徹夜憂傷。物尚如此,人何以堪?這就引出了“蕩滌放情志”的念頭。
這就是常說的“因景生情”,詩人把“放情志”的情懷,寫得入情入理,應驗了“人稟七情,應物斯感”的名言(《文心雕龍·明詩》)。
人生既然如此匆匆,不如放飛自我,怎么開心就怎么干,怎么快活就怎么活!
“蕩滌放情志”五字之中,“放”和“蕩”既是句中的關鍵,也是全詩的中心。
詩的前半部分寫何以要“放”“蕩”,后半部分寫如何去“放”“蕩”。
那么怎樣才算最好的“放情志”呢?
于是就轉入了詩的下半部分。
馬斯洛說,愛情是人的高峰體驗。清人吳淇認為,對于男性而言,“蓋人世一切,如宮室之美,車服之麗,珠寶之玩”,都抵不上佳人“切身受用”。另一個清人張庚也說,能讓自己“放情志”,能讓自己不“自結束”的,“莫若艷色新聲”。
“何為自結束”的顧慮一打消,聲色之欲就像被壓抑的火山噴發而出。要“放情志”就得找佳人,要找佳人就得去燕趙。
大家知道,戰國時期,燕的都城在薊,靠近今天的北京市。趙的都城在今天的邯鄲,在河北的南部。古人認為燕趙多美女,此時的詩人正在洛陽東城,到哪里去找燕趙佳人呢?
白日的風流夢里。
你們看,在他的風流夢里,想什么姑娘就來什么姑娘:“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燕趙佳人像玉一樣潔白,像玉一樣溫潤。我的個天!
讓人神魂顛倒的是,她的穿著是那樣入時,那樣得體,“被服羅裳衣”飄然而至,簡直像天上的仙女下凡。“羅”泛指綾羅綢緞,古時“衣”是指上衣,“裳”是指下衣,美人從上到下的行頭都雍容華貴。這是典型的“白富美”。
他的夢中情人還并不是頭腦空空的繡花枕頭,而是來到他窗前“低眉信手續續彈”,演奏的“清曲”是那樣悅耳動聽。她的審美趣味多么高雅,她的才藝又多么精湛!
他聽得如醉如癡:“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或許是弦柱調得過緊的緣故,琴聲越來越高亢激越,這種急管繁弦讓人悲涼。漢魏人對悲音有一種偏好,他們覺得歡樂之音難工,而愁苦之音易好,奏樂以悲音為榮,聽樂以悲音為雅。
再說,演奏時的“弦急”“柱促”,也表明佳人當時十分激動,不然,就不會有下兩句——“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馳情”其實就是感情撒野,或是想入非非。詩人在夢中與情人親密接觸,佳人也不由得雙頰飛紅,不禁下意識地“整巾帶”,一邊起身徘徊,一邊陷入沉吟。
正如吳淇所說的那樣:“曰‘美者,分明有個人選他(他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個人聽他;曰‘整巾帶,分明有個人看他;曰‘聊躑躅,分明有個人促他。”吳淇還說掉了一點,佳人知道身邊分明有個人愛她。
這就更容易理解了,她與他早已“心有靈犀一點通”,“弦急”表明她的激動,“整巾帶”說明她的矜持,“躑躅”表明她心如小鹿,“沉吟”更表明她在做決斷——“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佳人此刻已經芳心暗許,希望與他永結夫妻,兩人從此終生成雙成對。
在古代詩歌中,“雙飛燕”是夫婦和愛情的代名詞。這個比喻的后半部分太妙了,“銜泥巢君屋”不僅形象表現了“成雙入對”的恩愛,還表現了他們一起共筑愛巢的甜蜜。一位“美者顏如玉”的佳人,還沒等小伙子主動求愛,便迫不及待地要和他白頭偕老,真是天下掉下來大餡餅!
清代朱筠對這首詩的結尾贊不絕口:
結得又超脫、又縹緲,把一萬世才子佳人勾當,俱被他說盡。(《古詩十九首說》)
我真不忍心煞風景,可又不得不告訴大家,天上掉下來的這個大餡餅,其實就是詩人的一場風流夢,從“燕趙多佳人”到“銜泥巢君屋”,全是詩人“蕩滌放情志”的夢境,是他最希望“放蕩”的對象,“美者顏如玉”的燕趙佳人,其實就是他的夢中情人。從“何為自結束”的詩句看,詩人平時為人拘束內向。只有一輩子與風流韻事無緣的人,才會把風流韻事想得這般美好。
后來的李白也常常夢游,如名詩《夢游天姥吟留別》,但到最后夢都醒了,“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而此詩中的詩人一直還沉浸在風流夢中,還在和燕趙佳人一道“銜泥巢屋”,因為只要美夢一醒,自己仍然孑然一身,眼前還是家徒四壁,社會依舊烽火連天,百姓照樣流離失所……
只在風流夢中才能“放蕩”,只在溫柔鄉中才像個男人。
這首詩中情感的發展脈絡,上下兩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系,還有詩中比喻的妙處,我都和大家隨文細讀了一遍。“青青河畔草”的美像倡家女明艷照人,“東城高且長”的美似大家閨秀深藏不露,只要反復比較、咀嚼和品味,藝術鑒賞能力定會日益提高,審美感受定會不斷細膩。
不論是“青青河畔草”,還是“東城高且長”,它們既是漢魏人的覺醒的產物,同時又是漢魏人的覺醒的表現。
只有在人的覺醒的時代,人們才能直面自己心理和生理的渴求,男人才敢公開叫嚷“蕩滌放情志”,女人才敢公開坦承“空床難獨守”。
這兩首詩之所以成為傳世經典,就在于它們寫出了人人心中之所有,而人人口中卻不敢言的那種渴望。
它們的詩情都大膽得叫人驚心,它們的詩藝都高超得讓人驚艷。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首席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古代文學研究專家,曾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文學研究所所長,2023年3月入選“感動中國2022年度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