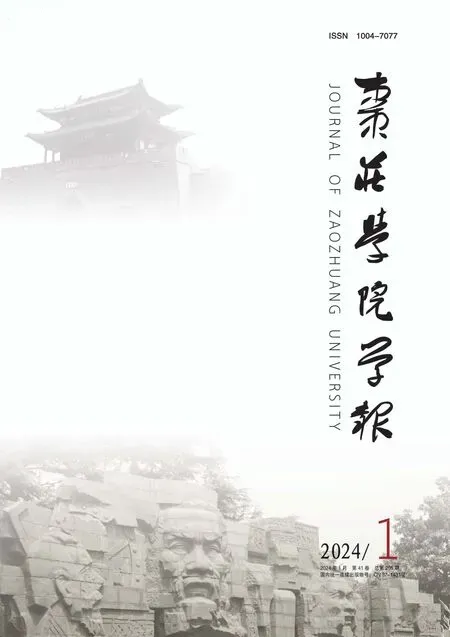《你是一條河》:女性角色的消解、反抗與建構
馬媛穎
(青海師范大學 文學院,青海 西寧 810016)
作為“新寫實”代表作家,池莉擅長以冷靜、客觀的態度,展現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剖析人生庸常與凡俗百態。中篇小說《你是一條河》是池莉少見的以母親為題材的小說,描寫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0世紀90年代,年輕的寡婦辣辣如何戰勝種種現實困難,獨自養活兒女們的人生經歷。如果說,在其“新寫實小說”代表作——“人生三部曲”中,池莉以“零度狀態”的敘述情感打碎了我們對愛情、婚姻神話的迷信,將人的存在沉降到現實大地之上,那么在《你是一條河》中,池莉則試圖通過塑造辣辣這一善惡并存、矛盾統一的女性形象,撕去歷史文化貼在“母親”角色上的“偉大”“無私”等固有標簽,還原現實生活中母親形象的復雜和真實,進而表現女性個體存在所面對的困境與迷思。
女性被認為是女兒、妻子和母親的統一體,女性個體的一生常常據此被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在這三個角色的轉換承接中,女性才得以體現出其個性、妻性和母性。在《不談愛情》《煩惱人生》《太陽出世》《你以為你是誰》等小說中,池莉把創作重心放在了女性人生的前兩個階段上,她以冷靜的觀察和理性的筆觸鋪展了愛情婚姻神話的幻滅,剖析女性由女兒到妻子的曲折的心路歷程,表達女性主體性與“女兒性”“妻性”間的拉鋸。在《你是一條河》中,女主人公辣辣始終沒有被提及姓氏與全名,其作為“女兒”的人生經歷也是缺失的。故事中的辣辣登場時,便已駕輕就熟地扮演著妻子和母親的角色,甚至很快因丈夫王賢木的意外去世而被剝奪了妻子身份,只剩下“母親”這一被賦予太多神圣意味的沉重角色需要擔負。于是,辣辣的人生就如小說名所喻示的那樣,像極了一條默默流向遠方和未來的無名河流。在流淌一生的過程中,她主動或被動地遺忘了自己的姓名和歷史,亦從不追問前路在何方,最終化身為一條被文化制度尊稱為“母親”的河。
一、對母親角色的消解
“母親”一直是文學言說的重要對象,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學的轉型以及作家視角的變遷,文學史上的母親形象也發生著流變。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母親形象是貞潔慈愛、堅強無私的,如“孟母三遷”“岳母刺字”中的母親,將哺育家族下一代并塑造兒女(一般而言是兒子)完美德性人格奉為自己人生價值和意義所在。到了現代中國,受到現代思潮的影響,一些作家開始重新審視家庭中的倫理關系,此時母親身上體現出“惡”的特征,如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就是一個典型的“惡母”形象。
“諾依曼在其對于女性的經典榮格式描述中,命名了四個極點作為女性原型形象的位置:慈母、惡母,消極阿尼瑪(蠱惑人心的年輕女巫)以及積極阿尼瑪(或者貞女索菲婭)。”[1](P74)作為母親,《你是一條河》中的辣辣兼具“慈母”“惡母”兩種女性原型形象的特征。她不再僅僅簡單表現出傳統母親的“善”,而是同時又有著現代文學中母親“惡”的一面,這種善惡交織的復雜人性是由其特殊的苦難人生經歷及其所處的歷史文化環境所決定的。她是一個被施加了“惡”之后而產生了“惡”的被毒化的靈魂,同時也是日常生活中可見且真實的母親形象。
(一)慈母形象與本能之善
母親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原型,這個原型經常用“水”“河”等陰性元素作為象征,如黃河被稱為“母親河”,喻指黃河就像母親一樣,孕育了中華文明,哺育了中華兒女。同時,“水”這一意象又常常用來指代女性的美和善。之所以將女性之美、善與水加以聯系,是因為“水”這一意象能表征豐富的文化意義:柔軟,似水溫柔;剛強,滴水穿石;純潔,無色無味;至高的善,亦即“上善若水”。進而,水化為河流,更疊加了一層意蘊——流動性,此種流動性既有一種原始的生命力,又代表著主體意識的自覺。因此,池莉將一部關于女性的小說命名為《你是一條河》,讓辣辣的故事發生在沔水鎮,而這個三十歲便守了寡的女人,仿若一條雖遭受風浪襲擊、礁石阻擋仍舊奔流向前的河流,在苦難的生活河道里艱難奔突,以完成其至高無上的神圣使命——成為善良、無私的母親。
小說中,辣辣的人生開始于丈夫慘烈的死亡。1964年的冬天,三十歲的辣辣親眼目睹了丈夫王賢木從戲樓摔到地面的開水鍋里并被火烤死的全過程,而后成了一名年輕的寡婦。丈夫留給她的是一場關于生存的惡戰,即如何在物質匱乏的艱難時代獨自撫養眾多孩子。怎樣盡量活得更好,這是母愛之善得以開展的背景,亦即一種因缺失而招致的苦難歷史。這里的缺失,一方面具體指向其個人生活中的“缺夫”——丈夫的不在場,使得母親辣辣得以成為家庭這一道德場內的權力主宰者,進而導致家庭成員間權力結構的變形和溫暖親情的貧乏;另一方面,則指向隱匿在私人生活背后的社會、時代、文化因素。借用這種敘事策略,池莉巧妙地將有關女性個人歷史的書寫與民族歷史相融,借助辣辣兒女們的姓名,借助辣辣及其兒女們的經歷,以一種不露神色的“客觀”面目將歷史事件呈現出來。
將苦難歷史設置為“地母”形象得以實現的背景,這是當代書寫母親、謳歌母親的文學作品的共性,只有母親們以常人無法做到的毅力,忍辱負重,飽經風霜,戰勝苦難,才足以體現出其母性的至善。守住貞潔是辣辣面對的第一個考驗。作為一個年輕的寡婦,辣辣有權利、有理由重新追求屬于自己的生活,但是她放棄改嫁,一次次拒絕了男人們的求婚。對于寡母辣辣而言,當務之急是怎樣活下去,這是她真實而具體的母愛。從選擇剁蓮子、搓麻繩、撿豬毛這三個加工工種來看,辣辣無疑是聰慧又敏銳的:這三個加工活都是把粗糙的半成品加工成精細一點的半成品,按勞付酬,又無需掌握太多技術,正適合這個家庭來完成。毫無社會工作經歷的辣辣無師自通地掌握了這個家庭式加工廠的管理方式:首先,她根據孩子們的年齡、能力和性格來進行分工,剁蓮子需要靈巧的手指并要學會使用鋒利的刀具,適合心靈手巧的兩個女兒艷春和冬兒;搓麻繩的工作簡單但需要手掌有勁,被分配給了老三——兒子得屋;老四社員和老五咬金年紀小又調皮,正好哄著他們像做游戲一樣,分撿出不同顏色的豬毛,還能一舉兩得地鍛煉孩子們辨別顏色的能力。辣辣還采用一些小策略來鼓動孩子們互相監督、彼此競爭。在“總工頭”辣辣的帶領下,這個家庭小加工廠運行有效,甚至可以每兩個月飽喝一頓沔水鎮的傳統名湯龍骨湯。“勞動分工”“內部監督”“獎懲機制”,辣辣也許不懂這些名詞,但她能夠做出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選擇。辣辣身上顯現出的樂觀的生活態度、頑強的生命力與質樸的生活智慧是中國大地上無數普通母親的共性:她們有時粗野,有時庸俗,卻有著共同的生存哲學,那就是“不屈不撓地活”。她們對生命有一種本能的愛,不管是艱難還是容易,不論是幸福還是不幸,只要活著就好,而這種愛恰是女性對生活不幸之“惡”的反抗。
不難發現,辣辣所做的一切并非是經由理性思考而采取的行動,而是本能地對所謂命運的順從接受。在辣辣看來,繁育后代是女性獨有的高貴本能,也是所有女性共同的命運。雖然她也曾想用跳河自殺的方式逃避太過沉重的人生,但被救后,一顆肚臍上方的紅痣令她回想起14年前相面先生對其未來的預言,于是辣辣把丈夫遭遇的不幸與自己聯系了起來,這顆痣正是她的原罪,她的命運注定。面對命運強大神秘的力量,除了坦然接受,人還能怎么做呢?辣辣接受了靈姑對她后半生的安排,她決定守住女人的志氣,做一個母親應該做和能做的一切,這是因為“一旦女性成為母親,這就是她生活中的角色,而且她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這個角色被定義的,更甚于男性由父親角色來被定義。母親身份深深影響了女性的自我感覺”[2](P609)。經由涅槃重生式的情節設置,辣辣聽到了命運的召喚,無怨無悔地擔負起一個母親的責任。于是,她將自己的陪嫁賣掉,甚至瞞著孩子們賣血謀生;福子身患重病,她恨不得也撞墻死去;貴子遠嫁時,她毫無保留地把自己賣血換來的所有積蓄塞給女兒;冬兒不知所蹤,辣辣臨死前還不忘囑咐兒子一定要找回她;社員因強奸罪被槍決時,辣辣目不轉睛地看著兒子被炸開的后腦勺,勇敢地送兒子最后一程……辣辣用盡自己一生所有愛著孩子們,雖然作為一個沒有受過教育也毫無社會經驗的普通勞動婦女,她愛的方式顯得如此原始粗放,甚至傷害到了孩子們幼小的心靈,給他們留下了終身不可治愈的精神之殤。
辣辣為破碎的家庭付出一生的心血,努力維持自己的尊嚴,種種行為的出發點在于她所理解認同并順從的“命運”。這一服從行動其實是一種責任和天性的體現,這種天性是屬于女性的,雖然有時以被動形式表現出來,卻是一種出自責任的主動作為。[1](P6)經由本能促使的行動使得辣辣的愛的方式是原始的、粗糙的,然而在種種粗糲的行動背后,愛的力量是強大堅韌和執著無私的,是一旦給予就決不收回的。這類母親也許目不識丁但懂得生活的智慧,也許粗俗不堪但純真灑脫,她們雖然飽經風霜但永遠對生活充滿希望,雖然瘦小纖弱但卻能以頑強的生命姿態去面對現實存在發出的種種挑戰。在辣辣身上,直接體現了傳統文化中習以為常并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母親原始而充滿力量的愛與善。
(二)惡母形象與反抗之惡
辣辣這一形象之所以讓讀者難忘,并不僅僅是前文所述母親身上共有的“善”令人感動,更在于她所展現出的極富個性、復雜性和悲劇性的母親“惡”的一面。具體呈現在文本中,是她以某種暴力的方式施加于孩子身上的畸形變態的愛。冬兒被辣辣打得鼻子噴血;性格懦弱的兒子得屋時常遭到辣辣的數落和鄙夷,因為青春懵懂期的不當行為遭到母親的毒打,差點丟掉了小命,“辣辣用兒子自己搓的麻繩將他吊在堂屋的橫梁上,渾身上下只留一條紅領巾改做的小褲衩。一盆鹽水、大竹條掃帚,掃帚蘸鹽水,不分上下狠命亂抽”[3](P26)。辣辣的“惡”還體現在她對孩子們從不加以管教。面對兒子社員的偷竊行為,辣辣放任溺愛,導致他滑向罪惡的深淵,最終因強奸未遂罪被槍斃;她對福子和貴子這對雙胞胎也不管不問,任由他們自生自滅,福子得病早夭,而貴子在母親的忽視中渾渾噩噩長大,卻不幸失智又失身,最終遠嫁給一個瞎子。對于女兒艷春和冬兒,辣辣以一種敵人般的態度嘲笑、鄙視和污蔑她們,尤其是她在冬兒心愛的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吐了一口濃痰,這一極其惡毒的行為徹底傷害了女兒,使得冬兒最終選擇徹底與家庭、母親決裂。從“活著”的生存角度看,辣辣在物質極其匱乏的客觀環境下創造了奇跡,無疑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但是,從“好好活著”的養育角度看,辣辣對孩子要么責打要么溺愛,要么忽視要么仇視,這樣兩極化的教育方式深刻影響了孩子們的性格。
如果追究辣辣“惡”的成因,根本在于生存環境的異化造成了人的異化。“有時,個體或集體會有意無意地招致他人身體或者精神上的痛苦。這是道德之惡——個體施加在他人身上的傷害。惡由此被誘生出來。”[1](P155)作為一個被設定在特殊環境中的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女性,辣辣一出場就遭遇了親人的死亡,丈夫留給她的是四個月的遺腹子和七張嗷嗷待哺的小嘴。在一個男性缺失的家庭環境和動蕩不安的社會歷史背景影響下,在這一極端特殊的情境中,所有事情都必定讓位于生存,苦難和對苦難的抗爭共同構成了這個家庭的生存基調。卑微求生存的壓力和肉體靈魂的雙重折磨使得辣辣的心靈也不由自主地受到侵蝕,“母親”這一角色被認為理應表現出來的無私和溫情為惡劣刻薄的態度所取代,導致她忽視了對孩子們正常情感的教育和健全人格的培養。此種“只養不育”的相處模式,既影響了孩子們的人生命運,也使她自己的精神靈魂在無形中遭受了“惡”的迫害,最終變形為一個愚昧、卑劣、暴力、狹隘的“惡母”。
當某個個體承受了來自他人、集體或環境(包括文化、歷史等諸多層面)施加的傷害時,個體也常常采用同樣“惡”的方式去反抗這種“惡”,這種“惡”又因其內在的反抗性力量而具有意義。就辣辣而言,她不自覺地用“恨”的方式去“愛”,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向命運抗爭,她朝冬兒書里吐的那口濃痰隱喻著她對自己不幸遭遇的苦難(即“命運”)的否定與拒斥。可惜的是,由于外部的現實生存壓力與文化對母親道德要求的桎梏力量實在過于強大,辣辣并沒有直面“惡”與拒絕“惡”的勇氣,于是只能以這種隱秘而邪惡的方式表達出內心的不甘。也許辣辣尚未有能力改變現實社會與外部因素施加于她的壓力,也許以辣辣為代表的女性生存是如此艱難坎坷,但恰恰是她不屈服、不認命的精神和最大范圍內尋找自我解放的努力使人感動,亦令人同情。盡管她采取的自我救贖方式違背了家庭倫理對一個母親“善”的要求,在客觀上形成了惡性循環并生產出更多的“惡”,但是誰也不能否認辣辣這一母親形象的真實性、復雜性和悲劇性。她既是悲劇的始作俑者,又是悲劇的犧牲品;她本能地進行了變形的反抗,卻缺少反思命運的理性意識。總之,作為母親,辣辣就像小說題目所喻示的那樣,既是一條哺育生命的偉大的河,又是一條深沉、渾濁、暗涌的河。她也許不是一個完美的母親,但卻是個真實的母親,其身上同時兼具的“善”與“惡”將母親形象從圣壇拉回到日常生活本身,彰顯出獨特的文本意義——這正是作為弱者的辣辣之“惡”作為一種反抗性力量所具有的意義。
二、對妻子/情人形象的反叛
辣辣的反抗意識不僅體現在她以“惡”戰“惡”的母親角色之上,更多的還體現在她對愛情婚姻的獨特看法之上。“使一個人成為女人的是一套社會關系的體制。社會性別制度提出來時有兩個最關鍵的討論領域,也就是婚姻和家庭。簡單地說,只有在婚姻和家庭的關系場域里,才使得一個女人成為女人。”[4](P73)女兒辣辣的歷史已被有意無意地遺忘,母親辣辣讓我們看到一個與生存之厄搏斗、同自我命運共沉浮的復雜女性,扮演著妻子和情人角色的辣辣也自有一套與眾不同的情感倫理,顯現在其與丈夫王賢木、小叔子王賢良、老李、老朱之間的情感糾葛中。
作為一個年輕的寡婦,在是不是貞操第一、要不要嚴守婦德的問題上,辣辣的言行呈現出一種矛盾、復雜和隨意的狀態。比如,對待糧店的老李,在自然災害嚴重、家中口糧短缺的情況下,辣辣瞞著丈夫“以身換糧”,她既不以失貞為恥,又不以此為偉大而屈辱的犧牲。當家里有了足夠的口糧,辣辣立即停止了此種關系。王賢木死后,老李妄圖再續前緣,沒料到卻被辣辣一番羞辱,遭遇“偷情不成蝕把米”的徹底失敗。對待鎮上幾個鰥夫的熱情追求,辣辣統統采取“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的策略,對于他們送來的禮物,辣辣一概收下,然后和孩子們高高興興地吃掉,所有男人都不知道辣辣的真實想法:“她打定主意不再嫁人……嫁人做什么?哪個男人不是看她會生養,會做事,她可不是傻子,這輩子再也不供什么孩子在家當大爺了。”[4](P16)對于小叔子王賢良的浪漫情詩攻勢,辣辣也只是覺得這書呆子挺有趣罷了,因為辣辣看穿了書生意氣的王賢良在嚴酷現實面前如此軟弱無力,他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更無法給這個家庭的生存境遇帶來根本性的改善。與血庫頭目老朱之間的情愛關系建立在同病相憐和惺惺相惜的基礎上,雖然他們在肉體上相互融合,但是在精神上卻互相尊重、絕不逾矩,他們各自為自己的孩子和家庭鞠躬盡瘁,從不提離婚再婚的事兒,也從不糾纏彼此。通過以上與不同男性間的情愛取舍,不難看出辣辣的情感邏輯:冷靜現實的生存取向與靈肉分離的灑脫態度。池莉筆下女性的情感選擇依托于生存,尋找“愛”的過程本質上是謀求高質量的生活。在辣辣的人生詞典里,生存是第一位的,愛情對她而言是遙不可及甚至毫無實用價值的東西。在生存問題面前,“愛情”“貞潔”這些話語顯得如此抽象和微不足道,因此辣辣既可以毫不猶豫地用身體換取生存的資源,也可以在遇到心動的人時大膽地獻上自己,這些行動都反映出辣辣對情愛的獨特見解,以及對自己真實內心的某種堅持。
正如前文所述,“水”的特征之一是“純潔”,通常用來形容一個人清白無暇、沒有污點。但是,當它被更普遍地用來形容女性的德性時,就加上了一層性別色彩。事實上,“純潔”等同于“貞潔”,體現了傳統男權文化對女性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品質要求。若無男人拯救,女人必將墮落;女人若想不墮落,就必須犧牲一切物質利益和人生享受,這幾乎是傳統男權文化書寫女性的一個固有模式。但是辣辣對貞潔的態度,對愛情的看法,對婚姻的抉擇,統統打破了這種模式,拒絕了此種所謂“命運”或“傳統”。“女性在父權中心社會中是以她的性交換她的生存,或者說她為了她的生存就不得不交出她的性。”[5](P166)雖然辣辣曾經向老李妥協過,但當此種交易不再攸關性命時便也沒有了繼續下去的必要,于是她斷然結束了這段關系,并用行動捍衛了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小叔子王賢良試圖在辣辣的人生中扮演偉大拯救者的角色,卻被辣辣看穿了他對自己身體的覬覦以及妄圖通過掌握她來重新回到家庭權力中心的欲望本質。辣辣用一個“仰面倒下”的動作,便嘲笑和消解了王賢良自以為神圣的愛情與居高臨下的拯救。
“女人的身體正是父權制存在的基礎。”[6](P54)社會要求女性以結婚(亦即家庭倫理關系)來證明她自己。這是因為愛情、婚姻和家庭被認為是可以將一個“人”塑造為“女人”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人格塑造機器”。簡而言之,婚姻和家庭是使一個“人”成為“女人”的關系場域。根據女性主義的理論,只有當女性擁有了選擇的權力,才有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兩性平等。因此,當一個女性敢于全權掌握自己的身體,便也掌握了自己的存在;當她可以在家庭關系中代替“夫”和“父”的角色,便也意味著她擁有了無須向他者證明自己的權力。就此種意義而言,《你是一條河》中,作為妻子和情人的辣辣,其自在隨心的貞潔觀與其拒絕浪漫愛情神話、現實高于一切的婚戀觀,無疑是對男性中心話語的無聲反諷與大膽僭越。
值得注意的是,《你是一條河》中的男性角色總體上呈現一種缺失、無力和失語的狀態。開篇即以丈夫王賢木的死亡宣告著家庭中父親和丈夫角色的缺席;小叔子王賢良連挑水、拾瓦這些日常勞作都無力承擔,老李、老朱也只是作為辣辣生命中的次要角色出現,他們的存在反而讓她更加清醒地認識到現實困境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擺脫。反過來說,正是這些既無男性魅力,又無生命力量的男性刺激促發了辣辣女性意識的覺醒。由此,男權社會中常見的男性主導權被徹底推翻,女性得以“篡權”,辣辣才得以成為家庭、子女和讀者眼中的唯一主角。
三、女兒的未來:投射與建構
“娜拉”的出走是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書寫女性的重要主題,逃離是她們覺醒后選擇的第一種姿態。《你是一條河》所講述的也是出走與逃離的女性覺醒故事,辣辣與女兒艷春、冬兒三個人從不同側面共同完成了尋找自我的覺醒之路。女兒仿佛一面魔鏡,既能照出母親的曾經,亦能預演母親的未來。同時,女兒對母親的不同情感取向導致了她們如何選擇自身命運:要么重復,要么顛覆。正如艷春對辣辣的認同和繼承,寓言母親的歷史將如何在一代又一代不幸的女性身上重復上演;而冬兒對辣辣的全面否定,則指向女性人生未來的另一種可能性。
長女艷春是一個典型的市井小女人。雖然她和冬兒都讀過辣辣偷來的一本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但是在遭遇了一場浪漫戀愛的幻滅后,艷春徹底地省悟到:書里描寫的浪漫愛情不過是幻夢一場,只有嫁個好人家才是可靠的人生出路。結婚后,艷春當上縣婦聯的干部,成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境遇。其實在父親去世后,艷春已經表現出渴望擁有管理家庭的權力,直至嫁入羅家后,她終于如愿獲得了權力和社會地位。從艷春的性格、為人處世以及對婚姻愛情的態度,都不難發現辣辣的影子,而通過艷春,我們也不難想象,還未成為母親的辣辣那些被遺忘了的歷史。以辣辣和艷春為代表的底層女性有著強烈的自我中心觀念,她們不畏人言,敢于大膽采取各種方式改變命運、追求幸福。雖然由于理性的匱乏,她們的反抗常常采取不恰當的盲目的方式,可是這種不認命、不甘心的努力畢竟表現出自強抗爭的生存意識,洋溢著一股可貴可敬的生命力。
與艷春一樣,冬兒也對自身的生存境遇進行了反抗。不同的是,艷春通過婚姻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命運,而冬兒則選擇“背叛”和“逃離”。冬兒與母親的關系復雜曲折,她對辣辣的情感經歷了從天然的親近到懷疑、鄙視、怨懟、仇恨的復雜過程。當年幼的冬兒親眼目睹父親的死亡場面,巨大的恐懼使她對母親無比依賴和渴望,可全身心忙于生存的辣辣無暇顧及這個小女孩稚嫩的心靈,以致冬兒失望至極。當八歲的冬兒識破母親和老李之間的不正當關系,卻遭到辣辣狠狠的一記耳光,正是耳光事件使母女關系發生了徹底的轉變,此后的冬兒站在了母親的對立面,愛演變成了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叔叔寫給母親的情詩喚醒了她內心對文明的向往,她以一個先覺者的眼光審視著母親的無情和家庭的墮落,直至最后爆發了一場母女之間徹底的決裂:辣辣口不擇言地惡意謾罵,冬兒則將母親的所有丑惡罪行一一揭露。
年少的冬兒渴望母親以愛的方式給予支持、認可,因為“母親是女兒成長過程中最初的角色榜樣,這些角色包括個人、愛人、妻子、母親和朋友。為了贏得母親的愛和贊譽,女兒一直艱難地尋找正確的方式去回應母親”[7](P12)。但是她失望地發現母親的一言一行都無法令人認同,想象中的女性互愛互助的同盟無以建立。覺醒后的冬兒試圖尋找某種方式改變自己的母親,讓其符合自己心目中神圣慈母的原型,但是她卻無力地發現自己既無法更改母親的歷史,也無法回到過去以讓母親的靈魂免遭“惡”的侵蝕。最終,冬兒毅然決然地離開,并為自己更名為“凈生”,單方面地斬斷了與母親的情感羈絆,也徹底清算了與自身“污濁”歷史的血緣關系。
引人深思的是,以冬兒為代表的女兒一代之所以得以實現個體意識的覺醒,掙脫歷史加諸女性身上的束縛而成功逃離,實質上是以母親一代個體壓抑的歷史為前提的。正是由于女兒像一面鏡子一樣映照出母親的丑陋,她才會反觀自身,激發出懷疑母親、否定母親、拒絕母親的獨立個體意識,最終在此基石上構建起一個迥異于母親的女性新自我。“厭母癥可以看作是女性的一種自我分裂,在那種想去徹底消除我們母親束縛的渴望著,使我們變成一個獨立與自由的人。在我們心中,母親代表著受害者、不自由的女人和殉難的女人。我們的人格仿佛是危險而模糊的,并且與我們母親的人格相互重疊,在一種想去了解何處是母親終結,何處是女兒開始的絕望的努力中,我們施行的是極端的外科手術。”[6](P287)就此種意義而言,冬兒的成功反叛是對辣辣遺憾缺失的補充完善,冬兒有幸擁有的新生活是辣辣曾經有可能實現的未來場景,她們是歷史河流不同階段中具有流動性的“我”。這么想來,便也對辣辣的命運少了一些可惜,多了一絲欣慰。要知道,辣辣從未怨恨過冬兒,在母親心中,與女兒的歷史血緣關系從未斬斷過。
結 語
年輕寡母辣辣善惡兼具的復雜形象,消解了傳統文學中對神圣慈母原型的書寫模式,在她對生存的近似饑渴的個體生命體驗中,反映出女性群體適應惡劣生存環境、頑強反抗艱難不平、“不屈不撓的活”的堅韌精神。同時,辣辣與男性間的婚戀關系、與女兒一代的母女關系,反映了以辣辣為代表的底層婦女在社會轉型期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發出疑問并進行反抗。也許辣辣未能成功找尋到女性存在的理想道路,但在冬兒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希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