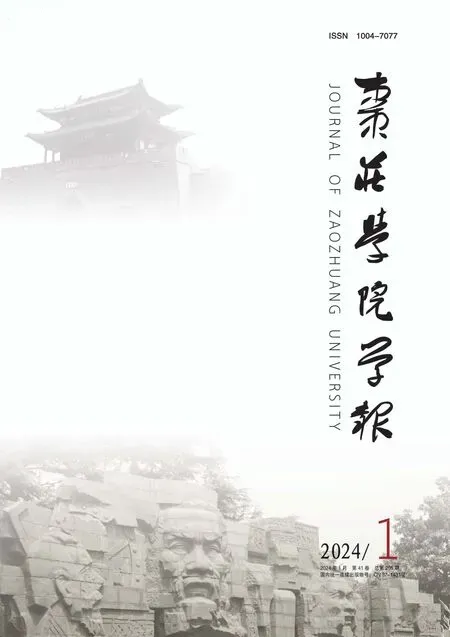全球華語學的理論建設與探索
——以刁晏斌教授的相關系列研究為例
徐涵韜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目前,全球華語研究方興未艾、成果豐碩,呈現出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的發展態勢。
北京師范大學刁晏斌教授是最早投身全球華語研究的學者之一,早期研究以海峽兩岸民族共同語為著力點,進而拓展至港澳臺地區現代漢語,近年來延及以新馬華語為代表的海外華語,相關研究成果豐富、理論色彩濃厚。2012年,刁晏斌教授首次提出“全球華語學”的設想[1],此后又作過稍微具體一點的表述[2](P40~41),2017年正式提出“全球華語學”的概念,定義為“一門研究全球華人共同語及相關對象的一個語言學分支學科”,并發出“呼喚全球華語學、走向全球華語學”的口號[3]。
“全球華語學”提出之后,得到學界積極響應[4],相關研究時有創獲,短短數年,就有了相當程度的拓展和加深,理論體系初具規模,方法路徑日漸明晰。刁晏斌教授作為“全球華語學”的首倡者,近年來更是持續致力于相關理論及方法的建設與探索,2018年出版的著作《全球華語的理論建構及實證研究》[5],作為第一部華語理論專著,彰顯了“實論結合”的研究特色及學術追求,2022年主持的“華語研究的理論與實踐”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近年來發表相關論文近40篇,在學界引起較大反響。本文著眼于全球華語學的理論建設與探索,以刁晏斌教授的相關系列研究為例,從本體論及方法論兩個方面進行介紹及說明并就全球華語學體系建設的特色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本體論的探索與思考
全球華語本體論探索,首先要解決華語是什么的問題,需要對華語的本質及存在方式等進行解釋。
(一)認識支點的新思考
面對華語這一客觀存在,主要有兩個認識及觀察的支點:一是全球華語的支點,二是百年現代漢語的支點。下面分別展開說明。
1.全球華語的支點
以全球華語為認識支點,通過事實發掘及實證考察,提升對其概念及內涵的認識,并由此展開對體系建設及學科建設的討論。
首先,在概念方面,著眼于“名”,通過梳理“漢語”系列的“漢語、大漢語、國際漢語、全球漢語”以及“華語”系列的“華語、大華語、全球華語”等形式,遵循立足現實、兼顧內外、堅定立場、適當分工的原則,確定整體華人共同語的指稱為“全球華語”,英語對譯形式是“Global Chinese”,并將全球華語分為“普通話圈”“臺港澳國語圈”及“海外華語圈”三個部分,每一部分具有下位層次的劃分,如海外華語圈可分出第三層次的“東南亞華語”及第四層次的“新加坡華語”等。[5](P2~5)著眼于“實”,隨著認識的深化,對已有的全球華語定義——“以傳統國語為基礎、以普通話為核心的華人共同語”[6]進行反思,基于包容性原則,指出原有定義不完全適用于“正在形成”北美華語及“略有雛形”歐洲華語[7],并從現實性原則出發,將其定義暫定為“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以為后期新內涵的增添預留足夠空間[8]。這一定義調整過程,也是對全球華語內涵認識的螺旋式上升與深化的過程。
其次,在學科建設方面,對全球華語學的本體研究及應用研究內容進行頂層設計,前者包括“了解語情,進行共時平面研究”“理清脈絡,進行歷時平面研究”以及“對比借鑒,進行橫向比較研究”三個方面,后者則涉及“面向語言規劃的研究”及“面向華語文教學的研究”等內容。[5](P118~128)基于已有成果,展望未來發展目標,提出“立地+頂天”的學術理念及愿景,指出應堅定立足于華語堅實而廣闊的“地”,堅持精耕細作的樸學傳統,全面、深入地發掘具體事實,并從“國外理論的引進、吸收和發展”與“創建具有原創性的華語理論”兩個方面討論相關理論研究應如何“刺破青天”,以達到新的高峰,為普通語言學建設添磚加瓦。[9]“立地+頂天”的學術愿景及相關探索,彰顯全球華語學的廣闊天地及豐富內涵,為后續華語實證及理論研究提供了可供遵循或借鑒的理論探索路徑。
2.百年現代漢語的支點
按照語言學界多數人的意見,現代漢語始于“五四”時期,業已經過百余年的發展過程。隨著對現代漢語發展演變認識的深化,“現代漢語史”思想應運而生,主張“用歷史發展的眼光來對現代漢語的發展變化進行全面、深入、細致的考察和分析”[10][11],并由此提出雙線并行的現代漢語發展變化圖[2](P428)。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百年現代漢語發展演變脈絡進一步明晰,目前的認識是普通話圈、國語圈與華語圈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三條線索中,臺港澳國語及海外華語起點相同,早于普通話,且前兩者起伏變化小于后者,相互之間更具一致性;改革開放以來,三條線索逐漸靠攏,三者今后會在趨同與存異這兩個趨勢下進一步發展,并加速互相傾斜的趨勢。[8]
以上三條發展線索中,普通話的發展演變已有較多討論[12][13],另外兩條線索則剛剛起步,近年來相關研究瞄準薄弱環節,將重心轉移至新馬華語史的構建。在相對宏觀的層面,將這條線索概括為“早期華語的形成:由中國大陸到南洋”“全球華語的初步形成:由港臺到全球”以及“普通話與華語的雙向互動”。[5](P146~156)在相對微觀的層面,對華語的發展歷史進行精細化的梳理與分析。其一,立足于共時,以中國的早期國語為參照,從“一致性”與“差異性”的角度描寫早期東南亞華語的基本樣貌,將其特點表述為“整體搬遷+局部改造”。[14][15]其二,立足于歷時,著眼于前端,將早期新馬華語的發展趨勢總結為中性化、本土化、歐化和規范化[16];著眼于全程,以詞匯為抓手,對1919年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華語發展變化進行歷時考察[17][18]。立足于百年現代漢語的支點來認識全球華語,不僅可以為其找到合理的歷史定位、理清其發展脈絡、促進華語本體研究的深化及細化,還可以進一步促進大漢語的資源觀、系統觀及歷時觀的確立與更新。[8]
(二)研究觀念的新收獲
隨著對華語及其研究認識的深入,其祖語本質、歷時屬性及資源性質得到進一步的重視與強調,由此形成華語祖語觀、歷時觀、資源觀,簡稱“三觀”。[19]其中,“祖語觀”將華語作為一種祖語或傳承語看待,指出華語的原祖語是20世紀前半葉的民族共同語,當今華語的重要特點來源于其作為祖語所具有的保守性,其變異性很大程度上可以從祖語學習/習得的不完全性上得到解釋。歷時觀和資源觀內涵較為豐富,下面分別說明。
歷時觀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華語的歷時觀,提出“全球華語史”的學科概念[20],并從宏觀角度進一步討論全球華語的源流及其發展,具體包括其形成及發展過程、主要載體及實踐領域、現狀及發展趨勢等[5](P145~174)。二是華語研究的歷時觀,在規律總結及理論歸納時應將歷時因素作為一個重要方面,在具體研究中也應該充分注意華語歷時發展以及與參照對象普通話關系及其變化的特殊性。[19]此外,歷時觀的深化與推進,在具體研究中衍生出更具指導性及操作性的理念,如在早期國語發展變化考察中,歸納和提煉了華語歷時研究的具體“三觀”,即華語形成與發展的動態觀、早期華語與早期國語的同步觀、華語發展的本土觀。[16]
在資源觀方面,全球華語的觀察視角之一就是作為語言資源的全球華語[5](P74~87),這一觀念強調,應將全球華語看作獨特的、豐富的、寶貴的語言資源,對其資源種類、載體、表現等進行多樣化、全方位的研究。華語研究成果也是一種資源,可加以充分利用,以推進后續普通話及華語的研究。在普通話研究方面,華語研究成果在共時層面有助于深入認識普通話的基本面貌及特點、拓展研究范圍、促進研究的深化與細化;在歷時層面,有助于理清百年漢語的發展線索、明晰普通話形成及發展的過程、增強具體現象的歷時研究。[21]此外,華語研究的資源觀還有三點助益:一是接續原有發現,既強調“開始做”,又強調歷時層面的“接著做”,對語言現象的發展變化進行追蹤考察;[22]二是應用已有實績,思考如何將其用于實踐領域,比如著眼于華語詞匯與普通話“隱性差異”,提出處理華語詞典與現代漢語規范詞典之間的關系的“若即若離”原則;[23]三是反思既有結論,對相關研究進行補缺及糾偏,如對馬來西亞華語“者”綴詞語的考察,糾正了該詞起源于共時變異的不正確認識,指出該詞對早期國語用法的繼承性及擴展性。[24]
除以上“三觀”外,全球華語還可以從其他角度進行觀察及研究,由此形成一系列重要觀念。例如,除了作為語言資源的全球華語外,還有作為華人共同語的全球華語、作為華語變體的全球華語、作為教學對象和教學媒介的全球華語等。[5](P74~87)這些觀察視角都可以作為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進行深入討論與分析。此外,華語語言安全觀也值得重視,語言安全視角下的全球華語及其研究,目前應當以“一二三”框架為主體,即一個基本點(語言認同)、兩條線索(全球華語從哪里來、向哪里去)和三個著力點(語言規劃、語言保護、語言服務)。[25]
二、方法論的探索與思考
方法論的前提是本體論,而方法論是否恰當首先取決于對研究對象本質的認識。[26]隨著對全球華語本體認識的深化,方法論建設也有較大的推進,主要體現為研究主體的拓展加深及研究視角的接續創新。
(一)研究主體的拓展加深
早在2000年,海峽兩岸民族共同語的對比研究就立足于“差異”與“融合”兩個主體展開。[27]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刁晏斌正式提出“差異與融合”兩翼模式[28],并不斷嘗試進行新的拓展與加深。
第一,針對“差異”,提出真性差異與假性差異、詞典差異與視角差異、顯性差異與隱性差異、完全差異與部分差異、共性差異與個性差異、歷史差異與現實差異六組相互對待的概念,初步建立“差異”的下位概念系統,體現了求真務實的研究追求。[29]其中,歷史差異與現實差異是著眼于時間因素與華語變體及其發展進行的劃分。以海峽兩岸民族共同語為例,前者主要立足于兩岸交流之初的詞匯狀況,同時也包括“以前”某一或某些時間點上的詞匯狀況;后者則立足于當下,著眼于兩岸語言關系的發展變化,即此消彼長、雙向互動,很多詞語由異趨同。這組概念的提出有助于進一步促進差異研究歷時觀的樹立及相關研究的開展,其內涵、范圍、相互關系及發展趨勢等都非常值得詳細分析。[22]
第二,針對“融合”,在體系建設方面,回顧已有相關研究,指明薄弱環節,展望未來發展方向,指出事實發掘應兼顧共時及歷時層面,強化對“難融合”“不融合”現象的調查分析;理論探索應進一步強化,值得討論的課題包括但不限于融合的定義內涵、融合度的概念、融合發展的預測、融合量化分析指標與界定等。[30]此外,融合的動態過程同樣值得關注,如區分出“借用—自用—化用”等三個前后相繼的階段[31],并用于華語融合研究[32]。在具體研究中,刁晏斌指出,融合包括“以普通話輸入為主”和“以普通話輸出為主”兩個階段,研究重心由此開始調整,開展普通話輸出及外向傳播的研究,初步建構相關理論框架,如區分官方傳播與民間傳播、直接傳播與間接傳播、首次傳播與二次傳播等傳播方式及途徑,并辨析傳播數量與質量的語言內因素,包括詞語性質、內容及其形式和構成方式等。[33]
第三,對“差異—融合”兩翼進行拓展與加深,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提升兩翼模式的系統性及完整性,辯證看待“差異中的融合”與“融合中的差異”。[22]由此進一步提出“顯性融合”與“隱性融合”的概念,前者主要指某一或某些現象在某一或某些區域從無到有或者從有到無,以及某個單區或雙區現象最終成為多區現象等,后者則主要指前者內部比較細微、因而較難引人注意的各種表現。基于此,將兩翼模式升級表述為“差異(顯性差異與隱性差異)+融合(顯性融合與隱性融合)”。[34]其二,促進兩翼模式向一體模式轉變。在具體的語言現象中,差異與融合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因此還應該進行交匯式的一體模式,它與兩翼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具體而言,前者更多地立足于宏觀,后者更多地著眼于微觀。很多具體現象中,差異與融合并存,并且具有復雜多樣的表現形式和相互關系,唯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形成對某一現象的完整考察與研究。[35]
(二)研究視角的接續創新
20世紀后期,邢福義先生提出“兩個三角”理論,其中,“大三角”即普通話、方言、古漢語(簡稱“普、方、古”)。[36]該理論基于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提出,但同樣適用于華語研究,李計偉證明了這一點。[37]在此基礎上,華語視角理論繼續發展,新增了外語視角,如田小琳針對香港社區提出的“普、方、古、外”比較原則[38],以及王曉梅闡述的馬來西亞華語“古、方、普、外”四角觀[39]。然而,視角理論的探索還在接續發展,并有較為顯著的拓展與突破,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拓展視角維度,增添早期國語及華語的視角,即“國”角和“華”角。[40]“國”角是增加的第五個視角。[41]華語發展的歷史事實及相關研究均已證明,早期國語與華語之間有源、流關系,后者為前者的變體,而“國”角的缺失已經造成已有研究的一些問題與不足,如結論不正確、歸因不完全、內容不完整等,因此“國”角的確立極其必要。[40]“華”角是“普”“方”“古”“外”“國”后增加的第六個視角,它具有三重屬性和功能:首先,作為本體視角有助于明確研究基本立足點,有助于擴大研究范圍,得出客觀、真實的結論;其次,作為外向視角,為漢語國際傳播及語言規劃提供較為宏觀的參照,并建立普通話及其研究的“國”語/華語視角,反哺普通話的語言事實梳理及相關理論建設[21];其三,作為內向視角,促進不同子社區的相互比較及參照研究,即考察各華語變體的共性表現與個性差異,細化對語言現象實時差異及互動情況的分析[42]。
第二,建立視角系統,對視角之間的區別與聯系進行討論及說明。[40]各視角的屬性、功能、定位、特點、影響力并不相同,不可等量齊觀,需要進一步思考、劃分及界定。如上所述,“華”角是基本視角,集本體視角、內向視角、外向視角于一身;“國”角作為來源視角,具有探源、求同、求異等功能,其歷時內涵尤為豐富;“方”角和“外”角都是重要的影響視角,二者兼具多元復雜、長時程的特點;“普”角為重要的參照視角,可用于華語領域的差異及融合研究;“古”角所代表的語言事實,很大程度上是經由其他視角進入華語的,因此可視之為“間接”角或“半”角。每個視角都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進行個性化的考察及討論,相關研究正在持續進行,如基于“外”角對華語“是時候+VP”句進行細致觀察及解釋等。[43]
第三,豐富視角層次,根據不同言語社區的實際,將以上立足于整個全球華語所得出的概括的“大六角”具體化為適用于各子社區語言研究的“小六角”。[44]以香港言語社區為例,“六角觀”的具體化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小六角”屬性及內涵的具體化,如相較于其他華語變體,“古”角對港式中文更具重要性,具有直接進入及間接進入雙重路徑,因而在相關研究中有可能并非“半”角而是“全”角;二是“小六角”研究布局及側重點的具體化,通過反思現有研究,前瞻未來研究的路線及方向,例如在現有港式中文研究中,“國”角的缺失較為嚴重,因而亟待“補課”,后續研究需要重點關注;三是在實證研究中,“小六角”操作思路的具體化,要根據不同研究主題及對象靈活調整“小六角”的使用。
三、理論建設與探索的特色
全球華語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思考與探索也表現出一定的自身特色,具體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理論建構的雙重路徑
1.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全球華語研究可以且應當充分利用普通語言學以及其他相關的理論研究資源和具體成果,以使之得到進一步的充實和完善。以社會語言學為例,言語社區理論用于全球華語研究,并形成了“全球華語言語社區”的新概念及重要觀念。[45][5](P95~106)在具體研究中,此觀念還可以衍生出新的概念與方法,如立足于兩岸民族共同語的融合研究,提出“言語社區特征詞”的概念[44],用于指稱不易被其他言語社區吸收的詞語,并思考華語融合中的不平衡表現以及未發生融合的“不融合”現象[5](P207),由此進一步將華語融合研究引向深入。
除普通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外,一些基于現代漢語普通話而提出的理論與方法同樣適用于全球華語研究,例如,在宏觀層面,直接借用普通話研究“立地+頂天”的理念,作為全球華語研究的學術愿景并加以論述;[9]在中觀層面,因地制宜地發展現代漢語語法的“大三角”理論,將其擴充為“六角”;在微觀層面,借由普通話已有的概念對華語同類現象進行考察及闡釋,例如,“外來移植義”最早用于表述普通話詞嫁接外來詞義的現象[47],隨后用之于華語同類現象的探討,由此展開系列研究,為了解和認識華語詞義的增長模式及途徑確立了一個新的認識角度。[48][49][50]此外,古代漢語研究的相關理論及方法對全球華語學建設也有一定助益。例如,“同義連文”本是古代漢語訓詁學及古漢語詞匯學所關注的現象,但語言事實說明,該現象貫穿古今,且在普通話及華語中差異較大,因此也可作為一個觀察角度來看華語詞匯運用的特色。[51]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漢語史是全球華語最重要的研究視域之一,因此,前者理論建設及方法探索的成果自然可以作為后者學科理論體系建設的養分。例如,在全球華語史的建構中,引入現代漢語史的視角,將其作為對比參照的重要基礎;同時,還可以將現代漢語史的研究框架與模式移植至全球華語史的研究中,如借用前者的下行式、上揚式、馬鞍式、浴缸式等發展模式來研究東南亞華語詞匯發展變化等。[17]
2.根植事實,自我出新
全球華語學還需要根植華語事實、自我出新,為漢語研究乃至普通話研究做出屬于自己的貢獻。根據研究主體的不同,此方面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接著做”,即接力前輩學者的創新成果進行推進,完善相關理論框架。隱性差異是李行健先生立足于海峽兩岸差異詞詞典編撰所提出的概念[52],引發了不少后續討論。刁晏斌教授敏銳地察覺到此概念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適時將其提升為全球華語領域的重要研究方向,進行集成式的專題研究,對薄弱環節進行重點攻關,較為詳細地探究其內涵外延、分布范圍、特點表現、成因機制等理論性問題,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進一步增強差異研究的精細度、顆粒度及理論色彩。[53][54]再如,“社區詞”的概念及思想最早是田小琳先生基于香港言語社區的詞匯現象提出的[55],而后在普通話標準視角及大華語標準視角下取得明顯進展。刁晏斌教授適時進行回顧及展望,指明該概念進一步發展的方向,即建立多維度層次觀、處理好分類問題、進一步理清社區詞跟其他詞類的關系、加強歷時層面的動態研究、進行更加全面多元的理論探索。[54]
第二,“開始做”,即首倡某一領域及某一方面的研究,構建理論框架,持續進行方法論的探索。立足于海峽兩岸民族共同語的對比研究,首倡“微觀對比”的概念及研究方法,由微觀的語言單位即“詞”入手,對其進行盡可能深入細致的考察分析;[46]隨后將微觀對比的層級從詞推進或深入到語素和義素層次,可稱之為“語素/義素本位”,進一步深化和細化了研究內容;[57]繼續將微觀對比的思想用于海外華語研究,提出共時描寫、歷時考察和橫向對比的三維模式,在此基礎上展望未來詞匯研究“全息式”分析的設想。[9]在此理論創新過程中,微觀對比的研究層次逐漸細化、框架趨于立體,已經成為華語詞匯研究的增長點之一。此外,起始式創新研究還包括華語詞匯運用的“舍取”系列研究,如“舍今取古”[58]、“舍小取大”[59]、“舍雙取單”[60]等,它們都是觀察華語詞匯使用特色的絕佳窗口。
(二)本體論及方法論的有機聯系
在理論及方法探索的過程中,立足于華語事實,準確提取各類語言現象的典型特征,并予以科學命名,創建了一套全球華語學的學術話語體系。此套話語體系呈現多元立體格局,本體論及方法論相互交織、互為參照,共同推進對語言事實的多角度觀察與分析。具體而言,呈現以下兩個特點:
1.對立統一,雙向互動
從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提出下位劃分,推動對某些現象及概念認識的深化,從而促進相應的方法創新。在此方面,已經有許多研究實績,如上文提及的關于“差異”的六組下位概念;而在融合方面,也有“顯性融合”與“隱性融合”的區分,二者之間的區別與聯系以及它們應當如何運用于兩翼模式及一體模式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究。這種思路還可以舉一反三,遷移至相關領域的研究。例如,已有的差異下位類型可為融合小類的劃分提供參考,仿照“歷史差異”與“現實差異”,或可提出“歷史融合”與“現實融合”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已完成的融合現象,后者則指正在進行的最新融合現象,更強調融合進程的動態性、實時性及即時性,由此可進一步強調融合及其研究的歷時觀,會帶來新的研究對象和內容,有可能成為華語研究新的增長點。在具體的研究中,對立統一的思路也將帶來新的認識角度及操作模式,例如近期關于馬來西亞特有詞語輸入的調查表明,立足于“進入”與“融入”、偶用與常用、“地普”和“標普”三個內部相對的維度,可以發現特有詞語的使用呈現較為明顯的不平衡性。[61]可見,以上指標的提出為融合現象的發掘提供了新的觀察角度以及新的呈現方式。
2.縱橫交錯,立體參照
在一個立體的學科系統中,概念、理論及方法之間是相因相生、相輔相成的,它們之間呈現縱橫交錯格局,可為一種或一類現象的考察及分析提供多樣化的角度。例如,在全球華語的初期研究中,語言接觸往往被視作華語特點的成因之一,但相關研究缺乏統一的分析框架,呈現平面化的離散趨勢。基于此,對久已存在的“歐化”概念進行反思,立足于歐化現象的社會/地域/功能分布,劃分出“普通話歐化”與“‘國’語/華語歐化”[62],二者的歧異又可從歐化程度、歐化方式、歐化階段與歐化來源的角度進行觀察及分析[63],其表現涉及多種語言要素,而“外來移植義”正是著眼于詞義歐化而生發的概念[48]。此外,華語作為祖語的變異性[19]、舍小取大現象[64]等都可以從歐化角度進行集成式考察及討論。不難發現,全球華語學視角下的歐化及其相關研究已呈現縱橫交織的立體拓展與延伸趨勢,這正是理論體系內部有機互動與多維聯系的重要表現。
結 語
總體而言,近年來全球華語學收獲不少,但尚未臻于至善,在許多方面仍猶有所待。在此過程中,更需要重量級學者的積極參與,他們的探索與實踐,將起到引領和示范作用,為相關研究指明進一步發展的方向。本文以刁晏斌教授的系列研究為例,從本體論及方法論兩個方面,對近年來全球華語學的思考與探索進行回顧與梳理,著眼于體系建構的雙重路徑及理論方法的有機聯系兩個角度,歸納此領域理論建設與探索的特色之處,為今后相關研究的理論深化及方法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及方略。我們相信,沿著重量級學者的已有探索繼續深入、持續創新、不懈奮斗,為全球華語學的理論框架添磚加瓦,循此以往,最后定能將全球華語學做成一門真學問、大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