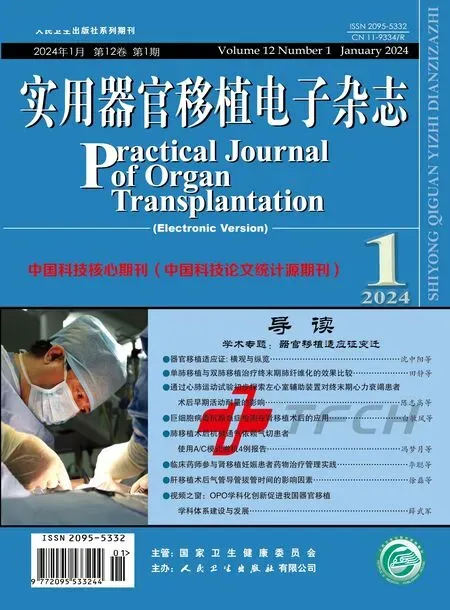器官移植適應證: 橫觀與縱覽
沈中陽,薛武軍(.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南開大學移植醫學研究院,天津3009;.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腎臟病醫院腎移植科,西安交通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 陜西 西安 7006)
適應證是熟知未必詳知、常用未必用準的醫學概念,是通用名詞——指征(indication)在醫藥領域的專屬化用語,其融匯指示與征象等基本詞義,用以指向性表述某一臨床措施的具體適用情形、證據或理由。適應證具有指示性與適當性雙重基本內涵,同時具有復雜性、時代性兩項基本特征。適應證通常是其所屬時代背景下科技進步程度和醫藥發展水平的生動寫照,追溯適應證變遷歷程可發掘醫學進步的內在動力與演進規律。
關于適應證的定義性表述不盡一致。在我國的《辭海》中定義為:適合于采用某一治療措施的疾病或情況;在《斯特德曼醫學辭典》中定義為:啟動疾病治療或診斷試驗的基礎,其匹配用于疾病病因的認知(因果適應證)、疾病呈現的癥狀(癥狀適應證)以及疾病的性質(特定適應證)。在證據醫學時代,也有醫學典籍將適應證簡要概括為:使用某種檢查、藥物、程序或手術的正當理由,旨在強調適應證是啟用某種醫學干預的證據。適應證常以賦予具體內涵的適應證標準(indication criteria)指導和規范臨床實踐,故應避免與表述某一特殊醫學狀況的臨床診斷相混淆。當前,基于循證醫學原理形成的醫學指南或共識等,日趨轉變為適應證的引申表述形式,用以指導臨床實踐。
禁忌證(contraindication)是適應證的反義詞,通常指某一診療措施的風險明顯大于益處而拒絕接受的原因或理由,用以指示或預示醫學干預措施的無效或危害,臨床上常用絕對禁忌證和相對禁忌證評估風險與預測結局。針對某一特定個體而言,適應證與禁忌證是并存的矛盾體,常可展現醫學診療的整體性、復雜性和特殊性。與確立適應證相比,判別禁忌證往往更具系統性和整體性,查找、發現、評估及管控禁忌證是臨床診療的重要任務和臨床決策的必要前提。適應證在臨床藥學領域又特化為“適應癥”(label indications),特指某一藥物適用的臨床癥狀或應用情形,其反義詞為“禁忌證”(off-label indications),臨床上應依據證據或理由出具用藥處方[1]。
現代器官移植學發軔于20 世紀初,繼而以1954 年12 月23 日默里(Dr.Joseph E.Murray)教授實施的同卵雙生兄弟間的成功腎臟移植為先導,各實體器官移植相繼跨入臨床應用階段,并伴隨社會與科技的進步而日臻成熟與規范。器官移植學的基本使命是克服重要臟器的終末期功能衰竭,橫觀與縱覽器官移植適應證的演變歷程,將加深器官移植醫學特殊性、先進性、復雜性、時代性的認知與思考,進而促進科技創新與學科發展。
器官移植適應證變遷的內在動力源于其特殊內在屬性,即征用異體器官資源的社會倫理屬性和免疫排斥異體器官的科技屬性[2],社會與科技以雙元與整合[3]方式促進新興技術與交叉學科的涌現,驅動器官移植適應證的不斷變遷。適應證變遷的動因與動機直接來源于器官移植臨床實踐[4]。諸如:為擴大供體資源及其利用,派生了一系列親體移植技術、邊緣器官修復與利用技術、肝移植系列創新技術(劈離式、輔助式、多米諾式)[5];為克服同種異體器官排斥反應演化出高致敏或ABO 血型不相容器官移植脫敏方案、腎移植供體交換計劃等;為發揮器官移植技術的屬性優勢,催生了肝移植腫瘤學的復興,派生了系統移植腫瘤學的新興[4];為避免器官資源浪費,引發了對肝臟、心臟、肺臟等器官移植“至重者優先”(sikest first)適應證原則上限的倫理質疑[6]。此外,生物醫藥技術的進步與創新,正在顯著改變器官移植適應疾病(丙型肝炎等)[7]和制約疾病(HIV 感染)的臨床結局,同樣促使了器官移植適應證或禁忌證的悄然變化。
總之,社會與科技的不斷進步,始終貫穿在器官移植學的發展進程中,并繪就了器官移植適應證生動、多彩的歷史畫卷。當前,再生醫學、異種移植、AI 技術等正在加速發展,社會與科技正處于飛速進步的VUCA 時代,器官移植適應證也必將呈現出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的演進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