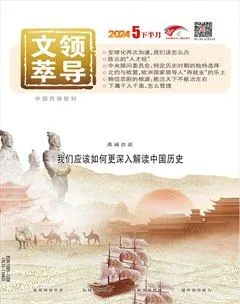錢瑛,我的引路人
馬識途
一
那是一九三八年一月的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們在大廳里燒起熊熊烈火,幾十個人圍火坐著。黨訓班的負責人方毅同志帶來一個身材矮小,約三十歲的大姐,向我們介紹說,她就是湖北省委的組織部長錢瑛同志,要我們都叫她錢大姐。
錢大姐對我們說了些什么,早已記不清了。但是我卻記得,她在我們鼓掌歡迎下,給我們唱了一支《國際歌》。我們都知道這是當時革命者的歌,錢大姐雖然不是一個歌手,但是我們聽起來,唱得真好。她昂著頭,晶亮的眼睛望著前方,唱得那么堅定而富于感情,就像眼見著在南京雨花臺和上海龍華的那些烈士拖著鐵鏈走向刑場時唱的一樣。
在以后的幾天,錢瑛找許多學員談話,這是她作為組織部長的分內事。她也和我談過話,問我今后的去向,我和許多青年一樣,都向往著去打游擊,到敵人后方去,她笑一笑說:“各方面都需要人,由組織分配吧。”
這年二月底我到漢口,見到了錢大姐。她為我舉行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儀式,并在入黨介紹人那里,簽上了她的名字。
我入黨后,錢大姐作為組織部長,分配我到漢口職工區委。后來,漢口職工區委又叫我到頤中煙廠去做工人工作。我在工廠附近辦了一個職工夜校,我從工人口里第一次聽到外國資本家駭人聽聞的壓迫和剝削。與其說是我在對工人進行教育,還不如說工人在教育我。我有空的時候去看望錢大姐,她總是熱情地問我的工作情況,并且告誡我,要脫下學生裝,穿上工人服,放下學生架子,常到工人家里去交朋友。錢大姐見我肯深入到工人中去,并且為工人的受苦感到憤慨,她表示很高興。但是在這時由于我的思想簡單,捅了一個婁子。
當時由于物價上漲,工人叫苦連天,在我們辦的夜課學校里學習的一批工人積極分子醞釀要漲工錢,不然就“擱生活”——罷工。他們去串聯一下,就像在干柴上投上幾顆火星,大家情緒激昂。但是外國資本家和中國買辦哪里肯干,以開除工人代表相威脅。工人們氣憤已極,首先在印刷廠罷了工,這一下驚動了國民黨市黨部,說共產黨答應不罷工的,為什么罷了工?黨內也有同志責備我是尾巴主義。錢大姐把我找去了,我是準備挨批評的。她仔細地詢問情況,卻一點責備我的意思都沒有,還說這是工人的覺悟提高了,敢于和資本家斗爭,肯定了我的工作。但也指出我沒有經驗,輕易讓工人使用罷工這個斗爭手段。她說,不能只看到少數先進分子的要求就同意罷工,煙廠工人大半是計件工資,一天不干活,就沒有工錢,又因女工很多,堅持起來比較困難。搞不好罷工可能失敗,就會給工人帶來更大困難。錢大姐這么一分析,我豁然開朗,知道我的簡單幼稚會給工作帶來損失。我問錢大姐怎么辦,她出點子說,可以答應市政府社會科的意見,先行復工。但是有條件,一是資方要出面談判按照物價提高工資,改善工人生活的問題;二是罷工期間的工資要照發;三是不得開除工人代表。
我一下開了竅,說服工人先復工,再談判。結果工人工資、福利都有點兒改善,這樣一來,我們辦的夜校實際上成為工會的辦事地方,夜校的積極分子實際上成為工人代表了,以后工人參加武漢的各種活動也多起來了。
這是我入黨后第一次做工人工作,出了婁子,錢大姐不是責備我,而是又批評又鼓勵,又出點子,使我增強了信心。錢大姐那種可親可敬的形象在我的腦子里一下子樹立起來,從此我把她看作給我引路的好大姐了。
我做了幾個月工人工作,錢大姐看我為人老實又積極,有一天,她叫我去,對我做了一次很嚴肅的談話。她說:“你愿意做一個職業革命家嗎?”我說,我愿意。她說:“職業革命家是黨的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卻又是最危險的工作,你可要想好。”我說想好了,革命一輩子。她很高興。從此我就在她的領導下,做黨的領導工作,從黨的支部書記一直做到地下黨的特委書記。
二
一九四六年我被調到成都川康特委任副書記。我怎么也不能忘記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去香港匯報工作,錢大姐給我整了一個月的“風”的日子。那次的收獲使我終生受益。
那時,我們在川康一帶一連搞了三次武裝暴動都沒有成功,不得不把準備搞的第四次暴動暫時停下來,進行總結。那時領導我們的上海分局已從上海搬到香港,我們決定到香港去向分管白區工作的錢大姐匯報工作。
錢大姐還是那個老習慣,抽著煙,把眼睛瞇起,專心一意聽我講。她不記筆記,不插一句話,除非有些情況她需要我們再詳細補充一下。匯報聽完了,她也不馬上分析或回答問題,叫我放開來休息兩天,她再來談。
過了兩天錢大姐來了,她首先簡單回顧了我們的工作,對于我們在十分嚴重的白色恐怖中,依靠群眾堅持斗爭所取得的成績充分肯定。接著她就分析我們三次武裝暴動失敗的原因,也基本同意了我們的看法。但是她說:“一次失敗了,你們再搞一次,這一次失敗了,你們還要來另一次。這是為什么?是一種什么思想阻礙你們認識問題?是一種什么思想使你們老撞南墻,死不回頭?”我實在回答不出來,就這么搞了半個月,醞釀、回憶、分析,老想不通。最后她嚴肅地給我指出:“最根本的是你們對黨的地下組織的任務還不明確,對于搞武裝暴動的目的是什么還不清楚。……武裝斗爭只要能拖住敵人,就是配合了老區的斗爭。因此不能把自己有限的一點兒力量拿去和敵人拼命。然而你們偏偏是這么搞,思想根源在哪里?”
她窮追不舍地問:“你們為什么認識不清楚呢?無外乎是想自己打出一個江山來,拉起一支隊伍來,以便將來論功行賞,排班坐交椅吧?”
我實在難以接受她這太刺激的批評,申辯說:“我是早已下決心掉腦袋的,根本沒有其他的想法。”她立即十分嚴厲地說:“同志,我們的一切都是屬于黨的,我們沒有權利浪費黨的財富,包括我們的生命。”
我要走了,錢大姐親自送行。她帶我到一家餐館去吃飯,給我叫了一份她說她從來也沒有吃過、價格昂貴的鮑魚,給我餞行,那人情味特別令我感動。在吃飯時,錢大姐對我說:“四川是敵人的特務窩子,川東地下黨的組織出了毛病,可能牽連到川康來。老實說,你這次回去是冒著很大危險的。”我點了一下頭。她舉起杯來,我忽然有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感覺。
一九四九年一月,川康特委遭到特務破壞,我在成都做了一個月的疏散工作,三月初再到香港匯報。錢大姐狠狠批了我一頓,說我不敢堅持原則同不正確的領導同志斗爭,還責備我疏散下面的同志不徹底,特別不滿意我們還在成都、重慶組織群眾運動向敵人進行反擊。
“難道你又忘了教訓,現在是什么時候了?你們還在那里斗,斗!難道斗爭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嗎?”她又這么批評我。
她接著給我分析,全國解放已成定局,沒有多少大仗可打了,再過幾個月,解放大軍要向西南進軍,幾乎可以說走過去就解放了。黨的地下組織的迫切任務就是保存現有力量,不受破壞,準備迎接解放。現在要辦的事是如何阻止敵人破壞,如何對敵人策反,如何收集資料,準備接管。現在再也不需要我們在敵我力量懸殊,敵人狗急跳墻的形勢下,還去和敵人硬拼。她反復說:“形勢變了,任務也該跟著變嘛。”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和錢大姐不在一起工作,只是我每次到北京,總要去看望她。她對我們這些老下級十分親熱,常常自己出錢去辦幾個菜來吃,甚至拉到四川飯店去吃高級菜。她一面吃一面詢問當地的情況,更多的是問到過去地下黨同志們的表現。我不能忘記她常常叫我們做好一切思想準備,說今后面臨新的任務、新的工作,要不斷學習新東西,適應新形勢,不要畏首畏尾,也不要滿不在乎,總之不掉隊,少跌跤。這些好像是隨便說的話,卻使我受益匪淺。
(摘自《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