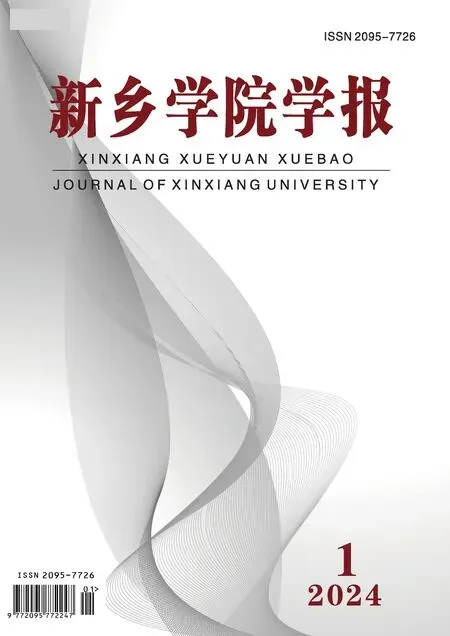《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的田園書寫
趙曉曉
(新鄉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3)
《法國中尉的女人》(1969)是英國后現代主義小說家約翰·福爾斯的巔峰之作,該小說既是對傳統維多利亞愛情故事的模仿與顛覆,又是對傳統田園書寫的繼承與創新。訂婚戀人查爾斯和歐內斯蒂娜去萊姆度假,偶遇有著“法國中尉的女人”綽號的薩拉,受其影響,查爾斯無可救藥地走上存在主義自由之路。該小說中有大量的自然景致描寫,使得福爾斯的田園書寫特點展露無遺。
一、田園中的動物
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福爾斯對田園中的動物進行了多次描寫。小說中間部分,敘述查爾斯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他很憂郁:他已經和錯誤的女孩訂了婚,而且剛剛被剝奪了祖傳財產的繼承權。當查爾斯進入萊姆·雷吉斯周圍的樹林時,道路上有一只狐貍穿過,還有一只公鹿在安靜地散步。這一景致堪比15世紀意大利藝術家皮薩內羅的畫作《尤斯塔斯的幻象》。盧克·賽森和迪利安·戈登指出,“這幅畫是為展示皮薩內羅描繪不同動物的技巧,并讓贊助人驚嘆于它們的詩意多樣性和林中居民的神秘性”[1]。皮薩內羅畫的不是羅馬士兵,而是意大利王子,這使得這幅畫更適合于貴族查爾斯的隱喻。就像皮薩內羅作品中的尤斯塔斯一樣,查爾斯與自然的相遇使他感到震驚。
自然界并非只是上面講的那兩只動物才重要。樹林中還有數不清的鳥兒在歌唱。黃鶯、白喉雀、鶇鳥、畫眉、白鷺、班尾鴿的歌聲在晨曦中蕩漾著,使清晨有著黃昏的靜謐,卻沒有黃昏的哀傷色彩。查爾斯覺得自己像是走在動物的世界里。他感到,每一片樹葉,每一只小鳥,小鳥唱的每一支歌,都是那樣美,但彼此間又有細微的差別,這就組成了一個完美的大千世界。[2]277
在《尤斯塔斯的幻象》中,有精心渲染的雄鹿、母鹿、熊、天鵝、鸛、鵜鶘和蒼鷺等動物群,而查爾斯所看到的各種鳥類都以“細微的區別”出現,這些動物似乎來自一個完美的世界。就像喬叟在《鳥的議會》中對自然的描述一樣,結合了自然學家描述的現實細節[3]。主人公的注意力被附近大嗓門的鷦鷯吸引了,這只鳥的高聲鳴叫充斥著他的頭腦。他在所有這些非人類生命的背景下思考自己的處境。而他在這一場景中的最后情緒是“我不知道”。敘述者解釋說:“他被關在外面,失去了伊甸園,像薩拉一樣——他可以站在伊甸園里,但不能享受它,只能羨慕鷦鷯的狂喜。”[2]278在這個場景中,查爾斯看到了“普遍存在的對等性”,看到了周圍的動物所處的和平環境,盡管它們的環境很卑微。然而,查爾斯沉浸在他個人的、存在的擔憂中,感到被拒之于這種平等的存在之外。
根據奧布里的說法,“平等存在”的概念最好的解釋是達爾文式的動物平等觀,它“掩蓋了垂直組織的、按等級排列的存在之大鏈的各個環節”[4]。奧布里將中世紀的“存在之鏈”概念與查爾斯在這一場景中的看法進行了對比。然而也應該看到,由于人類意識的性質,“存在的對等性”是復雜的。查爾斯在散步時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動物,并注意到這些動物就像他一樣,也有情感。因此,存在具有對等性。查爾斯也注意到它們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滿足,然而,查爾斯本人復雜的人類意識以及對過去和未來情景的把握,似乎讓他感到焦慮。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可能是人類的親戚,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某種平等的存在,或普遍共享的共同身份,但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并不同人類一樣有巨大的憂慮后世的潛力。
查爾斯凌晨四點后走到萊姆·雷吉斯的鄉下,一夜未眠,陷入沉思。遇到大自然“寧靜而滿足的臉”后,虛構的查爾斯感到“被驅逐出”黑帽和白頭翁所共享的和平境地。福爾斯不能被指責為一個虛無縹緲的自然作家,他將自然世界設定為一個良性的寧靜的地方,同時又默默地忽略了自然界使人類成為人類的特殊品質。這種“自然角”的陳詞濫調在福爾斯的小說中得以避免。在對福爾斯的一次采訪中,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提出了以下問題:“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你在自然界中發現的抒情表達所打動……然而,這種抒情難道不是一種錯誤的標準嗎?自然界是美麗、平靜和恢復性的,恰恰是因為它缺乏痛苦的自我懷疑……的人類世界。”[5]73這樣一個問題引來了反駁,福爾斯的小說并沒有假定一個非人類的世界。自然界的平靜和姿態,可以與人類生活相提并論。
《智者》是基于福爾斯在大學期間的哲學筆記的自畫像。這本書被編排成一個“筆錄集”,大概是受到了18世紀法國作家如帕斯卡爾和拉羅什作品的啟發。福爾斯認為,在正常條件下,自然界中所有有生命和有感情的生物都可以分享幸福,除了人類。
二、田園中的人物
對牧羊人、鐵匠、木工、農民的描寫是《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田園書寫的又一特點。小說中有這樣一個場景:一個陽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查爾斯的男仆薩姆來到他主人在萊姆·雷吉斯的臥室。
薩姆拉開窗簾,清晨的陽光灑滿了查爾斯的全身[2]44。
樓下傳來小蹄子啪嗒啪嗒的落地聲,接連不斷的咩咩叫聲。查爾斯站起來,向窗外望去。街上有兩個穿褶皺外套的老人,正面對面地站著講話。其中一人是牧羊人,用牧羊人的彎柄杖斜撐著身子。十二只母羊和一群大羊羔慌慌張張地呆在街上。古代英國流傳下來的這種衣著樣式到一八六七年雖并非罕見,但已不多,看起來很別致。每個村莊里都還有十來個老人穿這種外套。查爾斯想,要是自己會畫畫就好了。的確,鄉下真叫人陶醉。他轉身對仆人說:“說真的,薩姆,在這兒過這樣的日子,我再也不想回倫敦去 了。”[2]45
正如邁克爾·貝拉米所說,“查爾斯缺乏藝術天賦,預示著現代游客忘記了他們的相機”[7]。這個典型的田園組合——靠在羊角上的牧羊人、穿著罩衫的長者、咩咩叫的羊群,被查爾斯唯美化了。他希望畫出這兩個人和動物,暗示這種對場景的審美理解可能會取消這些人物所體現的獨特的思想和個性,把他們僅僅當作畫布上的裝飾品。
查爾斯的感嘆具有諷刺意味。“我再也不想回倫敦去了”,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一個舒適的臥室里。仆人正忙著準備給他做早飯,幫他刮胡子,然后,為他收集“雙份松餅”。眼神呆滯的查爾斯俯視著一個顯然沒有從舒適的環境中站起來的牧羊人,說出了這番話。牧羊人可能從黎明開始就已經出來了,當時撫摸著胸口的溫暖晨風可能并不那么具有詩意般的溫柔。
在這部小說中,這位可以輕易考慮“不想回倫敦去了”的紳士代表了整個英國社會的一個階層。在去他叔叔的鄉村莊園溫斯亞特的旅行中,查爾斯認為自己正在重新進入“萬古不變的平靜鄉間”[2]226。他的車子駛上了車道,“幾英里內都是春意融融的草地,威爾郡的廣闊平原盡收眼底。遠方的房屋已清晰可見。屋子灰白相間,兩側聳立著高大的雪松和著名的銅色山羊櫸樹,后面是隱約可見的成排馬廄”[2]226。查爾斯對莊園的觀察是連續的。
他們碰到了他伯父的幾個雇工,其中有鐵匠埃比尼澤,他正在一個小火盆旁將一根弄彎了的鐵欄桿打直。在鐵匠身后,有兩個木工向查爾斯問安。第四個是名叫本恩的老人,他身上穿著年輕時穿的外套,頭上戴著氈帽。他是鐵匠的父親,是十幾個獲準住在莊園領取養老金的老人之一。這些老人可以象莊園主一樣隨意在莊園里走動。這是溫斯亞特莊園八十多年來相沿成習的規矩,至今如此。[2]225
查爾斯看到一個鐵匠、兩個木工正在打發一天的時間。第四個人是一個長者,他仍然穿著年輕時的罩衫,戴著古老的小帽子。敘述者以特有的方式進行表達:英國大房子的主人喜歡勤奮勞作的農民,就像喜歡被精心照料的田地和牲畜一樣。
事實上,這個時代的農村不公正和貧困并沒有影響到溫斯亞特這樣的地方,但這些莊園主對員工的相對善意“可能只是他們追求家業興旺過程中的副產品”[2]226。對溫斯亞特的工人的介紹范圍很廣,他們順利地融入到視覺風格化的全景中。將英國社會的上層階級作為一種田園風光的消費者置于社會之中,一個侵入性的、諷刺性的敘述者的出現加強了這種表述。
三、田園中的景觀
田園中的景觀表述是《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的又一特色。景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世紀,這個時期的地主們在外出時看到克勞德的畫作時,學會了新的觀察方式,并回到英國在自己的莊園中創造這樣的前景。如威廉·肯特或蘭斯洛特·布朗,他們受雇于富有的莊園主來實現他們所期望的美學效果,在克勞德或普桑的藝術傳統中是“自然的”和阿卡迪亞的。在那之前,正式的花園都是在法國、意大利和荷蘭的影響下建成的,所以在景觀園林的歷史上,這是一個重要的品位轉變。烏維代爾爵士(1747—1829)在19世紀初影響了許多景觀設計師,他希望景觀要像著名藝術家的畫作那樣美麗。他寫道,場景應該是“如詩如畫”的,這個詞用來指的是“已經或可能在繪畫中得到良好效果的每一個物體和每一種風景”[8]。場景中的物體應該具有基本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些物體的紋理應該具有粗糙度和不規則性。
在《鄉村與城市》中,雷蒙德·威廉姆斯強調,18世紀的地主是一個有自我意識的業主。該世紀的景觀設計革命推動了“令人愉快的前景”這一概念的提出,這種景色從大窗戶、露臺和草坪等高處可以看到,并且隱含著一種控制和命令的表達。這種強調從一個遠處的、可控制的有利位置進行占有的做法,就是威廉姆斯所說的“占有的分離”[9]126。景觀園藝中創造令人愉悅的前景,意味著景觀園藝師、詩人、畫家和地主獲得了支持,并被賦予了抽象的審美。在與自然的關系中,重點都在視覺感知上,而視覺感知必須符合一種文化理想(風景被組織成美麗的圖片)。然而,人類與自然本身有一種距離。顯然,18世紀的莊園主和風景園林師并不厭惡綠色,但這是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中,自然只能從遠處看到,而且只有在它呈現出令人滿意的面貌時才能看到。
到了1867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的場景,英國景觀園藝的偉大革命已經成為鄉村的固定資產。當查爾斯沿著車道向他叔叔的房子走去時,他觀察到了田園風光“宜人的前景”和迷人的農民。然而,《法國中尉的女人》并不是一部19世紀的小說,這部1969年作品的作者被給予了更多的理論勇氣,因而不是簡單而不自覺地向讀者展示另一種牧歌式的田園詩。正如威廉姆斯所爭辯的那樣,這種對自然和那些從事自然工作的人的強調在任何時候都具有視覺上的魅力,是一種在控制土地及其前景方面的一種微妙的剝削[9]126。大房子的奶油色和灰色被其周圍的雪松所包圍,并以威爾特郡的山地為背景;各種各樣的農民心滿意足地在車道邊上磨蹭著;所有這一切都優美如畫。然而,這種自覺的觀察模式,必須從根本上將福爾斯本人以及他代表的整個階級分離出來。查爾斯看到了一幅美麗的圖畫,但他是作為一個牧民的消費者,而不是作為一個對農村生活有洞察力的觀察者。敘述者在他的旅程中插話說:“今天那種‘明智’的現代管理的目的可能也不會是為了對他人有利。不同之處在于,過去那些善良的剝削者追求的是‘家業興旺’,而今天這些善良的剝削者追求的是‘高生產率’。”[2]226與讀者可能期待簡·奧斯汀所展開的田園風光不同,福爾斯的后馬克思主義智慧在文本中體現在辨別阿卡迪亞全景下的經濟關系上。
根據馬里內利的說法,田園詩的最大特點在于它是一個理想的或至少是比較純潔的世界被感到失落時寫的,但又不至于完全摧毀對它的記憶,讓人對它產生懷疑,使得現在的現實和過去的完美之間產生想象性的交際[10]。
四、田園中的樹林
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查爾斯在一個清晨走過萊姆·雷吉斯旁邊的一叢樹林。樹冠被描述為藏有“無限”的陰影,枝繁葉茂,半遮半掩,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暗示性、不可預測性。“我一直厭惡平坦和缺少樹木的鄉村。那里的時間似乎是主宰,它像時鐘一樣無情地跳動。但樹木扭曲了時間,或者說創造了各種不同的時間:這里密集而突兀,那里平靜而蜿蜒……”11]7。
福爾斯說,不是時間被樹所改變,而是人的經驗被樹所改變。作為“流動”的時間確實是人的經驗,而梭羅說時間被他周圍的森林賦予了搖曳和陰影的復雜性。這位偉大的美國自然作家預示了福爾斯的信念,即神秘對人類生活的生命力,以及它在野生自然中的體現。在接受采訪時,福爾斯說:“我對小說研究的唯一持續興趣是我自己的自然史(和行為主義)。作為一個作家,我自己是一只小白鼠。”[5]72他在《樹》中又說:“我從來沒有嘗到在孤立的發現的經驗之外的任何滋味——就真正的地理探索而言,為了適當利用的發現。我對自然(和人類)史的許多分支都有所涉獵,但對任何一個分支都不了解。除此之外,無數的其他事物也是如此。我喜歡的是一種游蕩在森林中的熟人,僅此而已。我是一個業余愛好者,而不是一個演奏家;總是在綠色的混亂中,而不是在印刷的地圖上。”[11]57
伴隨著對神秘的欣賞,對發現的欣賞,福爾斯重視自然界的神秘性,也重視對這種神秘性的體驗性發掘。
五、結語
福爾斯的一生總是尋找機會遠離城市,作為一個業余田野自然主義者或作為一個華茲華斯般的自然愛好者,他曾到希臘、法國、斯堪的納維亞、美國、英格蘭的鄉村生活。“福爾斯的自然書寫既是其本人熱愛自然的情感表達,也是對英國田園文學傳統的傳承”[12]。福爾斯常年與自然為伴,常年經受自然的浸潤,這激發了福爾斯對自然的無限熱愛,成就了他小說中的田園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