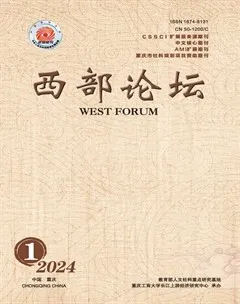數字普惠金融、勞動力流動與縣域經濟發展



摘要: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緩解金融排斥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并能夠通過增強縣域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和潛力促進勞動力的凈流入,從而提高縣域經濟發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個縣域的非平衡面板數據,分別以人均GDP、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勞動力凈流入率衡量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勞動力流動,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顯著促進了縣域經濟發展,且數字普惠金融3個維度的發展均具有縣域經濟發展促進效應,其中覆蓋廣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數字化程度提高的促進作用依次遞增;數字普惠金融對中西部地區縣域和貧困縣經濟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親貧性,有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促進勞動力流動的路徑來推動縣域經濟發展。應積極推進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尤其要加快欠發達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并統籌制定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政策和勞動力流動引導政策,通過要素流動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勞動力流動;縣域經濟;金融排斥;長尾效應
中圖分類號:F294.27;F83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24)0-0018-14
引用格式:梁桂保,張利杰,劉葵容.數字普惠金融、勞動力流動與縣域經濟發展[J].西部論壇,2024,34(1):18-31.
LIANG Gui-bao,ZHANG Li-jie,LIU Kui-ro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labor mobility and county economic growth[J]. West Forum, 2024, 34(1): 18-31.
一、引言
縣域經濟是指在縣級行政區劃的地域內,以城鎮為中心、以農村為基礎、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開發和利用各種經濟社會資源而形成的功能較為完備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綜合性區域經濟系統。縣域經濟不僅是國民經濟的基本單元,而且是聯結城鄉發展的橋梁和紐帶,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據基礎性地位,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鄉村振興具有重要影響。然而,目前我國縣域的產業發展基礎相對薄弱,經濟能級總體較低。同時,城市化的持續推進使得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資源要素進一步向大城市集聚,縣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受到基礎設施不完善、資金和金融服務不足、勞動力流失等多方面的約束(杜鑫,2022)[1]。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數字經濟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動能。其中,數字信息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催生并推動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數字普惠金融以向社會各主體提供機會平等、成本可負擔的金融服務為重要目標,能夠突破地理限制,擴大金融服務范圍,降低金融服務門檻,提高金融服務的可得性(郭峰 等,2020)[2],可以彌補傳統金融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排斥的缺陷,有利于縣域經濟發展。因此,深入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其機制,有助于進一步充分利用數字普惠金融的積極功效來有效促進縣域經濟發展。
作為國民經濟的血脈,金融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廣泛關注。盡管傳統金融的發展可以通過加速資金回流、推動產業發展、帶動創新創業等路徑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劉沖 等,2019;康繼軍 等,2020;張珩 等,2021)[3-5],但傳統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在實踐中存在諸多局限。一方面,基于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傳統金融機構的空間布局存在非均衡性,縣域金融機構的網點密度普遍低于城市,導致縣域金融服務供給不足,難以滿足縣域經濟主體的金融需求(尹振濤 等,2016)[6]。另一方面,基于風險控制的要求,傳統金融服務的門檻較高,且審批嚴格,對欠發達地區和弱勢群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排斥(康繼軍 等,2020)[4],削弱了金融服務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姚梅潔 等,2017)[7]。總之,由于縣域經濟能級偏低,企業的規模普遍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與金融機構的客戶需求和偏好存在一定差距,降低了傳統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動性及實際效果(周孟亮 等,2023)[8]。而數字普惠金融不同于傳統金融,其利用區塊鏈、大數據等數字信息技術開展各種金融服務(Gomber et al.,2017)[9],具有廣覆蓋、低門檻、高效率等諸多優勢,彌補了傳統金融的不足,從而可以更好地促進縣域經濟發展。
隨著數字金融的持續發展,關于數字(普惠)金融與區域經濟之間關系的研究也不斷深化。國內相關實證檢驗的結論大多支持數字金融可以顯著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觀點,然而已有文獻的經驗分析大多基于省級區域層面,較少從城市和縣域層面進行驗證。由于省級區域的地域范圍較大,且省內的地區差異明顯,僅從省域層面進行研究不利于全面細致地把握數字金融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及其機制。粟麟等(2022)分析表明,數字金融顯著促進了縣域經濟發展,該作用對西部縣域、貧困縣域、金融排斥較強縣域更強,數字金融可以通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來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提高資本配置和產出效率能夠強化數字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10]。汪雯羽和貝多廣(2022)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顯著促進了縣域經濟增長,政府干預對該影響具有調節作用,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完善傳統金融市場結構來促進縣域經濟增長[11]。潘啟娣(2023)分析認為,數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縣域經濟增長,并主要通過提高農業技術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三條路徑促進縣域經濟發展[12]。劉鑫和韓青(2023)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進縣域經濟增長,并可以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來促進縣域經濟增長,傳統金融效率提高可以強化數字普惠金融對縣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13]。
總體來看,雖然已有學者關注到數字普惠金融與縣域經濟發展的關系,但相比省域層面的研究,縣域層面的經驗分析較少,而金融排斥更多地體現在縣域層面,縣域經濟發展獲取金融支持的難度更大(粟芳 等,2016)[14]。因此,有必要加強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研究。同時,從作用機制來看,已有文獻探討了數字(普惠)金融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拉動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改善營商環境、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彌補傳統金融服務缺陷、增進資本積累、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及地區創業等來影響區域經濟發展(增長)的路徑(王儒奇 等,2023;尹少華 等,2023;魯釗陽 等,2023;王文姬 等 2023;張蕊 等,2021;宇超逸 等,2020;錢海章 等,2020;齊美東 等,2023;張賀,2021)[15-23],但缺少基于要素流動視角的機制研究。盡管有研究論及了數字(普惠)金融對資源要素配置的影響(王儒奇 等,2023;徐偉呈 等,2022)[15][24],但還未涉及要素流動層面,且更多的是討論資本要素的配置和積累(粟麟 等,2022;宇超逸 等,2020;齊美東 等;2023)[10][20][22],鮮見針對勞動力要素的探討,僅有徐偉呈等(2022)考察了數字金融通過促進勞動力分工影響區域高質量經濟增長的機制[24]。一方面,地區間的要素流動是促進結構紅利釋放的重要方式(王振華 等,2019)[25],合理的勞動力流動能夠有效提高勞動力配置效率(王婷 等,2020)[26],并對勞動力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會改變本地的生產和生活條件,進而影響勞動力的流入和流出。因此,有必要從勞動力流動的角度來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機制。基于上述考慮,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以縣域為研究對象,從勞動力流動視角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機制,以深化和拓展數字普惠金融的經濟效應研究,并為充分發揮數字普惠金融的積極作用,促進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經驗借鑒和路徑啟示。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1.數字普惠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數字普惠金融是現代信息技術與金融系統融合發展的產物,能夠彌補傳統金融的不足,有效緩解傳統金融因信息不對稱等問題造成的融資難、成本高等問題,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同時,數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低成本、廣覆蓋等特點,可以顯著緩解傳統金融存在的金融排斥,促使弱勢群體有更多機會獲取更便捷的金融服務,從而促進地區的投資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具體來講,數字普惠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數字普惠金融利用數字技術降低了金融服務門檻,拓展了長尾客戶群體。作為支撐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主體,中小企業的持續發展是促進縣域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重要基礎。但是,在傳統金融體系下,資本量和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中小企業等縣域經濟主體通常會面臨比大型企業和城市經濟主體更為嚴重的融資約束,而且獲取金融服務的成本往往也較高,導致縣域經濟發展受到較大制約。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手段降低金融機構的信息獲取成本(謝獲寶 等,2022)[27],還能通過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優化存貸服務流程、簡化支付方式等途徑降低交易成本(邢趙婷 等,2023)[28]。金融服務門檻和成本的降低使金融主體更有動力和可能拓展以低收入群體、小微企業為代表的長尾客戶,有利于緩解縣域經濟主體的融資約束,進而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第二,數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擴大金融服務范圍,增加縣域金融資源的有效供給。以線上模式為主的數字普惠金融突破了傳統金融的地域限制,能夠實現金融服務廣覆蓋,有效彌補因金融機構物理網點密度小引致的縣域金融服務有效供給不足(傅秋子 等,2018)[29],從而顯著增加縣域金融資源供給。同時,金融資源與勞動要素和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可以有效促進縣域生產力增長,釋放縣域結構紅利(王振華 等,2019)[25],推動縣域經濟發展。因此,作為一種緩解縣域經濟主體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有效手段,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助于推動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1: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縣域經濟發展。
由于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以及金融排斥程度各異,數字普惠金融對不同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能存在明顯差異。宇超逸等(2020)、何宜慶和王茂川(2021)分析認為,數字金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效果在欠發達地區更為顯著[20][30];方先明等(2022)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經濟增長效應在金融排斥效應越強的地區越顯著[31];陳嘯等(2023)分析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較強[32];粟麟等(2022)的研究也表明,數字金融對西部地區縣域、貧困縣域、金融排斥較強縣域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果較強[10]。與傳統金融相比,數字普惠金融的主要優勢在于其“長尾效應”,即通過減少交易成本和提高金融服務可達性,將被傳統金融機構排斥在外的客戶群體納入服務范圍,促進縣域金融業務的增長。因此,數字普惠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關鍵在于將金融服務范圍延伸至更多的縣域中小客戶,滿足被傳統金融長期排斥在外的長尾群體的金融需求,從而有效發揮其普惠效應。相比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在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金融資源的集聚水平總體上相對較低(江紅莉 等,2023)[33],金融排斥更加嚴重(粟芳 等,2016)[14],金融需求得不到充分滿足的情況更為普遍,此時數字普惠金融可以產生更強的“長尾效應”,從而對縣域經濟發展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2:相對于東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2.勞動力流動的中介作用
一般來講,勞動力流入有利于本地的經濟發展,而勞動力流出對本地經濟發展具有抑制作用。長期以來,人口外流帶來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過度流失問題嚴重阻礙了縣域產業轉型升級及經濟發展的進程(張杰 等,2019)[34]。以青壯年為主的勞動力外流,導致農村老齡化和空心化現象日趨嚴重,鄉村振興缺乏中堅力量支撐(彭長生 等,2019;陸杰華 等,2021)[35-36]。勞動力回流則會對縣域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第一,勞動力回流會產生聚集效應,不僅能夠增加縣域勞動力總量,也會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第二,回流勞動力不僅可為當地產業發展提供勞動力、資金和技術支持,還會成為重要的消費群體,進而引發產業聚集和消費拉動效應;第三,高技能勞動力回流,除其自身對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外,還會產生技術和知識溢出效應,從而形成乘數效應;第四,返鄉勞動力中以創業為目的的主動回流會直接帶動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可見,勞動力回流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人口老齡化、智力流失和發展活力不足等問題,有效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本文用“勞動力流動”指代縣域勞動力的凈流入,勞動力流動增長是指縣域勞動力流入的增加或勞動力流出的減少。因此,如果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具有顯著促進勞動力流動增長的作用,則促進勞動力流動成為其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一條有效路徑。
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降低了金融服務的獲取門檻和成本,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和發展機會(謝絢麗 等,2018;楊佳 等,2022;熊德平 等,2022)[37-39],這不但有助于吸納本地勞動力以減少勞動力流出,還能吸引勞動力回流和外地勞動力流入。人口遷移是遷移者在成本與收益比較基礎上做出的理性決策,推拉理論認為,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可以分為推力和拉力。從推力來看,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可以減小對勞動力流出的推力,從而降低勞動力流出規模。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提供低成本和便利的融資渠道,有助于提高本地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水平,減少勞動力外流的動機;另一方面,大數據技術和智能風控模型的開發應用,可以幫助金融機構更加精準地評估項目風險,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以及貸款項目質量,使勞動力獲得更穩定可靠的就業和發展機會,降低失業風險。從拉力來看,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可以加大對勞動力流入的拉力,從而擴大勞動力流入規模。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可以拓寬當地創業者和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增加投資和就業機會,吸引更多勞動力流入。對個人和家庭而言,數字普惠金融包含理財、保險等多樣化的金融服務,提供了更豐富的投資渠道,有利于居民投資性收入的增加;與此同時,數字化支付等服務的應用增強了縣域居民生活的便捷性。縣域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的增加、生活品質的提高均有利于增強對勞動力流入的拉力。此外,我國縣域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文化資源和旅游資源,發展潛力巨大,數字普惠金融為縣域發展提供了更多的資金支持,有利于盤活存量資源,釋放縣域發展紅利(方君娟,2022)[40],進一步增強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3: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可以通過促進勞動力流動來提高縣域經濟發展水平。
三、實證檢驗設計
1.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為檢驗縣域數字普惠金融水平提高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基準模型:
pgdpit=α0+α1indexit+α2XCONit+μi+λt+εit
其中,i表示縣域,t表示年度,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λ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被解釋變量(pgdp)為“經濟發展水平”,采用縣域人均GDP來衡量,該指標能真實準確地反映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李彥龍 等,2022)[41]。核心解釋變量(index)為“數字普惠金融”,采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縣域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衡量(進行除以100處理),該指標涵蓋了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3個維度和33個具體指標,能夠科學全面地反映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水平。參考潘啟娣(2023)等的研究[12],選取以下控制變量(XCON):一是“收入水平”,采用縣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衡量,用以反映縣域居民的消費能力;二是“財政依存度”,采用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用以反映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支持程度;三是“產業結構”,采用縣域第二、三產業生產總值之和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四是“金融發展水平”,采用縣域年末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
為檢驗勞動力流動在數字普惠金融影響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中介作用,參照溫忠麟等(2022)和程方方等(2013)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42-43],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migit=β0+β1indexit+β2XCONit+μi+λt+εit
pgdpit=η0+η1indexit+η2migit+η3XCONit+μi+λt+εit
其中,中介變量(mig)為“勞動力流動”,采用縣域勞動力凈流入率來衡量。參考段平忠(2013)和史桂芬(2020)等的研究[44-45],假定90%的遷移人口為能夠參與勞動的適齡人口,則勞動力凈流入率為“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之差乘以90%再除以戶籍人口”,勞動力凈流入率大于零的縣域為勞動力凈流入地,小于零的縣域為勞動力凈流出地。
2.樣本選擇與數據處理
本文以我國縣域為研究樣本,由于縣域層面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從2014年才開始統計,以2014—2020年為樣本期間。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自《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0年)》,縣域宏觀經濟數據來自《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縣市卷)》和各省(區、市)統計年鑒。剔除關鍵變量缺失的縣域樣本,使用插值法對個別缺失數據進行補充,最終獲得1 754個縣(市、區、旗)的面板數據。由于控制變量及工具變量的數據存在部分缺失,人工剔除不但會損失樣本容量,還可能破壞樣本的隨機性,因而采用非平衡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王珂英 等,2016)[46],這也是實證檢驗中樣本量發生變化的原因。
本文運用Stata 17.0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進一步分析變量間的相關性(限于篇幅,具體結果略,備索),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與控制變量“人均收入水平”的相關系數最高(0.658),相關系數的絕對值均在0.8以內,表明變量間的獨立性和可區分性在可接受范圍內;主要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分析結果顯示(見表2),最大的VIF值僅為1.94,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四、實證檢驗結果分析
1.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本文采用F檢驗與豪斯曼檢驗進行模型篩選,結果顯示:F檢驗統計量為50.40(Prob>F=0.000 0),表明個體效應顯著,拒絕使用混合效應模型;Hausman檢驗統計量為616.67(Prob>chi2=0.000 0),拒絕使用隨機效應模型。因此,本文將采用同時控制年份效應和縣域效應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基準模型的回歸結果見表3。(1)列未加入控制變量,(2)列加入控制變量,“數字普惠金融”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顯著促進了縣域經濟發展,本文提出的假說H1得到驗證。
進一步分別檢驗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三個子維度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3的(3)(4)(5)列。“覆蓋廣度”“使用深度”“數字化程度”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數字普惠金融三個維度的發展均能有效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從系數的顯著性和大小來看,“覆蓋廣度”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數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明顯大于“覆蓋廣度”的系數,“數字化程度”的系數又大于“使用深度”的系數,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數字化程度提高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大,使用深度加深的促進作用次之,覆蓋廣度拓展的促進作用最小,這與范曉莉(2023)的研究結論相一致[47]。其中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拓展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較小的原因可能在于,該維度的評價指標主要基于支付寶的賬號、用戶及使用情況,而支付寶的使用者主要是個人,未能全面反映數字普惠金融的推廣狀況。
2.內生性處理與穩健性檢驗
一方面,縣域經濟的發展會提高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促進理財、投資等金融活動,從而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另一方面,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因素眾多,回歸模型難免存在遺漏變量問題。為緩解由于反向因果關系、遺漏變量等引發的模型估計偏誤,采用工具變量法來處理內生性問題。參考郭峰等(2017)、黃群慧等(2019)、田杰等(2021)的方法[48-50],選取兩個工具變量:一是“數字普惠金融”的滯后1期項(“L1.數字普惠金融”),前一年的數字普惠金融水平不會受到當年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可以排除反向因果關系的影響。二是樣本縣域到杭州球面距離與上一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交互項(“距杭州距離×L1.數字普惠金融”)。再借鑒陳詩一和陳登科(2018)和劉松濤等(2023)的做法[51-52],將兩個工具變量同時納入模型,采用2SLS法的回歸結果見表4的Panel A。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顯示,兩個工具變量對“數字普惠金融”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且F檢驗值遠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表明,在緩解內生性問題后,數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依然對縣域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進一步進行以下穩健性檢驗:一是替換被解釋變量。考慮到夜間燈光亮度與經濟發展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Chen et al.,2011;Hendersno et al.,2012)[53-54],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GDP數據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及受地區間價格因素干擾等問題,參照李彥龍和沈艷(2022)的研究[41],使用VIIRS燈光亮度DN的總值除以柵格數得到縣域平均燈光亮度(“夜間燈光亮度”,數據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將其作為被解釋變量重新進行模型檢驗。二是增加控制變量,在模型中加入“消費水平”變量。三是對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上述檢驗結果見表4的Panel B,“數字普惠金融”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本文基準模型的分析結果是穩健的。
3.區域異質性分析
為驗證數字普惠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否存在區域異質性,將樣本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兩組 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吉林、黑龍江、遼寧;中西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分別進行模型檢驗,回歸結果見表5的(1)(2)列。“數字普惠金融”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無論是在東部地區還是在中西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提高都可以顯著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從系數大小來看,“中西部地區”組明顯大于“東部地區”組,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的縣域經濟發展促進效應在中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更為顯著,本文提出的假說H2得到驗證。進一步比較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在樣本期間的縣域平均發展水平(見表6),可以發現,中西部地區縣域雖然發展基礎較差(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勞動力凈流入率、人均GDP均小于東部地區),但發展速度較快,與東部地區的差距趨于縮小,表明欠發達地區較大的發展空間有助于數字普惠金融以較低成本激發“長尾效應”,從而對縣域經濟發展具有更大的促進效應。再根據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在2014年發布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名單將樣本劃分為“非貧困縣”和“貧困縣”兩組,分別進行模型檢驗,回歸結果見表5的(3)(4)列。“數字普惠金融”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貧困縣”組的系數明顯大于“非貧困縣”組,再次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親貧性,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
4.中介效應檢驗
中介效應模型的檢驗結果見表7,為避免內生性干擾,同時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勞動力流動”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顯著促進了縣域勞動力凈流入率的提高;“勞動力流動”對“經濟發展水平”的估計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縣域勞動力凈流入率的提高有利于縣域人均GDP的增長。可見,勞動力流動在數字普惠金融促進縣域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顯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可以通過促進勞動力流動來提升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說H3得到驗證。
五、結論與啟示
在傳統金融體系下,較為嚴重的金融排斥制約了縣域經濟的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對現代數字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夠顯著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和成本,從而可以通過長尾效應緩解傳統金融中的金融排斥,有效促進縣域經濟發展。與此同時,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就業和發展機會,并有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強了縣域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和潛力,不僅可以減少本地勞動力的流出,還能吸引勞動力回流和外地勞動力流入,而勞動力流出的減少和流入的增加均有利于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本文采用2014—2020年1 754個縣域的數據分析表明:(1)縣域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縣域人均GDP增長,數字普惠金融的數字化程度提高、使用深度加深、覆蓋廣度拓展均可以顯著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但三者的促進作用依次遞減;(2)數字普惠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表現為對中西部地區縣域和貧困縣經濟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反映出數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親貧性,有利于區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3)勞動力流動在數字普惠金融影響縣域經濟發展中具有顯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促進勞動力流動來推動縣域經濟發展。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得到以下啟示:第一,加快傳統金融的數字化轉型,促進縣域數字普惠金融進一步發展。金融業應準確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新趨勢,積極推進傳統金融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增加金融服務產品種類,拓寬金融融資渠道,不斷提高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深度和廣度,破解金融服務難以觸達的“最后一公里”難題,從而更好地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第二,打破地域限制,兼顧效率與公平,加快欠發達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速度,不斷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繼續推進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緩解區域間金融、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第三,統籌制定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政策和勞動力流動引導政策,暢通勞動力與資本要素的流動渠道。充分利用數字普惠金融促進勞動力流動的作用,不斷提高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吸引人才回流,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為縣域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1]杜鑫.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基于2020年全國10省份農戶調查數據的經驗研究[J].經濟問題,2022(3):104-115.
[2]郭峰,王靖一,王芳,等. 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征[J].經濟學(季刊),2020,19(4):1401-1418.
[3]劉沖,劉晨冉,孫騰.交通基礎設施、金融約束與縣域產業發展——基于“國道主干線系統”自然實驗的證據[J].管理世界,2019,35(7):78-88+203.
[4]康繼軍,楊琰軍,傅蘊英,等.轉型期中國金融排斥困境及其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基于中國2574個縣(市)數據的空間分析[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6(6):44-57.
[5]張珩,羅博文,程名望,等. “賜福”抑或“詛咒”:農信社發展對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J].中國農村經濟,2021(3):86-105.
[6]尹振濤,舒凱彤.我國普惠金融發展的模式、問題與對策[J].經濟縱橫,2016(1):103-107.
[7]姚梅潔,康繼軍,華瑩.金融排斥對中國縣域經濟影響研究:實現路徑與動態特征[J].財經研究,2017,43(8):96-108.
[8]周孟亮,王立聰.數字金融對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脆弱性的影響研究[J].財經論叢,2023(7):46-57.
[9]GOMBER P,KOCH J A,SIERING M. Digital finance and fin tech: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7,87(2):537-580.
[10]粟麟,何澤軍,楊偉明.數字金融與縣域經濟發展:影響機制與異質性研究[J].財經論叢,2022(9):59-68.
[11]汪雯羽,貝多廣.數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預與縣域經濟增長——基于門限面板回歸的實證分析[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2,42(2):41-53.
[12]潘啟娣.數字普惠金融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J].新金融,2023(2):46-55.
[13]劉鑫,韓青.數字普惠金融對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基于傳統金融和產業結構升級視角[J].中國流通經濟,2023,37(4):107-115.
[14]粟芳,方蕾.中國農村金融排斥的區域差異:供給不足還是需求不足?——銀行、保險和互聯網金融的比較分析[J].管理世界,2016(9):70-83.
[15]王儒奇,陶士貴.數字金融能否賦能實體經濟發展:機制分析與中國經驗[J].當代經濟管理,2023,45(7):71-82.
[16]尹少華,羅漢祥.數字金融、技術創新與區域經濟增長[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23(1):41-49.
[17]魯釗陽,杜雨潼,鄧琳鈺.數字普惠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J].財會月刊,2023,44(23):128-134.
[18]王文姬,夏杰長.數字金融、居民消費與地區經濟增長[J].求索,2023(4):96-105.
[19]張蕊,余進韜.數字金融、營商環境與經濟增長[J].現代經濟探討,2021(7):1-9.
[20]宇超逸,王雪標,孫光林.數字金融與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內在機制與經驗證據[J].經濟問題探索,2020(7):1-14.
[21]錢海章,陶云清,曹松威,等.中國數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與實證[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37(6):26-46
[22]齊美東,吳金科.數字普惠金融的實體經濟發展效應:異質性與作用機制[J].財會通訊,2023(13):84-90.
[23]張賀.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背景下數字普惠金融對我國西部經濟增長的影響[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38(5):55-62.
[24]徐偉呈,劉海瑞,范愛軍.數字金融如何驅動高質量經濟增長?——基于技術、資本和勞動力的三重內驅機制[J].投資研究,2022,41(4):113-133.
[25]王振華,孫學濤,李萌萌等.中國縣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基于結構紅利視角[J].軟科學,2019,33(8):68-72.
[26]王婷,程豪,王科斌.區域間勞動力流動、人口紅利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兼論新時代中國人口紅利轉型[J].人口研究,2020,44(2):18-32.
[27]謝獲寶,敬卓爾,惠麗麗.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資本結構優化[J].南方金融,2022(8):33-48.
[28]邢趙婷,鐘若愚.數字普惠金融、勞動力流動與產業結構優化——基于新經濟地理視角的實證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23(4):142-156.
[29]傅秋子,黃益平.數字金融對農村金融需求的異質性影響——來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證據[J].金融研究,2018(11):68-84.
[30]何宜慶,王茂川.數字普惠金融的非線性與異質性經濟增長效應——基于平滑轉換模型與分位數模型的實證研究[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8(1):54-64.
[31]方先明,劉韞爾,陳楚.數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來自我國省域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4(3):40-50+146-147.
[32]陳嘯,孫曉嬌,王國峰.數字普惠金融、數字創新與經濟增長——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考察[J].經濟問題,2023(6):34-40.
[33]江紅莉,蔣鵬程,黃丹曉.金融集聚、消費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J].宏觀質量研究,2023,11(1):27-37.
[34]張杰,張珂,趙峰.農業勞動力轉移性流失、耕地拋荒與“柔性”政策選擇研究[J].新疆社會科學,2019(6):131-140+159.
[35]彭長生,王全忠,鐘鈺.農地流轉率差異的演變及驅動因素研究——基于勞動力流動的視角[J].農業技術經濟,2019(3):49-62.
[36]陸杰華,劉芹.中國老齡社會新形態的特征、影響及其應對策略——基于“七普”數據的解讀[J].人口與經濟,2021(5):13-24.
[37]謝絢麗,沈艷,張皓星,等.數字金融能促進創業嗎?——來自中國的證據[J].經濟學(季刊),2018,17(4):1557-1580.
[38]楊佳,陸瑤,李紀珍,等.數字時代下普惠金融對創業的影響研究——來自中國家庭微觀調查的證據[J].管理科學學報,2022,25(11):43-68.
[39]熊德平,黃倩.數字普惠金融、農戶創業與多維相對貧困[J].東岳論叢,2022,43(9):38-48+191.
[40]方君娟.數字普惠金融對就業水平的影響效應研究[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22(10):75-79.
[41]李彥龍,沈艷.數字普惠金融與區域經濟不平衡[J].經濟學(季刊),2022,22(5):1805-1828.
[42]溫忠麟,方杰,謝晉艷,等.國內中介效應的方法學研究[J].心理科學進展,2022,30(8):1692-1702.
[43]程方方,孫曰瑤.數字產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差距:理論邏輯與實證檢驗[J].經濟體制改革,2023(4):61-69.
[44]段平忠.中國省際遷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異對經濟增長及地區差距的影響分析[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3(3):115-121.
[45]史桂芬,李真.人口流動助推地區經濟增長的機制研究——基于長三角城市群的面板數據[J].華東經濟管理,2020,34(6):10-18.
[46]王珂英,張鴻武.城鎮化與工業化對能源強度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截面相關和異質性回歸系數的非平衡面板數據模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6):122-129.
[47]范曉莉.數字金融發展、區域基礎設施與地區經濟增長——基于新經濟地理學視角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44(9):94-103.
[48]郭峰,孔濤,王靖一.互聯網金融空間集聚效應分析——來自互聯網金融發展指數的證據[J].國際金融研究,2017(8):75-85.
[49]黃群慧,余泳澤,張松林.互聯網發展與制造業生產率提升:內在機制與中國經驗[J].中國工業經濟,2019(8):5-23.
[50]田杰,譚秋云,陳一明.數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J].西部論壇,2021,31(4):82-96.
[51]陳詩一,陳登科.霧霾污染、政府治理與經濟高質量發展[J].經濟研究,2018,53(2):20-34.
[52]劉松濤,羅煒琳,梁穎欣.數字普惠金融與城市FDI流入——基于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的視角[J/OL].(2023-11-16).產業經濟評論, https://doi.org/10.19313/j.cnki.cn10-1223/f.20231116.001.
[53]CHEN X,NORDHAUS W D. Using luminosity data as a proxy for economic statistic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1,108(21):8589-8594.
[54]HENDERSON J V,STOREYGARD A,WEIL D N. Measur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outer spa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2):994-1028.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Labor Mobility and County Economic Growth
LIANG Gui-bao1,ZHANG Li-jie1, LIU Kui-rong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Chongq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50, China)
Abstract: As a bridge and link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economies, advanc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new countryside. However, constrain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he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ounties is weak, the overall economic capacity is low, and there is still a large space for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integration form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nc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DIF)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promoting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ED). Nevertheless, current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relatively few in number,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nd there is a lack of mechanism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mobility, which is yet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to carry out a more in-depth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counties from 2014 to 2020,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CED in China, and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after considering the night lighting data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ounty economy and endogenous problems. Furthermore,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F on CED.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coverage and depth of use, the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of DIF has a more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in poor counti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CED, reflecting the inclusive characteristics of DIF.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labor mobility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DIF and CED.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ands o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one hand, unlike existing studies that mostly take the provincial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unty level,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DIF and its sub-dimensions on CED,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based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geographical 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mobi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DIFs effect on CED and expands the previous path research from a brand-new perspective.
To a certain extent,our research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labor force as the most active and dynamic factor in all kinds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the influence of DFI on CED, which is helpful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labor mobility guidance meas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for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so a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labor mobility; county economy; financial exclusion; the long tail effect
CLC number:F294.27; F832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24)0-0018-14
(編輯:黃依潔;劉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