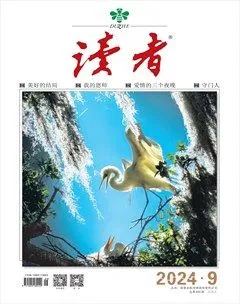文化在餐桌上延續
趙冬梅

我向一位德國的同行前輩感嘆,中國傳統文化在進入現代之際所遭遇的斷裂。他反駁說:“你說得不對。你看中國人的餐桌,文化就在那里延續。”我愣了一下,忽然有種“仿佛若有光”的感覺——他說得對。
相較于廟堂宮廷的歷史,日常飲食的歷史是最頑強堅韌,也是最具人民性的。營養的改善提升了人們的健康水平,改善了精神狀態;知識的拓展、觀念的轉移及商業營銷改變了食物的身價;餐桌上的禮儀奠定了一個人教養的基石,以及個體對社會秩序的最初認知;自幼熟習的配方和烹飪方式決定了我們衡量飲食優劣的標準。喬治·奧威爾曾說,日常飲食的變化可能比朝代更迭,甚至宗教變革來得更為重要。
直到今天,“炒菜”仍被視為中華飲食最具特色的烹飪技法,油煎快炒之法并非自古就有,而是起源于中古。要想“炒”起來,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要有鍋,能夠勝任炒菜的鍋,戰國時南方就已經出現了。第二要有油,魏晉時期,植物榨油技術有了較大發展。西晉張華的《博物志》中提到用麻油來制作豆豉。鍋里的油熱了,炒卻不會自然發生。要讓炒真正成為主流的烹飪技法,還需要第三個條件——燃料匱乏。“炒”是一種更為節能的烹飪技術,要想讓習慣了熬煮蒸烤的人改變烹飪方式——“炒”起來,還須等到燃料變得金貴,這恐怕是宋以后的事情了。形勢比人強,許多新技術的廣泛應用,都是形勢倒逼的結果。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味道一點一滴地豐富起來。從新石器時代開始,華夏先民就已經使用天然的霉菌和酵母制作曲和曲制品,這些曲制品包括醬、醬汁、腌肉、腌菜、酒和醋。梅子是天然的酸味來源。《左傳·昭公二十年》中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的記載,這是春秋時期的食譜,煮魚和肉用的調料有鹽、梅子、醬汁和醋。戰國乃至秦漢的隨葬品中常有梅子,這說明墓主人希望在另外一個世界里仍然能夠活得有滋有味。唐代以前,甜味的主要來源是蜂蜜和麥芽糖,曹丕得到從西方進口的蔗糖“石蜜”,便向東吳人炫耀說:“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乎?”甘蔗榨糖技術是唐朝從“西天”印度取來的“真經”。古代典籍中提到的“椒”多指花椒,長沙馬王堆漢墓就出土有西漢的花椒。漢魏時期,四川的蜀椒和甘肅、陜西的秦椒最為著名。胡椒大規模進入中國是在唐朝,宰相元載被抄家,“胡椒至八百石”,實在奢侈。辣椒則要到明末才進入中國,跟辣椒差不多是同時進來的,還有同樣產自新大陸的白薯、西紅柿和土豆。
飲食恒處于變化之中。人群的遷移,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異動,比如晉、宋皇室的南渡,以及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西遷,都將上層所主導的高雅飲食文化傳播到更廣闊的地域。上層的飲食追求與當地食材、食俗的結合,又會生發出新的驚艷滋味。中外飲食文化的交流,則將中國飲食帶往更遠的地方,也將遠方的滋味引入中國——多少我們自以為純粹的中國味道,其實是不同歷史時期的外來風物。人類的飲食和而不同,包容與開放才是美味之道。
(若 子摘自中信出版集團《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一書,宋 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