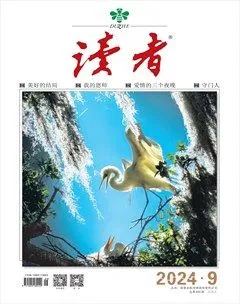一次哲學視角的日常審查
王小偉

為什么要從技術哲學的角度來追問我們的日常生活呢?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深度科技化的時代,技術已經沉降到生活的諸多方面。在這個時候去反思已成為日常生活現象的技術,就變得尤為重要。
我想跟大家探討3種技術現象:通勤、外賣和手機。
通勤:一種無意義的損耗
通勤對人的損耗是十分巨大的。首先,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在通勤當中變得非常微妙,擁擠和排隊會讓人產生敵對情緒。這個時候,群體不再是一種溫暖的存在,而是處于一種競爭狀態。
另外,通勤把行走變得特別單調。在通勤中,只有起點和終點是有意義的,而它的過程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損耗和我們需要去忍受的成本。
那我們就要追問,通勤是如何成為一種十分常見的生活現象的呢?一個回答是因為單位沒有宿舍,郊區的房租比較便宜,市中心的生活成本實在太高了。
但是,追問不能停在這個位置,我們要把它提升至哲學層面:在生存意義上,我們何以要忍受這樣的通勤呢?
有一位法國哲學家叫列斐伏爾,他提出了“日常批判”的概念。
列斐伏爾認為,要更好地理解現代社會中人的異化,就不應該再在馬克思所批評的工廠的語境里去觀察。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不是工廠時代,而是已經變成一個通盤的消費時代了。
城市的核心不是工廠,而是消費場所,所以現在,我們要把注意力從對工廠盤剝的批判,轉移到對日常消費生活的批判上去。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如果你去問一個工人什么叫通勤,他往往不知道答案,因為那時通勤并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北京的城市區域過去聚集著很多生產性勞動場所,它們旁邊通常會配套宿舍。宿舍不是商品化的,而是分配給職工的。所以那時,城市的核心是工廠和宿舍,它們沒有貨幣化。而今天,城市的核心是高檔消費場所,是各種繁華的商圈。
所有原來屬于生存領域沒有消費化的生存內容和生存空間,在整個城市變成消費櫥窗的情況下,就貨幣化了,成本變得特別高。大家會覺得消費這些東西就是過上好生活的指征,進而逐漸把自己的生活完全錨定在消費上,而忘了在消費之外,我們還有別的生活場景。
作為消費者,我可以每天出入這些場所;而作為真正的人,我準備回家時,就要走到城市的邊緣,或者前往郊區。
當然大家可能會說,我們今天的生存狀態不完全是列斐伏爾所批判的那種,只是有一些相似。現在的城市也在做一些對抗,我們有安置房、共有產權房、經濟適用房。這些實踐都在和城市作為消費空間的現實進行非常有力的對抗,要把生存領域繼續插入城市的中心,我想可能會慢慢地做得越來越好。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得記住,每天在擠地鐵的時候,要明白道路不僅是用來通勤的,不一定非要把生活和消費等同起來。通勤可以不是枯燥的成本,行走本身無須關注起點和終點,行走的過程也可以是一種生活。我覺得這個維度還是要保留的。
外賣:難吃,卻不得不吃
經過漫長的通勤,你到公司忙了一上午。到了中午,你最常說的一句話可能是“叫個外賣得了”。而你叫的外賣大概率是一個料理包。
外賣這么難吃,為什么大家還要吃呢?當然,生活性的解釋肯定是時間不夠,工作太忙了只能點外賣吃。但是,我們還是需要想一想,使吃外賣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方式的,那個最為一般的前提條件是什么?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關于技術的觀點,對我們理解外賣是有幫助的。他說,現代技術的本質不是一種工具,而是一種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是我們每個人都要承受的。
這種存在方式是把一切存在者都當作一種“持存”。什么叫“持存”呢?簡單地說,就是把持一個東西,然后任意地取舍、擺弄它——把每個存在者都看得無關緊要、沒有內在價值,認為這些存在者都是可以被隨意擺弄的。
我們可以通過水車和水電站來更好地理解“持存”這個概念。海德格爾認為,水車是一項技術,但它不是現代技術,是前現代技術。
水車這項技術沒有把河流持存化,盡管水車也把河流當作動力,但它不會改變河流的流向和生態。從遠處望去,河流仍然是富有詩意的存在。
但水電站的情況就大為不同了。水電站在給人類帶來便利的同時,會把河流上游的水位抬高,淹沒千頃良田,而且河流下游很多小的支流會斷流。
這時水電站就把河流完全變成一種可以隨意擺弄的東西,河流的詩意喪失了。河流被持存化了,變得什么也不是,只是推動渦輪機的動力。
在現代社會,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人的持存化。在現代技術的邏輯下,人被看作標準件,隨時都可以被替換。我們沒有內在的尊嚴和價值,吃東西就是為了別餓著,不斷地輸出勞動力。
與此同時,食物也變得持存化。既然人都無關緊要,食物也就不重要了。食物只是填飽肚子的營養物質。
當人和食物都變得無關緊要時,食物才會以外賣的形式出現。
只有你的母親看到你每天吃外賣時,才會覺得你不愛自己。
哲學家伯格曼把我們生活中的所有事物籠統地歸為兩類:一類叫焦點事物,另一類叫消費事物。
比如外賣就是消費事物,而焦點事物就是每個人應該投入巨大精力關注的事物,它需要我們進行關系性投入,而不僅僅是個人消費。
什么叫關系性投入呢?比如以前的家庭聚餐,桌子上的食物和外賣的區別不在于菜品,而在于為了做這一桌飯菜一定有人付出了很多辛勞,有人買菜、擇菜、洗菜、做飯。一家老少、親朋好友圍坐一桌,所以這張桌子上彌漫著濃郁的人情味。
人和人是通過特定的關系連接在一起的,這種關系性的投入是構成食物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這些情感因素在外賣中就完全被剔除了。
手機:蠶食一切身體性體驗
吃完外賣,忙了一下午,回到家中,你可能會遭遇第三種技術現象——手機。手機在帶來很多便利的同時,也束縛了我們。
伯格曼提出一個叫“裝置范式”的概念,我們可以套用這個概念來審視手機。伯格曼認為,現代技術和原來的技術之間是有巨大差異的,100年前技術的核心狀態是機器在工廠里轟鳴,而現代技術的特點是小巧化,將產品變成微小的裝置。
手機是一個典型的裝置范式,它是一個黑箱,把復雜的功能都隱藏在背后,排斥人對它的凝視。手機仿佛是一個幸福世界的開關,只要你滑動它的屏幕,所有的便利就會涌入你的現實生活。
有時候,我問我家的小朋友:“食物從哪里來?”他說:“食物是從冰箱里來的。”我又問他:“暖氣從哪兒來?”因為我經常用手機交取暖費,所以他說:“暖氣是從手機里來的。”
伯格曼認為,雖然手機這種裝置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便利,但它喪失了一個身體性的向度,割除了生活當中所有的操勞。他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我剛才說的用手機交取暖費和用壁爐取暖的區別。
用壁爐取暖是非常麻煩的。你要走進幽深的森林去選擇合適的樹,然后你需要劈砍、堆壘、曬干木材。
經過一天的勞作,你把壁爐引燃之后,坐在沙發上,妻子在旁邊織毛衣,孩子在地板上玩玩具,家貓蹲在旁邊取暖。看著爐子里的火,再看著外面漫天的白雪。在那個空間,人和人被連接起來,圍繞這個爐子,我們可以構建非常豐富溫馨的家庭情境。
但是,如果你用手機交取暖費,然后全家人一起坐在地板上玩手機,這個感覺就不對。肯定是哪里出了問題,似乎所有的幸福快樂都可以通過手機來購買和調度。
這會導致什么問題呢?最終手機將創造一個平行于我們現實生活的世界。人們因為在虛擬世界中不需要付出任何身體性的操勞就能獲得快感,從而逐漸對當下的現實生活失去耐心。人們會對虛擬世界越來越寬容,而對我們肉體存在的物理世界越來越苛刻。
手機還會和資本一起創造很多虛假的欲望,比方說,我每天關注線上購物平臺,就會覺得那些商品都是我應當擁有的,但是,它背后有人付出的操勞都和我無關。事實上,這些需求都是社交網絡渲染出來的虛假需求,它們本不屬于我們,但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煩惱。
技術在成為日常生活的同時,也在奪走我們的日常。通勤讓日常的行走消失,外賣讓好好吃飯消失,而手機讓身體性的體驗不斷地被蠶食。我們并沒有感受到技術帶來的便利背后的現代化承諾,仍然時常感到憤懣、焦慮和困惑。
奪回日常
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做的是奪回日常。以下是我嘗試奪回日常的實踐。
1.把城市看作一座雨林
列斐伏爾說,你可以把城市看作一件藝術品,藝術品不是消費品,它帶有超越性的維度。我想做得更徹底一點兒,把城市看作一座雨林。
我每天會花很多時間觀察綠化帶里的鮮花盛開,觀察單位樓下的野草生長,觀察街心公園里的鳥鳴蟲唱。觀察這座城市的細節,觀察城市在消費之外瘋長的部分,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治愈。
2.回到食物本身
回到食物本身,就是要“看到”味道,味道是有形狀、有模樣、有過程的。我嘗試種了一些薄荷,薄荷比較好養,而且葉片摘下來之后就可以泡薄荷水,加一點兒蜂蜜,味道非常好。
這時,你就能“看到”味道在陽光下逐日生長,然后將自己的生命同土地和植物重新連接起來。
3.為生活找到錨點
我們要重估操勞。身體性的付出和操勞可以是生活的錨點,而完全便利化的生活會讓我們無所適從。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每天接送孩子。接送孩子其實是很辛苦的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感覺自己因為對孩子的關注而建立了一種外部連接。在這種操勞的過程中,我生發出一種愛欲。我關注他者超過關注自己,我克服了自戀,這讓我變得沒有那么焦慮。
當然,奪回日常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回到過去,或者完全放棄現代技術。海德格爾的演講《泰然任之》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完全抵抗現代技術是愚蠢的,我們真正要具備的態度是,讓技術既在現實生活之中,又在精神世界之外,可以將其當作工具,但不讓它侵入作為人的根本。
不管是海德格爾,還是列斐伏爾,他們的理論對絕大部分人來說都是無關緊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從日常生活的細微處去改造自己的生活,這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勇氣。
(星 河摘自微信公眾號“一席”,本刊節選,Cyan Lin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