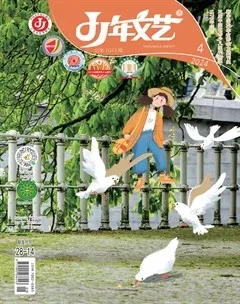養(yǎng)豬記
2024-04-29 08:27:05張學(xué)玲
少年文藝
2024年4期
張學(xué)玲

一
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在我們鄂西北農(nóng)村,家家戶戶都養(yǎng)豬。
我家常年養(yǎng)的是一頭老母豬。這頭老母豬體格健壯高大,特能吃。只要人一接近豬圈,它便哼哼起來,似乎在說“餓了餓了”。由于父母忙于地里的農(nóng)活,喂豬的活計,便落在年幼的我身上。
洗碗水、刷鍋水、剩飯菜,再加一瓢糠,就是豬的食物了。剛把豬食倒進豬槽,母豬便猛撲過來,“嗒嗒嗒”,風(fēng)卷殘云般一陣?yán)峭袒⒀剩劾锬屈c食物便已精光。然后,母豬抬起圓滾滾的頭,瞪著黑豆般的眼睛望向我,“哼哼哼”地叫個不停。我把瓢里的糠倒進豬槽,還沒來得及拿棍子攪和一下,母豬就迫不及待地“嗒嗒嗒”吞食,頭一拱一拱的,任憑我用和食棍怎么趕都趕不開。三下兩下,那點糠就被母豬吞進了肚里。接著,它又抬起頭,可憐巴巴地看著我,哼個不停,一副總是吃不飽的模樣。
“沒有了!”我愛莫能助地說,然后轉(zhuǎn)身離開。唉,就這點食物,怎么能填飽它那幾乎要拖到地上的大肚囊呢?
解決豬食匱乏的唯一辦法,就是割豬草。
每天放學(xué)后,我和村里幾個年齡相仿的女孩,都會結(jié)伴去割豬草。我們挎著竹筐,握著鐮刀,向田野里走去。藍瑩瑩的天幕下,一塊塊麥地、一壟壟紅薯秧里,夾雜著數(shù)不清的嫩油油的野草。豬最愛吃的有苜蓿、黑麥草、刺菜……我們彎著腰,頭不抬,手不停,飛速地把一棵棵豬草剜起來,放入竹筐里。天高地迥,清風(fēng)柔和,我們邊剜豬草邊說說笑笑,歡快的笑聲在四野飄蕩。同時,一種暗暗的較量,也在悄無聲息地進行,每個人都憋著一股勁兒,不時看看別人筐里的豬草,希望自己筐子里的草鼓得更高一些。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