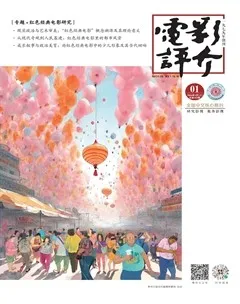融合修辭學(xué)視角下的《記憶》與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導(dǎo)演作品
于妲妮 謝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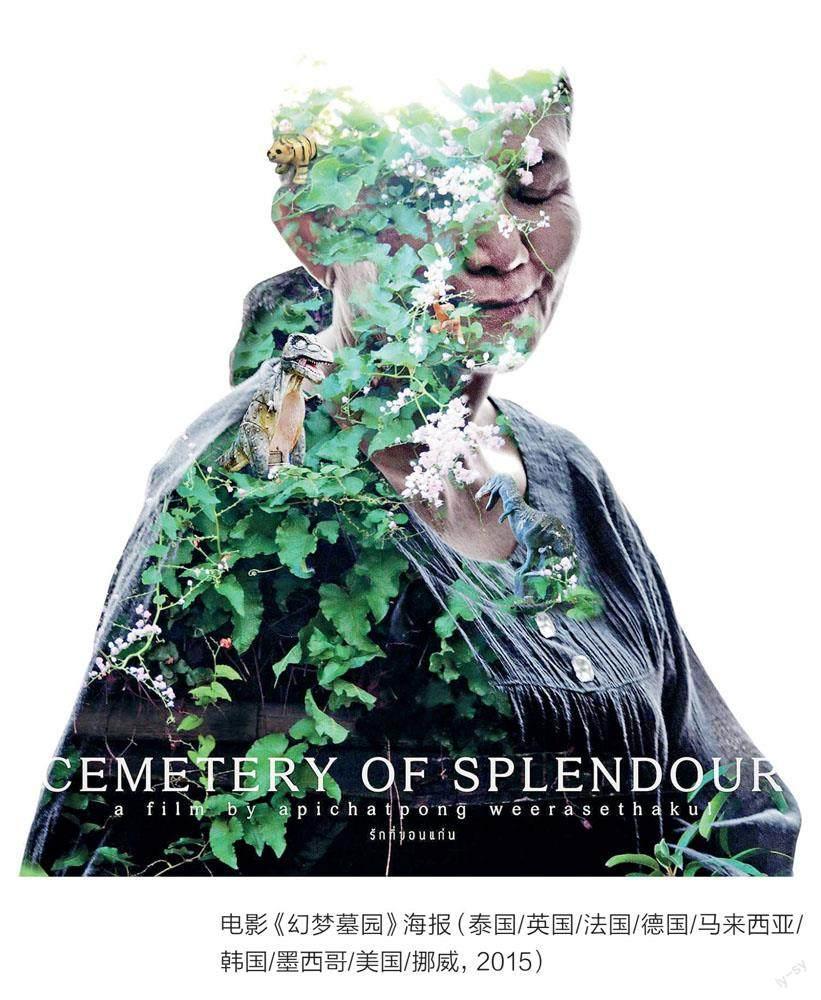

泰國導(dǎo)演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以下正文中簡稱為“阿彼察邦”)被譽(yù)為新一代亞洲電影大師,其電影作品獨(dú)具個人風(fēng)格,將光影、音效、長鏡頭融會貫通,往往以超長靜止鏡頭表現(xiàn)超然物外的主題,通過抽象夢境、記憶、前生今世等命題為觀眾帶來詩歌般的感性體驗。自長片處女作《正午顯影》(阿彼察邦,2000)被《電影評論》和《村聲周報》列為年度最佳電影之一以來[1],阿彼察邦憑借多部影片不斷獲得各大國際電影節(jié)青睞,在漫長的影視生涯中留下了許多具有獨(dú)特個人印記的作品。
2021年7月18日,阿彼察邦的新片《記憶》(2021)榮獲第74屆戛納國際電影節(jié)評審團(tuán)大獎。這部影片依然承襲阿彼察邦對于夢境與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偏好,同時打破了阿彼察邦自己的多項紀(jì)錄,除了使用專業(yè)演員、國際化團(tuán)隊,采用英語和西班牙語之外,《記憶》也是阿彼察邦從影20余年來第一次在泰國之外拍攝電影[2]。
2023年6月22日,《記憶》在中國內(nèi)地院線借助國家電影局大力推進(jìn)外國優(yōu)秀電影,助力我國電影行業(yè)迅速回暖的浪潮在國內(nèi)院線上映。盡管作為一部藝術(shù)電影,《記憶》很難在票房和話題上“出圈”,對比同期上映影片票房成績表現(xiàn)也并不盡如人意;但它卻是阿彼察邦的電影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商業(yè)院線與觀眾公開見面。本文將從融合修辭學(xué)視角出發(fā),探討《記憶》與阿彼察邦的其他電影作品。
一、視覺書寫中的隱藏世界與隱藏敘事者
電影《記憶》以實驗性的視聽手法講述一名旅居哥倫比亞的歐洲女性杰西卡,到波哥大看望生病的姐姐時意外被一聲突如其來的巨響所驚醒,并在這一神秘的聲響下失眠,進(jìn)而陷入一種似睡似醒的夢境狀態(tài)的故事。因為總是聽到奇怪的巨響,杰西卡試圖去找尋幻聽的根源,由此開始了一場由幻想與現(xiàn)實、偶遇與重逢組成的夢幻旅程。這部影片延續(xù)阿彼察邦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通過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來探究文化、文明的構(gòu)成。影片開始于杰西卡在幽暗的深夜被巨大的聲響驚醒,而觀眾同杰西卡一樣聽到這一神秘的聲音;從這里開始,影片就在敘事的視角上開始設(shè)置無法解答的謎題:巨響究竟來源于杰西卡的幻聽,抑或真實地發(fā)生和存在過?整個世界上還存在許多無法用科學(xué)解釋的超自然現(xiàn)象?為此,觀眾和杰西卡一起尋找聲音的來源,拜訪各色人物,傾聽他們對這一事件與世界本身的理解,卻遲遲未能得出答案。電影聲音是電影中傳達(dá)信息和情感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一般電影中,對話可以用來表現(xiàn)角色的互動和關(guān)系,同時也能揭示角色的性格和動機(jī);而獨(dú)白則更多地被用來表達(dá)角色的內(nèi)心世界和思考,或者用來交代電影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但與一般具有明確現(xiàn)實指涉性的電影影像不同,《記憶》中的聲音似乎更多在構(gòu)造不可被直接理解的謎團(tuán),體現(xiàn)為“異響”的聲音凸顯了夢境與現(xiàn)實間模糊不清的關(guān)系,不知為何突然鳴響又歸于沉寂的汽車、午夜時分被一聲神秘的巨響突然驚醒、熟悉的男人仿佛從未存在過一般忽然消失、無從旁證,在河邊又遇到同名的男人與之用幾乎譫妄的語言分享記憶等等,這些難以言喻的鏡頭畫面都在看似確定無疑的空間場景中制造出內(nèi)心的漩渦,每個角色平靜普通的外表下都暗藏玄機(jī)。
與在敘事便利和文化符號的意義上征用聲音的內(nèi)涵與外延、采取自然的表象按照心理的運(yùn)行順序重組并引起觀眾的情感的影片不同,《記憶》仿佛平靜的生活表面之下隱藏的一個巨大的記憶漩渦,夾雜著生活中各種超現(xiàn)實思考與想象的場景書寫出另一種“不可見”的現(xiàn)實,或是“表面現(xiàn)實”之下的“深層現(xiàn)實”。在這個層面上理解《記憶》,它的緩慢和曲折好像來源于另一個世界,它以此創(chuàng)造了一種通往記憶的媒介。在修辭敘事學(xué)派看來,電影或其他敘事系統(tǒng)在明顯可見的故事生產(chǎn)者、情景親歷者、敘事編碼者與權(quán)威建構(gòu)者之外還存在著一位不可見的“隱藏作者”,認(rèn)為這位不可見的“隱藏作者”在影片主創(chuàng)的創(chuàng)作、故事角色的行動、觀眾對文本意義的建構(gòu)和解讀外真正在作者、文本與受眾相互交流的敘事交流系統(tǒng)中起主導(dǎo)作用[3]。冥冥之中,杰西卡的神奇遭遇仿佛被不可知的隱藏作者所控制了,她在與村落男人埃爾南的交談中亦夢亦醒地追溯到最原初的記憶,忽然發(fā)現(xiàn)她曾經(jīng)在這間哥倫比亞的小屋中生活過,甚至還記得家具擺放的位置和生活的細(xì)節(jié);在探尋夢境的過程中,杰西卡進(jìn)入一間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阿涅斯邀請她戴上手套觸摸6000年前一位年輕女性的遺骸——杰西卡將手放在顱骨上輕輕觸摸;在稍后的鏡頭中,杰西卡在隧道中行駛的鏡頭與隧道內(nèi)考古施工考古人員發(fā)掘出更多骨頭的鏡頭被并置在一起,二者之間仿佛存在冥冥中的聯(lián)系。盡管這些動作都是杰西卡在絕對的主動位置上積極能動地完成的,一具被挖掘的遺骸并不會比她具備更多的能動性;但杰西卡并非“記憶”或另一個隱藏世界的開辟者,是隱藏的世界以敘事者身份主動找到了杰西卡,這強(qiáng)調(diào)了一種主體性的易位,完全失控的量子糾纏——聲音與記憶——操縱了杰西卡的主觀感知并促使她完成了精神向高維的躍遷。
阿彼察邦于哥倫比亞找到了現(xiàn)實世界與隱藏世界一體共存的異質(zhì)場域,讓數(shù)千年前的存在通過“遺骸”與“記憶”保留到了如今,考古學(xué)家找到的僅是物質(zhì)的遺留,杰西卡卻無意之中找到了精神交流的縫隙。通過超現(xiàn)實的重音在世界上留下的巨大裂痕,電影中的隱藏世界露出了冰山一角,并接納了整個《記憶》的世界,作為隱藏敘事者建構(gòu)起整個故事。由于電影是一門較為晚近的發(fā)明,電影研究的部分方法借鑒了文學(xué)的研究方法,電影敘事學(xué)的部分研究路徑也繼承并發(fā)展自文學(xué)敘事學(xué),因此也從文學(xué)的敘事學(xué)借鑒了諸多概念,例如“敘述者”“敘述行為”等。其中,電影中的敘事角色不同于文學(xué)作品中明顯可見,通過簡單文字描述勾勒出的“說書人”形象,而是依靠鏡頭和蒙太奇組織的視聽材料引導(dǎo)觀眾理解故事的綜合心理裝置。從某種程度上說,觀眾跟隨著這位不可見敘述者的視角進(jìn)入視覺建構(gòu)的綜合語境中,由此讓電影的終極意義在銀幕顯影[4]。這樣的裂痕無法通過一般意義上的諸如同情、尊重、關(guān)懷之類的情感來彌補(bǔ),只能通過記憶的恢復(fù)找尋;但正如一直生活在歐洲的杰西卡很難在一般意義上真正生活在哥倫比亞一樣,這里的“記憶”人們看到的并非以真實或虛構(gòu)來定義的歷史,而是情感虛無產(chǎn)生的真空記憶,所以它無限接近于人類精神景觀中超越個體視野的那些事物。這樣的電影書寫則創(chuàng)造了一種全新的寫作形式,“通過剪輯造就了一種由動態(tài)畫面和聲音構(gòu)成的藝術(shù)作品。……我的影片首先誕生于我的腦海中,然后死亡于劇本上;它又通過我所使用的活人和真實物品復(fù)活,然后又被殺死在膠片上,然而一旦被擺放在某種秩序中,被放映在銀幕上,則像水中的花朵躍然而生。”[5]在此,阿彼察邦的電影思想中體現(xiàn)出一種相生有機(jī)的思想,那便是電影審美體驗與日常生活的關(guān)系。當(dāng)人們看電影時,他們停下手中的一切去欣賞日常生活中一項被忽略的事物,此時。世界仿佛為觀眾而生,一般而全身心地投入到電影的審美體驗中的觀眾,也會感到世界為自己而生。
二、主體觀照中的流動表演與流動身份
在傳統(tǒng)的敘事學(xué)派中,角色產(chǎn)生的順序在角色關(guān)系之前,在文本層面源于劇本設(shè)定或在視聽層面源于演員演繹的角色通過感知、行動與其他角色發(fā)生互動,構(gòu)成了故事發(fā)展的基礎(chǔ)。[6]而在修辭敘事學(xué)派的認(rèn)知中,故事內(nèi)的行動者與敘述者一樣受到潛在的敘述意圖支配,因此角色的交互會反身性地定義行動者本身。“存在”不再依賴于真實/真相,而僅依賴于觀察/觀測即可。這樣解釋明顯更適合于阿彼察邦在電影中進(jìn)行的一系列狂想:在《幻夢墓園》(2015)中,推銷員小金到曾經(jīng)的學(xué)校、如今的戰(zhàn)地醫(yī)院中推銷襪子,兒時的記憶與一名無名沉睡的士兵的夢境重疊在一起,記憶、現(xiàn)實與夢境被交織與重構(gòu);他還聽說了當(dāng)?shù)卦?jīng)發(fā)生的戰(zhàn)爭,聽說國王的墓室也正好在學(xué)校中,而沉睡的士兵也曾經(jīng)是國王的手下;《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2010)中,身患絕癥的布米叔叔在鄉(xiāng)下獨(dú)居,遭遇了紅眼猩猩等許多他視為過世親人“化身”的動物;《熱帶疾病》(2004)中流傳著猛虎會化作少年的傳說,一名少年與一名士兵糾纏不清,士兵在叢林深處追捕一只傳說中的虎靈……夢境、記憶與傳說的時空在平靜的畫面中相互碰撞、重構(gòu),觀眾需要通過雙眼感受熱帶叢林中迷夢般的氛圍。“《幻夢墓園》的真實與虛幻在形式上沒有做出任何區(qū)分,就好像現(xiàn)實中存在著許多維度,有些事物是我們看不見的,它只是以一種形式出現(xiàn)在你的記憶中,就好像造型形象在時間中展開,電影是在觀眾的想象中展開,這是對經(jīng)驗時空的超越。而原本鏈接時間與記憶的身體,在靈異的設(shè)置下,使自由不再受到身體的限制,過去與現(xiàn)在、夢境與歷史便在現(xiàn)實時空中更加自由地互動。”[7]在敘述者本身不可見乃至成為故事一部分的情況下,所有的行動者或“角色”本身的身份也不再明確。姓名、容貌乃至行動本身都成為超越經(jīng)驗時空的、不可捉摸或預(yù)知的一部分,在變換的形式下展現(xiàn)出表演的流動性。
《記憶》與阿彼察邦的電影讓人們看到了一種角色、行動與意義的模棱兩可性。如果說《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2010)中的靈和紅眼猩猩雖然都是完全超驗的存在,但卻又都是一個完全自洽且可信的“另一個世界”;那么《記憶》中的杰西卡就是源于一個真實世界卻并不“真實”的行動者。女主人公杰西卡的扮演者蒂爾達(dá)在影片中的表演展示出了脆弱、透明、“非人”的質(zhì)感,這一形象本身便是對“人”的反問,即使影片中的兩名截然不同的“埃爾南”都比她的形象更具有實感。性別與性格范疇的干擾在蒂爾達(dá)不動聲色的演繹中被排除出去,她和男人、女人們都交往甚密,甚至比神經(jīng)質(zhì)的阿涅斯更接近于沒有任何特征的、均質(zhì)化的“人”的形象。可以說,她從相貌到表演方法都是完全異質(zhì)的,她只能作為一個概念上的視角,但卻無法有效分享她的感知。因此,盡管她在每一個場景中都竭盡全力去觸摸、去觀看、去感受,但最終只是創(chuàng)造出了一連串富有設(shè)計感的造型而已。蒂爾達(dá)在影片中呈現(xiàn)出的魅力正源自于“人”作為一種概念和審美對象本身。她無所不是、無處不在的“流動性”構(gòu)成了蒂爾達(dá)表演的關(guān)鍵。而正是這種流動本身,在第一展的層次以外,也殊途同歸地摧毀了觀察/觀測的固定維度,進(jìn)而摧毀了固定的存在本身。
早在20世紀(jì)30年代,精神分析學(xué)家拉康就已經(jīng)從“觀看”的機(jī)制角度出發(fā),分析了主體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guān)系;美國電影敘事學(xué)研究者丹尼爾·達(dá)揚(yáng)還援引了歐達(dá)爾與舍費(fèi)爾的古典繪畫分析,提出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正是利用“想象層”機(jī)能去阻止人們對客體獲得任何真實的知識。[8]從這一時期開始,電影敘事學(xué)就突破了古典規(guī)范,進(jìn)入了多重語義與意指重疊的現(xiàn)代/結(jié)構(gòu)主義時期;后續(xù)的電影研究更加從精神分析中的形象-想象理論研究的方法讓電影研究脫離了單一的文學(xué)文本模式,在電影敘事學(xué)研究的范疇內(nèi)提升了修辭融合的美學(xué)地位。阿彼察邦電影中的行動本身就是一種表演、一種游戲和中介區(qū)間。[9]就像導(dǎo)演、制片人和主演在戛納電影節(jié)上亮出的“SOS”旗幟一樣,阿彼察邦電影中的“游戲”本身即是危險,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它模仿和戲仿一切,卻從不最終認(rèn)同任何東西。因此,在電影融合修辭學(xué)的視角下,行動者的形象在主體想象中部分偏離文本“設(shè)定”,在與其他行動者的對比關(guān)照中流露出隱含的意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多重分化狀態(tài)的收束過程
通過融合修辭學(xué)的觀點(diǎn)審視《記憶》,會發(fā)現(xiàn)隱藏的敘述者與流動的行動者作為影片重要的話語過程系統(tǒng)出現(xiàn),配合“科學(xué)方法論”的引用,掩蓋并重新建構(gòu)了電影作品包含的豐沛的物質(zhì)性,以及隨之而來的超驗力量。在不再任由各種解釋自由發(fā)揮,將重重意義重新收束在某種“科學(xué)解答”的努力方面,《記憶》無疑是阿彼察邦的一次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或許是因為對大投資和跨國制片的初次涉足,或許是因為他自身的經(jīng)驗的改變,我們難以想象以前的他會使用國際明星,或拍攝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主人公參觀藝術(shù)展、向?qū)I(yè)心理醫(yī)生提出咨詢、在高級餐廳用餐的場景。與《熱帶疾病》中泰國民間的“虎靈化形”傳說與主人公互相舔舐雙手的原始沖動、《幻夢墓園》的熱帶密林中代代相傳的古老王國傳說與巫術(shù)的猜測不同,《記憶》將故事場景放在“文明世界”的城市空間中,通過引入多重“科學(xué)”的方法論來試圖說服觀眾謎題解答的可能性,女主人公杰西卡也被專業(yè)的心理醫(yī)生確診為一種現(xiàn)實中存在的神經(jīng)病癥——“爆炸頭綜合癥”。在此前阿彼察邦電影里尋求文本的意義,或許會更靠近神話的隱喻系統(tǒng),但《記憶》通過考古人員、擬音師、心理治療醫(yī)生等“專業(yè)人士”的視角試圖給出了關(guān)于“夢幻”的多層級解釋。
如果說電影視覺層次是建立象征的裝置,那么電影敘事的層次就是一種“神話”的組織,這種組織可以產(chǎn)生和表達(dá)對真實世界的看法。多層次的視聽要素在其統(tǒng)一下成為“孕育、驅(qū)動謎題縱深發(fā)展的敘事引擎,為電影制造出錯綜復(fù)雜、扣人心弦的謎題與心智游戲”,而敘事裝置本身也在文化規(guī)約和心理機(jī)制上同時“成為建構(gòu)多層級‘可能世界”[10],令賦予意義的象征過程成立并自然化的終極敘述者。例如在杰西卡與擬音師埃爾南交流的段落中,他們試圖用技術(shù)設(shè)備來還原出夢境中所聽到的聲音,卻不期然陷入了更大的謎題之中。此時背向攝影機(jī)、時而沉默,時而低聲交談的二人與其說是畫面中的主體,更像是畫面中的前景;而畫面的主體則是一套聲音剪輯器,簡單的操作面板放置在兩名角色身前,顯示器則與他們頭部高度齊平。伴隨著埃爾南的操作,觀眾可以從屏幕上看到他是怎樣將一段音頻從連續(xù)的聲音中剪輯下來,并通過各種參數(shù)的調(diào)整成為女主人公夢想中的“帶有泥土味的”“仿佛來自地心的”“圓潤的”“低沉的”聲音;伴隨著存在感強(qiáng)烈的背景音效,我們看到了電影中的一段聲音如何產(chǎn)生,如何以數(shù)據(jù)化的方式由單純的數(shù)字素材被改寫為抽象的、詩意的夢幻之聲。一段聲音同時以圖像和聲音的形式出現(xiàn)在電影的視聽空間中。別有意味的是當(dāng)杰西卡再次來到這間錄音室尋找埃爾南時,得到的答案卻是這里并沒有一個叫埃爾南的男人。當(dāng)杰西卡重回錄音室尋找埃爾南的時候,她試圖向別人描述這個被證實不存在的人,卻因?qū)Ψ教釂枴澳阌姓掌瑔帷保チ死^續(xù)追問的勇氣。正是這種情境轉(zhuǎn)換了鏡頭,改變了我們與影像的距離——我們(導(dǎo)演和觀眾們)不再是影像的觀測者,而是參與了“我們”和“他們”的共同構(gòu)成;我們和他們是糾纏在一起的,就像“主體”和“客體”相互構(gòu)成一樣,即“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主體的省略伴隨著與自然的渾然一體。同樣是描述只存在于她記憶中的事物,此前她腦海中的巨響也許可以被音效庫素材慢慢拼湊進(jìn)而還原,但對于一個人的再現(xiàn)卻早就有了更行之有效的方式——當(dāng)視覺上的還原已經(jīng)尋常到了理所當(dāng)然的程度,無法被復(fù)現(xiàn)為照片或發(fā)掘為遺骸的事物要如何證明曾經(jīng)存在過。在此,《記憶》提出的問題在于,如果被看到才能確認(rèn)存在,那么沒有留下圖像的事物怎么辦;如果被聽到聲音才被認(rèn)可,那么沒有聲音以及沒有記錄聲音的事物怎么辦?作為一個導(dǎo)演和藝術(shù)家,阿彼察邦同樣希望探討的是如何取消媒介本身對感知另一種個體經(jīng)驗的局限性。正是在此,攝影機(jī)鏡頭成為潛在的敘事者。透過它的觀察與“敘述”,人們得以重新觀察并理解整個世界,在緩慢、固定的鏡頭中——一種喃喃自語般的影像自述中通過個人的體驗理解自然規(guī)律的運(yùn)行,并以相對靜止之姿來凝視微觀/日常和宏觀/宇宙的混合造景。
來自“科學(xué)”的“偽解答”與哥倫比亞城市場景中莊嚴(yán)、沉默、靜止的姿態(tài)相配合,很大程度上消減了源于東南亞茂密的叢林中持續(xù)涌現(xiàn)的物質(zhì)性,以及東南亞地區(qū)民族傳說中超越現(xiàn)代文明的超驗力量。這不僅是類似《戀愛癥候群》(2006)和《幻夢墓園》里醫(yī)院作為一個生與死的糾纏的場所,而是基于知識的某種“科學(xué)”開始真正指涉影片文本提出的終極謎題。多重意義的分散與分化被強(qiáng)力地收束在一個事先錨定的抽象結(jié)構(gòu)中,這顯然顛倒了阿彼察邦前作中一以貫之的抽象與具象的辯證地位。但與此同時,阿彼察邦顯然又并無意于通過挖掘硬科學(xué)提供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就像影片以失眠的杰西卡“遭遇”或“發(fā)掘”了她的記憶結(jié)尾,但并沒有為她直接解決這一問題一樣,影片中的心理學(xué)、考古學(xué)、植物學(xué)、人類學(xué)甚至地層學(xué)等種種被“挪用”的科學(xué)知識,都在阿彼察邦的影像里經(jīng)歷了某種轉(zhuǎn)譯與再造。在阿彼察邦“御用攝影師”薩永普·穆克迪普羅姆的鏡頭之下,與“科學(xué)解答”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的電影終極意義依然與哥倫比亞城市的雕塑與圖畫、倒映出人影的大玻璃、鄉(xiāng)村的沉浸式綠色植物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在不可言喻的人和歷史的細(xì)節(jié)中,“記憶”維系的世界中以一種游離的狀態(tài)隨著杰西卡的探索共同漫游,加深了她周身的流離失所感。
結(jié)語
《記憶》中現(xiàn)實與虛構(gòu)混淆、真實世界與隱藏世界一體共生的背景,比一般敘事線索與人物清晰的故事片更加需要融合修辭路徑中的多重不可見因素進(jìn)行分析。在彌散在神秘空間中的氛圍、不可捉摸的實質(zhì)、不可言喻的細(xì)節(jié)與對既定事實的否定回答都極大地限制了主要角色的所見所聞時,電影通過鏡頭建構(gòu)本身成為最可信、最動人的敘事者本身。這個話語系統(tǒng)被說成是銀幕上的一個“縫合”主體與其話語鏈之間“裂隙”的系統(tǒng),掩蓋作用正是因此而生效的。
參考文獻(xiàn):
[1]張良.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創(chuàng)作年表[ J ].當(dāng)代電影,2019(11):62-63.
[2]張良.位移與交疊:阿彼察邦《記憶》的跨文化創(chuàng)作[ J ].電影評介,2023(04):33-38.
[3][9][10]姚睿.不可靠敘述者:謎題電影與心智游戲電影的敘事引擎[ J ].當(dāng)代電影,2022(11):22-29.
[4]郭鐘安.電影敘述者的主體性與敘述機(jī)制建構(gòu)[ J ].北京電影學(xué)院學(xué)報,2021(08):29-38.
[5][法]羅伯特·布列松.電影書寫札記[M].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51.
[6][美]路易斯·賈內(nèi)梯.認(rèn)識電影[M].焦雄屏,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10.
[7]張次禹,朱峰.《幻夢墓園》:阿彼察邦電影時間和空間的重塑[ J ].當(dāng)代電影,2019(11):55-58.
[8][英]約翰·伯格.看[M].劉慧媛,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13.
【作者簡介】? 于妲妮,女,遼寧沈陽人,首都師范大學(xué)初等教育學(xué)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戲劇影視文學(xué)研究;
謝 瑾,男,浙江寧波人,浙江師范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戲劇、歌劇、影視文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