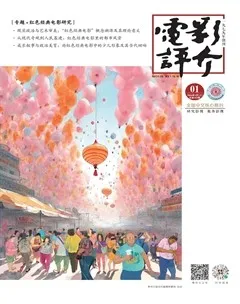電影影像的可塑性:基于電影史與現(xiàn)象學(xué)的超驗存在論



通常意義上,電影影像是固定和必然性的:它意味著其是經(jīng)由攝影機記錄、剪輯與后期處理,最后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的經(jīng)驗之物。拍攝者可能會從不同角度出發(fā)對同一內(nèi)容進行反復(fù)扮演和拍攝,但最后被甄選出來的總是符合其心理預(yù)期的結(jié)果。從電影發(fā)明歷史出發(fā),電影本身作為一種基于特定技術(shù)原理,并從根本上由人類想象力驅(qū)動的藝術(shù),“想象”本身的發(fā)散性始終銘刻在電影的媒介現(xiàn)實中,深刻地影響著其中的視聽展現(xiàn)內(nèi)容。
從感知角度來看,結(jié)論同樣如此:每個可視之物的每一次呈現(xiàn)都具有偶然性,攝影機也可以在多個時間段、從多個可能的感知角度進行觀察,電影后期的人工處理也帶有主觀創(chuàng)作的偏好性。換言之,從這一角度而言,電影影像具有“可塑性”。這種“可塑性”并不單單意味著電影拍攝過程中的人工干預(yù),對自然中的事物造成可見影響,更意味著電影影像由各方面因素影響而生成結(jié)果的隨機性更強,即使是其署名的“作者”也無從預(yù)料,只能接受并記錄其結(jié)果的超驗部分。本文將從電影史與現(xiàn)象學(xué)出發(fā),探討電影影像是如何被各方面不可控的超驗因素所“塑造”的。
一、電影的歷史:超越現(xiàn)實的媒介
回望電影的歷史,電影作為想象與技術(shù)的綜合物誕生于人類對探求世界有著深切渴望的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在這一時期,人類熱衷于以各種方式探索更深層的世界。在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方面,從牛頓力學(xué)到熱力學(xué)、電磁理論,量子物理發(fā)現(xiàn)前人類的“物理學(xué)大廈”已全部建成,顯微鏡、有線電報、有線電話、飛機作為將人與更遠時空相連的媒介,極大地拓展了人類觀察世界的視角與深度;而在想象力與藝術(shù)方面,也有現(xiàn)代技術(shù)文明的擁躉,從科學(xué)發(fā)明中得到靈感,提出以技術(shù)進步的方式探求更廣闊的世界。例如,意大利未來派藝術(shù)家馬利內(nèi)提早在1913年就在《無限想象力與自由狀態(tài)的未來派宣言》中提出:“像毫無興趣地仰望首次飛過的黎波里(利比亞首都)上空的飛機上的阿拉伯人那樣,對任何事物都不能深入地感觸,在這種的精神里這樣的可能性,激發(fā)不了任何好奇心……而科技所擁有的這些可能性,就好像速度變革了我們的感性一樣,看上去有著能改變我們的感覺的力量。”[1]馬利內(nèi)提的這種思考方式結(jié)合進化論的觀點,提出科技產(chǎn)業(yè)文明需要依靠想象與創(chuàng)新才能激發(fā)出最大活力,以人文學(xué)科的方式將“好奇心”與藝術(shù)想象與科技的創(chuàng)新與進步相聯(lián)系。在高速前進的科技產(chǎn)業(yè)文明中發(fā)展并“進化”著的人類意識,在進化系統(tǒng)的樹干上無限延伸,其中既有驟然新生的分枝,也有生長已經(jīng)停滯的分枝。從這些分枝的包圍中脫離、成長起來的樹干上,會誕生具備新感知能力的新人類。電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連接“技術(shù)”與“想象”的媒介被發(fā)明出來。
機械技術(shù)文明的合法邏輯,是憑借知識與理性的力量構(gòu)建出一個完整融洽、一切事物都按照合理規(guī)則運動的“理性世界”。其中的理性既聯(lián)系著啟蒙運動以來以科學(xué)驅(qū)逐宗教的陰影,以技術(shù)驅(qū)動生產(chǎn)力這一資本主義文明的根基;又是對機械技術(shù)主導(dǎo)的生產(chǎn)力崇拜的一種肯定;而電影卻作為一種技術(shù)發(fā)明顛覆了技術(shù)理性本身,它展現(xiàn)的內(nèi)容與方式超越了對現(xiàn)實的反映,將觀眾帶入夢幻之中,成為一種力圖超越現(xiàn)實情景的媒介。與未來主義者①的主張不同,電影將想象中的“新人類”置于與人類平等的地位,并且通過視聽藝術(shù)的手段試圖將這些“隱身”于現(xiàn)實生活之中的、不可見也不可知的事物挖掘出來。這些只能通過媒介揭示的形象并不明確,也并不能以常理去說明;只有在極其偶然的狀況下,那些“假想生物”才能隱隱約約地向人們展露一部分構(gòu)造和體質(zhì)。這些在特征上以與其相反的、非理性的記憶、夢境無意識或夢幻元素來對抗被各種理性意義所填充的現(xiàn)實,對抗現(xiàn)實,從理性主義手中還原現(xiàn)實的方法路徑或呈現(xiàn)方式被稱為“超現(xiàn)實”[2];而在這一意義上,電影本身就是一種蘊含了超現(xiàn)實因素的媒介,它的誕生與機械技術(shù)的進步乃至整個實用科學(xué)門類在現(xiàn)代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無論是攝影機通過曝光對現(xiàn)實事物進行捕捉,電影膠片通過化學(xué)藥劑顯影,還是放映時每秒24格的穩(wěn)定機械運動,都依賴著物理、化學(xué)等一系列現(xiàn)代學(xué)科的發(fā)展和進步,然而在視聽形式與效果上電影又以非限時的方式,在黑暗中投影出一片夢幻的空間,讓觀眾如做夢般忘乎所以、沉浸其中,流連忘返。在現(xiàn)實實踐的基礎(chǔ)上,電影與夢幻般的迷影效應(yīng)完成對現(xiàn)實邏輯的悖論。源于現(xiàn)實的實拍素材建構(gòu)出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虛幻空間,始于現(xiàn)實(攝影棚或片場)又終于現(xiàn)實(電影院或其他放映場合)的實踐制造出非現(xiàn)實的夢幻時刻——這便是電影作為一種超現(xiàn)實的藝術(shù)與現(xiàn)實之間的間隙。
美學(xué)核心在關(guān)聯(lián)意義上而言是原創(chuàng)性,藝術(shù)必須超越其媒介的同一性和重復(fù)性形式,以一種想象性的表達比喻給予其觀念性的內(nèi)容;而在存在論的意義上,美術(shù)則是作為一種審美觀念的存在狀態(tài),因此藝術(shù)在歷史和想象層面上具有雙重超驗性。超現(xiàn)實主義者的主張與實踐一樣,電影的超限時方向表現(xiàn)的實際上也是現(xiàn)實與“夢境”之間的關(guān)系;而科技與機械技術(shù)進步驅(qū)動的視聽效果迭代,也依然是當(dāng)下電影發(fā)展的重要方向。
在近年來的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中,諸多創(chuàng)作者在延續(xù)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道路上不約而同地進行“超現(xiàn)實”的想象。《不止不休》(王晶,2020)在強調(diào)實景真人的紀(jì)實手法基礎(chǔ)上拍攝了超現(xiàn)實的場景:2003年楊利偉乘坐神舟五號升空,完成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載人航天飛行。下定決心為所有人還原真相的韓東在家看著電視里播放著楊利偉在太空的新聞,手中的筆也如同楊利偉太空中的筆一樣,“同步”地漂浮起來。這一幕很容易讓人想到賈樟柯電影中對超現(xiàn)實手法的運用,例如《三峽好人》(賈樟柯,2006)中地面上的建筑拔地而起飛向太空、天空中神秘的飛碟掠過、走鋼絲的人游走在兩棟廢棄的大樓之間,飛人般凌駕于眾人頭頂上;《山河故人》(賈樟柯,2015)中當(dāng)沈濤去給梁子送請柬時,一架農(nóng)用飛機“莫名其妙”地墜毀在沈濤面前,而后面鏡頭里同樣的位置有一對母女在燒紙。太空和天空一直是夢想聯(lián)結(jié)之地,讓人與物件離開地面展現(xiàn)出一個民族實現(xiàn)夢想的代表性事件,是一個宏大的主題。這些都是典型的超現(xiàn)實主義隱喻蒙太奇,現(xiàn)實主義基調(diào)中插入性的物件或橋段讓原本準(zhǔn)確有序的一切忽然超脫現(xiàn)實,在日常與庸俗中帶給觀眾心靈上的沖擊。這些電影與超現(xiàn)實主義一樣,都是誕生于機械、又以夢幻對抗機械理性,以另一種方式超越并擁抱現(xiàn)實的形式。學(xué)者戴錦華曾經(jīng)對此作出過深刻的表述:“我覺得在《三峽好人》這個電影里面,從滑稽現(xiàn)實到超現(xiàn)實有一種內(nèi)在的遞進關(guān)系。賈樟柯式的‘土包子的超現(xiàn)實,其實是我們巨大的現(xiàn)實;緊緊扣住這樣一種現(xiàn)實,是強大的敘述者才能做到的事。”[3]而對于超現(xiàn)實藝術(shù)而言,超驗包含著一件作品隨著時間流逝,持續(xù)經(jīng)歷漸進的物質(zhì)形態(tài)的變化,這種變化本身可能暴露出真理;而觀者要在一個或多個部分的喪失或改變中,仍將物質(zhì)與精神作為一個整體進行關(guān)照,而不得超越現(xiàn)有的材料和條件,構(gòu)想一個觀念意義上的作品的整體性。
二、內(nèi)容的選擇:對現(xiàn)實空間的多重感受
從現(xiàn)象學(xué)①的角度而言,每一次實際具體的呈現(xiàn),或者通過機械手段對它外在形態(tài)進行的記錄,在存在論意義上都只能作為這個物體全部身份本質(zhì)的一部分。但電影影像保留的內(nèi)容具體能喚起何物始終是難以經(jīng)驗預(yù)測的。這些多變的維度讓電影影像成為具有隨機性的偶然性結(jié)論,每一幀影像的呈現(xiàn),都是無數(shù)種自然選擇疊加、相互影響或改變的結(jié)果。[4]法國哲學(xué)家、電影研究者吉爾·德勒茲在與法國電影導(dǎo)演和編劇帕斯卡·博尼澤和讓·納博尼的訪談中談到:“……我看到工廠,便認為看到囚犯……這不是一種線性的延續(xù),而是一種循環(huán),兩種影像圍繞著一個真實與想象不可分的點互相不停地追逐著。可以說,實在的影像與虛幻的影像在結(jié)晶。”[5]他通過《一九五一年的歐洲》(意大利,1952)對電影的表意方式進行反省,并從“圖像”與“意義”的糾纏中挖掘出凝結(jié)著整體時間與情感的“晶體-影像”。這部影片講述一個安于家庭生活的上流社會太太因喪子意外而逐漸覺醒,走出家庭投身于慈善事業(yè),但最終被自傲與缺乏同理心的社會宣判為離軌者而永久放逐到精神病院的故事。這部具有典型新現(xiàn)實主義特征的影片在人道和非人道之間,在存在的活躍和凍結(jié)狀態(tài)之間,在以自我為中心的物質(zhì)主義的狹隘和更大的、包羅萬象的愛的無限之間開拓了嶄新的視野。
為了擴大電影表現(xiàn)的范圍,《一九五一年的歐洲》的導(dǎo)演羅西里尼在視覺上拋棄了美麗、完美的形象,轉(zhuǎn)而以一種粗糙的,甚至有點像不經(jīng)意的風(fēng)格呈現(xiàn);它避開了傳統(tǒng)電影中自滿的、自我封閉的形式主義,由部分源于繪畫和靜態(tài)攝影的悠久歷史的靜止畫風(fēng)轉(zhuǎn)向反形式主義的新現(xiàn)實筆法。導(dǎo)演將現(xiàn)實視野的開放性延伸到電影形式上的畫面剪切、溶解和鏡頭移動中,這也擴大了觀眾所看到的背景,每一刻都打破了最后一刻,幾乎就像一個讓世界進入的傷口。這種由他的電視電影中無處不在的變焦鏡頭所產(chǎn)生的邊界推擠的效果,在他早期電影的視覺強度中也有所體現(xiàn),圖像似乎以一種超乎尋常的強度壓著它們的邊緣。德勒茲從《一九五一年的歐洲》中看到的不是“圖像-表意”這一粗淺的二元結(jié)構(gòu),而是“看見”這一最為本體論的動作被一個輕巧且全新的系統(tǒng)移植,持續(xù)不斷的描繪代替了被描繪的客體,而后成為從未有過的清晰的主體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
電影影像不是孤立的,它總是與別處發(fā)生關(guān)系,它隨時可能與精神的、虛幻的或反映的影像產(chǎn)生聯(lián)系。為了不人為地切斷影像與現(xiàn)實之間的聯(lián)系,許多電影創(chuàng)作者會在對“氛圍”或基本影調(diào)的把握下“放任”演員自由表演,這也是創(chuàng)作者對圖像的反復(fù)思索而達成影像最終形態(tài)的過程之一。在電影《刺客聶隱娘》(侯孝賢,2014)的幕后紀(jì)錄片《刺客侯孝賢》(楊笑梅,2015)中,導(dǎo)演侯孝賢堅持影像氛圍大于一切細枝末節(jié),甚至大于演員的面部與表演。與大多數(shù)導(dǎo)演不同,侯孝賢堅持讓演員在沒有提前彩排的前提下表演,給角色提供表演空間。在自然風(fēng)、自然光的引導(dǎo)下,只要演員體會到自己進入角色即可,不用特意做出迎合故事的表演。事實上,不做出表演指導(dǎo)與提前彩排的電影中,演員要更費力地全身心地感受一切影響“角色”表現(xiàn)的東西,這正是最為直接的、創(chuàng)作者在反復(fù)思索之后選擇用影像觸摸真實世界的途徑。作為一部本身臺詞極少且導(dǎo)演也很少主動讓攝影機停下的影片,《刺客聶隱娘》大多數(shù)時間都在對靜態(tài)場景與人物動作的刻畫中度過。在微風(fēng)吹拂的氛圍中,圖像指涉現(xiàn)實的本能經(jīng)由作者提純和強化,在真實和想象之間來回追逐,與庭院中搖曳的花草樹木一起,體現(xiàn)出角色在緘默中的無窮情思。侯孝賢的電影影像拒絕被按照經(jīng)驗方式加以暴力闡釋,影像本身較少的信息與符號也沒有為闡釋留下空間;它試圖以“氛圍”喚起觀眾的想象力與直覺,提示人們影像的本能來自通感。
三、影像的沖動:電影意義表達體系的揭示
作為術(shù)語本身的“超驗”在藝術(shù)和世俗語境中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超驗”這一術(shù)語被使用的情景總是在狀態(tài)的改變中。在萬物同時運動與變化的狀態(tài)中,其中某一事物在變化中被超越,從而在“必然的偶然”中揭露出某種不言自明的真相。從電影史與現(xiàn)象學(xué)的角度來看,電影本身似乎就是一種誕生于人類意圖又對此自反的媒介,電影史上較為“完美”和經(jīng)典的畫面經(jīng)常來自于偶然。不可否認,在長期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成為體系的電影攝制技術(shù)依然強烈地影響著影像的內(nèi)容生成,并讓電影始終處于人為主觀意圖的控制之下;但與此同時,電影攝影影像本身也可以包含行動范疇,人為與天然、主觀與客觀、技術(shù)與想象……“實際上,正是時間性喪失和空間性呈現(xiàn)之間所構(gòu)成的創(chuàng)造性張力,使照片成為不僅僅是那些至少存在過一次的東西的印記。在形而上的意義上,有關(guān)于此的重要性或許觸及更深層次的意義范圍。尼采曾說每一個事件都會不斷地進行重演。他對于這種信仰的解釋是非常具體和復(fù)雜的。但是,我們可以給予它一個更為寬泛的理由。”[6]電影畫面可以被看作一個系統(tǒng)性的連續(xù)性現(xiàn)實的時空交匯點。在多重元素的交匯中,超驗本身是一種積極要素,它指向一種趨向于某個物體的動勢,而非僅僅是已經(jīng)存在的某個事物自身的簡單否認和拒絕。
在多方力量的爭奪中,電影影像保持著將自身暴露為包含拍攝過程的、現(xiàn)實的沖動。在《河邊的錯誤》(魏書鈞,2023)中,電影中的時間和空間不再是固定的,而是變得流動和多變。主人公經(jīng)歷的時間不再是連續(xù)的線性過程,而是由多個時間片段組成,這些時間片段之間沒有明顯的先后與邏輯關(guān)系,主人公的調(diào)查因此變得困難重重;空間也不再是固定的場景,而是變得跳躍和流動,甚至讓諸多配角進入主人公的夢境世界中。這種敘事方式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電影中以時空為基礎(chǔ)的敘事模式,使得觀眾需要更加靈活地理解和接受故事的時空結(jié)構(gòu)。電影《河邊的錯誤》中的河流就像一面鏡子,使觀眾可以直觀地看到其所呈現(xiàn)的景象,這也是這部電影最獨特的地方。影片一開始就以戲謔的方式解構(gòu)電影的意義表達系統(tǒng),主人公將整個工作團隊搬到了一家電影院的舞臺之上,使整個電影故事的荒誕性得以徹底展現(xiàn)。此外,影片還運用許多充滿戲謔意味的鏡頭語言,例如“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人看電影了”“這是好事兒啊”,電影院的招牌在拆卸的過程轟然倒塌,攝像機在不止不休的放映中忽然熊熊燃燒等。在結(jié)局的反結(jié)構(gòu)上,導(dǎo)演將懸疑電影最核心的反轉(zhuǎn)給予較大程度的消解,沒有嘲諷,沒有態(tài)度,也沒有任何答案。
電影對表現(xiàn)物象的超越,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因為這使得觀眾面臨“解讀”和“對抗解讀”的問題,并以此重新審視電影現(xiàn)實與現(xiàn)實本身。巧妙地由故事片《吉祥》和紀(jì)錄影像《如意》兩個短片片段組成的《吉祥如意》(大鵬,2021)也涉及攝影機與拍攝過程的暴露與自反。《吉祥如意》在敘事結(jié)構(gòu)和影片組織方面表現(xiàn)出獨特的創(chuàng)新性,從吉祥、如意到吉祥如意,影片內(nèi)涵更加豐富,結(jié)構(gòu)也更變幻莫測。實際上,這部電影不斷回溯,導(dǎo)演大鵬摒棄了“家丑不可外揚”的觀念,勇敢地將私人記憶中最牽動人心、最凝滯的部分坦誠呈現(xiàn)。空間作為承載記憶的實體,它分解、配置并整合全部情緒和節(jié)奏,使影片更具深度和廣度。在另一部令人頗感意外的故事片《其他》(法國,1975)中,導(dǎo)演以暴露攝影機存在的方式向觀眾揭開一套“電影攝制”的神話體系。這部電影講述巴黎一名五十多歲的父親斯賓諾莎曾以為自己很了解兒子,卻在兒子死后感到仿佛不曾認識他;在整理兒子的遺物時,他試圖從兒子留下的劇本中尋找真相,卻被誤以為是兇手。這部超現(xiàn)實主義的法國電影劇本由桑蒂亞戈與文學(xué)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共同撰寫。在該影片開頭的十分鐘內(nèi),電影攝制工具屢次以各種方式將自己暴露:攝影機跟隨鏡頭前桑蒂亞戈的手勢多方向移動,或是在拍攝人物散步的同時將另一臺攝影機暴露,被暴露的攝影機在它們搭建的這個體系之中持續(xù)不斷地、變換姿態(tài)地運行,一次偶然的滑動動作失誤般地將景框外的博爾赫斯拍攝進圖像中。“人物和體系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為探求兒子死因的書商/父親在一連串的建筑與地標(biāo)間漫游來交互并且見證一連串自我的生成。”[7]攝影機的現(xiàn)身破壞了電影的幻覺,強調(diào)對真實世界的多元理解和尊重,它暗含著一種價值判斷——在攝影機與景框之外的每一個個體和群體都有其獨特性和價值。電影中的人物關(guān)系和情感變化,以及對于生活、人生和人際關(guān)系的探討,都體現(xiàn)了這種差異哲學(xué)的思考。從揭示電影意義表達體系的視角來看,這些直接將電影制作過程暴露給觀眾的做法是一種顛覆傳統(tǒng)線性敘事方式的表現(xiàn)手法。“暴露”并不涉及任何自反,也與幻象或象征無關(guān),是攝影機偶爾的沖動,所有機位規(guī)劃了這個體系內(nèi)的動力布局,且從來都不是為了指涉。它強調(diào)差異、多元和變化,挑戰(zhàn)傳統(tǒng)電影中以情節(jié)、時空和人物角色為線索的敘事模式,使得觀眾需要更加主動地參與解讀和構(gòu)建故事。這種敘事方式不僅豐富了電影藝術(shù)的表達手法,也為我們理解世界和自身提供了新的視角。
結(jié)語
基于電影史與現(xiàn)象學(xué)對電影可塑性的論述與對刻意控制的批判并非否定電影拍攝技術(shù)本身,而是對電影影像的既有存在方式提出異議。作為一種在深度上超越現(xiàn)實的媒介,電影的藝術(shù)活動始終圍繞現(xiàn)實社會中的神話體系這一主題,不僅要展現(xiàn)既有認知和文化,更要通過與既有文化摩擦和抵抗,以極高的藝術(shù)敏感性關(guān)涉現(xiàn)實,并在其中尋找批判的潛在對象與改造對象的邏輯方法,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藝術(shù)。
參考文獻:
[1][日]田淵晉也.縫紉機、蝙蝠傘邂逅于手術(shù)臺: 現(xiàn)代藝術(shù)新解[M].金晶,顧錚,審校.重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14:160.
[2]邵牧君.西方電影史概論[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31.
[3]張晨子.對話北京大學(xué)教授戴錦華“非觀眾”呼喚出的“非電影”正在統(tǒng)治中國電影[ J ].大眾電影,2015(11):8.
[4]周月亮.電影現(xiàn)象學(xu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0-12.
[5][法]吉爾·德勒茲,費利克斯·加塔利.什么是哲學(xué):卡夫卡——為弱勢文學(xué)而作[M].張祖建,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100.
[6][英]保羅·克勞瑟.視覺藝術(shù)的現(xiàn)象學(xué)[M].李牧,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1:29.
[7]Current89.長評|市郊的星群或有關(guān)Mercuriales[EB/OL].(2023-08-01)[2023-09-27].https://mp.weixin.qq.com/s/IgnuiZviTTAtiFMIWY6-xQ.
①未來主義是意大利20世紀(jì)初一場全方位的社會、文化和藝術(shù)運動,它也是最早的歐洲先鋒派之一。該運動的名稱由意大利詩人菲利波·托馬索·馬里內(nèi)蒂提出。未來主義者的靈感多來自于技術(shù)驅(qū)動與現(xiàn)代化生活的新鮮活力,他們在各個當(dāng)代文化領(lǐng)域進行革命,倡導(dǎo)一種新的文化和習(xí)俗,同時秉持與工業(yè)革命一致的價值觀——速度、效率,以及永不停步的科學(xué)和技術(shù)發(fā)展。未來主義與后續(xù)出現(xiàn)的許多全球性的前衛(wèi)藝術(shù)運動——從達達主義和超現(xiàn)實主義,到激浪派和即興藝術(shù),再到網(wǎng)絡(luò)藝術(shù)——重塑了現(xiàn)當(dāng)代文化史。
①現(xiàn)象學(xué)是一種重視經(jīng)驗世界的哲學(xué)方法和學(xué)派,以德國哲學(xué)家胡塞爾為代表。現(xiàn)象學(xué)致力于從現(xiàn)象本身出發(fā),描述和分析現(xiàn)象的本質(zhì)結(jié)構(gòu)和意義,以揭示人類經(jīng)驗的根本特征和世界的本質(zhì)。其核心思想是“回到事物本身”,即摒棄主觀、客觀的二元對立,直接面對人們的經(jīng)驗世界,追尋現(xiàn)象背后的本質(zhì)和意義。
【作者簡介】? 張蕓鵬,男,山西臨汾人,山西師范大學(xué)戲劇與影視學(xué)院博士生,主要從事電影史、新媒體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山西師范大學(xué)研究生教育創(chuàng)新項目“文明戲與中國早期電影的劇作關(guān)系”(編號:2021XBY00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