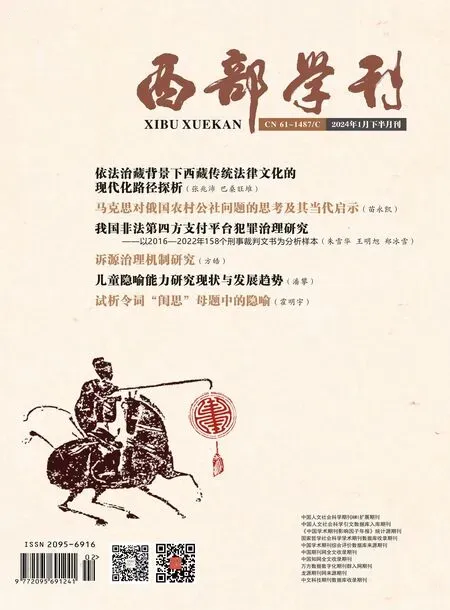負擔居住權住宅之出租問題研究
羅 兵 張淑蓉
(1.南京財經大學紅山學院,南京 210003;2.江蘇開放大學,南京 210036)
居住權制度最早產生于古羅馬時期,其建構目的在于為穩固婚姻家庭內部的財產繼承秩序提供居住保障。就其性質而言,居住權制度是為避免家庭內部成員居無定所,從而起到社會保障作用的人役權制度的一種[1]。我國《民法典》所確認的居住權制度受古羅馬居住權制度的影響,雖在法律架構中將居住權置于物權編用益物權的位置中,但是核心立法意旨仍在于使其發揮與婚姻家庭編、繼承編相同的社會保障作用,強化住宅在傳統婚姻家庭領域內的占有和使用價值。因此,《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條將居住權的權能范圍限制于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但是,從居住權制度的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囿于傳統社會保障定位的居住權制度并不能完全滿足大眾對于住宅的利用需求,居住權的社會性特征逐步向投資性轉變,居住權的種類和適用范圍亦在不斷擴張。《民法典》雖禁止了居住權的轉讓和繼承,但并未完全禁止負擔居住權的住宅出租,為以出租的方式利用住宅留有余地。
一、對負擔居住權住宅出租的肯定
關于負擔居住權的住宅是否可以出租,學界存在爭議。部分學者認為負擔居住權的住宅不應再被允許出租,原因是基于社會性居住權的傳統理念考慮,為保障婚姻家庭中的弱勢群體居住利益,負擔居住權的住宅應當嚴格限制于占有和使用,而出租住宅并非單純滿足生活需要(1)參見王勇旗:利益衡量理論在我國居住權立法中的應用[J].河北法學,2020(8):105-106.。但更多學者基于對居住權投資性價值的考量,認為出租住宅是多樣化利用住宅的一種方式,有利于充分發揮住宅的使用價值,應當允許住宅出租(2)參見汪洋:民法典意定居住權與居住權合同解釋論[J].比較法研究,2020(6):111.。或者認為,即使基于共同生活關系的具有幫扶性質的居住權也不能肯定居住權人的出租權利;而非基于共同生活關系設立的居住權,特殊情況下其權利人也可以具有出租住宅的權利[2]。實際上早在古羅馬時期,優士丁尼(3)優士丁尼(482—565年),東羅馬帝國皇帝。他組織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法典編纂活動,以蓋尤斯《法學階梯》為藍本另編優士丁尼《法學階梯》,此衍本對藍本做了諸多改進,并且具有理論化的傾向。全書共分為4卷98題830段,按內容又可分為序題、自由身份法、家族身份法等26個部分,囊括了羅馬人私領域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情形,處處彰顯民法乃生活理性之歸納的本質。就肯定居住權人可以出租房屋,允許他們不僅可以自己在房屋中過活,也可將之租與他人[3]。
我國民事法律體系已然將居住權界定為一種用益物權,雖立法意旨上重在發揮居住權的社會保障的作用,但居住權作為用益物權的基本屬性預留了負擔居住權的住宅再行出租的利用空間。故而《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條一方面基于居住權社會性特征的考量,規定設立居住權的住宅原則上不得出租;但另一方面又基于居住權投資性的衡平,賦予當事人可以約定負擔居住權的住宅出租權利。如此,雖然否定了法定出租權的存在,但卻肯定了約定出租權的合法性。于具體社會生活而言,允許負擔居住權的住宅出租是充分發揮住宅用益性價值的體現,如在“以房養老”的居住權司法實踐中,老人能夠通過保留居住權而轉讓房屋所有權來獲取收益,如其能夠通過出租住宅的一部分再獲取收益以滿足生活需要,則能夠最大程度上發揮住宅的用益性價值,使得居住權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真正地發揮保障權利人生存權的作用[4]。
二、出租人視角——所有權人與居住權人之權利界分
如對《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條簡單理解,則是對于負擔居住權住宅的出租,有約定從約定,沒有約定時不得出租住宅。然而,該種理解并不能完全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如約定不明時居住權人為滿足生活需要而出租住宅。于此,就負擔居住權的住宅出租過程,存在著基礎的出租人身份沖突問題——住宅所有權人作為出租人或是居住權人作為出租人。基于《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條的規定,我國居住權制度嚴格限定了居住權的權能范圍在于占有和使用,并未如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等用益物權一般明確了收益的權能,相對應地為所有權人保留了對于住宅的收益權和處分權。而租金屬于法定孳息的一種,將負擔居住權的住宅出租給他人并收取租金顯然屬于行使收益權的一種行為。以此而言,住宅所有權人可基于所有權對負擔居住權的住宅再行出租,以達到行使收益權的目的。且依照目前《民法典》對居住權的限制性規定及物權法定原則,為發揮居住權的社會保障功用,居住權人對于負擔居住權的住宅亦并不能再將占有和使用權利全部讓渡給他人。但是,居住權的法律定位是用益物權,其核心目的在于充分保障居住權人對于房屋的占有和使用,而出租住宅必然需要由承租人占有和使用住宅,如再為所有權人保留出租負擔居住權住宅的權利,則不可避免地發生所有權人行使收益權與居住權人對住宅的居住使用相沖突的問題。如欲解決上述矛盾,應當從所有權人與居住權人之權利界分的本質出發,通過厘析權利人的權利邊界來明確基礎的出租權歸屬。
自立法意旨而言,明晰出租權的歸屬應當確立居住權的優先保障性。居住權是為保障權利人居住權利益而產生并逐漸發展成熟的一項權利,雖然我國《民法典》將其定位于物權編中用益物權的位置,但從相關條文厘定和規則設置中,可以發現其核心目的在于保障婚姻家庭領域內弱勢群體的居住權益,滿足其基本生活居住需要,重在發揮居住權制度的社會保障作用,發揮住宅的投資性價值并非主要目的。而出租權僅是一種通過建立債權債務法律關系,以讓渡住宅的占有和使用來滿足物權層次上的收益需要,從而達到權利人行使收益權的目標,其實質上是一種投資性行為。因此,從居住權立法意旨而言,居住權應當以其保障權利人生存權而優先于出租權。故而,對于負擔居住權的住宅,雖然所有權人僅將占有和使用權能剝離并讓渡給了居住權人,保留了收益和處分權能,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權人仍享有為行使收益權而出租住宅的法定權利。
既然所有權人對于住宅的收益權并不能對抗居住權人對于房屋的占有和使用,那么是否居住權人在約定不明時即可對住宅行使出租權呢?有觀點認為,是否允許居住權人在此種情況下出租住宅應當以其獲得居住權時是否有償為判斷依據,對于以居住保障為目的而無償設立的居住權,居住權人并未支相應的對價,從權利與義務對等的角度來看,自然不應當允許其再行出租房屋獲取額外的收益;而對于有償設立居住權的住宅而言,因居住權人已經支付了相應的對價,自可允許其再行就獲得的房屋居住使用權利進行出租。此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關注焦點并未落定于居住權的本質為保障權利人的居住權益。即使居住權人以無償的方式獲得居住權,只要其行為指向并未與居住權的立法意旨相矛盾,則允許其出租住宅亦無不可。由于居住權本就以社會保障而生,并無須完全遵從等價有償原則。當然,居住權人出租住宅應當是有條件的,即以“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為前提。具體而言,居住權人首先應當以生活居住為目的對住宅進行使用,該種使用是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要而進行的物質性利用,并不應當指向投資性質的“商業性”利用。因此,就目前居住權的立法意旨來看,居住權人如需要出租住宅首先應當滿足自身的居住需求,而后其可以根據實際的生活需要將住宅出租來獲取收益,如獨居老人享有整套房屋的居住權時,在與所有權人約定不明的情況下,可以適當允許其為滿足生活需要而單獨劃分出住宅中的某一部分對外出租。
三、承租人視角——明確租賃權的對抗保護規則
如雙方當事人就負擔居住權的住宅出租問題達成一致意見,無論是所有權人還是居住權人行使約定出租權,都不應僅考慮其作為出租人的利益,還應當關注承租人的權益保障。于承租人而言,通過與出租人簽訂租賃合同而取得住宅的租賃權,性質上該行為是一種建立債權債務關系的法律行為,且租賃權也屬于典型的債權。如根據傳統民法理論——物權優先于債權,租賃權自然劣后于所有權人的所有權或者是居住權人的居住權。但若如此理解并執行,可能會嚴重侵害承租人的租賃權。例如,所有權人出租住宅,居住權人得以居住權遭受侵害為由要求承租人騰空房屋;又如,居住權人出租住宅,所有權人得以所有權遭受侵害為由要求承租人騰空房屋。《民法典》第四百零五條及第七百二十五條雖分別規定了租賃權與抵押權的對抗效力及租賃權與所有權的對抗效力,但目前相關條文中并無對承租人租賃權與居住權對抗效力規定。因而,以承租人視角而言,應當明確對承租人租賃權的對抗保護規則。
首先,如承租人的租賃權產生于居住權設立之前,即居住權在所有人將住宅出租給了承租人之后,又在住宅之上為他人設立居住權。此時從承租人的視角,其承租的住宅系所有權人基于所有權的合法出租行為,依照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五條的規定,租賃期限屆滿前租賃物發生所有權變動的,租賃合同的效力不變,承租人的租賃權可以對抗所有權人的所有權自不待言。又參照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五條的精神,對于成立在后的居住權而言,由于其設立于租賃權產生之后,因而承租人在先取得的租賃權自可以對抗設立在后的居住權,此為保護承租人作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其次,如承租人的租賃權產生于居住權設立之后,由于承租人取得的租賃權內容系對負擔居住權住宅的占有和使用,與在先產生的居住權人對住宅的占有和使用權利相沖突,應當從規則上對相關權利人的權利進行合理安排,以達到法律公平的價值要求。在此類情形之下,分情況進行處理較為適宜:若租賃權系住宅所有權人與居住權人在達成明確合意的基礎上產生的,那么無論是所有權人還是居住權人出租住宅,承租人僅在義務層面負擔不同租賃義務,如租金的交付對象有所差別,但是在權利層面租賃權內容無有變化,并且在效力上仍可參照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保持其租賃合同的效力不變。承租人取得租賃權后自可以對抗所有權,所有權自此后發生變動的不影響租賃權,而居住權因法定禁止轉讓自不待言。若所有權人與居住權人約定不明,所有權人或居住權人出租住宅,則由于居住權在先成立及物權優先規則,同為保護權利人居住權利的租賃權應當劣后于居住權或所有權。若所有權人與居住權人并無對住宅的出租約定,所有權人或者居住權人擅自出租住宅的,則因違反《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條的規定,出租行為無效。
四、負擔居住權住宅出租的其他問題
(一)約定出租權的登記
根據《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條的規定,設立居住權應當向登記機構申請登記,住宅所有人欲在住宅之上為他人設立居住權以設立登記為居住權生效要件。又根據《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第八條的規定,不動產登記簿應當記載的四類事項包括自然狀況、權屬狀況、權利限制提示事項以及其他相關事項,這與《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條關于居住權合同條款的規定核心內容是一致的。因而將所有權人與居住權人訂立的居住權合同內容詳盡記載于不動產登記簿是必要的。《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條允許當事人以約定的方式對負擔居住權的住宅進行出租,該約定可以是當事人在居住權設立合同中單獨協商一致產生,也可以是當事人在居住權設立后再行協商一致達成的補充協議。如當事人在居住權合同中就住宅出租事項已有約定,則該事項自可與居住權合同內容一同登記;如當事人在居住權設立登記時并未約定住宅出租事項,后又協商一致約定出租事項,則應當及時修改不動產登記簿記載事項,以免第三人未了解住宅的真實占有狀況而權益受損。
(二)約定出租期限的限制
《民法典》規定租賃合同需要對標的物的租賃期限進行約定,并且租賃期限最長不得超過20年。因此,所有權人或者居住權人向承租人出租房屋的最長期限以約定為準,最長亦不得超過20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居住權制度明確了居住權人應當按照居住權合同中關于居住權期限的約定享有居住權,居住權期限屆滿或者居住權人死亡時居住權消滅[5]。因此,就居住權人基于居住權而向承租人出租住宅的,其約定的出租期限不但應當滿足最長不超過20年的限制,而且須不得超過居住權存續期限,否則出租的權源合法性就會產生問題。故居住權人與承租人關于出租期限的約定不得超過居住權期限,即使約定期限超過居住權期限,超過部分也應當歸于無效;居住權人死亡的居住權消滅,基于居住權產生的住宅租賃權合法性也喪失,如此居住權人死亡后的期限約定也自無效。
(三)權利救濟的途徑
無論是所有權人和居住權人對于房屋的出租權,還是承租人對于房屋的租賃權,都面臨著權利遭受侵犯的可能。為保障不同權利人在出租負擔居住權住宅過程中的合法權益,應當厘清不同權利人尋求權利救濟時的途徑。首先,就住宅所有權人和居住權人而言,其可以基于相互之間居住權設立約定,依據《民法典》物權編關于物權保護的規定尋求物權保護救濟,也可以基于與承租人之間的租賃合同約定,依據《民法典》合同編通則及租賃合同規定尋求債權保護救濟;就承租人而言,由于其對住宅并無物權相關權利,因而其僅可以通過債權保護規定尋求救濟,即行使債權請求權,要求相關權利人遵守債權債務之約定,按照約定履行相應的義務。但需要注意的是,依照上述關于建構租賃權對抗保護規則的論述,承租人的租賃權相對于一般債權而言效力更強,因而在權利救濟方面法律對其保護也較為全面。
五、結束語
居住權制度是落實《憲法》規定的公民生存權的重要法律制度。宏觀層面,居住權制度在社會發展中承擔著重要的居住保障功能,穩固了社會關系和家庭關系,奠定了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微觀層面,居住權制度的創設增加了用益物權的種類,便利了居住權人對住宅居住權的行使,為住宅的多樣化利用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徑。而出租設有居住權的住宅是進一步強化居住權人權利,充分發揮居住權社會保障功能的重要方式。因此,多角度地分析并解決設有居住權住宅的出租相關問題,對于完善我國居住權制度具有突出的理論和實踐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