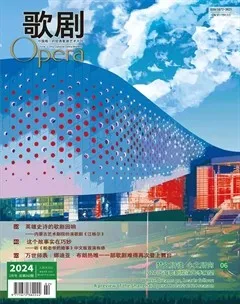創造性轉化 創新性發展
陳姝婧 張建國

《幸福的煙火》是由中共三明市委宣傳部、三明市文化與旅游局、中共沙縣區委共同打造,由三明市歌舞劇院和上海歌劇院聯袂推出的原創音樂劇舞臺作品。這是一部視聽效果和時代鮮度兼顧得不錯的新作,既有藝術性也不乏思想性。故事圍繞沙縣小吃跨時空產業發展中人們生存、生計、生活的現實經歷,通過聚焦沙縣小吃從業者群體的小人物之常情、常理、常態的命運際遇,引發人們省思人生命題。我們在面對永遠存在變量的生活方式、生存境況、社會現實的時候,究竟要如何妥善、及時地安放好我們內心深處那份玉壺冰心的生命情感?顯然,本劇主創團隊給出了清晰的答案。雖距演出觀摩已有頗多時日,雜感良多,然略一回味,難抑筆者對此劇的溢美之沖動。
(一)
沈亮導演對全劇的把握,顯得輕松有余。這一點不在于如何體現出她對文本基礎上的開拓性和創造性,而是在條件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幾乎并不影響她對這個劇目體裁在舞臺整體藝術呈現上格調水準的發揮與拿捏,這便是實力。都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這一點已經是真心難得。沈亮執導的這部劇目有一種令人不可名狀的感染力。她的藝術創構和別具匠心,在條件極為欠缺的情況下,絲毫不減地驚艷到了大家。從客觀上說,出品方三明歌舞劇院是個地市級的藝術生產單位,無論是人力、財力、物力各方面,還是綜合實力都難以和一線城市同日而語,還存在演出場所的局限、舞臺軟硬件的缺乏、臺前幕后行動力的短板等現實問題,會直接對演出質量造成不可避免的影響。然而,《幸福的煙火》在沈亮主導的主創團隊的精誠協作下,獻給觀眾的是一席視聽藝術盛宴,故事跌宕起伏,演出精彩不斷。臨場之下,誰也不會覺得這是在“將就”環境中進行的“攻堅克難”。比如,劇中男主林茂生與妻子吳慧珍的幾次對話,需要妥善處理空間上的轉換和交代場景上的陰陽相隔關系。沒有旋轉舞臺,沈亮就充分加強演員和燈光的舞臺調度,呈現出的效果令人看得明白,故事理得清楚,一點不影響觀眾從視覺邏輯上的理解。可以說,沈導在全劇的二度創作上,故事展開的主輔線與人物關系條理性分明,思想性與藝術性兼具。至于還需不需要進行提升修改的問題,正如沈亮導演自己所說的那句話,“主要在于對標”。“對標”?說實話,乍聽起來略有“不接受反駁”的味道。但是也說明了,沈亮對劇目打造是面對市場還是面對評委,是面對領導還是面對百姓,她心中有——且實實在在地有那桿秤。筆者竊以為有這桿秤的導演一定會是個好導演。

一部戲給人以極盡奢華的視聽感受,往往是容易的。相比之,藝術品相留給人以極盡匠心的沖擊力,則顯得尤為難得。要特別指出的是,《幸福的煙火》不僅體現出藝術家團隊的敬業品質,同時也體現了出品方以及當地主管部門的精明能干。遠離“人傻錢多”“盲目高大上”,恥于“假大空”“面子工程”,鄙視“亂作為”“瞎作為”,旗幟鮮明標榜“真善美”——讓納稅人的每一分錢花得其所啊!此處,理應獲得掌聲。
(二)
《幸福的煙火》編劇楊碩有著很好的題材敏銳性,直面現實的時空事物,對城鎮化、現代化、城市化等帶來的新舊分歧與老少隔閡等鄉村振興戰略上難以避免的社情民意,能較好地以詩性的筆觸書寫人們對守護精神家園的本真愿望,既有同情又存有光明。
首先劇目名稱是筆者很是喜歡的。“煙火”一詞在中國人心中有種特別的共情基礎、價值認同、親切感、厚重感。煙火,它是關乎宗親的、族類的、文化的,甚至是關乎靈魂的。它是傳統的也是經久彌新的。農耕時代“煙火”是必需的,工業時代它也是不可少的;數字時代它需要被重新重視,智能時代它仍然為時不過,而且更需要激活它的溫度。正如該劇作者想表達的那樣,無論智能時代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節奏,我們始終是以家為單元的人——對于中國人而言,家園就是情感安放的棲所。
大方向大氣磅礴,有現實性又不乏思想性。這是筆者對楊碩的故事創構最為欣賞的地方。當然,也不是說除此之外就是完美的。比如對于如何表述城鄉之間條件懸殊的心理認知問題,至少在價值立場和措辭上應謹慎視之,應體現出知識分子、藝術家們以化解社會矛盾倡導優秀價值觀為己任的神圣使命。舉個例子,劇中人物香奈兒的登場,筆者個人認為過于概念化,多少有些生硬。筆者能理解作者意愿是好的,是對現實反映的深刻性體現。但作為文藝的塑造對象,好的切入點便能帶來好的共鳴和良性反思。歌劇《茶花女》《波希米亞人》等核心人物從社會價值觀上看都挺“負面”的,但戲劇效果上卻并不會令人“不適”,便是這個道理。

楊碩的臺本文辭才情有余,唱段的文字結構很具備音樂的曲式結構性,顯見作者在這方面的得心應手。楊碩對韻腳的使用較為嚴謹,長短句的穿插安排平衡感不錯,音律感把握也很穩,“這個劇本很音樂劇”這是筆者在觀摩中特別強烈的印象。一個劇目一個團隊,成員之間相向而行彼此多走近一點就有不一樣的藝術成色產生。目前唱段的抒情性做得都很足,筆者覺得美中不足的是,在于抒情性之外,對敘事性、諧謔性、悲情性以及哲理性等方面的音樂形象對比空間幅度較小較平,略有單一之嫌,特別是唱段之間在全劇的整體規劃上偏“單曲”并聯,缺戲劇表現一體性,有點像“話劇式對白”加“歌曲連唱”而使得音樂戲劇性動力性不足。由于現場觀摩來不及推敲,不確定是音樂還是本子上的問題。音樂劇除了劇本故事本身的巧思妙構外,一個重點是要在音樂本體唱段、樂段藝術形象的精心設計上,另一個就是舞段的重點打磨上。一旦可看性、記憶點得以落實,這個劇目的市場價值就有了質量保證,劇目就能夠走得更遠。
本劇的角色安排和舞臺表演方面游刃有余,軸心性的人物關系預設建議進一步推演確定。沙縣小吃是一個企業脈系極其發達的商業現象,也是一種中國大地上事業發展較有代表性的文化現象。講好這個故事很不容易,但是有著很可觀的現實意義。劇作家愿意傾力在這個著眼點上下功夫,其用意是難能可貴的。其難在于,要把某種程度上已然與現代城市節奏存在一定違和感的“煙火”闡釋到“幸福”層面的人生哲學高度,并能充分博得在場觀眾的認同和共鳴,這是本劇最難為且又最必須傾注的無形筆墨,很考驗劇作家的情理架構智慧和情節安排匠心。

吳慧珍作為林茂生的妻子,勤勞賢惠,最后積勞成疾,是舞臺上虛化空間的登場人物,也是目前故事中父子沖突關系的節點性人物。兒子不能夠原諒父親的偏執心理和父親對兒子的愛不得償,都是源于母親的陰陽相隔。女一號演員扮相好,造型上可以不那么唯美、陽光,或可以增強一些稍顯孱弱又不缺其精明干練的氣質。在故事演繹的調度處理上,夫妻之間陰陽虛實的對話形式以及舞臺情境呈現重復得可能多了些。但所有這些都調節到理想狀態的話,筆者還是認為,吳慧珍作為一號人物感覺欠缺了分量和必要性。一個不成熟的建議是能否將兒子林夏至作為一號,會不會更契合“煙火”的主題性。林夏至有留守家鄉孤獨艱辛的童年,有青春期缺乏陪伴落寞危險的少年,有對母親陰陽相隔而在靈魂深處埋藏的錐痛點,更有對父親及其生活變故導致的新動向的抵觸與排斥。更重要的是作為新時代年輕人對家為軸心的“煙火”情懷的覺醒,對“煙火”對家庭回歸的認同等等,倘若將林夏至作為核心性人物,這些著眼點都有助于盤活整個故事中的人物關系互動。
陳秀珠形神內外都較為準確,適當地在故事中安排她在林家店鋪的生活存在,既有助于林茂生情感正面性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有助于增強父子矛盾與和解的真實性、復雜性以及深刻性的具體推動落實。目前的呈現,她和父子間必要的關系沒形成充分的或者說較為令人感動且信服的作用力。林夏至是個富有時代氣息的小伙子。他對父親、父親與陳秀珠乃至對煙火氣的沙縣小吃等問題,有一個誤解到和解的過程,本質上是受教育而后逐漸成熟起來的過程,韓笑笑只是給林夏至的轉變提供個契機而已。核心五個人物的合理歸位,是直接決定本劇目戲劇表現高度的內在因素,值得好好審視。音樂劇亦俗亦雅,打磨得好,前路無限,戲會也就會走得遠。
(三)
盧榮昱的唱段設計,讓我們看到中國演員以母語歌唱的優勢。本劇中,幾乎所有的唱段、旋律和臺詞的交融度處理都相當好,凸顯了通俗音樂語感的共性特征,充分體現了作曲家對語言音樂性的優秀駕馭能力。筆者一直呼吁中國作曲家對漢語音樂性的重視,甚至倡導“語言大于音樂”的作曲理念,這也是筆者深耕于傳統唱腔“依字行腔”諺訣深度教學實踐中略有所得的。中西語言差異的本質,是語調語義性和音節語義性的不同,這是東西方文化基因中的差異,一定不可漠然視之。
還有,本劇在配器方面的基礎性呈現都較為均衡協和。基于“沙縣小吃”這一故事題材,筆者有一個較為不成熟的建議:是否能讓音樂在個性值上做加法?比如,以鍋碗瓢盆碰撞聲的原聲提取、顧客用餐聲響的藝術形象加工,以及城市喧囂的建筑工地聲、鄉村鄉野的自然環境聲等的音樂化處理貫穿鋪墊,并在整體的布局和著色上有意識、有目的性地融合到劇情的展開之中。

舞蹈對于音樂劇本體而言,分量不可小覷。目前舞段的進出、虛實、渲染等,從呈現來說,就像一幅剛處于打底色階段的大開面畫作,雖面面俱到,但深入的藝術表達尚有些欠火候。筆者期待,其中的有些舞段更具備可看性、觀賞性、藝術性,不要都是那么克制、點綴。因為本劇的人物個性都是可以被放大渲染,無論主要人物還是有不同身份的類型化人物。比如,和面、包餃子、舀湯等職業動作,也可以抽象加工為舞蹈動律的素材點,這些舞蹈都可以撐起舞臺場面,甚至可以作為肢體技藝的表現,渲染舞臺表演熱度。這種個性化的舞蹈處理,做好的話可以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為劇目品相大大加分。
《幸福的煙火》全劇在嗓音藝術形象塑造方面,總體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上海歌劇院、三明歌舞劇院的獨唱演員都有扎實而科學的發聲技巧,而且看得出都有一定的舞臺經驗,演繹“輕量級”的音樂劇可謂駕輕就熟。最為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洋”唱法在身的演員們,并未陷入“聲音規模”“聲音規格”的窠臼之中。當然,從音樂劇的角度來看,特別是中國音樂劇的角度,筆者認為語氣的變化和強調,在人物聲音和形體造型等方面,還有磨合空間;聲音造型中的情感渲染有待進一步加強,聲線收放的鋪排也值得進一步平衡。目前的舞臺呈現,在人物的自我定位上還缺乏一些小細節。人物會因為交流產生身份的自我確認,隨物賦形地形成自我塑造。比如交流對象的不同,語氣、語調一定是不一樣的。現在人物在舞臺上,某種程度上來說缺乏更深層面的塑造和升華。

“煙火氣”是一種幸福。它關乎中國社會特色的生命情感、人生哲理和文化傳統的接續,指向以家為樞紐的中國社會特性。喚醒煙火氣的價值認同,對中國人來說,也是一種失而復得的共情點。煙火,在筆者看來,或許是本劇最為核心的藝術書寫對象,是普適的,是新時代下值得打造的一個很有內涵的文化熱點。音樂劇《幸福的煙火》,一方面是文化事業日益繁榮的具體實踐,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增強文化自信的作用。這正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