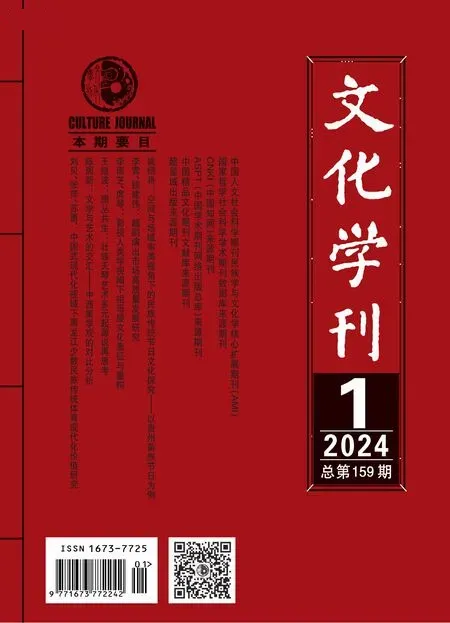淺析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的適用
沈靖川
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傳統(tǒng)民法理論所秉持的,只有守約方才享有合同解除權(quán)的觀點遭到了嚴重的挑戰(zhàn)。《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于2006年所刊載的“新宇公司與馮玉梅買賣合同糾紛”案,揭開了“賦予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的面紗,即在司法實踐中首次確認了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quán),此后,違約方為了降低自己的損失,請求法院解除合同的情況日益激增。從2019年聚焦民商事審判工作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48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的第580條[1],從爭論不休到蓋棺定論,法律對違約方能否享有合同解除權(quán),以及如何行使此項權(quán)利的規(guī)定仍處于起步階段,立法層面尚且如此,司法層面的實踐不言而喻,在我國裁判文書網(wǎng)上登載的案例中,在各地司法機關(guān)對于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quán)的相關(guān)判例中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現(xiàn)象。筆者將通過梳理典型案例,對違約方解除合同的相關(guān)問題進行研究,分析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quán)存在的理論爭議,并肯定其存在的積極意義,再從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quán)在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入手,提出相關(guān)的完善建議,以期更好地運用于司法實踐。
一、問題的提出
(一)相關(guān)案件事實與法律裁判
1.魏某與陳某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
2014年4月,陳某向魏某租賃一間店鋪并簽訂《租賃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約定:魏某將其所有的一套面積162.64平方米的房產(chǎn)出租給陳某;合同簽訂后,陳某又向魏某繳納租金至2016年12月31日,后就未再支付租金。2017年3月29日,陳某向魏某等業(yè)主發(fā)微信表示,因經(jīng)營餐廳長期虧損無以為繼,于2016年12月31日停止經(jīng)營,此前已多次與各業(yè)主協(xié)商關(guān)店事宜,但協(xié)商未果,于2017年3月30日下午與各業(yè)主再行協(xié)商。魏某回復(fù)微信不同意解除雙方租賃合同。2017年4月7日,陳某向魏某發(fā)出經(jīng)過公證的解除合同通知書,提出因經(jīng)濟蕭條,陳某經(jīng)營的餐廳無法維持,通知魏某解除合同。但魏某于2017年4月10日收到通知書后,要求陳某繼續(xù)履行合同,雙方協(xié)商未果,故魏某訴至法院。
法院認為,魏某與陳某簽訂的租賃合同,符合合同成立生效的各項有效要件,應(yīng)屬合法有效訂立的合同,雙方均應(yīng)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依約履行。當出現(xiàn)合同僵局的情況下,守約方和違約方當事人對是否繼續(xù)履行合同存在爭議,同時違約方當事人繼續(xù)履行合同會喪失預(yù)期利益,對違約方明顯不公。此時二人所訂立的合同已然不具有能夠繼續(xù)履行的基礎(chǔ)條件,而司法機關(guān)從雙方當事人利益損失之間進行衡量的角度出發(fā),賦予違約方解除權(quán),解除合同并承擔相應(yīng)的違約責任。合同履行過程中陳某因自身經(jīng)營困難等原因從2016年年底開始向魏某協(xié)商解除雙方租賃合同,并于2017年4月10日向魏某送達了解除合同通知書,要求提前解除租賃合同,且陳某已停止經(jīng)營,無法繼續(xù)履行所訂立的租賃合同,故本院認定雙方合同于2017年4月10日解除。
2.李某與劉某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
2015年11月21日,以原告李某為甲方(賣房方)、以被告劉某為乙方(買房方),訂立房屋買賣合同一份,現(xiàn)李某因政策的原因,無法辦理房屋所有權(quán)證書,也無法將房屋過戶給劉某,導(dǎo)致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的目的不能實現(xiàn)。要求解除房屋買賣合同。
法院認為,李某與劉某之間即形成房屋買賣合同法律關(guān)系。該合同系原、被告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nèi)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效力性強制性規(guī)定,應(yīng)為有效合同。故原、被告雙方理應(yīng)按照合同的約定全面完整地履行義務(wù),在沒有法律規(guī)定或者雙方合意約定的情況下禁止變更及解除合同。《民法典》出臺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明確規(guī)定因一方當事人違約而賦予守約方的權(quán)利,并未賦予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quán)利。該條款賦予的是守約方對合同解除的選擇權(quán),以警示雙方當事人不能輕易違約,使合同當事人放心地履行合同,從而有利于促進交易安全,維護社會經(jīng)濟秩序。誠實信用原則是貫穿訂立合同始終的基本原則,合同一旦經(jīng)雙方合意訂立,雙方即受到合同權(quán)利義務(wù)的必要約束,如果未經(jīng)守約一方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僅僅基于違約方自身利益而賦予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無疑是對此種約束置若罔聞,市場的交易秩序也將受到破壞。在本案中,結(jié)合現(xiàn)已查明的事實,被告劉某已經(jīng)依約向原告李某支付了100萬元購房款,而原告李某并未依約為被告劉某辦理房屋所有權(quán)證,該行為已經(jīng)構(gòu)成違約,這種違約不屬于合同法上的不可抗力所致,根據(jù)上述法律規(guī)定,作為違約方的李某并不能對合同行使解除權(quán),應(yīng)遵守合同約定繼續(xù)履行合同義務(wù)。
(二)案例所顯現(xiàn)的法律問題
1.能否賦予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
淺析上述司法判例不難推斷,全國各地的司法機關(guān)對違約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權(quán)的看法仍未統(tǒng)一,其中一部分法院從平衡雙方當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fā),判決賦予違約方解除權(quán),另一部分法院則從合同的約束力以及市場交易秩序等角度進行裁判,判決違約方不能夠解除合同,從而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現(xiàn)象發(fā)生。這就造成了《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在適用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需要進行大量理論研究來完善該法律條文。
2.如何解釋和適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的規(guī)定
對于《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的規(guī)定,理論界與實務(wù)界存在巨大的爭議,一部分學者認為,該條文賦予了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同時肯定了其打破合同僵局,提高經(jīng)濟效率的積極意義,另一部分學者持相反的觀點,認為如果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quán),則會違反誠實信用原則,鼓勵違約,影響交易安全。因此,我們需要對此項規(guī)定所體現(xiàn)出來的理論依據(jù),以及賦予違約方解除權(quán)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等問題進行深入探究,這樣才能發(fā)現(xiàn)和完善該規(guī)定可能適用的路徑[2]。
二、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的理論爭議
《民法典》正式出臺后,學者對其第五百八十條所規(guī)定的“合同僵局下違約方的合同解除權(quán)”的爭議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限制肯定說
該學說認為,我國目前現(xiàn)有的法律體系降低了對效率價值的考量,該立法理念使得法律在公民權(quán)益保護的規(guī)定上做出了部分妥協(xié),更加傾向于高效解決現(xiàn)實存在的糾紛,提倡“無訟、少訟”[3]。該條款對于違約方在遇到合同僵局的情況下如何具體行使合同解除權(quán),并沒有詳盡規(guī)定,而此規(guī)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是否會被濫用,故勢必要對此做出嚴格的限制,以此來應(yīng)對賦予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所帶來的交易秩序被破壞的潛在風險。同時,崔建遠教授認為,作為救濟法、補償法的民法既不能過分保護守約方,也不能過分懲罰違約方,尤其是當合同陷入僵局,無法繼續(xù)履行時,合理分配守約方和違約方的權(quán)利義務(wù)和責任承擔就顯得尤為重要[4]。徐博瀚博士則認為,守約方為了獲得訂立合同時的預(yù)期利益,其可向違約方主張繼續(xù)履行合同,同時也可以通過向違約方主張損害賠償責任或者消滅合同效力的方式來彌補自己履行合同所受損失以及預(yù)期利益[5]。
(二)根本否定說
此學說認為,作為違約的一方當事人本就不應(yīng)該享有合同解除權(quán),整個合同訂立的過程就是雙方當事人合意的過程,法律應(yīng)保護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訂立及履行的過程中得到充分貫徹。出現(xiàn)合同僵局后,在未經(jīng)守約方同意的情況下,僅僅為減少違約方所受損失而賦予其消滅現(xiàn)存的合同法律關(guān)系的權(quán)利,勢必會使得合同雙方突破合同的約束對公平交易秩序造成破壞。而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quán)在司法實踐領(lǐng)域并沒有得到完全支持,同時對于此項權(quán)利的理論指導(dǎo)少之又少。而該觀點雖與《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的規(guī)定背道而馳,但其仍具有理論研究價值。其一,該觀點對于破解“合同僵局”提供了一定的解決思路;其二,該主張所引證適用的國外司法實踐案例以及相應(yīng)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對實現(xiàn)我國合同法現(xiàn)代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6]。郝麗燕教授認為,一旦允許違約方擁有合同解除權(quán)極大可能會對社會交易的誠信制度造成巨大沖擊,對社會誠信制度的建設(shè)產(chǎn)生不利影響。解除權(quán)作為形成權(quán)的分支,其權(quán)利本身要受到除斥期間的規(guī)范和限制,無論如何都不應(yīng)通過要求守約一方讓渡一部分自己的權(quán)利去迎合失信一方。如果賦予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quán)利,勢必會使得上述權(quán)利的保護路徑產(chǎn)生實質(zhì)性的影響[7]。蔡睿博士認為,在“合同僵局”發(fā)生的情況下,繼續(xù)履行成為能夠彌補守約方所受損失的首要方式,排除守約方的繼續(xù)履行合同的請求權(quán),在此基礎(chǔ)上賦予其向違約方主張?zhí)娲再r償?shù)臋?quán)利即可,并不一定要通過解除合同來分配損失[8]。
三、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的正當性證成
(一)提高交易效率,打破合同僵局
《民法典》五百八十條規(guī)定,如果出現(xiàn)違約方無法履行合同債務(wù)或者履行合同債務(wù)成本過高的情況,繼續(xù)履行合同已經(jīng)無法實現(xiàn)訂立合同時的主要目的,其長期處于無法履行又未被解除的狀態(tài)下,不利于雙方開展其他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同時對市場資源的使用也屬于一種變相的浪費[9]。
(二)健全法律體系,添補立法空白
在《民法典》出臺以前,違約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權(quán)在立法層面處于空白狀態(tài),使得在出現(xiàn)“合同僵局”后合同雙方無法可依,更加不利于合同僵局的化解,同時也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現(xiàn)象,與我國司法實踐所倡導(dǎo)的理念背道而馳,《民法典》創(chuàng)造性的賦予違約方化解合同僵局的途徑,健全了合同法解除權(quán)的設(shè)置體系,是我國在合同法司法實踐中的創(chuàng)新之舉,為在司法實踐中解決“合同僵局”提供了新的路徑。
四、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quán)存在的問題
(一)未明確違約方請求解除合同時的主觀狀態(tài)
《民法典》對于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quán)的過程并沒有做出詳盡規(guī)定,違約方在行使解除權(quán)時的主觀狀態(tài)并未明確,這就導(dǎo)致了法院或仲裁機構(gòu)受理違約方解除合同的請求后,只要符合該條文的規(guī)定,無需考慮違約方是出于惡意還是為了減少損失而違約的主觀狀態(tài),即可機械性地適用解除合同這一規(guī)定,這就會縱容違約方惡意違約而肆意請求解除合同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從而喪失立法者設(shè)立此項制度的初衷。故違約方違約時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應(yīng)當作為是否適用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的必要要件之一。
(二)未確定違約方解除合同后的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第二款規(guī)定,并沒有對違約方解除合同后的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方式以及需要承擔的責任范圍予以明確的規(guī)定。《民法典》對損害賠償責任的規(guī)定不明確,使得司法實踐的過程中產(chǎn)生很多分歧,比如損害賠償責任的范圍如何定位?是否包括合同履行的可得利益?若肯定包括可得利益的賠償,賦予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有何必要?違約方本就無力繼續(xù)履行合同,又如何賠償范圍更廣的損害賠償責任[10]?法院對于此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同案不同判的情況時有發(fā)生,這些都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五、完善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的建議
(一)明確規(guī)定違約方非惡意違約
筆者認為應(yīng)明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所規(guī)定的違約方解除權(quán)屬于非惡意違約,當事人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陷入無法履行困境或者按合同的約定履行的成本過高等迫不得已的原因,因此,當事人為了及時止損而請求終止合同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11]。主動違約是違約方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而不顧對方當事人合法權(quán)益的機會主義行徑。這一行徑不僅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也違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規(guī)定,所以,應(yīng)當堅決排除違約方惡意違約時的合同解除權(quán)。
(二)確定違約方解除合同后的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在合同解除前,首先應(yīng)該明確違約方需對守約方遭受的損失進行賠償。從而確保守約方的利益得以實現(xiàn),防止守約方在解除合同后處于不利地位。在向違約方施壓的同時,對守約方也是一種保護,迫使違約方盡快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來擺脫合同陷入“僵局”的狀態(tài)。第二,明確違約方需承擔賠償責任的范圍,在違約方申請解除合同時,司法機關(guān)應(yīng)當首先確定損害賠償責任范圍,來平衡雙方的利益得失,實現(xiàn)個案正義。同時為避免對守約方造成二次傷害,應(yīng)確保守約方的損失能夠得到完全賠償。
六、結(jié)語
賦予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是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客觀需要,也是對司法實踐經(jīng)驗的科學總結(jié),應(yīng)當肯定其正當性和積極意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賦予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可能會引發(fā)違約方為了自身利益而違約的機會主義行為,這就需要我們從嚴把握違約方合同解除權(quán)。《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的規(guī)定運用于司法實踐時不可避免地有所缺陷,需要我們在實踐的過程中進一步完善,更好地發(fā)揮其價值,促進經(jīng)濟社會公平有序地發(fā)展。